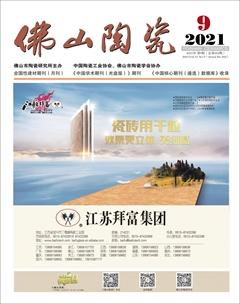域外文化對中國陶瓷的影響分析
摘 要: 本文分析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西方文化等外來文化對中國瓷器創新發展的影響。中國瓷器在唐宋時期就到無與倫比的境界。在當時,中國瓷器燒造技術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是,由于缺乏外部先進文化的刺激,當時的中國瓷器長期處在單調守舊的狀態,無法自我發展和突破。元朝之后,多虧來得正是時候的外來先進文化和技術,結合自身的實力和需要,中國本土瓷器得以不斷發展壯大。中國瓷器的發展軌跡和業績充分說明本土文化的發展,都需要有外來文化的刺激。
關鍵詞:瓷器;本土文化;域外文化;創新驅動力
1 前言
中國瓷器,似玉非玉勝似玉,更有經高溫爐火煉就的優美、絢麗、高雅人文畫卷和自然景致,既是日常生活用具和手工藝品,又是具有收藏價值的藝術品,有些甚至成為價值連城的文物古董,是古今中外令人無比向往的器物。中國瓷器源于3500多年前商代中期的原始瓷,公元2世紀的漢代末期便出現了成熟青瓷,隋唐時期北方白釉瓷燒制工藝實現突破,雖然期間出現了始于唐代的三彩瓷、復彩瓷及青花瓷,以及以鈞窯、哥窯、官窯、汝窯、定窯等名窯為代表的宋朝瓷業繁榮時期,大量精美絕倫的中國瓷器也從唐代起開始大量走向世界,但是直到宋代,無論形制,還是色彩及景致,中國瓷器都是比較簡潔單調[1-2]。隨著中國瓷器不斷走出國門,一方面,中國優秀瓷器產品及燒造技藝不斷地傳播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也同時將世界各地先進的瓷器相關的原料、技法、設計理念等引入和融入中國,使得以景德鎮瓷器為代表的中國瓷器,從元朝開始在工藝技術和藝術水平上一直處在獨占鰲頭的突出地位,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中國瓷器是中國最早走向世界的產業,也是第一個成功與世界交流交融中不斷發展壯大的產業,盡管尚有缺陷和不足,但是其地位和行業引領作用時至今日仍然無法被他人撼動,舉世認同。唯物辯證法認為世間事物的變化發展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內因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只是事物變化發展的外部條件,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促使事物的變化發展[3]。中國著名藝術人類學家方李莉也指出“本土手工藝者有很好的本土技術,熟悉本土的材料,但僅僅這一點是不夠的,每一種本土文化的發展,都需要有外來文化的刺激” [4]。中國瓷器的發展軌跡和業績也充分展示了“外來文化的引入和融合正好成就了中國本土瓷器的不斷壯大發展”這一辯證關系。為此,本文擬從內因與外因辯證關系角度,分析域外文化對中國瓷器發展的推動作用,為中國瓷器產業進一步更好更健康地發展提供建議和參考。
2 佛教文化對中國陶瓷的影響
作為一種源自古印度的外來文化,佛教被引入中國的時間正是中國瓷器趨于逐漸成熟之時的漢朝[5]。因為佛主釋迦牟尼降生在熱帶的古印度,四季與鮮花相伴,與植物結下了不解之緣,因此,向佛獻花是供佛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禮儀。據鳩摩羅什翻譯的《佛說千佛因緣經》記載,信徒向佛獻花可以獲得善果和福報[6]。以鮮花供佛,不但能夠讓諸佛歡喜,有求必應,而且還能積累功德、獲得福報。因此,時至今日信奉佛教國度的信徒們仍然以花鬘、曼陀羅(一種將花朵或花瓣擺放在地上或大盤上的獻花方式)、泛花及散花四種方式向諸佛獻花。因中國低溫干燥氣候導致鮮花來源有限的原因,這些古印度向佛獻花的方式傳入中國后就不得不變更為瓶花獻佛。將鮮花插于貯水花器中的瓶花獻花方式,不但可以減少鮮花用量,還可以使鮮花長久不萎。這種有別于佛教發源地的中式獻花方式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典型范例,同時也促進了中國陶瓷花瓶的誕生、推廣及興盛。由于長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在文人雅士的推崇和陶瓷匠人的刻意追求之下,陶瓷花瓶的禮儀性和審美性功用不斷得到強化,中國陶瓷花瓶走向極致,許多陶瓷花瓶自身甚至可以達到無花勝有花的境界,變成飾品、擺件、藝術品、古董、文物[7]。由于蓮花,潔凈高雅,是佛教大德的象征,因此,蓮花及蓮花紋一直是中國陶瓷廣泛采用的經典裝飾圖樣[8]。由法輪、法螺、寶傘、白蓋、蓮花、寶瓶、金魚、盤長組合而成的藏傳佛教八吉祥紋也已廣泛用于各種陶瓷產品設計,其中由藏傳佛教八吉祥紋與梵文、藏文等并用構成的圖案,如纏枝蓮托八吉祥、蓮瓣內飾八吉祥、折枝蓮托八吉祥等紋樣構成的青花、斗彩、五彩、綠地黃瓷器最受到人們的青睞[9]。正是佛教文化的推動,使得中國陶瓷變得如此絢麗多彩,不斷走向輝煌、走向極致、走向藝術巔峰。
3 伊斯蘭彩陶文化對中國青花文化發展影響
無論是青瓷或白瓷,還是青白瓷,唐宋時期的中國瓷器就已達到質地細膩、胎薄質堅、釉色瑩潤、光澤華美的境界,具有天然玉石的質感和氣質。當時的中國瓷器燒造技術已經相當成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作為崇尚玉器的國度,人們刻意追求中國瓷器所展現出的“瓷如玉璧, 色似煙嵐”品格,因此,國人一直對青瓷、白瓷或青白瓷情有獨鐘,青瓷、白瓷或青白瓷也一直是唐、宋、元時期行銷海內外的主打瓷器。雖然期間出現了青釉、白釉、綠釉、醬釉、鈞窯釉等各種色釉[1],也有諸如釉下彩、圖形紋飾、文字紋飾等一些新型技法[10],甚至還有唐三彩、釉下彩、唐青花涌現[11],但是唐宋及以前的中國瓷器,無論形制,還是色彩及景致,仍然顯得簡單單調,異常保守守舊。但是與唐宋同一時代的7-14世紀,在遙遠的中東地區,隨著阿拉伯帝國的創立,伊斯蘭彩陶文化卻日趨繁榮,涌現出拉斯塔虹彩陶、三彩噴濺陶、泥漿彩繪陶等一系列藝術彩陶。例如,八世紀中葉,阿巴斯王朝(750-1258年),因黃金白銀不足,嚴禁用貴重金屬打造生活器具。為此,當時的美索不達米亞陶工參照摩爾人樣式,借用玻璃器珠光彩繪技術,以錫釉陶白坯為底,以金、銀、銅等具有美麗光澤的貴金屬氧化物作發色劑進行彩繪,再經1000℃的還原焰二次燒成具有金屬質感的彩虹般光澤的單彩或多彩陶制品。此類模仿金屬器彩陶被稱為拉斯塔彩陶。從初創時的單彩逐步發展成在白釉上施以各種圖案的多彩,窯址遍布中東地區,如伊拉克的巴士拉、伊朗的卡尚、敘利亞的拉卡等重要城市,并隨著王公貴族雇主的意愿而四處遷徙,九世紀發端于伊拉克,十世紀轉移到埃及,十二世紀到敘利亞和伊朗,十四世紀中葉消逝在卡尚、十五世紀泯滅于拉卡,前后持續發展近千年[12]。阿拉伯民族非常注重通過幾何、植物、文字等簡潔抽象藝術形式構置和凝練出各種繁復有序、滿而不亂、構圖飽滿、絢麗多彩、千變萬化, 獨樹一幟的陶瓷紋飾,并通過這些陶瓷紋飾彰顯阿拉伯民族文化特征和伊斯蘭美學思想[13]。以圓形、三角形及四方形等為基本形式,通過60度或90度的交錯并加入方格及圓弧,衍化出各種各樣的幾何紋圖案,可以讓伊斯蘭陶瓷和建筑變得如萬花筒般的絢麗迷幻,展現出各種高深莫測的幻想意念,蘊藏著阿拉伯數學智慧。植物紋飾則通過自由彎曲莖蔓與花葉相互穿插、互相重合, 構置在有限的空間中呈現無限的延續和工整華麗的氛圍,以彰顯生命律動的美感。書法紋飾則更注重格式與器型的配合,通過文字自身的節奏感、裝飾性、紋樣化,體現文字美感,并以簡潔流暢曲線效果展現出一個無限循環的世界。正是這些獨具特色的“阿拉伯紋飾”使得伊斯蘭彩陶變得如此絢麗多彩、生機昂然。相比之下,處在同一時代的唐宋陶瓷卻是相對呆滯守舊,而波斯地區正好是伊斯蘭陶器蓬勃發展的興盛時期。期間,伊斯蘭彩陶經歷了從浮雕模印向平面彩繪轉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釉上/釉下彩繪技法,其中又以鈷藍料彩繪的釉下彩青花陶器最具特色。伊斯蘭彩陶發端于西亞的阿拉伯半島,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而拓展到亞州、北非、南歐,所到之處又與當地文化交融,不斷形成新器型和風格,例如:“波斯的卡尙陶器”、“西班牙的摩爾陶器”、“土耳其的伊茲尼克陶器”,等等。與東方的中國瓷器制造中心遙相呼應,當時的波斯地區也逐漸演變成另一個光輝燦爛的世界先進陶瓷中心。雖然從唐朝就開啟了通往包括波斯地區在內的海外瓷器貿易,期間也有證據表明兩地之間在陶瓷工藝技術及藝術技法方面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鑒、相互促進活動一直未斷[14-17],但是在唐代安史之亂之后,特別是宋朝,中國實際版圖不斷縮小,與西域國家的實際交往受到極大限制,阻隔了彼此間的交流。
在阿巴斯王朝的后期,一支來自中亞吉爾吉斯的游牧突厥人塞爾柱武力攻占了巴格達后,其首領成為阿巴斯王朝哈里發的攝政王,史稱塞爾柱王朝(1037-1194年)。塞爾柱王朝時期伊斯蘭彩陶達到一個全新的高度,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塞爾柱陶工創造性地將一定比例的石英粉摻到胎泥中,使陶胚呈現出一定瓷質感。改良后的陶土白凈堅硬,便于彩繪和施釉。伊斯蘭陶工在白色陶胚上以藍、青、黑等色料,尤其是以氧化鈷為主要成分的鈷藍色料,進行彩繪后再施以透明釉或青釉燒造。此類伊斯蘭彩陶燒造技法與后來發展成熟的中國青花瓷器燒造技法十分類似[18]。塞爾柱王朝之后的阿巴斯王朝快速走向衰落,于1258年最終被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率領的蒙古大軍徹底殲滅。旭烈兀于1264年建立伊爾汗國(1256-1353年),并承認忽必烈的元朝為宗主國。此外,從東起西太平洋,西止東歐,橫跨整片歐亞大陸的疆域基本上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所建的大蒙古帝國,如:欽察汗國(成吉思汗之孫拔都)、察合臺汗國(成吉思汗次子察合臺封地)、窩闊臺汗國(成吉思汗三子窩闊臺封地)。由于這些汗國與元朝存在宗藩關系,因此,除了原有海路之外,當時中國還可以通過陸路便利通暢地與各地穆斯林交往,元朝成為中國與阿拉伯地區聯系最為密切的時代[19]。由于伊爾汗國非常重視民族手工業技術和文化,精湛的伊斯蘭彩陶技藝在繼承塞爾柱王朝時期優秀傳統的基礎上繼續得以發揚光大。事實上,波斯地區伊爾汗國之后的帖木兒王朝(1370-1507年)也都屬于突厥或蒙古民族統治,與漢人長期保持密切交流關系,因此,元朝之后,正是由于阻隔中國與西方阿拉伯民族交流的障礙被徹底消除,使得東西方文化與技術交流加速,也為中國青花瓷的誕生、發展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外部條件。
景德鎮盛產瓷土,自古以來都是瓷器燒造理想之地,至五代時便成為南方最早燒造白瓷之地,從而打破了南方只產青瓷的局面。從唐代起,因躲避戰亂,四面八方的能工巧匠云集于此,以瓷為生,南宋時期景德鎮的青白瓷燒造技法就已經出類拔萃,景德鎮青白瓷深受海內外的歡迎和廣泛需求。蒙元時期,由于戰亂,北方白瓷窯普遍衰落或無法正常運轉,只有南方地處偏僻盛產青瓷的浙江龍泉窯和盛產清白瓷的景德鎮尚存,未受到戰亂影響,然而卻只有景德鎮瓷器從元朝開始逐步走向更大的輝煌,而龍泉窯卻逐步走向衰弱[20]。由于青瓷的胎釉中氧化鐵含量較高,高溫燒制后顏色轉青且厚重,透明度較差;而青白瓷,特別是白瓷,其胎釉中氧化鐵含量較低,高溫燒制后顏色白中閃青,青中閃白,甚至純白,釉面光亮透明[21]。因此,青瓷雖好,但是不適合釉下彩繪,而白瓷幾近白色,釉面光亮透明,卻是后期發展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等各色瓷器的理想平臺和胚子。據此推測明清之后,景德鎮瓷器從此逐步走向更大的輝煌,而龍泉窯卻逐步走向衰弱的緣由之一應與此有關,更是元朝至元十五年在江西浮梁縣專設浮梁條件磁局的根本緣由。因此,宋末元初時期,景德鎮就具有進一步發展瓷器所必需的得天獨厚的基礎和條件。此外,元朝非常重視民族手工業技術和文化,并于至元十五年在江西浮梁縣專設浮梁磁局,執掌磁器燒造,兼管漆造、馬尾、棕、藤、笠帽等事宜,是元朝中央轄下直接為宮廷燒造瓷器的機構。元朝通過浮梁磁局,既要滿足皇家宮廷需要,還要負責民窯瓷器、漆造、馬尾、棕、藤、笠帽等的生產管理事務,這與前朝,以及之后明清時期的官窯或御窯設置僅僅滿足皇家宮廷需要的模式有著巨大區別。正是得益于浮梁瓷局的有效管理,使得許多精美絕倫的元代青白瓷、卵白瓷及元青花得以走向了帝王的書齋廳堂,也走向外部世界,其中許多成為當今世界各國珍藏的藝術瑰寶[22]。據考證,景德鎮早期元青花瓷器年代不早于1323 年。通過對景德鎮紅衛影院窯址出土的早期元青花瓷器的器形、紋飾、繪畫手法、文字等方面進行分析后得出,景德鎮早期元青花瓷器與波斯地區確實有密切關系,所用色料(包括鈷料和銅紅料)均來自波斯,其制作上甚至還有波斯陶工直接參與的痕跡。在至正元青花瓷器成熟之前,元青花瓷器確實有一個外來技術引進、吸收和轉化的過程。正是波斯的原料、伊斯蘭彩陶技術與設計,結合景德鎮的胎、釉、燒造工藝,僅需十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就催生了早期元青花瓷器[23]。最初,中國青花瓷所采用的色料多為進口色料,只是到明朝中后期才改用國產色料。元朝期間,借助大蒙古帝國的實力和便捷的驛站網絡,原產于波斯地區的青花鈷料被源源不斷地運到景德鎮,而景德鎮所產瓷器也可以經由波斯而銷往世界各地。正是由于伊爾汗國與元朝這種密切關系,才使得青花瓷相關的源自伊斯蘭的原料、紋飾、彩繪、器型、工藝及設計,被源源不斷地輸往中國,促使中國青花瓷技藝快速成熟[24]。
雖然中國青花瓷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唐代中期,但是卻一直是星星點點,不成氣候,直到元朝,才呈現出巨大轉折。這一切的變遷與元朝時局這一外部因素或條件呈現密切相關。元至正青花瓷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產生并成熟,需要快速掌控和調動諸如高端紋樣、設計、畫工、材料、制作人員等資源要素,只有宮廷直轄的浮梁磁局才有能力確保快速獲取與整合這些資源[25]。事實上,波斯地區伊爾汗國之后的帖木兒王朝(1370-1507年)也都屬于突厥或蒙古民族統治,與漢人長期保持密切交流關系,因此,元朝之后,正是由于阻隔中國與西方阿拉伯民族交流的障礙被徹底消除,使得東西方文化與技術交流加速,也為中國青花瓷的誕生、發展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外部條件。雖然唐宋時期中國瓷器技法和品質就已經達到了世界巔峰,但是卻是長期無法自我求新變革。只有待到伊斯蘭釉下彩陶技術成熟、伊爾汗國及大蒙古帝國建立、元朝對包括瓷器在內的民族手工業技術和文化高度重視等核心要素同時出現,中國瓷器才可能由此走向新的輝煌,源自域外的伊斯蘭彩陶文化成全了中國青花文化發展需要。
4 西方文化的影響推動中國瓷器走向更大輝煌
從元朝開始至明朝早期,景德鎮在繼續燒造青白瓷的同時,還開始燒造青花瓷、釉里紅、卵白瓷、釉上彩、斗彩、五彩、素三彩和各種單色釉瓷,成為世界制瓷創新中心和瓷都,享譽海內外。中國瓷器,特別是景德鎮瓷器,沿著大蒙古帝國的疆域和商業脈絡,特別是隨著鄭和七下西洋和海上絲綢之路走向世界各地。但是在16世紀之前,即葡萄牙船隊到達廣州前,歐洲人只能以轉口貿易方式從西亞和埃及市場獲得少量中國瓷器,多數歐洲人沒見過中國瓷器。葡萄牙人是最早直接從中國將景德鎮青花瓷器帶入歐洲的歐洲人。雖然中國瓷器到達歐洲后價格飛漲,但是歐洲人還是非常喜歡,市場需求巨大。 一方面,從16 世紀開始,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歐洲人開辟了通達中國的遠洋航道,直接與中國進行瓷器貿易,從而開辟了全新的歐洲市場,拓展了景德鎮瓷器的銷售空間和數量。僅16-18 世紀的三百年內, 大約有三億件景德鎮瓷器被帶到歐洲, 還有數量巨大的景德鎮瓷器被銷往東亞及東南亞各地[26]。期間,先后有日、英、法、德等多個國家引進中國技術和原料,仿造中國瓷器。另一方面,在外銷瓷器走向世界過程中,中國瓷器也不斷進行改進,以適應市場的需求,潛移默化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這在客觀上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國瓷器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不斷豐富完善,而且這樣的變化一直沿續到今天。
在日本江戶時代,日本佐賀縣西松浦郡有田町及其鄰近地區引進、借鑒、模仿景德鎮瓷器造型、裝飾及燒造技術燒造的具有濃郁中國風格的瓷器。由于明末至康熙初年間,清朝實行禁海令,阻斷了歐洲商船來華采購中國瓷器,于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將目光轉向了日本瓷器,作為中國瓷器的替代品。由于日本瓷器始發港口為伊萬里港,因此這些瓷器被稱為日本伊萬里瓷器。為了歐洲受眾的需求,日本匠人還在乳白色胎上加入紅、黃、綠等色彩,或在彩繪瓷器上用金彩進行描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柿右衛門”、“金襕手”等風格的彩繪瓷器,受到了歐洲人和日本人的喜愛。清朝平定臺灣后,又逐漸開放海禁,歐洲人再度來華采購和定制瓷器,并且中國工匠在原有釉下彩和釉上彩基礎上也以真金勾勒創制出屬于中國的類似“柿右衛門”、“金襕手”等風格的彩繪技法。這些風格瓷器甚至也有人稱為“中國伊萬里”瓷器。康熙中后期,景德鎮瓷器再度繁榮,而日本伊萬里瓷器卻處于劣勢,逐漸淡出世界舞臺[27]。
最初,歐洲人直接采購景德鎮瓷器成品,后來由于文化及生活習慣不同而改為定制生產。從16世紀開始,為了更好地制作符合他們需求的產品,外商人開始提供上色的圖稿或者模型,更有甚者提供了玻璃、木器、金屬器等實物模型,而中國瓷窯則按照歐洲人的要求專門配套生產。這應該是瓷器行業最早的代工(OEM)生產模式。為此,在明早期至晚期,景德鎮先后在胎釉、成型、燒成等各方面工藝技術上,進行改進和革新,從而大大推動了景德鎮制瓷工藝技術的發展[28]。景德鎮陶瓷器型主要受到元代及明代早期受伊斯蘭風格影響;明代晚期受歐洲風格影響加重,同時還受到日本風格影響;清代則受歐洲風格影響濃重[29]。十七世紀初及其以前, 歐洲人只是崇拜和接受中國瓷器,對中國瓷器的造型、裝飾、繪畫沒有特別的渴求。但是,十七世紀后半葉,歐洲各國畫家和藝術家們開始設計了大量歐洲人鐘愛的瓷器樣品和草圖,例如,將英國版畫家納薩尼爾·帕爾、法國畫家尼古拉斯? 朗克雷、荷蘭畫家考納利斯·普朗克、意大利畫家雅各布? 安尼戈尼等著名藝術家的版畫、素描、油畫等作瓷器裝飾,這些圖案不僅豐富了中國陶瓷繪畫的裝飾題材,也為陶瓷繪畫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后,景德鎮陶瓷繪畫風格也受到影響,不再僅局限于傳統技法和圖案,也將源自于生活的動物、版畫、民間故事以及漁、樵、耕、牧、讀、游等生活場景用于陶瓷繪畫裝飾,深受國內外受眾的喜歡,不僅改變國內消費者傳統審美風格,還不斷銷往海外,對海外消費者產生影響[30]。諸如此類的變革不勝枚舉。本來所有這些變革最初只是針對對外貿易的需要,但是久而久之,國人,甚至包括宮廷,也慢慢地喜歡這些創新變化,漸漸地融入到景德鎮傳統瓷器風格之中,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結束語
凡事都是由小變大,由弱變強,但是最后能否真正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周圍因素或條件卻是至關重要。作為瓷器國度,唐宋時期的中國瓷器就已達到無與倫比的境界,中國瓷器燒造技術也已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然而,當時的中國瓷器無論形制,還是色彩及景致卻長期處在單調守舊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元末明初。雖然自身功底和積淀豐厚扎實,但是當時的中國瓷器卻處在“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的狀態,無法自我突破。不求變革,不求突破,遲早總會被淘汰出局。在這關鍵時刻,景德鎮瓷器遇到了元帝國及浮梁瓷局的創立,迎來了來自伊爾汗國的伊斯蘭釉下彩陶技法、青花鈷料及工匠,在既有的青白瓷胎、釉、燒造工藝基礎上,短時間內催生了舉世矚目的元青花瓷器。此后,景德鎮的工匠們一直奮斗到明朝早中期,除了青花瓷外,還陸續推出釉里紅、卵白瓷、釉上彩、斗彩、五彩、素三彩和各種單色釉瓷,終使景德鎮成為世界制瓷創新中心和瓷都,享譽海內外。若是缺乏這些彌足珍貴的外援,中國瓷器的局面和結局難以想象。事實上,中國瓷器從初創時期開始就一直受到佛教文化、伊斯蘭文化、西方文化等外來文化的影響,在走出去的同時也將世界各地先進的技術和設計理念引進來,外來文化引入和融合,促使中國本土瓷器不斷壯大發展。
參考文獻
[1] 李家治.簡論中國古代陶瓷科技發展史[J].建筑材料學報, 2000,3(1):7-13.
[2] 歐陽景山.中國古代陶瓷與現代陶瓷的發展[J].中國陶瓷,? 2006,42(11): 67-67,80.
[3] 王建新.談談內因和外因在粵爵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關系[J].內蒙古師大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1):53-56。
[4] 方李莉.設計·手藝與中國文化復興.https://www.sohu.com/a/401049142_120066051
[5] 楊維中.佛教傳入中土的三條路線再議[J].中國文化研究,2013,(4):24-31。
[6] 鳩摩羅什譯.佛說千佛因緣經[M].大正藏,第 14 冊,第 69 頁.
[7] 鄧海蓮.走向極致的中國陶瓷花瓶演變趨勢分析[J].陶瓷學報,2020,41(4).
[8] 劉開敏.蓮花紋在陶瓷裝飾中的運用[J].陶瓷研究,2019,34(129):132-136.
[9]徐家星.淺談明代陶瓷上的八寶紋飾演變-藏傳佛教八吉祥紋的演變[J].景德鎮陶瓷,2013,(2):31-32.
[10]翦建文.試析長沙窯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的地位[J].民族論壇,2009,(2):55,63.
[11]張志剛,郭演儀,陳堯成.唐代青花瓷器研討[J].景德鎮陶瓷學院學報,1989,10(2):65-72,87-88.
[12]東方曉.追尋陶瓷上消失的彩虹[J].東方收藏,2012,(12):55-59.
[13]陳健捷.東西融匯的奇葩-伊斯蘭陶器裝飾初探[J].北方工業大學學報,2012,24(4):84-90.
[14]張然,翟毅.古代中國與伊朗南部地區陶瓷貿易管窺-以安德魯.喬治.威廉姆森的調查為中心[J].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7):13-23,109.
[15]朱峻熹,鄒曉松.7至14世紀伊斯蘭世界陶器發展研究[J].陶瓷研究,2019,34(134):32-36.
[16] 賈永華,何人可,黃雪妍,高原.伊斯蘭藝術對長沙窯裝飾風格之影響.藝術與設計(理論),2007,(5):152-154.
[17]韓釗.試論唐黃堡窯裝飾藝術中的伊斯蘭風格[J].考古與文物,200,(2):76-79,82.
[18]吳靜.波斯細密畫的陶瓷器具研究[J].景德鎮陶瓷學院,2012.
[19]畢奧南.元朝疆域格局概述[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10(4):1-21.
[20]董亮,董偉.中國歷代瓷窯興衰原因探析[J].中國陶瓷,2006,42(7):77-79.
[21]蒲昱曉.青瓷燒造中釉色的控制分析[J].南方文物,2019,(3):292-293+259.
[22]陸明華.元代景德鎮官窯瓷燒造及相關問題研究[J].上海博物館集刊,2005,(0):197-209.
[23]黃薇,黃清華.元青花瓷器早期類型的新發現-從實證角度論元青花瓷器的起源[J].文物,2012,(11):79-88.
[24]李璇.異域文化對元明青花瓷的影響[J].景德鎮陶瓷學院,2014.
[25]陳潔.浮梁磁局與元代官瓷-兼論至正型元青花的性質[J].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9):78-95,111.
[26]楊璐,宋燕輝.論景德鎮在古代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景德鎮外銷瓷在中國陶瓷貿易史中的歷史地位[J].景德鎮學院學報,2019,34(1):107-111.
[27]劉浩霖.伊萬里,移萬里[J].陶瓷研究,2019,34(130):92-95.
[28]江凌,董亮,郭小麗.域外因素影響下的明代景德鎮制瓷工藝技術之變[J].中國陶瓷,2009,45(10):75-77.
[29] 郭小麗,江 凌,吳國華.景德鎮陶瓷文化景觀域外器型因素探究[J].中國陶瓷,2009,45(4):43-45.
[30]劉迎紅.十七世紀瓷器貿易與景德鎮陶瓷繪畫[J].景德鎮陶瓷,2014,(1):11-12.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 on Chinese Ceramics
DENG Hai-li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5300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t culture, Islamic culture, western culture and other foreign cultures o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rcelain. Chinese porcelain reached an unparalleled level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t that time, China's porcelain firing technology was also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external advanced culture stimulation, Chinese porcelain at that time was in a monotonous and conservative state for a long time, unable to self-development and breakthrough. After the Yuan Dynasty, thanks to the foreign advanced culture and technology at the right time, combined with its own strength and needs, China's native porcelain was able to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grow. The development track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porcelain fully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needs the stimulation of foreign culture.
Keywords: Porcelain, Local culture, Foreign culture, Innovation driving 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