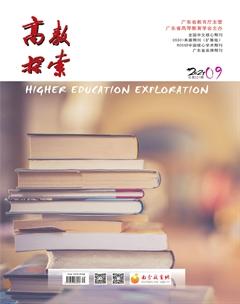大學生心理控制源的特征及其對學業成績的影響



摘 要: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對廣東某高校53個專業6600名大學生進行測量,研究了大學生心理控制源(IE)的分布特點,用相關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心理控制源與學業成績(AP)的關系,用回歸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心理控制源對學業成績的預測力。結果表明:大多數本科生為內控特征者;心理控制源與學業成績負相關關系顯著,內控特征者的學業成績高于外控特征者;心理控制源對學業成績有預測作用,心理控制源是學業成績的負向預測源。
關鍵詞:大學生;心理控制源;學業成績;特征;影響
Rotter的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心理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是有關個人性格及(或)行為與事件結局間關系的泛化性期待,這種泛化性期待與個體的行為模式直接相關。個體之間存在內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的差異,這種差異導致個體對事件結果和對自己行為期待的不同看法,內控者相信自己的努力程度能夠決定事件的好壞,當他們希望獲得成功時就會全力以赴地工作,外控者則相反。[1]高秀梅采用問卷對大學生心理控制源等進行測量,研究了心理控制源與學習動機的關系,結果表明內控特征者學習動機更強。[2]既然心理控制源與學習動機直接相關,那么學習行為和效果也可能與心理控制源相關,例如,大學生厭學可能是身心健康出現問題。羅清旭對488名大學生心理控制源和學習成績進行調查,發現大學生心理控制源傾向與學習成績之間沒有明顯關系。[3]傅茂筍等以295名醫學本科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學生學習成績和個性特征與心理控制源傾向的關系,結果表明情緒穩定、性格偏內向和非精神質特征可促進學習成績的提高,心理控制源偏內控者學習成績高于偏外控者。[4]但是,現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樣本量偏少等問題,也未能系統刻畫心理控制源與學業成績之間的關系。因此,系統研究大學生心理控制源的特征,及其對學業成績的影響,對促進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積極意義,研究結果可為加強學風建設、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供實證依據和新的工作思路。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廣東某高校53個專業的在校本科學生,每1個本科專業、每1個年級選擇1個班級作為被試(共有285個班級,含專業方向班),樣本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最小樣本為學生個體(人),共有6648名學生(男生4241人,女生2407人)參加測試。本次調查有效樣本為6600人(男生4211人,女生2389人),無效樣本為48人,樣本有效率為99.28%。
二、研究工具
(一)大學生基本信息問卷(自編)
主要包含學號、性別、年齡、生源地、專業、年級等人口學信息。
(二)內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I-E量表)
該量表共含23 個項目和 6 個插入題。每個項目均為一組內控性陳述和外控性陳述,要求被試從中選擇一個,對外控性選擇記分,得分范圍在 0(極端內控)到 23(極端外控)之間。心理控制源得分低者內控性較強,心理控制源得分高者外控性較強。I-E量表由Rotter在1966年編制,由于該量表在多種類型的樣本中應用過,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0[5],所以本研究未對I-E量表進行效度、信度檢驗。
三、研究方法
(一)數據獲取
1.心理控制源數據采用IT技術進行數據收集
學生以班級為單位到計算機房回答基本信息問卷和I-E量表,所有被試均在知情同意的情況下參與調查。研究者在現場指導,施測前向學生明確調查采用匿名形式,問卷前面也有清楚的指導語,以保證絕大部分的被試認真作答,所有被試在25分鐘內回答完問卷并當場提交。調查問卷系統設定了學號判斷、漏答判斷和重復答卷判斷,有效減少了無效問卷的數量。
2.學業成績直接從學校綜合教務管理系統的成績庫中獲取
以被試該學期所學課程的期末考試成績為記錄內容,計算每個學生的平均成績和班級平均成績,并以平均成績最低班級的平均成績為基準值,其他班級的平均成績與基準值相減獲得各個班級的調整值;用調整值對每個學生的成績進行調整,使得個人成績具有可比性。
(二)統計處理
使用SPSS 15.0對大學生心理控制源、學業成績等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統計方法包括F檢驗、t檢驗、相關分析、回歸分析等。
四、結果與分析
(一)大學生心理控制源的特征
有效被試的心理控制源得分的分布情況見表1,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根據心理控制源的總均分(M)及其標準差(SD),將所有有效被試按照“總分 對心理控制源的界定根據兩個維度,即內控特征(IE≤11)、外控特征(IE≥12)。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在有效被試中,內控特征者(IE≤11)為4427人,占67.1%(表1)。心理控制源(IE)的平均得分為9.71,全距較大(0至22),但總體分布比較集中(中分組占70.3%),具體詳見表2、表3。 (二)心理控制源與學業成績的相關分析 為了研究心理控制源與學業成績之間的關系,對二者進行相關分析,結果發現二者負相關關系非常顯著(r=-0.086**,P=0.000)。相關系數為負,表示隨著大學生心理控制源得分增加,學業成績有下降趨勢。分析結果表明,內控特征者學業成績較好。 (三)學業成績對心理控制源的回歸分析 在初步了解大學生心理控制源與學業成績的相關關系后,本研究用回歸分析方法確定心理控制源與學業成績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 1.學業成績對心理控制源的線性回歸分析 以學業成績(AP)為因變量、心理控制源(IE)為自變量進行線性回歸分析(表4)。
表4數據表明,調整確定系數值為0.007,F值為49.063,在0.000的水平上顯著。心理控制源對學業成績的最優非標準化回歸方程為:AP=67.161-0.126×(IE)。從方差解釋比例來看,心理控制源解釋了學業成績的方差變化的0.7%。心理控制源對學業成績有預測作用。
2.學業成績對心理控制源的曲線回歸分析
以心理控制源(IE)作為預測變量、學業成績(AP)為效果變量進行曲線回歸分析(表5、圖1)。
從表5和圖1可以看出,直線回歸、二次曲線回歸、三次曲線回歸的結果相似,3種回歸的擬合優度值都已經達到顯著水平。大學生學業成績會隨著心理控制源得分的增加而下降,即內控特征者學業成績好,內控性越強的學生學業成績越好。從確定系數看來,觀測值對三次曲線的擬合值最高,其具體方程模型可表述為:AP=66.826+0.026×(IE)-0.018×(IE)2+0.001×(IE)3。心理控制源對學業成績有預測作用,是大學生學業成績的負向預測源。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從Rotter社會學習理論的角度,系統研究了廣東某高校53個本科專業4個年級6600名大學生心理控制源的分布情況、等級百分比等特征,利用相關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心理控制源與學業成績的關系,利用線性回歸、曲線回歸的方法研究了心理控制源對學業成績的影響作用和預測力。
(一)大多數本科生是內控特征者
有效被試的心理控制源平均得分為9.71(≤11),內控特征者(IE≤11)占67.1%,表明大多數本科生為內控特征者(IE≤11)。這與楊琳靜在公安院校大學生所做的研究結果不同[6],但與研究者以往在廣東某高校大學新生中所做的研究結果相同。[7]研究者認為,在學習中,絕大部分本科生會認為事件取決于自己的努力程度或相對持久的特性,這種觀念會使他們在學習中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取得更好的學業成績。
(二)心理控制源與學業成績呈顯著負相關
相關分析的結果表明,心理控制源與大學生學業成績有非常顯著的線性負相關關系,內控特征者學業成績高于外控特征者,內控性越強的學生越能取得好的學業成績。這與羅清旭的研究結果不同,與傅茂筍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似。研究者認為,心理控制源是個人對于自身還是外界決定成敗的一種心理認知,內控特征者認為學業成績好壞與自己的努力程度息息相關,會產生積極持久的學習行為,所以有較好的學業成就;外控特征者認為學習成敗由外部因素決定,學習中的情感反應消極,學業成績較差。實證研究結果驗證了Rotter的社會學習理論。
(三)心理控制源是學業成績的負向預測源
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學業成績隨著心理控制源得分的增加而下降,外控性越強的學生學業成績越差,心理控制源是大學生學業成績的負向預測源,具體方程模型可表述為:AP=66.826+0.026×(IE)-0.018×(IE)2+0.001×(IE)3。研究者認為,內控特征者的行動力更強,他們在認定了自己的選擇之后,會用積極主動的學習行為證明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聚焦于高質量地完成學習任務,學業成績更好,而外控特征者則相反。因此,作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個性特征,心理控制源對大學生的學業成績具有較好的預測作用。研究結果豐富了以前的結論。
大學階段正值個體心理發育日趨成熟、適應社會的關鍵時期,大學生的學業成績受智力、非智力因素的綜合影響,其心理健康和學業狀況從微觀上看影響個體發展,向外延伸會影響家庭和學校,從宏觀上看則關乎整個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8]所以,高等學校應當在積極心理學的視角下探討大學生的認知因素,根據心理控制源存在內控、外控差異的特點進行認知歸因訓練,不斷提高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大學生要不斷調整自己的認知觀念,正確處理理想與現實、近景與遠景的關系,從多元的角度客觀地認識自己的潛質,有機地解決智力活動和非智力活動的心理沖突,不斷增強信念,積極面對學習中的挫折與困難,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自我價值。
總體上講,本研究以廣東某大學53個本科專業6600名本科生為對象,樣本量大且具有較好的代表性。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本科生為內控特征者,心理控制源與學業成績負相關關系顯著,心理控制源是學業成績的負向預測源。實證研究結果驗證了Rotter的社會學習理論,豐富了以前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未涉及影響學業成績的其他智力、非智力因素;其次,本研究是基于同一所高校的問卷調查,沒有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對一些特殊學生的心理控制源等做深入的個案分析,有待以后進行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ROTTER J B.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J].Psychological Monographs:General and Applied,1966,80(1):1-28.
[2]高秀梅.大學生心理控制源與學習動機的關系[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20,28(4):599-603.
[3]羅清旭.大學生控制源傾向及其與學習成績的關系研究[J].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5):44-49.
[4]傅茂筍,李軍,侯淑君,等.醫學生學習成績和個性特征與心理控制源傾向的關系探討[J].中國高等醫學教育,1997(2):26-28.
[5]于欣.心理控制源評定[M]//汪向東,王希林,馬弘,等.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3:265-266.
[6]楊琳靜.關于公安院校學生心理控制源現狀的調查與分析[J].鐵道警察學院學報,2015(4):94-97.
[7]高秀梅,李文利,徐文歆,等.大學新生心理控制源、學習動機和學業成績的關系[J].廣東海洋大學學報,2010(2):99-103.
[8]高秀梅.當代大學生學習動機的特征及其對學業成績的影響[J].高教探索,2020(1):43-47.
(責任編輯 陳春陽)
收稿日期:2021-05-21
作者簡介:高秀梅,廣東海洋大學副校長,三級教授,管理學博士。(湛江/524088)
本文系廣東省科學計劃項目“多科性海洋大學創新性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與實踐”(粵科計字〔2007〕173號,廣東省科技廳軟科學研究課題),廣東省高等教育改革項目“學分制背景下大學生學業支持體系的研究與實踐”(粵教高函〔2015〕173號),廣東省本科高校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立項建設項目“廣東海洋大學創新創業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粵教高函〔2016〕233號)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