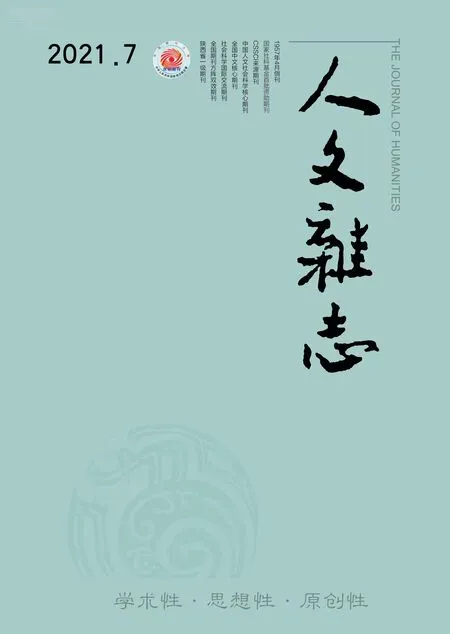清代近場社會扶貧困境與制度變革
呂小琴
關鍵詞清代 近場社會 老少牌鹽條例 社會救助
傳統中國自古就有養濟“窮而無告”之民的傳統,以彰顯王朝仁政治國的理念。清朝建國伊始便下令實施社會救助措施,但是受財政限制,地方州縣收養孤貧的數額十分有限,救濟經費也時常缺乏保障。在毗鄰鹽場的地方社會(簡稱近場社會),貧民很早就形成販賣零星鹽斤糊口的傳統。清廷認可近場社會的此種生計模式,并先后出臺弛禁貧民販鹽條例和老少牌鹽條例。它是清廷在近場社會實施的一種特殊的扶貧制度,兼具救助貧民和治理近場私鹽兩種目的。當前學界對此有一定研究,①但缺乏救助本位的制度探討。拙文擬以社會救助為視角系統考察清代近場社會販鹽救助制度的內涵、運作實效及其變革,以推動清代鹽業史研究和區域社會救助研究的深入。
一、從弛禁貧民販鹽條例到老少牌鹽條例
近場社會貧民販鹽謀生的方式與明初禁止一切私販的鹽法相悖。后明廷逐漸認識到,以暴利為目的的私鹽活動事關財政,應當禁止;以生存為目的的近場私鹽事關民生,應當弛禁。故自明中葉起,明廷出臺弛禁貧民販鹽條例,“弘治十三年奏準,凡貧難軍民,將私鹽有肩挑背負,易米度日,不必禁捕。”②該條例旨在通過承認近場社會貧民的生計方式來達到恤民和私鹽治理的雙重目的,但實施效果并不理想,“奈何近年來,因有肩挑背負不必禁捕之例,致使射利之徒肆無忌憚,或收買豪灶余課,或截買奸商私鹽,有船裝運,堆積盈室”。① 制度簡陋、管理無力是明代近場社會貧民販鹽自助失敗的主要原因。至明末,明廷始終沒有找到防范的良策。
1.弛禁貧民販鹽條例
明清鼎革,清廷深諳近場“窮民專藉挑負私鹽以謀生,窮究禁緝,必致鋌而走險”,②故立國之初便仿照明廷出臺恤貧民的鹽法條例。順治十七年,議準“貧民食鹽四十斤以下者免稅;四十斤以上者仍令納課。”③該條例劃定了貧民每日販鹽的上限,這是對明代弛禁貧民販鹽條例的發展完善,也是明中葉以來探尋防范奸徒利用該善政的一次有益嘗試。
但該條例未確定“貧困”資格,這易滋生奸民冒濫和緝私官弁蓄意抓捕貧民以完成緝私任務的亂象。如康熙十二年,云南道監察御史熊焯在《為立法分別貧難軍民與私販事題本》中指出:“有鹽徒勾連貧難軍民者,有貧難軍民影射鹽徒者。同一私販也,同一無引無數之鹽也,此中何所分別乎?甚至鹽捕作奸賄放真正鹽徒,專捕貧難人塞責者有之矣。”④為此,他奏請除了定斤數之外,還應從查姓名、給印票、限賣地三個方面進一步完善弛禁貧民販鹽條例,“竊以為分別之法,在查其姓名,給其印票,定其斤數,限其賣地,使私販之徒不得借名行奸,累貧民而壞鹽法斯已矣。”⑤ 但其建議未被清廷采納。此后半個多世紀,不法民人依然利用該項條例擾亂鹽業市場,清廷亦始終沒有出臺應對舉措。
2.老少牌鹽政策
雍正五年,浙江總督李衛改革兩浙鹽法時,發現兩浙鹽產區存在假冒貧民聚眾販私的現象嚴重,“無知愚民或被梟徒煽惑,或為地棍誘引,俱以販私為業,甚而結黨成群,假冒貧難名色,船裝陸運,潑膽公行。”⑥他吸收前述熊焯的治理思想,認為加強貧民販鹽資格管理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故規定在產鹽處所只有“貧難小民內六十歲以外十五歲以內及殘廢者”,才有免稅販鹽資格,可在不銷官引地方負鹽易米度日。⑦ 此外,他還認為向貧民提供販鹽憑證至關重要,故規定向貧民發放籌牌(或稱烙牌、木籌),⑧因此該舉措亦被稱為“老少牌鹽政策”。
老少牌鹽政策是李衛全面整頓兩浙鹽務的配套措施,加上李衛“為世宗所激賞”,故被批準在兩浙實施。據“雍正六年五月,總督李衛頒給院烙木籌,貧老少殘廢之人,令其赴院呈明詳給,許赴灶買鹽二十斤,負易度日”⑨可知,該政策的實施時間最晚不遲于雍正六年五月。又據乾隆元年浙江總督兼鹽政嵇曾筠考察,該政策實施的區域僅限于浙江省的石門、海鹽、山陰、會稽、上虞、蕭山、余姚、鄞縣、慈溪、象山、海寧、仁和、錢塘十三縣,瑏瑠后來又新增黃巖、太平和寧海三縣,共十六縣。
又稱溫臺有灶之地共計七縣,內惟黃巖、太平、寧海三縣各設有貧難老少一百名,給以腰牌,每日許赴公店挑賣數十斤,照依民間買價每斤減銀一厘,貧難老少將鹽轉售每日可得數十文,盡足糊口。
從黃巖、太平和寧海三縣老少牌鹽實施可知,老少牌鹽制度有如下規定:符合規定的老少貧民在獲得免稅販鹽憑證后,再以低于市場價格一厘銀的優惠價格,赴公店購買鹽斤后轉售他處,從中每日可獲得數十文的利潤。筆者推測其他縣份老少牌鹽制度規定也大體如此。與順治朝出臺的弛禁貧民販鹽條例相較,兩浙老少牌鹽制度在設計上更加周密、細致,其試圖通過年齡限制來精確救助對象,從而減少老少販鹽對鹽業市場的干擾與破壞。
雍正六年七月,署理江南總督范時繹和兩淮鹽臣噶爾泰指出,“兩淮止有貧難小民許其負鹽四十斤,并無老幼之分”,瑏瑢這導致奸民假冒之弊嚴重,故他們奏請仿照兩浙之例在兩淮也推行老少鹽牌政策。雍正帝咨詢李衛,李衛則表示反對,其理由是兩浙老少牌鹽制度運作中存在奸徒謊報年歲冒充資格及易于引誘近場鄉民舍本逐末的問題。① 但雍正帝在贊賞李衛全面整頓兩浙鹽務、令浙江鹽政氣象一新②的同時,充分肯定其在兩浙實施的老少牌鹽政策,認為“此法甚善,窮民既得覓利以資生,肩販不致營私而虧課,于鹺政有益。”③雍正帝的肯定與李衛的自省看似矛盾,其實不然。前者著眼鹽政,兩浙老少牌鹽制度既無私鹽泛濫,保證了鹽課,又救助了貧民,所以是良政,至于部分貧民捏報年齡則無關大局,可不予計較,這是充分肯定了李衛的治理能力。后者對兩浙老少牌鹽實施中問題的總結及自省則反映出他的清醒和見識。所以,君臣關于兩浙老少牌鹽實施效果貌似矛盾的態度其實反映出這樣一個現實:主政者的治理能力是老少牌鹽制度實施成敗的關鍵。因此,雍正指責江南督撫、鹽政等官員不能像李衛一樣實心辦事,對于奸徒利用弛禁貧民販鹽條例大肆興販私鹽或熟視無睹,或無力整治,這應是他否決兩淮推行老少牌鹽政策提議的主要原因。
終雍正之世,老少牌鹽制度只在兩浙十六縣實施,其他鹽區概不準行。唯一的例外是兩淮通州等八州縣。雍正十二年,兩江總督趙宏恩奏請,在坐落近場的通州、如皋、泰州、興化、東臺、鹽城、阜寧、安東八州縣,向貧民發放號籌作為販鹽憑證,其具體實施細則是,“查明各處戶口所食并腌切所需,議定酌留數目,造循環號籌,分別遠近,限定日期,循去環來,謂之‘籌鹽。其鹽不得過四十斤之數,過者即以私論。其鹽不入官引,亦不設店。”④結果“世宗從宏恩言,命給貧民循環號籌”。⑤ 此可稱之為“貧民鹽籌政策”,其也是對順治朝出臺的弛禁貧民販鹽條例的改進,但不如兩浙的弛禁老少販鹽政策周密。
3.老少牌鹽條例
雍正因諸種顧慮不準在兩浙外的鹽區實行老少牌鹽政策,但近場私鹽弛禁亂象并未有所收斂,反而愈演愈烈,甚至鹽商所雇私役也從中牟利。如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署理兵部侍郎王士俊指出,“而鹽商又有雇請私役分遣查拿,其所雇之人多系無賴棍徒,強狠生事,往往私梟大販,受賄縱放,專于鄉鎮之內偵探老少貧難,肩挑背負之人指為私鹽。”⑥這些鹽商所雇之人避重就輕,庇護和放縱奸商大梟,肆意抓捕老少貧難,強指其所販為私鹽。再如乾隆元年,調任直隸總督的李衛也指出“天津一帶無賴、棍徒販私騷擾”,情況十分嚴重。清廷設計近場社會弛禁貧民販鹽條例的初衷,是通過寬恤貧難而向天下昭示仁政,但其在實際運行中卻淪為奸民私販和不法緝私官弁謀私的工具。至此,加強近場貧難人群販鹽管理已經是大勢所趨。
首倡在兩浙之外實行老少牌鹽政策的大臣是從兩浙總督調任直隸總督的李衛。乾隆元年,他和長蘆鹽政三保聯名題請在長蘆鹽產區也推行老少牌鹽政策。
會題天津、青縣、靜海、滄州、鹽山等十三州縣近海地方,實在貧民年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少壯之有殘疾、婦女之老而孤獨者,各赴本地方官報名給牌,日許往來灘灶買鹽四十斤背負,在本境無引鹽地方售賣糊口。其津城內外菜鹽名色永遠革除。
李衛等人特別強調一旦實施老少牌鹽政策后,必須革除天津城內的菜鹽。所謂“菜鹽”,指專用于腌菜的食鹽。菜鹽價格低廉,一斤不過銀一二厘,銷量巨大,若同時允許菜鹽和老少牌鹽的流通,勢必嚴重沖擊引鹽市場。李衛仿照兩浙成例在長蘆推廣老少牌鹽的建議得到戶部的高度重視。
戶部意欲整治各地近場社會“奸民借口貧苦,結黨販私”行為,此時恰可以此為契機在全國近場社會推廣老少牌鹽政策,加強近場社會救助管理。但考慮到各地的特殊性,戶部下令各省督撫、鹽政就此事發表看法。
浙江總督兼鹽政嵇曾筠態度比較積極,思考也較為深入。他提議除了之前的十六縣之外再添設臨海、永嘉、樂清、瑞安四縣作為老少牌鹽政策實施的地區。
此外,他還建議從生產根源上杜絕牌私,并據此懇請清廷發幣銀四萬兩令兩浙鹽場大肆收買余鹽,近場老少貧民則赴鹽場鯪倉購鹽興販。
內華亭、奉賢、南匯、金山四縣每場各發銀三千兩,仁和場發銀三千兩,許村西路二場每場各發銀二千兩,鮑郎、海沙、蘆瀝、石堰、清泉、穿長六場每場各發銀一千五百兩,錢清、三江、曹娥、鳴鶴、大嵩五場每場各發銀二千兩,共發銀三萬八千兩,交場員收買余鹽,分給濱海近灶實在貧難老少肩負貨賣,免致對灶交鹽售私偷販等弊。其下剩銀二千兩,俟辦有頭緒,再行酌量發收。……老少赴鯪支鹽,準其銀錢并收,所賣銀錢按旬解貯縣庫,逐月解道,每于年底銷算一次,至次年再發新幣。
該提議旨在切斷貧難老少與灶民之間的直接交易,從而在源頭上控制私鹽。
不僅如此,嵇曾筠還制定了更加細致的實施章程。該章程規定了給籌鹽斤的上限、給籌的日期、發放牌鹽的官員人選及其職責、老少貧民發賣牌鹽的地方等內容,具體如下:
但事屬創始,若不定以章程,則爭端易起。臣查察情形,當以場分之廣削,銷地之廣狹,定給籌之多寡;每逢三六九日,令場員會同該縣佐雜官一員,于卯、辰二時在鯪監放;每名準給二三十斤至四十斤為準;老幼貧難不能負重至遠,止許在附近場灶十里之內挑賣,不許逾越境外及往城市有引之地與商爭售;亦不許令灶丁代挑,用船裝載,致滋影射。如有故違,仍以私鹽論罪,將鹽入官。其給籌之處則責成有司循例確查,驗取結備,籌由道申送鹽政衙門烙發,凡年六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及少壯之有殘疾,老年婦女孤獨無依者,查明實在貧難方為合例。若非近灶之人,與有親可靠、有業可守、年力壯盛者,不在此例。……如老少殘疾之內,或系成丁,或有事故,
令有司查實追籌繳銷,另選合例之人領籌頂充。②嵇曾筠從老少貧民實際出發,將鹽場產量、市場大小、運輸方式、身體狀況、發售時間,甚至老少貧民何種情況失去貧民資格等動態情況均考慮在內,所以其制定章程十分周密,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也反映出兩浙積累了十分豐富的老少牌鹽制度實施經驗。
兩浙之外,持贊同意見的還有兩淮、山東等。如署理兩淮鹽政尹會在兩浙老少牌鹽制度基礎上,結合以往兩淮近場社會貧民販鹽中存在的問題,做了不準車載馬馱、不準年少婦女販鹽、不準結隊成群興販等補充說明。③ 山東巡撫岳浚也表示贊同,理由是以往緝私官弁不力,以零星小販塞責,推行老少牌鹽制度有助于避免貧難民人由受惠者變成受害者。
反對實施老少牌鹽制度的督撫為兩廣總督鄂彌達和閩浙總督郝玉麟。鄂彌達先是以“受地理條件的限制,不便查驗老少貧民的資格”為由,表達反對態度,主張維持舊有的弛禁貧民販鹽條例即可。
其廣肇等七府屬既離州縣衙署有遠至數十里、百余里不等,貧難老少報驗非易……將貼近場灶之貧難老少男婦于境內負賣者,仍照舊例,不作私鹽,免其禁捕,毋庸令其報驗給賣,致滋更張。
從上可見,兩廣多山的地理條件的確為老少牌鹽實施帶來很多困難,所以鄂彌達救助近場貧民時,“仍照舊例,不作私鹽”,對老少牌鹽制度實施做了因地制宜的變通。閩浙總督郝玉麟反對老少牌鹽制度的理由與兩廣不同,主要原因是福建地區的貧難民人過多、所販鹽數額過大,已經擠占正鹽市場。他為此甚至提議廢除既有的弛禁貧民販鹽條例,改由地方州縣出銀救助近場貧民,“令將額定貧難七百九十六名,每名日給錢十文,于錢水項下動給”
將各地督撫及鹽政官員意見匯總后,戶部遂奏報朝廷進行決斷。乾隆帝雖決意在全國推廣老少牌鹽制度,但在獲悉各地督撫意見后對此事態度更加慎重。為此,他一方面安撫持反對意見的閩浙總督:“此奏在事后之調濟則善矣,若未雨之綢繆則未也。故傳云:‘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夫朕之本意豈令其如是哉?天津、淮鹽等處皆有此弊,已經部議矣。卿其酌量妥辦可也”,①并且最終同意了閩浙總督郝玉麟直接給錢救濟的提議;另一方面,他又特意于同年七月咨詢重臣張廷玉的意見。張廷玉十分支持老少牌鹽制度的推廣,其《為遵旨議奏事》所表達的意見與兩浙成例基本一致。
接準部咨;六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至少壯之有殘疾,及婦女之老年孤獨無依者,許其負鹽四十斤易米度日。如不合例之人,概不許借端興販。至稽查之法,于本縣報名驗實注冊,給以印烙、腰牌、木籌,每日卯辰二時赴場買鹽挑賣,一日止許一次,不許船裝。倘越境成群結隊,并一日數次,積少成多,窩囤轉販者,分別禁止。
得到張廷玉的支持后,乾隆帝于乾隆元年下令在全國主要近場社會推廣老少牌鹽政策,并將之列入大清鹽法條例,以示重視。③ 老少牌鹽條例以資格認定為核心,力圖通過加強對老少貧民販鹽自助的管理,減輕牌鹽銷售對鹽業市場正常秩序的沖擊。這是對近場社會貧民販鹽自助管理制度的重要補充和完善。
二、從牌鹽到牌私:多地老少牌鹽條例在實際運作中陷入困境
鹽利的誘惑及各地參差的執行環境使得各地老少牌鹽制度運行過程中充滿各種挑戰,尤以牌私為最,“自設貧販以來,奸徒收賣牌鹽,私販充斥,官引難銷”。④ 牌私上虧國課,下損貧民,使國家善政反為弊政,于國于民都產生嚴重損害。
1.長蘆牌鹽淪為鹽徒的護身符
長蘆鹽產區位近京畿,其地牌私最早引起清廷關注。乾隆八年,長蘆鹽商王志德向長蘆鹽運使鄧釗反映,長蘆牌私嚴重侵占正鹽引地,致使官鹽滯銷,懇請予以停止。為達目的,他以退運鹽斤向鹽運使鄧釗施壓。⑤ 鹽商退運關系重大,其影響不僅在于長蘆鹽運使需重選鹽商,而“另招他商接認承辦,彼見前車既覆,畏首畏尾,亦俱退縮不前”,⑥ 更重要的是這將導致鹽課不能及時完成。鹽運使鄧釗明曉其中利害關系,遂重視王志德的提議,命令薊永掣通判,轉飭灤州、遷安、樂亭、豐潤、寧河五處州縣官就此事發表看法。州縣官的考成與當地鹽斤銷售直接掛鉤,⑦因此他們一致提議順應商情,廢除老少牌鹽。據此,鄧釗向長蘆鹽政伊拉齊反映了牌私泛濫、沖擊鹽業市場的嚴重問題,“竊查老幼殘疾孤獨無依,準給腰牌負鹽零賣,原乃養活無告窮民而設。惟是奸徒勾通老幼囤積販賣,若不亟請變通,則官引更加壅滯”
伊拉齊高度重視牌私沖擊引鹽銷售一事,于乾隆九年十一月會同直隸總督高斌和巡撫那蘇圖,向清廷上《為鹽務變通事奏折》:
不意設立貧販以來,官引日見難銷,私梟日甚一日。現在灤、遷等五州縣貧販四五六十名不等,以每人每日負鹽四十斤,合計一年約共一萬一千余引之鹽,官引已占過半,即使貧販毫無影射行私,而官引已有鹽壅課絀之虞。況場灶阻隔,遠近不齊,徒假老少貧民之名色,實為奸梟、囤戶之護符。如孤寡殘弱無告之貧民,老者六十歲以外,少者十五歲以內,兼有疲癃廢疾,赴場籌買,近則數十里,遠則百十余里,步履尚屬艱難,何堪背負奔走?若以道途之遠近計跋涉之行蹤,必得一二日至二三日始獲負鹽一次,沿街叫賣,隨時出售,所余利息已不敷往返食用。設遇酷暑嚴寒、風霜雨雪之時,雖欲赴場負鹽,亦勢所難能。因而有種不法奸徒,勾串貧販,就產鹽場灶之處覓一偏僻地面,用賤價收買窩囤,今日過東,明日轉西,并無一定下落,或藉老少名目重復混買;或串頑猾灶戶,盜賣行私,盈千累萬。早夜搬運,車載肩挑,公然無忌。一經拿獲,輕則棄鹽逃走,重則拒捕傷人。且地方遼闊,有數巡役焉能宗宗究結?即如獲送到官之犯,審訊時皆以買之老少牌鹽為詞,竟而漏網!如此弊端,不可枚舉。
從上可見,長蘆老少牌鹽制度在實際運行中存在不少問題,如牌鹽發放數量過多,甚至超過官引,這已引起官鹽滯銷,損害了國家鹽政。但該制度最大問題還在于設計立場自上而下,沒有考慮救助對象的實際,如伊拉齊所述,老少貧民往來背負牌鹽十分不便,甚至出現售鹽所得不抵運鹽所費,這就給了私鹽販利誘老少貧民倒賣牌鹽的機會;更有甚者,私鹽販直接串通灶戶,盜賣私鹽。這極大地增加了執法難度:一方面因地域廣闊,執法人員力量單薄,“有數巡役焉能宗宗究結”,無法有效緝拿牌私,遂使“老少之利源變而為私梟之弊藪”;①另一方面,即使抓住鹽販,其仍可以所買為牌鹽來開脫,老少牌鹽制度成為私鹽販的護身符,令執法人員無可奈何。伊拉齊的奏折揭示了長蘆老少牌鹽制度的運作實情,暴露出老少牌鹽制度在設計及運作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遂引起清廷的重視。
2.兩淮牌鹽淪為鹽梟的弊藪
除長蘆外,兩淮也出現牌私泛濫現象。如乾隆六年,鹽政準泰指出,“伏查上元等四縣濱臨大江,巡緝稍疏,私販透漏,兼有場灶貧民肩負零鹽,遂致官引壅滯”。② 又如乾隆十年,兩江總督尹繼善指出老少牌鹽沖擊正鹽引地,“淮北營銷食鹽之山陽、清河、桃源、邳州、宿遷、睢寧、贛榆、沭陽八州縣,地方土瘠民貧,又皆逼近鹽場壩所,貧難老弱零換灶鹽及掃積泥鹽,小民貪賤買食,遂致官鹽壅積不銷”。③還如乾隆十一年,兩淮鹽政吉慶指出,高郵州和寶應縣的正引因老少貧民販鹽而壅滯,“緣該州縣近接場灶,貧難老少多以零散泥鹽,易換食物,是以民間鮮買官鹽”。④ 再如乾隆十四年,總漕瑚寶指出,老少牌鹽成為漕私的來源之一,“天津、阿城、淮安、儀征等產鹽之鄉,老幼男婦貨賣鹽斤者,一遇漕艘經過,即充塞河干,混行售賣,甚有黑夜備船,私相包送,無知舵丁水手暗行夾帶。”⑤為此,他奏請由漕運所經省份的督撫加強巡查貧難老少販私的力度和重申舵丁和水手夾帶私鹽的禁令。
盡管兩淮地方督撫及鹽政們多次指出兩淮老少牌鹽條例在實施中弊端叢生,嚴重沖擊正鹽市場,但清廷對此的態度并不積極,其認為地方州縣私鹽泛濫的主要原因是緝私官弁不認真稽查,并非老少牌鹽,故應對策略是加強緝私。如戶部在批復兩江總督尹繼善的奏折中所說:
各該州縣地近場灶,貧難老弱零換灶鹽,則各省附場之區均有老少貧民換買零鹽,而每年營銷鹽引未嘗不按額全完,何獨山清等八州縣遂有官引壅滯之患,該鹽政不務設法緝私,以清食地積壓之源。
因此,直到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山東爆發大型鹽梟案,清廷才對其他地方牌私問題予以重視。
山東嶧縣縣役獲悉境內有49名私鹽販推著鹽車沿途售賣私鹽,他們前去查拿時,鹽梟依仗人多勢眾,持械拒捕,致傷斃巡役官,奪走鹽車,四處逃逸。⑦ 鹽販殺傷官差,性質嚴重,引起了清廷高度重視。清律規定:一經查獲私鹽,務必從源頭上追查所販私鹽的來源。⑧ 山東巡撫國泰追查出此次鹽徒所販私鹽的具體來源。
朱思恭在崇逢[集]開設歇店,平素零星收買老少男婦私鹽囤積在家,轉賣圖利……李順,李倫,陳四等一伙系在郯城崇逢集零星收買,背負鹽斤寄在朱思恭家。宋四夸子、袁文舉一伙系在海贛交界處零買老少鹽,用車裝載,乘夜推至蘇斌店內住歇,輾轉赴嶧縣運賣。……而張莊寺一處尤與海贛相近,蔣太、王子悅、程選、王九等在該處向肩挑背負之人收買鹽斤,寓歇尤格車店,該店家亦屬知情。
山東鹽梟案的案發地雖然在山東,但鹽梟所販私鹽卻來自兩淮鹽產區海州和贛榆縣的老少牌鹽。乾隆帝通過山東鹽梟案的來龍去脈已然洞悉老少牌鹽問題之根本:鹽梟可假手近場貧難人群觸及被政府嚴格控制的鹽業生產領域。若此僅為一地現象,則因量少尚不致產生嚴重后果,但此時鹽梟可利用老少牌鹽條例在山東、兩淮等多地收購牌鹽走私,如此積少成多,勢必嚴重擾亂清廷嚴格控制下的鹽業市場秩序。但在鹽梟供認的同時,兩江總督高晉堅稱兩淮巡防嚴密,不存在牌私。正在雙方膠著之際,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江蘇鹽城鹽梟走私案的發生則坐實了兩淮牌私的大量存在。
現據楊魁奏訊鹽城一案私梟供詞,即稱各向灶戶及老少鹽擔買得私鹽二三百斤至四五百斤不等,分貯小船等語,是老少鹽擔實為私販弊源。
江蘇鹽城鹽梟案就發生在兩淮鹽區境內,且據案犯供述,牌私確為私鹽重要來源之一。此外,通過審訊還查出,兩淮緝私官弁因循塞責。“至向來緝私之法,文武兵役俱有責成,又有特委之員懲獎之吏,奈日久因循視為泛常,甚至鹽城縣私梟拒捕案內有王三等代為說合販賣之事。”②至此,兩淮存在牌私和緝私官弁放縱的事實明白無誤。
乾隆帝遂令兩淮官員再上奏議論。同年五月,兩淮鹽政伊齡阿在《酌收買余鹽事宜疏》指出,現在查辦老少余鹽一事,“實為鹽務緊要關鍵。”他認為,老少牌鹽從源頭上擾亂鹽業管理秩序。“但向來煎鹽之灶有稽查火伏之例,曬鹽之池亦有磚塊丈尺之限,立法原自周詳。緣有老少余鹽藉名隱混,于是附近場灶之州縣,片引不行,而私販之徒益加充斥。”③至此,兩淮鹽政官員也承認牌私嚴重沖擊了引鹽市場。
從以上長蘆和兩淮鹽產區老少牌鹽實際運作情況可知,鹽徒、鹽梟通過操縱真實的或假冒的近場貧民,得以從源頭上獲取被清廷嚴格控制的鹽斤,加上緝私官弁的敷衍塞責,甚至受賄縱放,致使各地牌私泛濫,擠占正鹽銷售市場,使“老少之利源變而為私梟之弊藪”。④ 這使多地督撫上奏懇請取締老少牌鹽制度,也迫使清廷不得不慎重思考老少牌鹽制度的存廢問題。
三、乾隆中后期老少牌鹽條例的逐漸廢除
長蘆鹽區位近京畿,牌私問題迅速得到朝廷關注,因此率先廢除老少牌鹽制度。乾隆九年十一月,長蘆鹽政伊拉齊會同直隸總督高斌和巡撫那蘇圖,向清廷上《為鹽務變通事奏折》,指出老少牌鹽不僅引發牌私,還誘發灶私,從源頭上開啟私鹽之弊,故懇請“將此老少貧民照閩省之例,商捐折給錢文,以資養贍。”⑤乾隆十年,清廷批準廢除直隸下屬的灤州、遷安、樂亭、豐潤、寧河、盧龍、撫寧和昌黎的老少牌鹽制度,⑥其老少鹽斤改由鹽商運銷后,由鹽商給散銀錢救助近場貧民,但是,以“因商力不敷,尚仍牌鹽之舊”⑦為由,駁回了天津、靜海、青縣、滄州和鹽山五州縣的奏請。
至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長蘆鹽政、天津總兵吉慶會同直隸總督方觀承《奏請厘老少牌鹽謹陳贍養之法折》再次奏請仿照灤州成例,廢除天津、靜海、青縣、滄州、鹽山五個州縣的老少牌鹽政策,改由鹽商行銷老少余鹽。“因老少牌鹽賣制錢二文半,商人賠累起見”,吉慶提議抬高鹽商行銷老少牌鹽的價格,規定“每斤止售小制錢五文”。但是,上述提議遭到天津士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定該奏折是官商勾結的產物,意圖讓他們食貴鹽。
裁掣老少鹽牌,改給養贍錢文,原為靖私疏引起見。天津士民,恐改行引鹽,商人王志德得以壟斷,遂創為浮議。有云鹽臣吉慶與王志德同宗者,有云運使盧見曾與王志德親厚者。
同年五月,乾隆帝命令直隸總督方觀承前往天津查辦此案。⑨ 總督方觀承回京復命,說天津“老少牌鹽案”風波已平息:“經臣曉諭,鹽價照牌鹽之舊,定以每斤小制錢五文,民間仍可食賤,眾情乃知此舉鹽政非為瞻顧商人王志德而設。”瑏瑠至此,乾隆帝批準廢除天津、靜海、青縣、滄州、鹽山五州縣的老少牌鹽政策,還給予了天津鹽商免課行銷老少余鹽的優惠政策。“核計成本,商力難以賠墊,請將天津縣所銷余引,免其輸課。”
此后25年間,除長蘆外,各地依然保留老少牌鹽制度。直至乾隆四十二年山東鹽梟案爆發后,乾隆帝開始謀劃全面廢止老少牌鹽條例,“朕意與其存此例以滋弊,莫若去此例以防奸。”他還指示清廷出銀錢散給近場貧民,其老少余鹽改由鹽商領銷或買用。
因思山東曹、沂一帶,鹽梟之案已經屢犯。由于其地與海贛鹽場相近,而各場所出余鹽,舊例原為贍恤貧乏之用,日久遂為奸民牟利之資。即或嚴為查禁,非肩挑背負,不許出場,而此等梟眾,無難私雇窮人在場,如數攜出。彼即從旁收買,一落其手,仍可積少成多,販行無忌。是此例不除,流弊終難盡絕,不可不通盤籌畫,以期妥善也。……諭將各場所出余鹽,貧民肩挑背負,歲可獲利若干,通行核計,即照數官為收買,散給貧民。其一切肩挑背負之例,悉行停止。其收買之鹽,或仍給商領銷,或并聽商買用。
雖然有意全面廢除老少牌鹽制度,但乾隆帝顧慮到各省省情不一,態度依然十分慎重,下令讓各省督撫、鹽政就此事表態。
鑒于老少牌鹽的難以管理并在事實上成為私鹽重要來源,嚴重干擾引鹽市場,損害國家鹽政,各省督撫及鹽政官員對廢除老少牌鹽制度大都持贊同態度。如直隸總督周元理贊同長蘆廢除老少牌鹽,但堅持一如既往地由鹽商出資濟貧。“從前原準日買場鹽四十斤,嗣因私販藉圖影射,歷經奏準,每名日給制錢二十四文,令商捐交各州縣發給,鹽斤均歸商賣,日久相安,毋庸另籌。”③山東巡撫也表示贊同,“永利、濤雒二場奏停老少鹽牌,加余票一千六百八十張”,④其近場貧民仿照長蘆成例,由鹽商給散銀錢予以救助。兩廣總督桂林指出,“此中間有奸徒囤販等弊,往往藉口收買零鹽,事發到官,地方官聽其狡展,沿途盤詰,巡役亦不能攔阻,均屬勢所必有”,⑤故也贊同廢除老少牌鹽政策。四川總督文綬也以老少牌私侵引蠹課為由表示贊同廢除老少牌鹽。“敘州府屬富順縣、嘉定府屬犍為縣產鹽較旺,配引之外,不無余鹽,向有老少貧民易米養贍之例。奸販因而零星收買,積少成多,私行販運,在所不免”
廢除老少牌鹽制度的阻力主要來自兩淮。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江蘇鹽城鹽梟案成為推動兩淮老少牌鹽制度廢止的關鍵。隨后,兩淮鹽政伊齡阿上奏《籌備老少余鹽酌定章程》,提議由國家出資令鹽商按時和依時價收買灶戶余鹽,再依工本價售賣。
海濱窮灶俯仰之資,惟賴于鹽。因停運之時,綱商未能隨時收買,不若肩挑背負之眾,晨夕往來,可以任意交易,故以為便。今飭商收買余鹽,應確查工本之數,按依時價,源源收買。在灶戶自可不致妄想售私,而商人照撥負買鹽之價收買,即令照本轉輸,亦不得過于抬價。
但是,軍機大臣認為它不是防杜私梟的良策:“查私梟囤販,悉由影射余鹽。若但令該商等按依時價,源源收買,而窮灶之賣給商人,與賣給撥負之民窮無以異,仍恐未能盡杜私售之弊。”⑧ 同年閏六月,乾隆帝贊同軍機大臣的看法,不再與兩淮鹽官展開拉鋸式談判,下令“所有江省現在情形,可否照兩廣之例,將老少鹽名目,永遠革除之處。應令妥協籌議。”⑨面對乾隆帝廢除兩淮牌鹽的強硬態度,總督高晉會同江蘇巡撫楊魁、兩淮鹽政伊齡阿,奏請廢除老少牌鹽名目,重新回歸到遵行弛禁貧民販鹽條例上。結果獲得批準。
兩淮附近場灶向不營銷官引之通州、海州、泰州、東臺、興化、鹽城、阜寧、如皋、安東各州縣濱海貧民,仍照向例,官給循環號籌,赴場買鹽,挑負該處村莊售賣。并查明各州縣見在滋生戶口,歲需民食鹽斤若干,令各場商人于按額配引之外,照數酌留驗籌賣給,將老少鹽名目永遠革除。一切給籌更換定地,限日造冊申報。稽查透漏各事,宜悉照舊例,責成各地方官暨場員辦理。
與其他鹽區順利地廢除老少牌鹽政策相比,兩淮鹽區廢除過程曲折,原因主要在于牌私已然成為兩淮鹽區各方利益群體重要的獲利渠道,這使得兩淮督撫、鹽政在如何廢止老少牌鹽制度上與朝廷展開反復博弈。至此,除兩浙外,各省均廢除老少牌鹽制度,而如何救助近場貧民則需各省因地制宜,重構救助機制。
四、近場社會多元救助機制的構建及消解
第一種是牌鹽救助機制。兩浙鹽區為老少牌鹽制度發源地,且救助總體效果良好,因此乾隆四十三年,兩浙督撫明確反對廢除老少牌鹽制度,并從四個方面陳述了反對意見:一是兩浙近場貧難老少群體總人數約六百人,他們以販賣牌鹽為糊口的生計;二是兩浙鹽區的老少牌鹽制度實施效果良好,不存在越界私販侵害引地的不良現象;三是方便濱海村落居民買食鹽斤;四是廢止老少牌鹽制度的后果,可能使貧難老少群體淪為流民,引發基層社會治安問題。② 乾隆帝對此表示認可,并允許兩浙保留老少牌鹽制度。③迄清末,兩浙一直維持老少牌鹽制度。光緒二十九年,戶部指出兩浙老少牌鹽(又稱籌鹽)成為梟私射利之途,提議予以廢除,一律改行票鹽。④ 至此,兩浙老少牌鹽制度正式廢除,以老少牌鹽為核心的兩浙近場社會救助機制不復存在。
第二種是鹽商救助機制。老少牌鹽廢止后,部分鹽區以鹽商為核心構建近場社會救助機制,如“老少鹽牌各省皆有,……本善政也。然刁民往往藉此為走私之地,故由商捐貲散給口食,停其負販。”⑤又如“后以貧民過多停牌鹽,每名日給錢十文至二十四文。”⑥改折錢文后鹽商需要在鹽課之外再額外支出一筆錢財,但保障了引地不被侵占,從而保護了其核心利益,鹽商也樂意為之。最早實施近場社會鹽商救助機制的是長蘆鹽區。乾隆十年,長蘆鹽區的部分近場州縣就改由鹽商折給錢文以養贍貧民。“照依閩省之例,按名每日折給大制錢二十四文,每月需錢萬千,飭令該商于每月下旬捐交該管州縣貯庫,月朔傳齊老少,按名散給,誠為商民兩便。”⑦乾隆四十三年全面廢除老少牌鹽后,山東鹽區規定“仿照天津等州縣給錢停販之例,每老少一名日給制錢二十四文,飭該地商人按數捐輸,繳存縣庫,地方官按月散給,以資養贍,將舊設牌鹽永行停止。”⑧四川鹽區也規定,鹽商帶銷牌鹽后需出資養贍貧民。“應仿照收養孤貧之例,飭令犍為、富順二縣,查照舊時報驗注冊挑負零鹽之老少貧民共有若干名口,每名酌給銀二分以資養贍,半月一領,即于照票所收息銀內核實支銷。”⑨四川鹽商出資救濟近場貧民的人數眾多。如乾隆五十一年,犍為縣鹽商出資二千六百七十六千三百六十文,散給貧民劉文黃等353人。瑏瑠此外,他們救濟近場貧民的行為還具有持續性,“乾隆四十四年迄今嘉慶十八年,均照奉發水票五百張,所繳息銀依數令繳錢散給貧民每日二十文,每月一領。”
實施以鹽商為主的近場社會救助機制需以鹽商獲取巨額鹽利為前提和基礎。乾隆時期是清代鹽業發展史上的巔峰,道光以后鹽引日漸滯銷,鹽商處境艱難,無暇顧及救助近場貧民,上述鹽區近場社會貧民由鹽商出資養贍機制被迫中斷。如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定郡王載銓在《單呈會議酌改長蘆鹽務章程條款》中奏請,刪除由長蘆鹽商提供的老少鹽牌經費開支,以恤商艱。
第三種是籌鹽救助機制。老少牌鹽制度廢除后,兩淮鹽區恢復了雍正十二年的“貧民鹽籌政策”,以籌鹽為核心重建近場社會救助機制。但至嘉慶晚期,籌私如同牌私一樣淪為奸徒牟利的工具,①這給近場社會籌鹽救助機制以沉重打擊。
面對籌私泛濫,嘉慶帝多次下旨嚴厲打擊販賣籌私及奸徒,力圖以此維系兩淮近場社會籌鹽救助機制,而不是如兩淮督撫、鹽政們所請取締籌鹽,②但整治效果不甚理想。至道光年間,兩江總督陶澍再次指出兩淮近場社會籌鹽救助亂象導致籌私泛濫,其中淮北老少籌鹽的弊端是奸民藉老少牌鹽暗中接濟私梟,給緝私帶來很大困擾。③ 此外,他在《請將淮北滯岸試行票引章程折子》中還指出淮北籌鹽不僅是梟私的重要來源,還給緝私官弁縱放私鹽提供借口。④ 為此,陶澍于道光十二年淮北推行票鹽法時,以“籌鹽不停,場私透漏之弊不絕”⑤為由,奏請廢除淮北籌鹽,一律該行票鹽。⑥ 但票鹽法只在形式上賦予所有人販鹽權利,事實上貧民根本無法與鹽商競爭,更遑論以販鹽謀生,廢籌改票在現實中等于奪民衣食,逼迫近場社會貧民鋌而走險,販賣私鹽,甚至對抗緝私官兵。⑦ 然而,晚清官府似乎只在意確保國家鹽課收入,至于票鹽法是否發揮近場社會救助功能,則不在其考慮之中。于是,不僅淮北禁止籌鹽,不久之后,陸建瀛也于淮南廢籌改票,兩淮近場社會籌鹽救助機制至此全部廢止。
結語
近場社會靠鹽吃鹽,歷史上既已形成貧難人群以販賣少量食鹽為主的生計模式。清承明制,建國伊始即實施近場私鹽弛禁條例,通過合法化近場私鹽來解決近場社會救助問題。與官府救助相比,販鹽自助的長處在于能減輕地方官府財政負擔,同時增多救助人數,事倍而功半。但是,販鹽以販鹽為自助手段,鹽為利藪,易被各方覬覦,因此其不斷受到私鹽問題的影響。于是,近場社會販鹽自助與近場私鹽治理交織一起,相互影響,大大增加了救助管理的難度。
這使清廷有意加強近場社會救助的頂層設計,老少牌鹽制度即為清廷經過大量討論后慎重出臺的應對舉措。從規范管理看,老少牌鹽制度以“貧難”資格認證為核心,設計周密規范,可操作性比較強,是對近場社會販鹽自助機制重要的發展與完善。但40多年的實踐證明,老少牌鹽制度不僅沒有減少私鹽弛禁后的走私活動,牌鹽反而成為私鹽交易的又一源頭,致使私鹽活動有愈演愈烈之勢。清廷近場社會救助變革由此遭遇重挫。
表面看,老少牌鹽制度實施失敗的原因在于其管理成本過高。老少牌鹽制度設計周密,且以全面強化對近場貧難人口販賣鹽斤的管理,來彌補此前近場私鹽弛禁條例內容甚為簡單、可操作性差等不足,但代價則是執行和監督所需人力物力遠超以前,更重要的是其難以適應不同鹽產區復雜的鹽業生態。這導致老少牌鹽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因執行不力而變形走樣,進而滋生越界私販、侵害引地等違法現象,甚至為私梟所利用,不但未能獲得良好的社會救助效果,反而嚴重沖擊了鹽業市場和近場社會的正常秩序。
但事實上,老少牌鹽制度失敗的原因在于其已成為威脅鹽業管理體制的漏洞和缺口。近場私鹽弛禁政策賦予近場社會貧難人口進入鹽業市場的特權。這種特權的取得有嚴格的限制條件,但其畢竟使民間社會力量由此得以進入鹽業流通領域。同時,參與鹽業流通的民間社會力量需從鹽場灶民手中購買余鹽,由此民間社會力量又得以接觸官府控制最為嚴格的鹽業生產。這就為販賣私鹽者利用這些民間社會力量接觸鹽業生產,進而走私牟利提供了可能。因此,清朝廷若要徹底根除近場私鹽弛禁的治理問題,則不僅需要完善弛禁條例、老少牌鹽制度等鹽業流通流域的相關制度,還需制定與之關系密切的鹽業生產領域、銷售領域的相關制度。這將使清廷面對鹽業經濟領域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需要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來為解決上述問題奠定制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