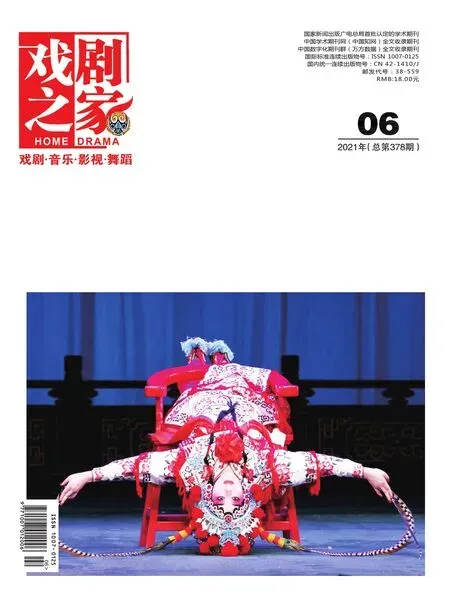教化:先秦儒家的當代價值審視
(山東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山東 濟南 250014)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以來,學校廢經學而分科教學,那么儒家尤其是作為儒家濫觴的先秦儒家的教化哲學思想體系是否還能適應現代社會?要回答此問題,就必須探究先秦儒家教化哲學思想的本源與內涵,以追根溯源,為當今教育及其未來發展提供啟示與借鑒。
一、天人一體:先秦儒家教化的本源
儒家教化作為儒家精神的內核,貫穿儒家精神始終,儒家精神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教化之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將其性命定在人身上而成為人性,人性就是人之為人的規定性,而人的價值的實現就是人性的充分展開與實現。因此,儒家教化以其天命觀為基礎和前提,究教化之旨,則不能不明儒家天命觀。儒家的天命觀一言以概之,即天人一體。
《中庸》的天命觀以“誠”為核心,并通過“誠”再一次言明天道與人道的關系。“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天之道也”,是說天道的運行是誠的,是自自然然的。“誠之者,人之道也”,是說承天道之誠就是人之道。天道本是誠的,故而人道也是誠的。但是人性之誠不能自然而然地顯現,需要教化。所以《中庸》又言:“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本性之誠在于天道之自然,但此誠的彰顯則是教化之功,就是讓人通過自身的努力在日常行為中貫通,反身而誠,一言一行都做到誠,才能達到“至誠”。可見,此誠是自我教化之功。那么如何實現自我教化呢?《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皆為情,情生于性,情之未發即性之本然狀態,就是“中”。當人與外物相接,情有所發,且合于節度,就是“和”。達到“中和”境界的過程就是盡性的過程。盡性的過程即教化的過程,也就是圣人在自我教化的同時教化天下,使天下之人、天下之物都進行自我教化。圣人在教化的過程中實現了天命,與天的生命節律相契合,就意味著人與天地為一,也就實現了天人一體。
二、先秦儒家之教化
人生而有天性,德就在人性中,但人性之德無法自然彰顯,需通過教化。“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故人之為人,文質不可偏勝,偏于任何一方都不能充分彰顯德性之本然、自然。若要培養君子之德,則必行忠恕之道。
(一)教化之旨:君子
在儒家看來,人生的意義在于盡性成德,教化的過程就是個體盡性成德,并興發他人感受生命的真實意義的過程。于述勝先生將其稱之為“意義——感通”之學。在儒家看來,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人才稱得上是君子。
修己以敬,既是“以敬修己”,也是通過修己來達到敬。何為敬,敬的是什么呢?皇侃曰“身正則民從,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也。”劉宗周道出“修己以敬正是尊德性而道問學。”郝敬解“尊德性”為“必尊奉之為主宰”,即德性為一身之主宰,不為物欲所牽。德性即天性,天性分而命之,一物有一物之性,命定在人身上即為人性,人性即天性。修身就是盡性,敬的正是人性。天地廣生萬物,并使萬物按照各自的“性”展開以完成各自的生命,此生生之德是天地間最大的德,人為萬物之靈,得天地間最靈之氣,至圣之人可參贊天地之化育,正是因為圣人盡其性,所以敬的不僅是給予生命無限意義的人性,更是天地生生之德。
修己以敬是君子自修的內在功夫,君子在修己的過程中,身心安定,有所依止,在各種人倫關系中彰顯己德,以情與他人相感通,他人也能夠感受到君子內心的安寧與安定,因而能夠自安。“安人”、“安百姓”,一方面是使他人感受到君子內心的安定,另一方面則是使人人能夠仿效君子修身,以實現每個人的安止。這正是《大學》所言的修身以達于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君子教化天下的過程,也正是儒家教化之道。
(二)行仁在于行忠恕之道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仁是什么?相對于如何對“仁”進行定義,儒家更為強調的是如何行仁。行仁,在于行忠恕之道。
孔子之道一以貫之,曾子認為此“一貫之道”就是“忠恕”。程子注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后世學者多沿用其說。己,兼身心而言,人有耳目口鼻等百體,而心為主宰,內具天德良知。因此,盡己就是盡心,就是充分顯現本已具有的天德良知,彰顯人之為人的本性,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盡心知性”。人性即天性,盡己就是盡天性。推己及人之謂恕,恕是以情為基礎的。人皆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此情是相通的,故能夠以己之情通人之情,人之間能夠實現共情。恕即推己及人,以我之心度他人之心,以我之情度他人之情。所以當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盡己是從修身成德方面說,推己是從成人安人方面說,而修身成德離不開人倫關系,個體修身的過程也是成就他人的過程,而成人與成己又是一體兩面之事,在成己的過程中成人,同時成人的過程也實現著成己,故朱熹注曰:“忠者,體;恕者,用。”忠恕是體用關系,行忠恕之道就是成己成人,就是行仁的開端了。
三、先秦儒家教化的當下之境
教化關涉人的存在,探求人的內在世界,以本性之善充盈生命,這正是儒家教化生命力強大的根本原因。然而實際情況是教化傳統不斷衰落,逐漸被等同于學校中的道德教育,出現了“教而無化”等問題,教育中多了工具性,少了自然性與人性。接續教化傳統,教育才能更有生命力。
(一)教化與當代道德教育
儒家教人修身成德以化成天下。德是為人之本,有德方能體驗到人生意義,弘德方能實現對社會的教化。儒家強調通過以君子為榜樣,進行社會教化。“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者的德性為萬民觀瞻,故不能不慎乎其言行。“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為政者若能孝敬己之老者,愛敬己之長者,同情、救濟孤兒,則天下之民皆能仿效行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君子彰明其德于天下,民眾仿而效之,以自我教化實現社會之教化。
近代以來,社會形態更迭,隨著西方教育的引入,中國的教育形態發生了重大改變,德育成為學校教育的一部分。有學者認為,德育是在學校中施行的嚴格意義上的道德教育,強調在道德知識認知的基礎上,使學生在面對價值判斷時,能夠做出道德選擇,實質上這是一種預設的價值不斷內化的過程。因此,現代道德教育的難題“在于如何使抽象的理性概念灌注生命情感和真實感受的內容”,缺少了情的道德教育是沒有溫度的。道德教育的應然與實然狀態都應從興發學生的本性之德出發,讓學生從這種興發中體驗到德性與生命的真實意義,這正是先秦儒家教化與當代道德教育的最大不同所在。
(二)教化的傳承與轉化
教化不等同于學校教育,學校教育是實現教化的途徑和方式,但不能代替教化。在當今實現儒家教化,首先要提升教化的意識,興發起人盡性成德的自覺。教化實現于人的日常行為之中,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修身之事非一日之功,自明其德需新而又新、明而又明,不斷切磋、琢磨,生命不息則修身不止,生命的意義即在于日修其身。修身無法脫離日用倫常,人在生活中待人應物處事,皆不離修身,生命中的細微之事皆離不開教化。
儒家重君子與小人之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與小人的根本區別在于是否知天命。君子于事行忠恕之道,反躬自省,畏人道,畏天道,識得人性本于天命,因此內含誠敬之心。君子知天命,知其所當為與不能為,不會再為事情的功利結果而困擾,小人不知天命,以利為利,無所畏懼。君子言行為世人提供了普遍的道德法則,世人以君子言行為榜樣,仿而效之,由此實現君子的社會教化。然教化的根本在于喚醒人本性具有的天德良知,啟發人的道德自覺,達到高度道德自律。以君子為榜樣是“他化”,并沒有真正實現教化,“他化”的最終目的是“自化”。如何實現由“他化”到“自化”的轉變呢?這就要在教化的過程中引入情。所謂“通情達理”,情相通以后才能在理上達到一致。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皆始于共情,共情使得人與人之間的生命節律相契合,由此便能達致和樂之境。故教化應以共情為前提和基礎,道德情意興發,道德認知和道德實踐才能實現一致。
注釋:
①(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02:17.
②周衛勇,曾繼耘.生生之道:先秦儒家教化哲學的理論基礎——以《中庸》為主體的研究[J].教育學報,2018,14(05):102-108.
③李景林著.教養的本源 哲學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論.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06:05.
④(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02:31.
⑤(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02:32.
⑥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第1 簡。
⑦(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02:89.
⑧于述勝,向輝.“意義—感通”的教化哲學——儒家教育思想要義新釋[J].教育學報,2016,12(06):104-110.
⑨(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02:160.
⑩梁皇侃撰.論語義疏.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08.
?吳光主編吳光點校.劉宗周全集·經術·論語學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明)郝敬撰.禮記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劉蘭娟.<大學>“修己安人”的學理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8.
?(宋)程顥,程頤著.二程集上·論語解.北京:中華書局,2004.02.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02:53.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02:10.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02:9.
?徐繼存.教化的旨趣與境遇[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54(01):120.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02:5.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0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