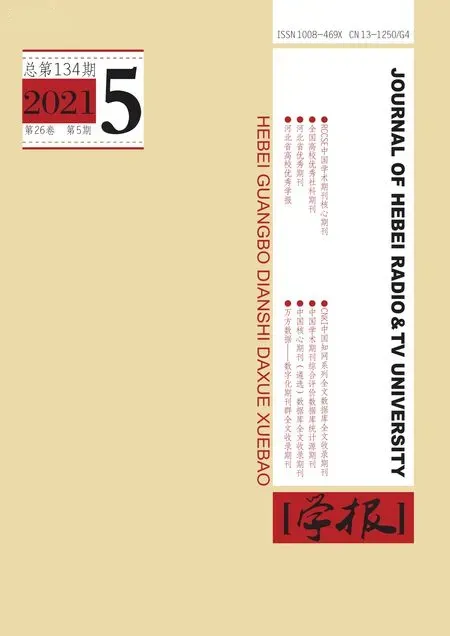民國時期私立北京聾啞學校探析
于博文
(河北師范大學 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河北 石家莊 050024)
特殊教育是運用特別設計的課程與教學手段對特殊人群進行的教育。聾啞教育屬于特殊教育的一種,是指對有生理發展缺陷的兒童進行的教育。鴉片戰爭后,由于西方教育的強行進入,來華的傳教士增多,中國的特殊教育開啟了由傳教士創辦的階段。民國以后,隨著國人陸續出國考察,留洋歸國的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倡導教育救國,特殊教育逐步轉向本土化。本文主要以杜文昌在華北創辦的第一所私立特殊學校——私立北京聾啞學校為切入點,考察私立北京聾啞學校發展情況。
一、私立北京聾啞學校創立背景
中國近代的特殊學校最初是由西方傳教士創立。鴉片戰爭以后,來華傳教士人數逐漸增多,起初他們活動范圍限于沿海地區,隨著內地通商口岸的不斷開放,其活動范圍延伸到內地。1887年,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梅理士夫婦在山東登州創辦了中國第一所聾校,招收聾啞學生入學。1888年,學校取名為登州啟喑學館,后校址遷至煙臺,改名煙臺啟喑學館。1914年畢業于山東齊魯大學的杜文昌,立志以聾啞教育為己任,投學于當時創辦的煙臺啟喑學校師范班研習5年。學成以后,隨即只身前往北京,創辦聾啞學校。
二、私立北京聾啞學校生源情況
1.學生人數
起初因社會人士對聾啞教育不理解,許多人不太愿意將自己子女送入聾啞學校,故該校第一批只有“7人入學”(1)華北聾啞學校編:《華北聾啞學校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19—1949)》,北京:華北聾啞學校,1949年版,第5頁。,1927年“學生添至35名,男生25名、女生10名(寄宿生23名、走讀生12名)”(2)北京聾啞學校編:《北京聾啞學校一覽》,北京:北京聾啞學校,1927年版,第19頁。,1932年有“75名學生,男生51名、女生24名(寄宿生60名、走讀生15名)”(3)北平聾啞學校編:《北平聾啞學校特刊》,北京:北平聾啞學校,1932年版,第16頁。,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共有“學生118名,其中男生83名、女生35名(寄宿生63名,走讀生55名)”(4)華北聾啞學校編:《華北聾啞學校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19—1949)》,北京:華北聾啞學校,1949年版,第8頁。。新中國成立前,私立北京聾啞學校學生人數不斷增多,從走讀生人數來看,家在北京當地的學生越來越多。
2.學生年齡
學校的入學年齡也有限制,一般“由10歲到16歲”(1)華北聾啞學校編:《華北聾啞學校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19—1949)》,北京:華北聾啞學校,1949年版,第8頁。。1927年學生的年齡情況“最小的7歲,最大的22歲,平均在15歲。”(2)北京聾啞學校編:《北京聾啞學校一覽》,北京:北京聾啞學校,1927年版,第19頁。1932年學生入學年齡仍限制在“10歲到16歲”,但“八九歲不住校也可以,16歲到20歲只能讀書不能說話了”(3)北平聾啞學校編:《北平聾啞學校特刊》,北京:北平聾啞學校,1932年版,第16頁。。1949年統計的118名學生中,“9歲的5人、10歲至16歲的(包括16歲)有82人、17歲至19歲的有25人、21歲的有6人”(4)華北聾啞學校編:《華北聾啞學校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19—1949)》,北京:華北聾啞學校,1949年版,第31頁。。從統計的數據來看,雖然年齡上有高于或低于限制年齡的情況存在,但也是少數情況,大部分的學生都在10歲至16歲適齡之間。
3.學生籍貫
1927年該校統計了39名學生,其中“直隸京兆地區11人,河南5人、沈陽1人、湖北3人、山東3人、安徽1人、四川2人、江蘇2人、江西1人、吉林1人、福建1人、浙江2人、廣東3人、內蒙古1人”(5)北京聾啞學校編:《北京聾啞學校一覽》,北京:北京聾啞學校,1927年版,第22-25頁。。1932年統計的75名學生中,“河北36人、遼寧4人、吉林1人、察哈爾2人、山西3人、山東5人、河南6人、江蘇3人、湖北2人、浙江5人、湖南1人、福建1人、廣東4人”(6)北平聾啞學校編:《北平聾啞學校特刊》,北京:北平聾啞學校,1932年版,第23頁。。1949年統計的118名學生中,“河北45人、北京34人、天津6人、山東8人、山西4人、察哈爾2人、陜西1人、綏遠3人,福建、河南、江蘇、熱河、四川、湖北、浙江、遼東、上海各1人,沈陽、大連、濟南各2人”。從學生的籍貫來看,來自全國各地,但主要集中在華北地區,聾啞教育呈現地域性特征。
4.學生聾啞原因
1927年統計該校的39名學生中,聾啞原因“天生7人、血統2人、自幼因病25人,4歲、6歲、8歲、11歲、12歲因病各1人”(7)北京聾啞學校編:《北京聾啞學校一覽》,北京:北京聾啞學校,1927年版,第22-25頁。。1949年統計的118名學生中,“先天38人(原因不詳23人、血族結婚1人、遺傳9人、疑因乳毒5人),后天80人(腦膜炎29人、熱病31人、瘟疹8人、擊傷4人、耳炎3人、摔傷3人、傷寒1人、其他1人)”(8)華北聾啞學校編:《華北聾啞學校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19—1949)》,北京:華北聾啞學校,1949年版,第32頁。。1936年10月17日杜文昌在中央廣播電臺講演時,提到學生聾的原因說道,“據全國聾啞學校統計,先天的聾啞,占20%,后天因病的占70%,因傷的占10%。”(9)《聾啞教育及私立北平聾啞學校之概況》,《中央日報》1936年10月20日—21日。由此可知后天導致聾啞的原因可達半數以上,聾啞兒童的家長對于子女的衛生問題并沒有引起太多重視。
三、私立北京聾啞學校課程設置
1.學制與教材
私立北京聾啞學校教學內容大致分為三方面,主要是基礎課程、唇讀法及手勢課、職業技術教育課。
聾啞生的課程設置按照普通中小學課程加以刪減,不開音樂課,其中“預科2年,每周10節習音、5節看口、5節識字、3節算術、1節地理、5節體操”,初小4年和高小2年,一樣的課程是“3節算術、2節自然、2節工用、3節形象、5節日記、5節習字、5節體操、1節故事”。不同的是,“初小1節地理、高小2節地理,初小5節國語、高小4節國語,初小額外學5節會話、3節社會,高小額外學2節歷史、2節公民、2節衛生”。(10)北京聾啞學校編:《北京聾啞學校一覽》,北京:北京聾啞學校,1927年版,第32-34頁。以上課程的設置,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在普遍的文化課上,各地的聾啞學校并無太多差異,只是內容有所刪減,在特殊課程設置上,聾啞學校更注重的是學會聽、說、看口型識別文字。但手勢語相對于口語來說屬于舊的教學方法,對于普通教育的教學內容傳授有限,教學效果不是特別理想,聾啞兒童的邏輯思維帶動不起來。
2.職業技術教育
特殊學校注重職業技術教育,這是特殊學校與普通中小學的一個顯著區別。職業教育“最直接的作用即為了未來的職業做準備,如果能夠掌握幾門手藝,那么在就業方面要容易得多,即使未能夠被正式聘用,也可以憑借自己的手藝進行簡單就業養家糊口”。(1)曲鐵華、劉盈楠:《民國時期特殊教育實施的特點及啟示》,《教育文化論壇》,2019年第3期。該校于1924年設立織襪工廠,1932年又添設紡織科,1933年添設紗帶科、木工科,1934年添設裝印科、縫紉科。不僅可以培養動手能力,還可以幫助無力繳納膳食費的學生半工半讀。
四、私立北京聾啞學校管理體系
1.校址與基礎設施
校址與基礎設施是學校創辦最基本的物質前提。從1919年至1928年,由于經費的短缺,校址幾經變動,“初假安定門交道口夜校教室”的三間平房作為臨時校址。1921年由于“嗣學者日多,校舍狹窄,不敷應用”,校址遷至頭條道濟醫院的東院。1926年以“該院擴充,乃租十二條老君堂”(2)《北京聾啞學校之概況》,《益世報》(北京)1927年11月10日。。1928年春租清代醇親王的馬圈,后一直到1945年春季“房東違約,將房間售于敵寇,強迫本校遷移,經抗拒至暑假始得將西部遷出”,一周以后“敵即投降,房產歸公”,該校隨即“呈請當局,準予繼續使用”。(3)華北聾啞學校編:《華北聾啞學校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19—1949)》,北京:華北聾啞學校,1949年版,第6頁。
2.經費籌措
學校經費的來源分為收取學費、社會募集、政府官廳撥款補助三種。學費方面,雖規定一學期“納小米80斤”,但學校為救濟殘疾、普及教育,“十分之八免費,十分之一減費,只有十分之一納全費”。(4)華北聾啞學校編:《華北聾啞學校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19—1949)》,北京:華北聾啞學校,1949年版,第8頁。在主動捐款方面,據《北平聾啞學校一覽》1923年至1926年和《北平聾啞學校特刊》1930年至1932年統計,捐款者有以個人名義的,也有如協和醫院服務部、宣內服務團等社會團體為名義的,捐款數目從2元至690元不等,捐款多用于常年經費和桌椅費等。
在經費短缺時,杜文昌還帶領學生主動向社會各界進行募捐,1927年,為了擴大聾啞教育影響,杜文昌于春季帶領兩名學生赴京津各大中學宣傳表演。1928年10月,杜文昌帶領兩名學生赴華北、華東、華中各大城市表演宣傳。(5)華北聾啞學校編:《華北聾啞學校三十周年紀念特刊(1919—1949)》,北京:華北聾啞學校,1949年版,第5頁。1936年暑假師生到青島旅行表演宣傳,同年10月4日,杜文昌針對全國聾啞教育的慘淡現狀,“攜該校聾啞學生許慶銘、王玉群,同赴南京,然后赴上海、杭州、福州、廣東、長沙、漢口、西安等各大都市表演,預計可得一萬個贊助者,每人捐洋五元,總計可得五萬元為該校基金云”。(6)《聾啞學生赴各地表演,杜文昌攜領募該校資金》,《益世報》(北京)1936年10月5日。1937年2月10日,在香港青年會講演的杜文昌由于受到歡迎,且大多對聾啞教育接受,決定于3月赴新加坡、馬來西亞、暹羅、緬甸、印度、爪哇、蘇門答臘、安南等地進行募捐,此時恰逢七七事變,日軍入侵華北之際,杜文昌不愿做順民,且由于抗戰爆發,交通梗阻,學生人數大為減少,開支困難。杜文昌一行于1939年10月歸國后與11月15日來昆明考察抗戰后方救亡建設情形并前往各學校參觀表演宣傳,在昆明逗留十余日后,云南省省國民政府主席龍云夫人“以熱心為殘廢兒童謀福利,深為嘉許,特慨助旅費國幣一千元,劉淑清夫人及女青年會均有所資助,滇越鐵路公司并贈送頭等車票兩張”。(7)《聾啞教育家杜文昌離滇,龍夫人資助一千元將過港赴美考察》,《中央日報》(昆明)1939年12月8日。
3.收入開支
《北平聾啞學校一覽》和《北平聾啞學校特刊》統計了1926年9月至1933年7月間6個時間段的收支情況。1925年9月至1926年8月,“學宿費和捐款收入1 783.4元,宿舍、薪金、工資、器具、消耗、圖書、辦公、印刷、修繕、難費支出3 052.57元,虧欠1 269.3元”。1926年9月至1927年8月,“學宿費、捐款和補助收入2 440元,宿舍、薪金、工資、器具、消耗、圖書、辦公、印刷、修繕、難費、房租、電話支出5 759.3元,虧欠3 319.3元”(8)北京聾啞學校編:《北京聾啞學校一覽》,北京:北京聾啞學校,1927年版,第29-30頁。。1929年至1933年間大體收支平衡,且余存一部分,支出方面主要是教職工薪金支出占絕大部分。
五、私立北京聾啞學校成效與局限
民國時期,政局動蕩,戰爭給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帶來沖擊,特殊教育事業在夾縫中勉強發展,部分學校因日偽接管,教學秩序被打亂,無力招生。聾啞教育畢竟處于幼稚階段,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很多不足之處。
首先,政府重視程度不夠。由于政府投入力度不大和社會重視程度不夠,學校基礎設施配備較少,無法擴充自身的力量,其規模遠遠比不上普通學校和傳教士創辦的學校的。且在戰火中頻繁搬遷校址,舊的設施沒有完善,新的問題又出現,學生的基礎生活很難保障,只能勉強解決基本溫飽。到1947年,由于物價上漲,生活變得更拮據,“一切未能依如預算,復以籌措維艱。故現經費深感支絀,困頓之情況已達極點”。(1)顧定倩、樸永馨、劉艷虹:《中國特殊教育史資料選》(上卷),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2頁。
其次,師資力量不充足且水平有限。學校創辦之初只有杜文昌1人任教員,到1949年也僅有教員15人,要負責100多人以上的聾啞學生力不從心,且大多數的教師僅初中或小學畢業就投身教學,本身對聾啞專業知識與教學方法不甚了解,還要花費時間和學生一起學習,出現教師和學生互動不積極等現象。在師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部分學校“只能降低特殊教育師資標準的門檻,在教師的專業化程度等方面作出讓步,讓并沒有受過完整的、專業的培訓的人來擔任教師,進入特殊教育教師體系”。(2)曲鐵華、劉盈楠:《民國時期特殊教育實施的特點及啟示》,《教育文化論壇》,2019年第3期。
最后,社會關注力量不夠。特殊教育的理念在國人心中尚屬空白,很多人不理解聾啞教育到底是什么,對聾啞教育產生質疑與疑慮。當時在中國工作了54年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浦根據觀察得到“依照普遍的信念,跛子、瞎子,尤其是那些獨眼龍、聾子、禿頭、斗雞眼,所有這些人,都是應該避免接觸的”。(3)明恩浦著,匡雁鵬譯:《中國人的特性》,北京:光明日報社,1998年版,第125頁。由此可見,許多國人固有的觀念把生理上有殘疾的人視為“異類”與“廢人”。1948年新中國成立前,從《華北日報》一位讀者來信中也可得知“北平有兩所聾啞學校:市立聾啞學校……私立華北聾啞學校……”,(4)《聾啞學校現有兩處》,《華北日報》1948年1月17日。說明在當時混亂的背景下,存留下來的聾啞學校少之又少,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北京也只有兩所聾啞學校,全國也只不過40余所。
民國時期,在杜文昌的四處奔波和社會上一部分執心人士的努力資助下,私立北京聾啞學校得以慢慢發展起來。但是,由于經費嚴重缺乏,又受軍閥混戰和抗日戰爭影響,盲聾啞特殊教育自身的局限以及政府、社會民眾對盲聾啞殘疾人的教育支持力度有限,使其發展規模終究難以與普通教育比肩。開辦特殊教育是當時所處時代下的創新突破,填補了華北盲聾啞特殊教育的空白,為社會上培養了許多技術性人才。以史為鑒,我們更應該重新看待與探討其經驗,真正的重視殘疾人事業,給予殘疾人以平等待遇,這不僅是廣大國民的殷切希望,更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殘疾人群也應該被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