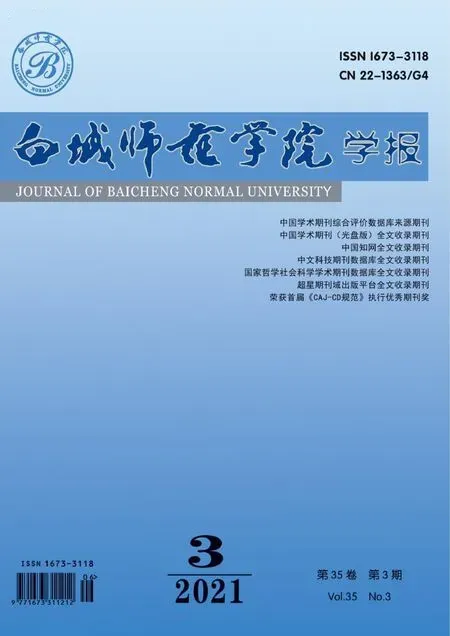《憤怒的葡萄》矛盾解讀:人物形象與人性價值
陳 忱
(福建商學院 外國語學院,福州 350016)
美國1940 年獲普利策文學獎的小說《憤怒的葡萄》以20 世紀30 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作為故事背景,講述了在資本家壓迫下,農民團結在一起反抗不公平社會的故事。資本家自私貪婪、缺乏人性,農民因為缺少資源,只能被迫被資本家所統治,承擔著極為嚴苛的工作任務,卻只能收獲微薄的薪水。約翰·斯坦貝克用小說中人物的視角、思維和行動,傳達了對人性中負面因素的批判,也實現了對人性積極價值的肯定。《憤怒的葡萄》在人物形象刻畫和人性的描寫上并沒有用臉譜化的形式去塑造壞人或好人,而是用一種辯證性的思維方式,設立了多個在初期矛盾掙扎的形象,并通過一些事件作為觸點激活了這些角色人性中積極的一面,利用這些人物呈現出了比較理想化的社會面貌。通過《憤怒的葡萄》中生動的人物形象來探究作者在小說中所傳達出的人性價值,成為分析這部經典作品的關鍵所在。
一、牧師凱西的身先士卒
牧師凱西并不是小說的主角,也不是主角喬德一家的家庭成員,但他在整部作品中的精神引領作用卻不容忽視,甚至可以說凱西是整部小說中將人性正面價值徹底落實的一個核心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凱西這一形象代表了作者對于人性的期待和向往,他在精神上已經達到忘我的境界。《憤怒的葡萄》的創作背景是20 世紀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在這一時期的美國,上層階級擁有這個世界上最多的財富和最為絕對的自由,但他們的行為卻是自私自利、完全不顧其他階層同胞的;而底層階級的人數眾多,雖然他們是整個國家和社會最主要的勞動力來源,但勤勤懇懇地工作卻并不能為他們帶來應得的勞動報酬。兩個階層的人之間從來都無法互相理解,他們之間存在著必然的、無法被輕易消解的矛盾,且他們之間的矛盾從未得到解決。[1]
作者塑造了凱西這個既不屬于上層社會也不屬于底層社會的角色,希望通過凱西的人性價值使兩個階層矛盾得以緩解。小說開始,作者交代了凱西曾經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但他后來卻背叛了基督教。作者之所以塑造這樣一個形象,是為了讓凱西的矛盾性吸引讀者去探究其背叛宗教的原因,而凱西背叛宗教的原因已經在他的名字中得到了暗示,凱西的全名是吉姆·凱西,縮寫是J·K,和耶穌名字的縮寫完全一致,這實際上代表了作者塑造這個人物的根本目的,希望將他塑造成一個和耶穌一樣具有領導能力的悲劇性人物,而之所以作者在故事中將凱西設計為背叛和脫離了基督教的矛盾形象,也是為了讓凱西高尚的品格可以脫離單個思想體系的限制,得到更加宏觀的升華。故事后期對凱西這一人物形象的立體化塑造,則驗證了這一點。
小說中真正的主角喬德一家,原本生活在俄克拉荷馬州,是敬畏土地、愛護土地的農民家庭。但在經濟大蕭條的沖擊下,他們不得已將家里所有值錢的東西變賣,換來了一輛破舊的二手老板車前往加州,西行途中,他們遇到了凱西。喬德對凱西的第一印象是:“他是個形象和行為上都比較傳統的人”。[2]的確,未脫離基督教前的凱西十分虔誠,熱衷于傳道。但當他親眼看到因經濟沖擊而無家可歸的農民們流離失所、食不果腹,尤其是到達加州后又看到遍地都是飽受壓迫的農民時,他開始對自己虔誠的信仰產生了懷疑。善良的凱西想要幫助這些窮苦的農民,但他以往堅定的宗教信仰,卻無法令他對現狀做出一絲的改變。在眼前的慘狀和無力改變現實的雙重打擊下,凱西開始懷疑自己過去的信仰。因此,凱西逐漸產生了一種全新的、充滿博愛的信仰,至此,凱西脫離了基督教,轉而為了饑寒交迫的農民四處呼吁,幫助他們改善生活境遇,教會他們如何對抗不公平的待遇。在所有的抗爭中,凱西都身先士卒、親力親為。
凱西無疑是一名智者,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出了這個社會的真正矛盾。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凱西像基督那樣,前往一片荒野中開始了超然的思考。在他看來,一個真正和諧幸福的社會,不應該從個體的視角出發,也不應該從某個群體的視角出發,而是應該站在“人”的視角,回歸到最根本的問題上去思考。“得到一百萬畝土地不會真正滿足、壓迫別人不會真正滿足、內心空虛麻木不仁的人更加不會滿足”。[3]凱西認為真正的生活,應該是得到心靈上的滿足,只有那些愿意為了大家的利益去犧牲自我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這一次的荒野思考令凱西意識到如何去解決這一根本矛盾,于是他開始全心投入。他代替喬德受過,此舉是為了報答喬德一家的恩情,是為了一個真正的“整體”,也正是這一舉動,令他真正認識到為了“整體”的利益犧牲自我是最為正確的道路。出獄后的凱西看到在自己的呼吁下,農民和工人們開始團結一心,懂得正視自己的價值,也懂得用團結的力量去對抗不公平。凱西深受感動,他加入到農民和工人的隊伍中去,不斷為了集體利益而奮斗。他組織了罷工斗爭,教會工人們如何爭取應有的薪資。他不但成功地帶領農民打出了對抗不公平的第一槍,也在斗爭中深刻地影響了喬德,使喬德從一個不諳世事的農民的孩子,變成了和凱西一樣有著大愛、既懂得認知自我又愿意為了“整體”奉獻自我的人。雖然在小說中,凱西死在了警察的亂棍之下,但凱西就像耶穌一樣通過犧牲自己的肉身,為更多人做出了榜樣,凱西用自己的一生,去驗證了熱愛“整體”的人性的價值。
二、農民喬德的純真質樸
相較于凱西而言,喬德的人物形象更貼近于現實生活。在小說的一開始,喬德就像所有年輕的小伙子一樣,性格直來直去、講義氣、肯吃苦,但不會控制自己的情緒。他和他的家人都是淳樸的農民,對土地和老家的感情非常深。因此,在他們被迫來到加州后,看到加州也是一番人間煉獄般的景象后,喬德理所當然地開始自暴自棄,變成了一個脾氣暴躁的流浪漢。喬德就像社會中許許多多的人一樣,對生活有著美好的向往,但在受到殘酷現實的打擊后,便陷入到負面的情緒中。如果說凱西是作者和讀者最向往的人物的話,那么喬德就是讀者們最能與之共情的一個角色。因為他既擁有美好的一面,也有脆弱的一面,正是這種堅強又脆弱的矛盾感,才能夠喚起人們的共鳴。
因為貧窮、無助,也因為對社會存在的罪惡毫無還手之力,喬德開始變得越發的自暴自棄,而他的家人也在西行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矛盾,每個人都只看得到自己眼前的利益,自己是否有所得,于是喬德一家開始各揣心腹事。他們到達加州后,卻并沒有過上預想的生活,反而被資本家壓迫,喬德又因與人爭斗誤殺了人。原本喬德以為自己的一生就將這樣結束,再也沒有辦法過上理想中的生活了,但就在此時凱西挺身而出,認下了喬德的罪過,代替喬德入獄,這一行為深深地震撼和感動了喬德,喬德開始審視自己的過去,審視自己的家庭所面對的一切困境。他開始思考發生的一切:他們失去了房子和土地,全部的錢只能換來一輛破舊的老板車,家庭成員分崩離析,這使喬德的意識逐漸清醒,尤其是凱西出獄后,喬德和凱西再次相遇,他開始追隨凱西,為了農民和工人們的利益去努力和奮斗。喬德的家庭也在他和凱西的努力下,漸漸開始互相信賴、互相取暖。喬德開始感受到,雖然在經濟上自己依舊一貧如洗,但在某種程度上自己的生活卻在越變越好,這種改變正是來自于他對集體的認可和依賴,但凱西的意外死亡,令他再次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他離開了家庭躲進了空無一人的山洞,就像當時在荒野中思考的凱西一樣,喬德也開始思考人生的真正意義。他回憶起自己的家庭和威爾遜一家互幫互助的情景,兩個家庭曾經互相取暖,才令慌亂的喬德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他意識到即使身處社會最底層,也可以通過互助和友愛改變生活現狀。因此,在山洞中的喬德暗下決心,他要像凱西一樣,成為一個為了“整體”而奉獻自我的人。于是喬德回到了家,告訴母親自己將要暫時離開家庭,為更大的“家庭”去斗爭,他對母親說:“從今往后,凡是有不公平的地方就有我在;凡是有人吃不飽飯,無法斗爭的地方,就有我在。”[4]喬德這一形象所彰顯出的人性的價值在于,人身處社會之中,無法預測自己的未來,但卻可以決定怎樣面對困難。經濟大蕭條時期個人或某個集體無法去改變歷史的軌跡,但人們可以做到團結一心、努力工作,為自己應得的利益去抗爭,堅定自我,不懈努力,才能體現人生的價值。
三、喬德媽媽的偉大母性
除了凱西和喬德這兩個比較典型的男性人物,喬德媽媽作為一名女性角色也在小說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喬德媽媽是個理想化的形象,她是個淳樸善良的農民,在家庭中能夠起到幫扶丈夫、教育兒子的積極作用,可以說,喬德正是在媽媽的引導下,變成了一個具有正義感和良好品性的孩子。雖然在他們西行前往加州的過程中,因為遇到了一些問題,使得喬德變得脾氣暴躁,但喬德媽媽始終沒有放棄兒子,反而在面對喬德所犯下的罪行時,還能夠像過去一樣以溫柔的態度安慰喬德。喬德媽媽的形象在整部小說中起到了一個安定人心的作用,她和高尚的凱西有著本質上的一致性,但凱西并不屬于農民,而喬德媽媽來自于農民群體之中,她真正感受到了階級的壓迫。即使如此,喬德媽媽仍然保持著冷靜與和藹的態度,更有著較強的情緒控制力。作者曾以喬德的視角來對母親的形象進行了總結,喬德這樣說道:“母親那雙茶色的眼睛,包含著許多復雜的情感,那是一種對于悲劇的體悟,對于痛苦和磨難的對抗和對親人的那種由內而生的關愛,這種眼神無數次令我平靜下來,讓我可以有勇氣回頭看看我自己做出的一切。”[5]對于喬德來說,媽媽是自己的定心丸,而對于喬德一家其他人來說,母親更像是無與倫比的粘合劑。在喬德一家前往加州的途中,購買的老板車不斷地出故障,喬德爸爸產生了十分強烈的負面情緒,導致一家人面臨著分崩離析的狀態,而母親則一改往常的溫柔與慈愛,嚴厲地與爸爸對峙,才使得這一家沒有四分五裂。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喬德媽媽這個角色更像是生命之源的本體,有著最為核心的人性內涵。并且,喬德媽媽所作出的善舉沒有任何個人的目的性可言,從這個角度來說,即使是高尚的牧師凱西,也會為了實現整體的和諧而去奉獻自我,這個目的雖然是美好的,但的確是在目的性的驅使下行動的;喬德更是本著去繼承凱西的衣缽,而接下了為了“整體”去奉獻自我的任務,但無論是照顧家人、關愛鄰里,還是給予其他人平等的尊重和幫助,喬德媽媽都沒有行為上的明顯的目的性,她作出這些善舉不需要理由,完全是偉大母性的自然流露,也正因為喬德媽媽這種慈愛、善良,既有勇氣又堅忍、豁達地應對人生,才令喬德的轉變變得合情合理。喬德媽媽是整部小說中潛在的、最能體現人性根本的重要人物。簡單地說,作者塑造喬德媽媽這個擁有偉大母性的形象,是想告訴人們善良是人應該有的本性,這種善良要超越自我,擺脫所有的禁錮,真正從本心出發,不帶任何目的,為了“整體”的和諧而奉獻出自己的全部,也只有做到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出人性的價值所在。[6]
四、結語
《憤怒的葡萄》這部小說包含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并由多個人物形象構成了一個生動形象的世界。人們在對這些人物進行了解和共情的過程中,就會體悟到故事深層意義下的真正的文學內涵。《憤怒的葡萄》把故事設置在美國經濟大蕭條背景下,是因為這一時期社會資源短缺,階級矛盾激化,人們開始冷靜地審視社會,小說通過對積極、正面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來告訴讀者,人性真正的價值在于審視生命的意義,努力實現人性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