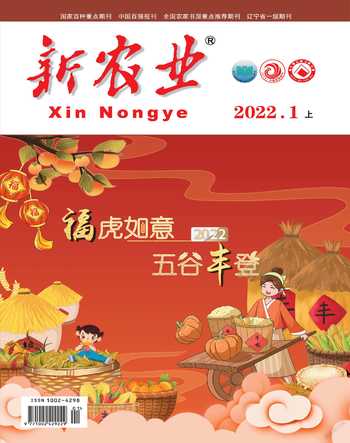農村“外嫁女”土地承包權益保護分析
摘要:農業的穩定關乎整個社會的發展,土地的穩定關乎農業產業的興衰。在農村地區,“外嫁女”的土地承包權益保護問題比較突出,“外嫁女”的戶口被強行遷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被強制收回,這種情況時有發生,究其緣由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問題未得到合理解決。2018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部分條款中的變更可以為“外嫁女”的土地承包權益保護提供一定的依據。
關鍵詞:農村土地承包法;婦女權益;土地承包經營權
在我國農村地區,由于傳統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較大,農村戶口女性一旦外嫁,娘家所在地的村委會就要求其必須將戶口遷出,同時收回其在娘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理由是其生活地域發生變化,不再屬于村集體成員,故自然喪失農村土地承包權。這樣一方面導致“外嫁女”失去自主選擇土地承包權的權利,另一方面導致部分富裕地區的農村戶口女性不愿或不能外嫁,對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婦女權益保護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響。
農村“外嫁女”土地承包權產生糾紛的主要原因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問題未得到有效解決,而集體組織成員的認定程度又受到以下兩個方面因素的影響。
1.1 國家并未出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標準
農村土地承包權益糾紛的產生的主要根源是認定婦女是否具有集體成員資格,而對外嫁女的立法保護目前仍有不太完善的方面,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立法方面,《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條規定了有權承包農村土地的主體,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成員資格認定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農村外嫁女獲得土地權益的主要依據,而外嫁女的土地承包權被剝奪,本質上是由于村集體不認同婦女在出嫁后還具有本集體的成員資格導致的。因此,無論婦女離婚還是嫁娶,都有可能存在婦女成員資格身份的變動,這就要求以成員資格為基礎的承包經營權也發生變動。目前我國沒有制定出統一的認定集體成員資格的法律標準,這也是目前存在的一大難題。集體成員的認定標準,各地并不完全一致,2017年福建省政府《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規定:成員身份確認必須統籌考慮戶籍關系、土地承包關系、對集體積累的貢獻等因素。《四川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界定指導意見》規定在界定成員資格時除了與上述文件相同的戶籍和土地承包要素外,還需要考慮居住狀況和義務履行情況。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認問題的意見》也認為不宜采取單一的戶籍標準,應考慮的因素有三點,第一即為戶籍(是否是落戶在本集體經濟組織中的農業戶口);第二考慮是否在本集體生產、生活;第三最為根本,考慮是否以本集體經濟組織土地為本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上述規定的進步性在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本就是一個極其繁冗復雜的問題,現實中復雜情況各式各樣,這些情況的出現更是層出不窮,天津市高院考慮了在成員認定標準發生沖突時的處理,提出上述3個認定條件中,第三個“生活保障要素”才是本質特征,而前兩個只是成員資格的主要表現形式。當“戶籍”和“生產生活”這兩個表現形式不統一或者不具備主要表現形式時,應當從本質特征也就是“生活保障要素”出發進行判斷。此外,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取得中,還規定了基于婚姻關系將戶口遷入本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并在本集體經濟組織生產、生活的人員可以取得成員資格,屬于加入取得,這即肯定了外嫁女可以成為婆家所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天津市高院在公民不符合全部認定標準時并沒有直接否定該個體的成員資格,而是做了評定要素優先性的排序,更為全面的考慮到了現實情況,也更能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體現了對涉及公民基本民事權利的成員資格認定審慎的態度。
1.2 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認定的核心標準,是否獲得可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
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認為成員資格認定應依據有關法律法規,統籌考慮戶籍關系、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對集體積累的貢獻等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出了涉及集體成員資格認定的一些注意事項,即要綜合考慮戶籍、當事人的生產生活情況、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對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并且以是否獲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為實質性要件。在2015年《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又重申了“要以當事人是否獲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為重要考量因素”。因為土地是農村地區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在沒有獲得其他替代性保障如加入城市的社保體系時,享有承包土地的資格對其十分重要,對農民來說承包地便是其生活和收入來源,保障了其基本生活,所以,是否獲得“可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應是界定成員資格的核心標準。對于符合此核心標準的人員,即使戶籍不在本地,也應認定為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但要注意此“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是指獲得了較為固定的生產生活條件,不依賴于農村集體土地。
“外嫁女”權益糾紛的根源在于婚姻關系變動帶來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喪失。有學者提出了解決方案,即應盡快完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認定標準。確認成員身份,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基礎性工作,涉及農民的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也有利于保護婦女的土地權益。目前,全國關于成員資格的認定未有統一的立法,多是各地自行規定。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出臺之前,在確認“外嫁女”是否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時,婦女是否獲得可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也是考慮的首要因素。
2018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簡稱《農村土地承包法》)亮點之一就是新增第二十四條第二款,加強對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益的保護。該款規定,具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全部家庭成員都應列入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或者林權證。新增條款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保護具有重要意義,是解決人地矛盾、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良策。將成員姓名列入權證并沒有改變以戶為單位的家庭承包,同時又賦予了婦女選擇的權利。將姓名加入權證,有助于確認農村婦女尤其是“外嫁女”的成員身份,切實維護婦女的土地承包權益。????
修正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兩項規定,家庭成員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權益(《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條第二款)和將具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全部家庭成員列入權證(《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不僅是對婦女承包經營權的保護,更是對戶里全體成員的保護。婦女婚姻狀況的變更不是損害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理由,將其姓名列入土地承包經營權證,能起到證上有名,名下有權的作用,我們不能忽視這一公示制度所帶來的巨大進步,將家庭成員列入,并不影響以戶為單位的承包經營體制,相反,確權登記更是解決人地矛盾、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良策,堅持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針和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精神。
維護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才能真正實現農村女性發展的自由。這是農業現代化的要求,是黨和國家一直以來致力的目標,也是政策與法律的方向。土地定才能人心安,人心安才能農業興。農村婦女享有和農村男子平等的權益,不僅可以緩和家庭和社會矛盾,促進家庭收入的增長和農村生產力的提高,更有利于農村婦女的全面發展,維護穩定而和諧的社會秩序,對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也有重要影響。
作者簡介:劉雨璇(1998-),法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農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