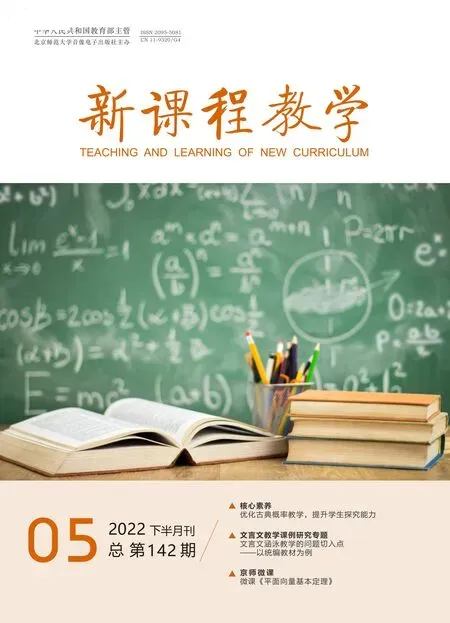借助虛詞解讀文言文的情感脈絡與精神境界
——以《記承天寺夜游》為例
北京市通州區潞河中學 李倩玉
統編版語文教材八年級上冊中的《記承天寺夜游》,是蘇軾的散文名篇。在本文的教學中,教師往往注重品析月夜景色的描寫和“閑人”一詞的多重內涵,其實,文中乍看“不起眼”的虛詞也可以成為學生解讀文章的重要抓手,更可作為學生探索作者情感世界的入口。借助虛詞學生可以品出真味,可以讀出蘇軾超越流俗、與眾不同的人格魅力,體悟其曠達樂觀、冰清玉潔的精神境界。
這篇游記十分短小精悍,全文不過85個字,卻包含多種表達方式。文中先是記敘,寫明了時間、地點、人物,與觀賞月夜景色的前因;進而描寫,用比喻的修辭手法,展現了月華如水的妙境;最后議論,含蓄地點染出作者內心的苦悶,也表現出作者曠達、灑脫的精神境界。寥寥幾筆,便做到了事件清晰、景物如畫、境界全出,可謂不蔓不枝、字字珠璣,“讀之覺玉宇瓊樓,高寒澄澈”,得到后世的高度評價。而從教學角度看,言辭的簡短平易既使本文容易進入,又使本文難以深入。對這一學段的學生而言,要從如此精練的文本中捕捉作者極復雜、極幽微的心境,進而體悟其光風霽月、冰清玉潔的精神境界,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往往有較大的困難。借助背景資料雖十分必要,也能較快引出結論,但容易使部分學生忽視文本分析的過程,對文章內涵的理解流于表面,成為一種對作者人生經歷、性格特點的記憶,而缺乏對文章詞句的真正品味,也許認同了作者人格之“高”,卻并不一定能徹底認同文章之“好”。“我們閱讀的任務就是用心去品味,把作者良苦用心挖掘出來,故不可放過其中一個字。要在教學中‘淺出’,教師首先必須‘深入’,然后再根據學生的情況做調整。尤其是《記承天寺夜游》這樣的經典名篇,字字精警動人,更需要于看似不經意中,于看似平淡處,細細咀嚼、深思,讀出其中的玄機和精妙。因為,僅僅領會文章的思想感情是容易的,而作品藝術魅力的挖掘是艱辛的,也是有趣的。”解讀作者的情感脈絡與精神境界,不能過分依靠背景資料的補充,而要引導學生從字里行間尋找“蛛絲馬跡”,破譯作者的“情感密碼”,進而洞察作者的精神境界。文中幾個重要的虛詞“遂”“亦”“蓋”“但”“耳”,有助于學生把握全文的情感脈絡,有助于學生深入領會蘇軾的精神境界,這在教學中是不應忽略的。
一、從“遂”“亦”看平淡敘述中的起伏心緒
本文以記敘開篇,蘇軾出門賞月,因無人同游,“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遂”字中有一種毫不猶豫的意味,很能說明蘇軾與張懷民的關系,這是常被談到的。張懷民于元豐六年被貶至黃州,寓居承天寺,而此時已是蘇軾被貶的第四年。據蘇轍《黃州快哉亭記》,張懷民曾在住所旁筑亭,蘇軾名之曰“快哉亭”。蘇轍這樣評價張懷民:“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可見,張懷民仕途受挫,與蘇軾處境相似;且張懷民個性灑脫,與蘇軾興趣相投。因此,蘇軾在缺少一位賞月的同伴時,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此外,聯系前文,既已“解衣欲睡”,又一時“無與為樂者”,干脆回房接著睡覺未嘗不是一種選擇,蘇軾卻并未加以考慮,一來是因為月不可不賞,二來大約也是因為覺實難安睡。不負月色,是有閑雅之趣;不能成眠,是有賦閑之苦。再者,既然有了月便可“欣然起行”,興頭本是十足的,何必非要“與人為樂”,月下獨酌不也是美事一樁嗎?這個不假思索的“遂”字,更證明了蘇軾“解衣欲睡”時內心的輾轉與寂寞。月色不是他放棄安眠的理由,也不足以驅散他內心的愁緒,而他深夜出行、尋景訪友是以排遣苦悶為由頭。此時的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至黃州,遭受著仕途多舛、政治失意、遠離家鄉、骨肉分離等不幸,內心不可能不苦悶、不可能不郁結,所以才會因無所事事、百無聊賴而“解衣欲睡”,又會因憂心忡忡、愁腸百結而輾轉反側。然而,一縷月光的悄然到來,就能讓他遣散愁苦、“欣然起行”,這就是蘇軾的可愛之處——生活再艱難、人生再坎坷,一點點美好就能讓他歡喜起來、讓他樂觀起來。更令他欣喜的是,這“說走就走”的訪友之旅不是“一廂情愿”,尋至承天寺,發現“懷民亦未寢”——與他處境相似、心境相通的好友張懷民果然也沒有入睡。這個“亦”字當中,包藏同病相憐的了然與慨嘆,更飽含覓得知音的欣喜與安慰。
二、從“蓋”看月色描摹中的澄明心境
“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這幾句對月色的描寫是本文的華彩部分,歷來最受人稱道。蘇軾與月是舊相識。他著名的悼亡詞《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中,“明月夜,短松岡”的凄愴讓人不忍卒讀。正是這明月,陪伴著蘇軾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思親的寒夜。七年前身在密州,他曾留下歌詠明月的千古絕唱《水調歌頭》,七年間有多少次的月缺月圓,年近半百的蘇軾又經歷了多少離合悲歡,“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美好期望,到今天依然難以實現。這個夜晚,月光又一次來到他身旁,像一位老友前來疏解他內心的惆悵。描寫月光的語句不過十余字,卻寫得格外動人。寂靜的庭院里,月光朗照,地面光影流轉,如水般空靈清透。月光如水,本也不是十分新奇的比喻,奇就奇在下一句:“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庭院中亭亭的翠竹、森森的蒼柏,白日里總是挺拔而威嚴的姿態,在月色的旖旎之中,竟也化作搖曳纏綿的身影,仿佛水中蕩漾的水草,輕盈而嫵媚。但細細想來,前有以水喻月色,后將竹柏的月影比作水草,倒也自然合理。這個比喻給人帶來的驚喜之感,其實多半來自“故弄玄虛”的句式排布,也來自一個“故弄玄虛”的“蓋”字。試比較:
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
庭下月光如積水空明,竹柏影似藻、荇交橫。
這幾句中,原本有“月光——積水”“竹柏影——藻、荇”兩對本體和喻體,蘇軾故意先隱去本體,將兩個喻體組合起來作為謎面,引人猜疑,再將謎底揭開一半,還用一個表推測的“蓋”字欲蓋彌彰,終不著一“月”字,匠心之中,更有情致。其實,原本無水,何來水草?這本是明擺著的事實,蘇軾卻偏偏視而不見,還用一個不起眼的“蓋”字輕輕繞過,讓我們也跟著他神思恍惚起來,仿佛因月光而迷離沉醉,分不清所思與所見,分不清夢境與現實。“蓋”是不經意間的發現,是發現后的好奇與揣測,是揣測后的恍然大悟,是恍然大悟后的欣喜與心動。讀至此處,蘇東坡手舞足蹈,如醉如癡的情態猶在眼前,也就只有他,在這樣艱難的境遇之下,還會因為這樣簡單的瞬間,煥發出這樣的天真無邪和通透灑脫。月光讓萬物變得溫柔沉靜,也讓蘇軾重歸淡然安寧。其實,蘇軾的內心世界又何嘗不是月般高潔、水般澄明呢?終日為渦角虛名、蠅頭微利而虛苦勞神的世俗之人,又怎會有閑暇、有心思、有情致去欣賞月夜之景,又怎能體會這看似尋常的景物中格外動人的美好呢?也正如后文所說,這世間缺少的從來不是月影婆娑的靜夜,而是能靜心賞月的人罷了。
三、從“但”“耳”看議論抒懷中的超拔心懷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文末以幾句自問自答收尾,議論抒懷。“但”字轉折,譯為“只不過”,緊承上文兩個“何”字引起的反問,強調景實為尋常之景,人卻非尋常之人。最后“耳”字收筆,無盡心緒輕輕綰結于一句“罷了”。這一轉一收,極大地豐富了“閑人”一詞的情感內涵。前文中潛藏暗涌的政治失意之悲,在這里以一種自嘲、自解的形式表露,又更多地轉化為一種自適、自得。逆境中自我開解的一般思路,是“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是“人生難免經歷苦痛掙扎”,文中蘇軾卻身處逆境而著眼順境——人生哪里沒有美景呢?不過是順境中不易留心,而我們二人恰巧身處逆境罷了。“但”和“耳”甚至有一種“自謙”的口吻,仿佛在為那些不“閑”之人開脫,其心境情致實非常人可有,胸襟氣度絕非凡俗可達。人生確如逆旅,常會驟逢山雨,穿林打葉,難免乍臨深淵,驚濤拍岸,但只要心中總有明月高懸,不論陰晴圓缺,總能在無塵清夜里遍灑如銀的光輝,那么在這旅程之中,縱使有險境,不會有迷途。
虛詞之中品真味,這短短一段“從胸中自然流出”的文字,幾個似乎只是隨手寫就的字眼,卻是詩人人格精神的光輝寫照。我們從中讀到的,是蘇東坡繁華落盡后依然天真、高潔的秉性,命運摧折中仍舊灑脫、豁達的心胸,是顛撲不破、矢志不渝的情懷與理想。正所謂“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千百年后,竹柏的倒影依然在月影下搖曳生姿,我們也依然在詩人澄澈洞明的文字中深深感慕,靜靜追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