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滿洲國教科書的殖民話語策略分析
劉學(xué)利,陳 彤
(1.湖北師范大學(xué) 教育科學(xué)學(xué)院,湖北 黃石 435002;2.中國醫(yī)科大學(xué) 第一臨床學(xué)院,遼寧 沈陽 110001)
偽滿洲國是抗日戰(zhàn)爭時(shí)期由日本關(guān)東軍一手策劃、打造、操縱的殖民地政權(quán),其政治、軍事、經(jīng)濟(jì)、文化、教育等諸領(lǐng)域皆受控于日本。偽滿洲國“有別于中國其他淪陷區(qū),在世界帝國主義殖民史上,也是一個(gè)罕見的以‘國家’面貌出現(xiàn),實(shí)行實(shí)質(zhì)的軍事殖民統(tǒng)治、掠奪的典型。”[1]偽滿政權(quán)為統(tǒng)一“國民”思想,鞏固殖民統(tǒng)治,自編教科書供學(xué)生使用,傳播偽滿洲國的意識(shí)形態(tài)。
“殖民話語”是由薩義德最先使用的,用以“描述一種在其中產(chǎn)生著廣泛‘殖民’活動(dòng)的實(shí)踐體系”。[2]因此,殖民話語是“組成殖民關(guān)系內(nèi)社會(huì)存在和社會(huì)再生產(chǎn)的復(fù)雜的符號(hào)和實(shí)踐。”[3]殖民話語建構(gòu)的是一套殖民地被殖民者所觀看、觸摸、處置的話語闡述體系。[4]偽滿政權(quán)利用教科書,建構(gòu)了一套殖民話語體系,通過篡改歷史、曲解事實(shí)或構(gòu)建失真的形象,粉飾其殖民統(tǒng)治,同時(shí)在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奴化中國東北地區(qū)的青少年一代。
在教科書中,話語以文本的形式呈現(xiàn)。一個(gè)文本通常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表層意義,是教科書中公開的、明示的、語言文字本身直接表達(dá)的意義;另一方面是深層意義,是教科書語言背后所內(nèi)隱的、鑲嵌或附著在文字背后的意義。[5]要揭示出教科書語言背后的深層意義,就必須對其進(jìn)行話語分析。教科書話語分析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是對其文本內(nèi)容的分析。教科書話語分析主要涉及以下基本話語策略:命名策略,主要考察教科書中的人、物、現(xiàn)象、事件、行動(dòng)及其過程是用何種話語命名的;宣稱策略,主要考察教科書中的人、物、現(xiàn)象、事件、行動(dòng)及其過程被賦予了何種價(jià)值特征;論證策略,主要是考察教科書通過提出哪些論點(diǎn)或開展哪些論證來將特定人或社會(huì)團(tuán)體對他人的排斥與壓制合理化和合法化;視角策略,主要考察教科書中的命名話語、宣稱話語和論證話語從什么視角進(jìn)行表達(dá);強(qiáng)化或弱化策略,主要考察教科書如何公開表達(dá)各自的話語,其中強(qiáng)化或弱化了哪些話語。[6]
偽滿洲國初級小學(xué)《國文教科書》共八冊,由偽滿文教部編寫、校訂,于1937年由偽滿洲圖書株式會(huì)社出版發(fā)行。該套教科書共有300余篇課文,體裁為記敘文、說明文、詩歌、議論文以及劇本。根據(jù)課文內(nèi)容可見這套教科書的話語主題是傳播偽滿洲國的意識(shí)形態(tài)。本文旨在通過分析《國文教科書》文本,力圖揭示在殖民話語機(jī)制下偽滿教科書如何構(gòu)建出一個(gè)物產(chǎn)豐富、安居樂業(yè)、王道樂土的“國家幻象”,如何制造一個(gè)為偽滿政權(quán)所認(rèn)同的“歷史記憶”。
一、極力灌輸偽滿洲國的“國家觀念”
國家是“階級的統(tǒng)治機(jī)關(guān)”。恩格斯指出:國家設(shè)有公共權(quán)力,并按照地區(qū)劃分組織他的國民。[7]偽滿教科書在課文中大量使用表達(dá)“國家觀念”的詞語、重新介紹地區(qū)劃分、大力宣揚(yáng)與“建國”相關(guān)的活動(dòng),目的在于將偽滿洲國的“國家觀念”深深烙印在學(xué)生心中。
(一)頻繁使用“我國”等表達(dá)“國家觀念”的詞語
據(jù)統(tǒng)計(jì),偽滿洲國初級小學(xué)《國文教科書》中使用“我國”“吾國”“建國”“滿洲國”“滿洲”“國旗”等表達(dá)國家觀念的詞語多達(dá)80余次,如“師生向國旗三鞠躬”(出自《國文教科書》第三冊第一課《開學(xué)》)、“為吾國建國紀(jì)念之良辰”(出自《國文教科書》第五冊第一課《建國日之晨》)、“今我國實(shí)業(yè)部”(出自《國文教科書》第六冊第三十一課《綿羊》)、“我滿洲國內(nèi)”(出自《國文教科書》第八冊第五課《滿洲之森林》)等。這些詞語的使用在表達(dá)上使用了強(qiáng)化策略,在語言實(shí)現(xiàn)形式上屬于“分類”,公開表達(dá)偽滿洲國的“國家”觀念,具有十分強(qiáng)烈的立場傾向。這些詞語在潛在意義上代表著極強(qiáng)的偽滿洲國的意識(shí)形態(tài),時(shí)時(shí)刻刻向?qū)W生強(qiáng)調(diào)偽滿政權(quán)所謂的“國家觀念”。
《國文教科書》第二冊第四十七課《同生與德生》寫道:“同生乃大同元年所生,德生乃康德元年所生,起此二名為表紀(jì)念之意”。[8]47“同生”“德生”兩個(gè)詞語在表達(dá)時(shí)使用了命名策略。教科書編寫者將父母以偽滿洲國年號(hào)給孩子起名的故事編寫進(jìn)書中,反映了極強(qiáng)的“國家”意識(shí)形態(tài),讓學(xué)生通過“建國”的時(shí)間觀念形成“國家”意識(shí)。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作用是遮蔽一個(gè)社會(huì)統(tǒng)治思想的源頭,而表現(xiàn)出普遍的、大眾接受的“自明之理”。[9]而這種“普遍真理”服務(wù)的是特定群體的利益。日偽統(tǒng)治者想通過偽滿洲國教科書這一載體,灌輸偽滿洲國的“國家觀念”,以此達(dá)到認(rèn)同偽滿洲國文化,進(jìn)而認(rèn)同日本文化的目的。
(二)重新介紹偽滿洲國的地區(qū)劃分
偽滿洲國將“新京”確立為“首都”,《國文教科書》第二冊第二十二課“新京”的篇幅為46個(gè)字,第六冊第一課“新京”的篇幅為521個(gè)字(含標(biāo)點(diǎn))。不同冊的課文標(biāo)題皆為“新京”,采用了話語分析的強(qiáng)化策略,潛移默化地向?qū)W生傳達(dá)“新國家”的觀念。除此之外,教科書還介紹了吉林、奉天、大連、旅順、哈爾濱、山海關(guān)、龍江(如今的齊齊哈爾)等城市。課文在介紹這些地區(qū)時(shí),大量使用宣稱策略,使用諸如“壯麗”“寬闊整潔”“面目復(fù)一新”“人煙稠密、商業(yè)繁榮”等詞句。宣稱策略表示限定或評價(jià),通過課文對這些偽滿洲國城市的介紹,不斷向?qū)W生傳達(dá)偽滿洲國這一“新國家”是如此美好的價(jià)值觀念。
(三)大力宣揚(yáng)與“建國”相關(guān)的活動(dòng)
《國文教科書》中編寫了數(shù)篇與“建國”相關(guān)的課文,如第五冊第一課“建國日之晨”、第二課“建國慰靈大祭”、第七冊第十三課“建國紀(jì)念大運(yùn)動(dòng)會(huì)”、第八冊第三課“建國宣言”等。這些課文在語言表述上大量使用宣稱策略,同時(shí)運(yùn)用“情態(tài)”這一語言實(shí)現(xiàn)形式。如第五冊第一課“建國日之晨”開篇寫道:“康德二年三月一日,為吾國建國紀(jì)念之良辰。朝起后,見旭日漸異,照射屋瓦,光華燦爛,比戶皆懸國旗,隨風(fēng)飄揚(yáng),市民俱現(xiàn)興高采烈之色。”[10]這些課文渲染了“建國日”及相關(guān)活動(dòng)的熱鬧氛圍,表達(dá)了擁護(hù)偽滿洲國成立的立場與態(tài)度,意在使學(xué)生在這些課文的影響下形成偽滿洲國的“國家觀念”。
二、大力塑造偽滿洲國的“國民形象”
“國民形象是公民素質(zhì)、行為、道德、理念和精神追求的抽象整合”。[11]國民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一個(gè)國家的整體精神面貌。偽滿洲國初級小學(xué)《國文教科書》大量使用論證策略與宣稱策略,塑造偽滿洲國良好的“國民形象”,這些形象承載了日本侵略者的意識(shí),以此來型塑青少年的思想與行為,起到鞏固日偽統(tǒng)治的目的。
(一)塑造忠貞愛國與愛崗敬業(yè)的偽滿洲國“國民形象”
《國文教科書》第六冊第三課《東儒語錄》第二則為“赤心報(bào)國”,課文題目點(diǎn)明中心,塑造了忠貞愛國的“國民形象”。第三冊第四十七課《迷路》描寫了巡警送迷路幼童回家的故事。課文運(yùn)用論述策略,在描寫巡警時(shí)提及“抱起安慰”“巡警抱之行”。兩個(gè)“抱”字動(dòng)作感十分強(qiáng)烈,突出巡警對幼童的關(guān)愛,意圖塑造偽滿洲國巡警的“親民形象”,反映其“敬業(yè)精神”。偽滿政權(quán)讓東北青少年從小學(xué)階段起就學(xué)習(xí)偽滿教科書塑造的這些愛國敬業(yè)的“國民形象”,企圖將之馴化為服從日偽統(tǒng)治的忠順良民。
(二)塑造母慈子孝與兄友弟恭的偽滿洲國“國民形象”
《國文教科書》第二冊第十一課《納涼》寫道:“母親坐椅上,大姐立椅旁,兄姐聽母講故事,吾與小妹捉迷藏。”[8]11第十五課《中秋節(jié)》寫道:“父講月宮故事,母分月餅,一同賞月,兄弟姊妹歌且舞。”[8]15兩篇課文在話語上使用了宣稱策略,用樸素的語言描繪一個(gè)偽滿洲國普通家庭闔家美滿的幸福、溫馨畫面,意圖讓學(xué)習(xí)課文的學(xué)生對偽滿洲國的生活產(chǎn)生無限向往之情。
(三)塑造勤勞勇敢與團(tuán)結(jié)他人的偽滿洲國“國民形象”
《國文教科書》第八冊第九課《童子園天幕生活之一日》寫道:“弟兄八人,各自開始工作。有預(yù)備早餐者。有整理天幕者。有結(jié)籬者……無一柚手旁觀者。”[12]20-21課文運(yùn)用了排比的修辭手法,使語言節(jié)奏更加鮮明,更加有利于塑造勤勞的偽滿洲國“國民形象”。第六冊第十二課《不守紀(jì)律之雁》通過描繪不守紀(jì)律的大雁的悲慘下場,警示學(xué)生在集體中要守紀(jì)律、要團(tuán)結(jié)。課文使用了借代的修辭手法,用不守紀(jì)律之雁的故事教育學(xué)生要團(tuán)結(jié)守紀(jì);還使用了隱喻的語言實(shí)現(xiàn)形式,用不守紀(jì)律之雁暗指那些不服從偽滿洲國統(tǒng)治的國民,間接“教育”學(xué)生不服從偽滿洲國的統(tǒng)治得不到好下場。
(四)塑造崇儒重道與博愛尚禮的偽滿洲國“國民形象”
《國文教科書》第七冊第二十二課《賢母》寫道:“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為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13]61教科書通過描述偽滿洲國的一位母親對兒子的教育,向?qū)W生傳達(dá)不能因公假私的思想。第二十三課《勸孝》寫道:“故父母之命,非不得己,慎勿違之……而累父母之名。則不孝之尤者矣。”[13]63-64課文向?qū)W生傳達(dá)了偽滿洲國“國民”注重封建孝道。第二十四課《至圣林》寫道:“游圣林者,親見孔子莊嚴(yán)之墓地,思其偉大之道德不禁傾心膜拜”。[13]68課文意在體現(xiàn)偽滿洲國崇尚儒家之道的價(jià)值觀。
三、大肆宣揚(yáng)偽滿洲國環(huán)境優(yōu)美、物資豐富
偽滿洲國初級小學(xué)《國文教科書》運(yùn)用大量的舉例,論證了偽滿洲國擁有優(yōu)美的自然環(huán)境與豐富的物質(zhì)資源。
(一)宣揚(yáng)偽滿洲國優(yōu)美的自然環(huán)境
《國文教科書》大量使用宣稱策略,如第三冊第十九課《遠(yuǎn)足》寫道:“春雨之后,柳舒花放,野外風(fēng)景漸佳,綠水青山,花香鳥語”。[14]20-21第六冊第十六課《萬泉河》寫道:“河中均種紅白荷花。每至夏日,楊柳風(fēng)清,芰荷香遠(yuǎn),為絕好一大納涼園”。[15]教科書在描寫自然環(huán)境時(shí),多使用優(yōu)美的形容詞加以修飾、限定,如香、清、佳、奇等,賦予偽滿洲國自然環(huán)境優(yōu)美的特征。第三冊第三十一課《江上風(fēng)景》使用隱喻的語言表現(xiàn)形式,寫道:“遠(yuǎn)望隔岸,山村隱約,沙鳥群飛,時(shí)上時(shí)下,有如一幅名畫”。[14]34
(二)宣揚(yáng)偽滿洲國豐富的物質(zhì)資源
在編寫這部分內(nèi)容時(shí),《國文教科書》編寫者大量運(yùn)用論證策略。如第八冊第十二課《我國之農(nóng)村及農(nóng)產(chǎn)物》寫道:“我國主要之農(nóng)產(chǎn)物,以大豆為第一,占世界大豆產(chǎn)額十分之六。據(jù)最近統(tǒng)計(jì),年產(chǎn)三千八百萬石以上,占全滿谷物一億五千萬石中四分之一。”[12]36課文對物產(chǎn)產(chǎn)量的說明運(yùn)用了列數(shù)字的方法,直觀、清楚、準(zhǔn)確地說明大豆的產(chǎn)量豐富,以便理解。第七冊第二課《滿洲之梨》寫道:“滿洲水果,除南滿洲之蘋果外,復(fù)有數(shù)種山梨。如熊岳城之紅梨……北鎮(zhèn)之鴨梨、皆甚著名”。[13]5通過這些敘述,意圖使學(xué)生在頭腦中逐漸形成偽滿洲國物質(zhì)資源極大豐富的認(rèn)識(shí)。
四、高度稱贊日本民族“卓越的”事跡
分析話語中建構(gòu)的聯(lián)系,是話語分析常用的技巧。偽滿洲國初級小學(xué)《國文教科書》提及“日本”多達(dá)40次,高度稱贊日本民族“卓越的”事跡,欲引起學(xué)生對日本的向往。這反映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以自身的文化特性、民族精神來消弭并取代東北青少年原有的中華民族身份。這部分課文內(nèi)容主要介紹了日本的自然風(fēng)光優(yōu)美、日本人民的高尚品質(zhì)、日本軍事力量的優(yōu)越。
(一)稱贊日本的自然風(fēng)光優(yōu)美
《國文教科書》第七冊第十一課《富士山》介紹了富士山的風(fēng)光,寫道:“富士之于日本,伊古以來,詠為詩歌,繪圖畫猶不足以盡之”。[13]32-33教科書編寫者運(yùn)用宣稱策略,賦予了日本環(huán)境優(yōu)美的形象,意圖使學(xué)生產(chǎn)生對日本的向往之情。
(二)稱贊日本人品質(zhì)高尚
偽滿教科書將日本大和民族美化為世界最優(yōu)秀的民族,塑造完美的日本人形象。《國文教科書》第八冊第二課《今上圣德紀(jì)要》使用強(qiáng)化策略,大力夸贊日本天皇,塑造了其勤政、好學(xué)的形象。第七冊第十課《日本人與櫻花》運(yùn)用隱喻的手法,將日本人比作櫻花,突出其光明、淡泊、尚武、樂天的品性,極力美化日本人。
(三)稱贊日本軍事力量優(yōu)越
《國文教科書》中多次提到日俄海戰(zhàn)。第八冊第十課《日本海大海戰(zhàn)》結(jié)尾寫道:“日本海上、煙波浩淼、己不復(fù)見俄艦片影矣。然日軍之損害、僅失水雷艇三艘而己”。[12]29教科書編寫者運(yùn)用視角策略,表明偽滿洲國的觀點(diǎn)與立場,即稱頌日本海軍艦隊(duì)以少勝多、英勇非凡、戰(zhàn)功顯赫。
五、結(jié)語
阿普爾曾提到,“教科書是學(xué)校教育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也是學(xué)生接受知識(shí)的重要途徑”。可以說,教科書是學(xué)生學(xué)習(xí)知識(shí)最直接的材料。從近代斯賓塞提出“什么知識(shí)最有價(jià)值”這一經(jīng)典問題以來,教育學(xué)者不斷對其進(jìn)行討論與商榷,進(jìn)一步分析“誰的知識(shí)最有價(jià)值”。“誰的知識(shí)最有價(jià)值”的背后反映的則是意識(shí)形態(tài)問題。日本侵略者重視偽滿洲國的教育,尤為重視教科書的特殊作用,利用教科書宣揚(yáng)偽滿洲國的意識(shí)形態(tài),塑造符合日偽政權(quán)所需要的“國民”,以此麻痹學(xué)生思想,消解反抗意識(shí),進(jìn)而達(dá)到奴化教育的終極目的。偽滿洲國教科書的話語是典型的殖民話語,運(yùn)用論證策略、宣稱策略、視角策略、強(qiáng)化或弱化等話語策略,歪曲事實(shí),篡改歷史,使偽滿教科書徹底淪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地區(qū)的工具。通過對偽滿教科書的話語分析,可以揭示日本侵略者妄圖亡我中華文化之企圖、侵我中華之罪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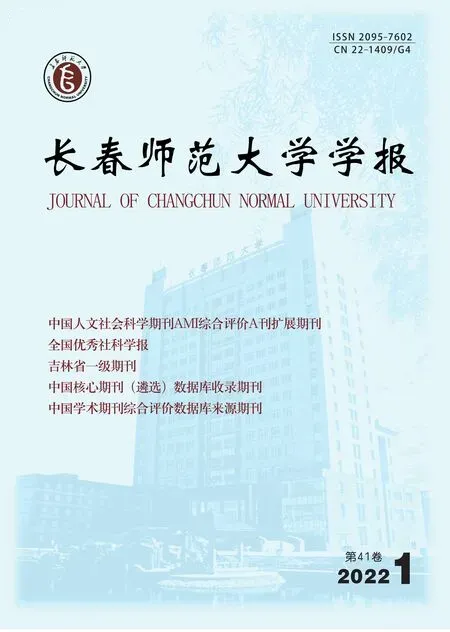 長春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2年1期
長春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22年1期
- 長春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多元化教學(xué)模式在《昭明文選》課程中的應(yīng)用
- 基于產(chǎn)出導(dǎo)向法的大學(xué)外語“金課”建設(shè)研究
- 問題導(dǎo)向與文本闡發(fā):基于“問題式”教學(xué)法的外國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改革與實(shí)踐
- 以學(xué)生為中心的高校思政課實(shí)踐教學(xué)實(shí)現(xiàn)形式探究
- 大數(shù)據(jù)經(jīng)濟(jì)背景下應(yīng)用型本科院校會(huì)計(jì)學(xué)專業(yè)培養(yǎng)模式研究
- 高校心理委員隊(duì)伍建設(shè)存在問題及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