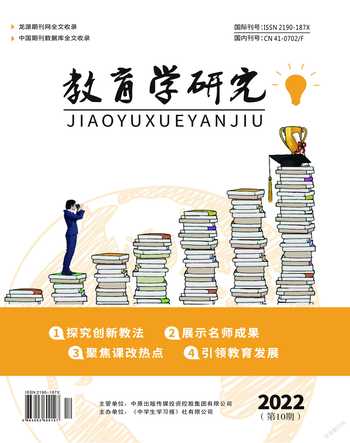迷人的想象,悲哀的現實:論唐亞平《黑色睡裙》中的戲劇性
摘要:《黑色睡裙》一詩因其鮮明的敘事特征而獲得了戲劇性的藝術效果,成為唐亞平《黑色沙漠》組詩中獨一無二的一個現象。本文通過對詩歌中戲劇性情境、戲劇性動作、戲劇性語言、戲劇性結構和戲劇性沖突的分析,從中探究詩人如何通過這些表現手段來抒發情感,對現代人的精神世界進行揭示,對現代化轉型語境下的都市文明進行藝術化解構,筆者希望本文能為詩歌評論拓展話語空間,也為當代詩歌創作中多種文體的有機融合提供一些可能的啟示。
關鍵詞:敘事;戲劇性;表現手段;現代化轉型;隱喻
《黑色睡裙》是唐亞平《黑色沙漠》組詩中的一首。這組創作于1985年的詩歌使詩人成功躋身中國第三代女詩人之列,形成了當代女性詩人對“黑夜意識”的預感[1]。與組詩中其余十來首詩一樣,《黑色睡裙》題目中引人注目的“黑色”既代表了詩人彼時詩歌創作的藝術特色,也表達了那個年代人們的普遍情緒。由詩人的女性身份而產生的女性詩學已成為學界自然且慣常的批評視角,這一視角將女性的身體寫作、女性的生命體驗、女性的靈魂自白、女性的價值立場都進行了較為深刻的闡釋。
新批評理論家伯克 (Kenneth Burke)認為文學作品是有關人生障礙的表現和對其象征性的解決,因而所有文學作品形式必定含有戲劇的成分[2]。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進一步提出“詩的結論是各種張力的結果——統一的取得是經過戲劇性的過程,而不是一種邏輯性的過程”,主張把詩中所有成分都看成戲劇臺詞[2]。如果說伯克和布魯克斯是從較為寬泛和普遍的意義上去強調人類所有文學作品的戲劇性,那么《黑色睡裙》一詩則集中體現了詩歌這一文體中的戲劇性特質:它雖以抒情為鵠的,但文本肌理卻整體顯現出敘事的特點,因為敘事者“我”以自己所處的內視角敘述了一個簡短而完整的故事,使詩歌具備完整的情節,包含敘事者的所見、所聞、所感。而通常來講,敘事詩中往往具有戲劇成分,這是因為,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情節是戲劇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素。
遺憾的是,除了陳劍瀾在其文章中提到《黑色睡裙》是《黑色沙漠》里唯一一首敘事詩之外[3],評論界至今鮮有論者從戲劇性角度對這首詩進行過研究。基于此種現狀,本文試圖結合戲劇的基本要素對這首詩進行分析,旨在探討詩人唐亞平運用了哪些戲劇性表現手法使詩歌獲得了特殊的藝術效果,希望能為詩歌評論拓展話語空間,也為詩歌創作提供一些可能的啟示。
根據通常的戲劇理論觀點來看,戲劇性主要體現在戲劇動作、戲劇語言、戲劇沖突、戲劇情境、戲劇懸念、戲劇場面和戲劇結構等幾個方面。本文將根據《黑色睡裙》這個詩歌文本中所實際表現出的戲劇特性進行分析。
一、戲劇性的情境
蘭色姆對詩歌戲劇性之一的戲劇情境有過這樣的描述:“要理解詩歌,‘戲劇情境’差不多是第一門徑。誠如理恰茲所言,許多詩歌如沒有它幾乎乏善可陳。如果失去戲劇情境的吸引力,勃朗寧的戲劇獨白一定十分單薄,因為它根本缺乏我們希望在詩歌中看到的那種總體肌質”[4]。而所謂的戲劇情境,在我國戲劇理論家譚霈生看來,是指促使戲劇沖突爆發、發展的契機,是使人物產生特有動作的條件[5],具體體現在兩個關系最緊密的要素之上:一是事件、一是人物關系[5]。
在詩歌的開端部分,敘事者“我”便交代了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和“我”的處境,這些要素共同構成了詩歌中事件發生、發展的前提和條件:
我在深不可測的瓶子里灌滿洗腳水/下雨的夜晚最有意味/約一個男人來吹牛[6]
第一詩句中的敘述借助“瓶子”這一容器隱喻來形象說明,“我”的身體空空蕩蕩,需要借助外物來填充,從后文得知,空虛的感覺主要來自情欲之火的灼燒,所以即使用洗腳水也難以將其填補,如果說第一詩句所形成的困境主要是緣于主體的身體原因,那么第二詩句中外界寂寥而喧鬧的雨聲則烘托了“我”的心靈困境,因為雨的存在阻隔了“我”與外界的聯系,從而陷入身心雙重困境,讓“我”無比孤單寂寞。在這種處境下,第三詩句中“約一個男人”來家里便成為解除困境的一個最佳辦法。其中,數量詞“一個”說明將要到場的男人只不過是萬千世界中很隨機的一個符號,其年齡、身份和性格都是不確定的,充其量只是滿足特定情境下“我”的需要的一個工具人,而“我”和他也顯然是陌生人的關系。但我無法給自己找一個合適的借口,所以“來吹牛”便成了一個可以被替換為“制造意義”的自欺欺人的蹩腳理由。顯然,明明“我”內心的動機是解除身心困境,但口中的理由是吹牛,這就為后來詩歌中事件的發展既設置了懸念又埋下了伏筆。這樣一來,充滿未知數的戲劇性情境就成為人物行動的特殊實驗室,在這里上演的行動將最終檢測出人物的真假、善惡與美丑。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雖然后文中詩歌的戲劇性事件在不斷發展變化,但這一情境依然是人物一系列行動的起點,在繼續為行動提供緣由。
二、戲劇性的動作
動作作為戲劇的基本表現手段,向來在戲劇藝術中非常關鍵。戲劇動作從表現形式上,可分為外在動作和內在動作。外在動作是可觀看的動作;內在動作是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展現。黑格爾說:“能把個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現出來的是動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過動作才能見諸現實”[5]。 同時,需要進一步指出,戲劇的主要因素不是實際的動作情節,而是揭示引起這種動作的內在精神[7]。
由于這首詩中的人物只有敘事者“我”和“一個男人”,所以詩歌中的動作表現為兩個人互動的結果。由前文得知,因為是“我”主動約請別人到我家中,所以“我”等待客人到來的一系列動作便自然而然首先出現在讀者眼前:
我放下紫色的窗簾開一盞發紅的壁燈/黑裙子在屋里蕩了一圈[6]
由“放下紫色的窗簾”、“開一盞發紅的壁燈”、“穿黑裙”、“在屋里蕩了一圈”等動作可以看出,敘事者“我”是一個喜歡浪漫且性格奔放的女人,雖然自稱是叫人來吹牛,但“我”的一系列肢體動作說明,為了讓心向往之的約會能夠成功,“我”在用心營造溫馨迷人的氛圍,幻想著浪漫的二人世界,并預演著釋放本我的激情之夜。
而接下來,在“我”打開房門之后,眼中來客的動作卻是這樣的:
他進門的時候帶著一把黑傘/撐在屋子中間的地板上[6]
來客“帶著一把黑傘”的動作說明,即使在這樣一個密雨如織的夜晚,他也害怕在眾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行動,所以才用黑色雨傘來進行遮掩。這樣的動作不禁讓人推測到,來者要么是一個有婦之夫,要么就是對此次約會心存戒備。而他將雨傘“撐在屋子中間地板上”的細節動作一方面暗示出他沒想和眼前穿著黑色睡裙的女人共舞,另一方面也說明這是一個見機行事,隨時準備逃離現場的膽小鬼。
在看到這幅情景時,“我”不再對約會抱有希望,但由于是自己主動邀請對方前來“吹牛”,所以這時候,將見面模式由“約會”切換為“吹牛”便成為無奈中的權宜之計:
我們開始喝濃茶/高貴的阿諛自來水一樣嘩嘩流淌/甜蜜的謊言星星一樣的動人/我漸漸隨意地靠著沙發/以學者的冷漠講述老處女的故事/在我們之間上帝開始潛逃/捂著耳朵掉了一只拖鞋[6]
用濃茶來招待客人,說明“我”切換回了自己的主人身份,開始努力將兩人的關系保持在一個非常客套的距離之內,并時刻保持清醒和理智,使自己不至于因為心靈空虛和身體饑渴而淪陷在這樣一個男人面前。但由于兩人之間的談話空洞無物,華而不實,所以“我”的坐姿也漸漸慵懶隨意,不再故作莊重,“我”給對方講述老處女的故事,既是對自己人生經歷的嘲諷,也是對對方的戲謔和鄙視。
所以,雖然整首詩歌中的戲劇性動作是外在的,但這些動作卻是對人的內在精神中最深刻方面的精彩折射,它們將人物內心的深層動機和心理變化通過形象的外部動作顯現出來,實現了戲劇性動作的內在和外在統一。
三、戲劇性的語言
頗有意味的是,在這首敘事性極強的詩歌中,除了敘事者“我”和來客的動作描述之外,人物之間沒有具體的對話內容,而是自始至終通過“我”的獨白式語言來展開故事的全部情節。同時,敘事者使用的語言又是滑稽諷刺的,它們除了揭示人物的心理現實外,還富有形而上的哲學意味。
比如,在客人到來之前,對于“我”的一系列精心準備,敘事者的自述是“他到來之前我什么也沒有想”,“門已被敲響三次”“我”才去打開。這與她預演浪漫、充滿期待的真實心理形成了極大的悖論。這些自述至少說明,一方面,“我”是一個想要以強大姿態示人的女人,如果坦率表露自己對約會的滿懷期待,可能就無法為自己接下來的失望和尷尬留下余地;另一方面,對于都市男女雨夜約會這樣的事情,“我”在潛意識里并不覺得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只能故作淡定矜持,心口不一。
在故事的轉折部分,在“我”漸漸識破來者偽君子的真實面目之后,詩歌的語言表現出更大的反諷意味:詩人用“高貴”修飾“阿諛”,并將后者比喻為自來水,說明“我們”之間的談話索然無味,缺少實質性的內容;用“甜蜜”形容“謊言”,還說它像星星一樣動人,是對兩個成年人之間廉價的逢場作戲的辛辣諷刺。
就這樣,男女主人公仿佛是當眾表演的演員,在觀眾面前上演著一出滑稽諷刺的現代喜劇,將人生無意義的東西撕裂開來丟在人們面前。本來,世界上并不存在上帝,但哲學專業出身的唐亞平長于對人生和宇宙的思考,并能夠運用語言這一媒介將現實和想象巧妙裁剪拼貼,形成了極具張力的藝術表現空間。于是,鑒于主人公的滑稽表演,詩人便引入上帝這樣一個代表西方世界里信仰、真理和本質的重要形象出場,讓他作為全知全能型的觀眾和裁判,注視兩位演員的表演并做出道德審判。但在親眼目睹了現代人的可鄙可悲面貌之后,就連上帝也是如坐針氈,最后竟然狼狽潛逃。“潛逃”一詞在此發揮了畫龍點睛的功效:它既說明了上帝開始嚴重懷疑自己掌握所造之物靈魂和行為的能力,為自己不能仲裁現代人的靈魂糾紛而深感汗顏難堪,更重要的是對上帝神圣形象進行消解,使他也淪落為一個在讀者眼前落荒而逃且掉了拖鞋的小丑,從而實現對深受西方現代文明影響的都市文明的解構。借助這樣的戲劇性語言,讀者起初會對詩歌中的人物形象和情節動作忍俊不禁,但在笑過之后,難免會思考黑色幽默敘事背后的荒誕現實。
在詩歌最后,敘事者再次將場景切換到雨夜:
在夜晚吹牛有種渾然的效果/在講故事的時候/夜色越濃越好/雨越下越大越好
如果說開端時的雨景更多烘托了“我”孤單寂寞的心緒,那么結尾處詩人再次動用黑夜和雨景則不應該被理解為是一種簡單重復。它的出現不但強化了抒情主人公內心的悲哀,也使得詩歌蒙上了一層陰郁的色彩。與尤金·奧尼爾在《瓊斯皇》一劇中鼓聲的表現主義手法相似,它們將“我”內心的絕望、無力和悲哀用具體可感的顏色和聲音得以外化,實現了內外交融,情景合一的藝術功效。
四、戲劇性的結構
完整性和統一性是任何樣式的文藝作品都必須注意的問題,是藝術標準之一。而實現藝術作品的完整性和統一性是結構的課題[5]。通常來講,對于戲劇作品而言,動作是最主要、最基本的表現手段,因為它能夠將戲劇的沖突、情節、場面等串聯起來。所以戲劇結構的基本任務就是選擇不同人物的動作并將它們組織在一起,使它達到完整性和統一性。《黑色睡裙》一詩在結構上的特色也是使其富有戲劇性的另一重要原因。
在這首篇幅不算太長的詩歌中,故事發生在雨夜里一對男女身上,如果按照動作單元構成情節的觀點來看,那么詩歌的戲劇性結構呈現出明顯的環形反諷特征:
(1)動作的開端——希望約會:雨夜里“我”由于身心的空虛寂寞,想找一個男人來約會;
(2)動作的發展——準備約會:“我”制造浪漫氣氛,預演激情之夜;
(3)動作的高潮——“約會”的過程:兩個人在交流過程中一個故作矜持、欲擒故縱,一個畏首畏尾、虛情假意,所以約會最終降為虛偽、無聊、滑稽、廉價的過場戲;
(4)動作的落潮——對“約會”的失望:“我”漸漸識破對方的偽君子面目,約會希望破滅,故而索性拿“老處女的故事”來褻瀆游戲對方;
(5)動作的結尾——雨夜中的絕望:夜色和雨景加重了我的哀傷,孤獨的陰影面積比之前更為擴大。
可以看出,從詩歌開始時“我”對約會的熱烈希望,到最終互動后的絕望,詩歌完成了一個完整的反諷式結構;從開始到結尾一直伴有雨景,形成了一個首尾呼應的環形結構,但前后兩個雨景因為“我”心境和情緒的巨大反差說明了生活不但停滯不前,反而在無聊的重復中增加了哀傷失望,愈加顯出現實的灰暗殘酷。
五、戲劇性的沖突
“沖突”作為戲劇藝術特性和本質之一,具有廣泛而牢固的理論基礎。在談及戲劇沖突時,黑格爾說過:“人類情感或活動的本質意蘊如果要成為戲劇性的,就必須分化成一些不同的對立的目的,這樣,某一個別人物的動作就會從其他發出動作的個別人物方面受到阻力,因而就要碰到糾紛和矛盾,矛盾的各方面就要互相斗爭,要求實現自己的目的”[7]。
詩歌雖然是以敘事者“我”的人稱來講述,但真正牽動意志之線的顯然是詩人本人。作為一位在20世紀80年代登上中國詩壇的女詩人,唐亞平以其深邃而敏銳的藝術眼光洞察到了由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所引發的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巨大變遷。表現在這首詩歌中,女人是在家發出邀約的主人,而男子是被動赴約的客人;女人是寧愿堅守老處女身份的強女人,而男人則是唯唯諾諾、軟弱順從,缺乏男性氣質的膽小鬼。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負陰抱陽式的兩性和諧相比,現代男女的角色在此發生了結構性的顛倒錯位,所以即使是萬能的上帝也只能潛逃,宣告約會失敗。
可見,雖然詩歌中的人物沒有明顯的外在沖突,卻因為雙方內心深處的較量而使沖突變得復雜尖銳。由現代化轉型所引發的男女角色和地位的深刻變化成為詩歌內在戲劇性沖突的深層原因:女性在與男性的激烈競爭中逐漸擠進社會舞臺中央,但在心靈深處又希望從男性那里獲得回應,有所依靠;男性愿意出演女性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但又無法接受女性咄咄逼人的強勢姿態。在男女們為自己爭取舞臺話語之時,雙方內心深處的焦灼和撕扯便使得他們不愿表現真實自我而是互相較量。于是,兩性雖然同臺演出,卻按照各自擬定的劇本自說自話,身體雖近在咫尺,而心靈卻有如萬水千山之隔,由努力控制社會話語權力的一個極端不幸滑向了生物性別異化的另一個極端。所以,黑色睡裙成為這場沖突的一個道具,其出場時的華麗迷人和落幕時的灰暗哀傷正深刻隱喻了發生在現代社會男女兩性之間和諧的破壞和難以和解的震蕩性危機。
六、結語
著名戲劇人類學理論家巴爾巴(Eugenio Barba)認為那種被現代人遺失的戲劇是一種社會行為方式:“什么是戲劇,如果試圖減少這個詞到某種明確的東西,我發現是男人和女人,人類相遇在一起。戲劇是在一種被選取的環境中的一種特殊關系——一種文化意義上和人類學意義上的戲劇概念,那便是人類的相遇、交流,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8]。戲劇作為與時俱進的人類藝術,在現代社會越來越致力于對人類危機境遇的揭示和對人生價值的思考。也許,正是詩人唐亞平洞察到了戲劇的本質精神,發現了戲劇精神對于文學乃至整個人類的重大意義,所以她在詩歌創作中便運用了戲劇性的表現手段,而這些手段不僅讓《黑色睡裙》在她的“黑色姊妹”中獨具一格,而且將現代人在生存的殘酷自然法則和社會通則中須臾不能離棄的敘事本領提高到一個形而上的高度,引發讀者的深沉思考。
參考文獻:
[1]汪劍釗.女性自白詩歌:“黑夜意識”的預感[J].詩探索,1995:80.
[2]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72.
[3]陳劍瀾.誰的80年代?——重讀唐亞平《黑色沙漠》[J].南方文壇,2017(3):131.
[4]約翰·克羅·蘭色姆.新批評[M].王臘寶,張哲譯.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2006:41.
[5]譚霈生.論戲劇性[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98;102;11;209.
[6]岑晨鈺.唐亞平組詩《黑色沙漠》.2016.10.7.<http://www.douban.com.>
[7]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M].朱光潛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8:248;257.
[8]陳世雄,周寧,鄭尚憲.西方戲劇理論史[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1119.
作者簡介:吳生艷(1984- ),女,寧夏鹽池人。 寧夏師范學院副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為歐美文學、俄羅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