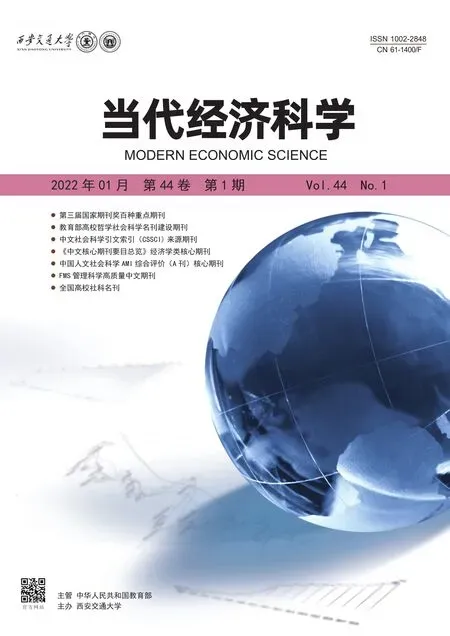財政干預改變了企業融資傾向嗎?
鄭田丹 莫東序



摘要:?企業融資問題不僅受到金融貨幣政策的影響,財政干預對于企業融資傾向的影響也不容忽視。通過構建財政干預政策與企業融資傾向指標,利用多元面板logit模型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財政干預政策推動企業選擇股權融資作為外部融資的首選手段。對企業進行分組檢驗發現,企業的所有制、行業性質、規模等不同,企業受到財政干預政策的影響不同。以企業經濟預期作為中介變量檢驗發現,財政干預政策通過影響企業對經濟的預期而影響企業融資決策。以市場金融化程度作為政策環境沖擊分析發現,當前“脫實向虛”的經濟走勢顯著影響了財政干預政策對企業融資傾向的作用效果。因此,新常態下的財政干預政策要著眼于微觀企業的異質性,同時結合金融貨幣政策保障企業融資市場的有序。
關鍵詞:?財政干預;企業融資;金融發展;經濟預期;金融化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8482022(01)001312
一、研究背景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一個典型特征是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建設的影響力度越來越大。根據Cournede等[1]的定義,我國狹義和廣義金融發展指數①分別從2000年的482%和4796%提高到2017年的808%和7255%(見圖1)。中國經濟增長中來自金融體系的貢獻越來越大。經濟增長結構的重大變化對就業、收入分配、經濟波動等顯然有著重要影響。Christiano等[2]通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驗證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周期的穩定器作用。金融體系通過傳導貨幣政策對經濟產生影響,并間接影響微觀實體的投資效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金融體系演進是可以有力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但金融發展到了一定水平也可能會加劇金融風險。當金融業發展到過度吸納社會財富的程度時,會引致金融危機并造成經濟萎靡。
企業債務過度積累和杠桿率的過度提高,極大傷害了經濟增長潛力和投資效率,且易引發全面經濟危機。2017年,中央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要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2019年7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四部門發布《2019年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要點》,強調要促進企業的市場化債轉股增量,完善企業債務風險監測預警機制。
企業為了保證投資效率,會采取多元化融資方式對金融風險進行規避[3]。當內源資金無法支撐企業發展時,企業必然要轉而尋求外部融資,通過開展多元化融資降低綜合融資成本。融資優序理論[4]認為,在企業家充分掌握企業信息時,企業融資方式將依序選擇“內部融資—債務融資—股權融資”等方式。也有學者進一步考察多因素后認為,即使企業內部現金和債務額度足夠多,部分企業仍會選擇股權融資[5],這種融資選擇有降低成本的考慮,也可能是為了降低金融風險。為了保證金融市場穩定和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政府通過貨幣政策影響金融市場,或者選擇財政政策影響企業投資和融資行為。貨幣政策通過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等方式改變信貸供給量,導致企業內部融資與外部融資的成本差異,影響企業融資行為。
財政支出水平采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長率,股權融資和債務融資指標參考蘇冬蔚等[6]的研究分別設定為股東權益合計與總資產之比以及總債務與總資產之比。圖2微觀數據范圍為2002與2018年上交所與深交所非金融行業上市企業數據進行全行業加總,財政干預度數據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ZW)]。可以發現,財政支出水平對企業的不同融資傾向均具有一定的影響。債務融資傾向變動趨勢基本與財政支出水平的變化方向一致,并同時在2008年達到最高點,在2014年達到最低點。歷年股權融資傾向變動趨勢正好相反:在2008年股權融資依賴度最低,在2014年重返最高點。隨著金融化程度的提高,為保證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更好地融合發展,防范金融風險,2012年7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財政政策要配合信貸政策,優化經濟結構,有效防范和化解潛在金融風險。為了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中央和地方均出臺了眾多財政干預政策,如完善政府采購制度等。
目前學界針對財政干預影響企業融資傾向的政策效果研究較少,研究視角主要有兩種。第一,大部分學者研究了稅收征管對企業避稅活動和融資選擇的影響,即非債務稅盾理論[7],內在機制是避稅活動增加了企業內部現金流,從而降低債務融資規模。而劉行等[8]通過檢驗發現,上述“非債務稅盾效應”并不存在,因此稅收征管有助于企業獲取債務融資。國內學者進行了相關的實證驗證,結論不一。有學者認為稅收征管加劇了企業融資約束[9],對企業的稅收優惠也沒有顯著提高融資能力;也有學者發現稅收征管可以通過“激勵效應”使高評級企業融資約束顯著降低[10]。童錦治等[11]研究發現,不同融資方式對稅收活動加強的反應不一,企業避稅會提高企業債務融資成本、降低股權融資成本。第二,還有一部分學者關注包括財政補貼在內的財政支出政策對于企業融資的影響。Thoreten等[12]證明了財政補貼可以增加中小企業融資機會、緩解融資約束。魏志華等[13]研究發現,財政補貼雖然可以緩解融資約束,但是同時也會導致企業的過度投資。
已有研究主要停留在貨幣政策影響企業融資的傳導機制中。而為數不多的關于財政干預對企業融資傾向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國外研究仍主要關注的是財政基本政策,且文獻較陳舊,缺乏對于我國財政政策的及時關注;第二,國內學者對此類問題的研究主要以現象分析為主,實證研究較少且研究結論不一甚至相反,個中原因較多,如指標選擇較為片面、異質性原因考慮不足、融資約束沒有納入分析等;第三,已有研究證明財政干預對于企業融資傾向有影響,卻沒有關注內在傳導路徑問題。基于此,本文可能的創新點如下:
首先,對財政干預機制全面有效梳理,在考察視角上創新;
其次,全面考察企業異質性對于上述傳導機制的影響,研究結論具有較強適用性;
最后,全面考察財政干預對企業融資傾向的影響機制,并研究金融化環境給財政干預政策的作用效果帶來的影響。
二、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說
早期對企業融資問題的研究[14]都以完美資本市場作為前提假設,即企業融資傾向的不同不影響融資成本的變動,不同融資方式間可以完全替代。但現實資本市場中,金融摩擦一直客觀存在,在分析問題時無法忽視。因此,考察企業融資傾向及其影響因素對企業規避融資成本、提高融資效率至關重要。Myers等[4]通過加入信息不對稱條件設定非完美資本市場假設,研究發現企業內部融資的成本要顯著低于外部融資產生的成本。宏觀經濟政策會顯著影響企業的融資傾向,金融市場上的國家政策能夠影響企業融資傾向的主要是以信貸政策為代表的貨幣政策,這一研究已逐漸成熟。貨幣政策收緊將導致企業進行外部融資的渠道變窄,企業融資傾向將以銀行信貸為主[3]。與發達國家經濟結構以滿足消費為主不同,我國實體經濟目前仍以投資拉動為主。在財政政策不斷干預下,實體投資會被政府投資帶動起來,企業投資機會增加,企業資金需求增加,對企業融資活動有正面影響。企業資金鏈的暢通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生存,因此融資成本的高低影響企業的發展。然而融資成本常年占據企業經營利潤的大部分空間,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積極財政干預政策可以改善實體經濟環境,降低企業融資約束。同時,財政干預政策也可以釋放需求側潛力,推動投資和出口提升,為企業走出資金困境提供引力,優化企業內部現金流的調配。財政干預對企業活動最為直接的影響包括提高企業生產資本的供給,通過財政補貼、特定稅收優惠、融資質押擔保等形式為企業提供財政支持,使得企業增加內部現金流,減少外部融資規模。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H1:財政干預政策對企業融資傾向有顯著影響,企業在財政干預影響下優先選擇內部現金流作為資金來源。
相比于國有企業而言,非國有企業對稅收的敏感性更強,這源于國有企業的政企關系緊密度更高[15]。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預算軟約束有別于其他企業的社會效益最大化目標,導致其進行投融資決策時對稅收的敏感性較低。無論稅負是否加重、政府補貼是否提高,國有企業仍會選擇其原有的融資模式不變,因此對于政府補貼與稅收優惠等干預政策,國有企業的融資決策響應程度不如非國有企業。此外,以銀行為代表的資金提供方出于風控管理預期,提高非國有企業的融資門檻,降低該類企業融資抵押標的物的價值、提高其融資利率。從信貸配給角度來說,國有企業在信貸資金供給市場獲得了巨大的優勢,客觀上也造成了對非國有企業的信貸歧視,“惜貸”情況頻出。
企業所有制形式不是唯一可以影響財政干預對企業融資傾向作用效果的企業異質性因素。其他諸如企業規模、行業性質等都會改變這一機制的效果。中小規模企業相比于大企業而言會有信貸資源獲取上的天然劣勢,這一劣勢來自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銀行傾向于將貸款更多地投放于財務制度更健全、財務信息更規范的大型企業,以此對貸款項目進行風險控制。不同行業的企業受到信貸和金融市場的青睞程度不同,國家支柱產業如高鐵、航天、光伏等高新行業可以以更低的融資成本獲得外部資金。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H2:企業異質性因素會改變財政干預對企業融資傾向的影響效果。
財政干預政策的變動天然不如貨幣政策工具靈活,因此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財政干預政策的出臺要在相對長的周期內延續政策執行度,保證政策受眾能夠建立相應的政策形勢判斷,做出有效的投資決策。財政干預政策的實施,不僅在實質上減輕了企業稅收壓力,也因其特惠式減稅向普惠式減稅的模式轉變而提高了企業投資者對于既定經濟形勢下企業經營情況的預期。這種預期的改善源于兩方面:第一,財政干預政策增加企業內部現金流,實際稅率顯著降低,企業平均利潤率得到有效提升;第二,減稅降費帶來的是投資環境改善和融資約束減輕[16],企業出于營利目標會擴大再生產規模,帶來的融資需求提升和融資成本下降使得經濟預期轉向樂觀。因此,財政干預可以改善企業經濟預期。
企業現金持有理論認為,企業家經濟預期直接影響企業對現金持有的需求動機。企業家對經濟預期悲觀時,出于預防性動機,企業將增加現金持有,以預防經營的不確定性;企業家經濟預期改善,企業的外部融資約束會預期減輕[16]。而企業現金持有水平存在序列負相關性質的自發調整行為,外部融資成本降低會促使企業減持現金持有,適當增加外部融資規模,表現為企業融資傾向的改變。財政干預政策通過影響企業家對企業經營預期的改善,進而影響企業融資行為的決策改變。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說。
H3:財政干預政策通過改變經濟預期來施加對企業融資傾向的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基于本文研究樣本的數據結構和研究目的,結合本文研究對象融資傾向的多樣性,選擇多元面板logit模型對研究假說和傳導機制進行檢驗。
將融資傾向作為因變量,將財政干預作為自變量,通過多元面板logit模型考察二者間的關系。企業選擇第j種融資模式的概率為
其中,Yi代表第i個企業所選擇的融資模式,i=1,2,3,Xi代表影響企業融資傾向的因素,βj為待估參數。本文將企業融資模式分為4類,即股權融資P(F1)、債務融資P(F2)、混合融資P(F3)和內源融資P(F4),Fj代表每個企業對應的Yi=j時的融資模式。以內源融資模式作為對照組,建立n-1元logit模型。基于上述設定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m表示自變量的個數,Hyi表示企業的異質性變量。本文采用極大似然法對上述多元面板logit模型進行估計,并使用迭代法得到參數估計值,用以考察財政干預政策對于企業融資傾向的影響。
(二)變量設定與數據說明
1.被解釋變量
企業融資方式主要有內部現金、銀行貸款、上市融資、企業債券、信托等,本文將上述融資方式分為股權融資、債權融資、內源融資三種形式。指標的具體度量方式在Hovakimian等[17]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其中,A表示新增總債務與總資產之比,B表示(新增所有者權益-新增留存收益)/總資產
股權融資指標參考Beck等[18]的研究進行重新設計,總資產為企業各項資產項目總額,以國泰安統計數據庫中總資產條目作為標準進行統計。
上述指標定義將每年度每個上市企業的融資方式加以分類,并將其定義為虛擬變量,更直觀地體現企業融資的傾向。[WTBZ]
2.解釋變量
不同于已有研究將一般財政收入和一般財政支出作為指標,本文采用更為微觀的指標。傳統指標存在不精準的問題,而關注財政收入對于微觀企業的干預,需要關注企業稅收優惠的變動趨勢。針對企業的財政支出指標主要以財政補貼與財政定向撥款為主。本文參考柳光強[19]的做法將財政干預指標定義為正向影響指標,計算方法為企業接受的政府補貼與企業資產總額之比。其中,本文對上市企業歷年獲得的稅收優惠、財政貼息、財政撥款等項目進行手工整理加總,作為該企業接受的實際政府補貼水平。
3.控制變量
現金流:企業內部資金是否充沛,決定企業是否需要對外融資以及對外融資的規模大小,本文采用如下方式計算企業現金流。企業現金流=(稅后營業利潤+折舊-資本支出-營運資本增加額)/總資產賬面值。Tobin?Q=(流通股市值+非流通每股凈資產×非流通股股數+負債總額)/總資產賬面值。資產負債率:企業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之比。凈資產收益率:2×凈利潤/(股東權益期末余額+股東權益上年期末余額)。成長性:本年度主營業務收入/上年度主營業務收入-1。上市年限:企業上市年限直接影響其融資決策的路徑變遷,同時金融市場對企業的影響程度也因上市年限不同而有不同。
4.異質性變量
為考察企業異質性對于目標傳導機制的調節作用,本文結合已有研究經驗定義如下變量作為企業異質性特征。
(1)企業所有制虛擬變量:本文以國泰安數據庫為依據,定義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為國有性質,定義民營企業、社會團體、自然人為民營性質。分類后將其定義為二值虛擬變量。其中,將國有企業賦值1,非國有企業賦值2;
(2)企業行業性質虛擬變量:本文將2012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的18個大類、90個小類劃分為金融、公用事業、房地產、綜合、工業、商業等6個主要行業,在剔除綜合企業、金融業與房地產業后保留剩余3個行業,設置為相應的行業虛擬變量。分別將公用事業、綜合、工業、商業等行業賦值1~4;
(3)企業規模虛擬變量:在選取樣本范圍內對每年度所有企業的總資產對數依照大小進行排序,取中位數作為分類節點,將企業定義為大、小規模企業。將小規模企業賦值1,大規模企業賦值2。本文所選樣本均為上市企業,因此并不存在真實經濟環境中的小微企業。
此處分類僅做考察需要,即分析企業規模對于實證回歸結果的扭曲影響。將企業按照規模進行分類后將其定義為二值虛擬變量。
本文設定研究樣本區間為2007—2019年,樣本范圍為在上證和深證上市企業,并做如下處理:(1)剔除在樣本區間內沒有持續經營的上市企業、剔除ST、PT的股票數據,剔除行業性質為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的企業;(2)剔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企業;(3)剔除財務狀況存在空缺值的企業。本文數據均來自上市企業歷年年報、中國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CSMAR)與Wind金融數據庫。實證中將非虛擬變量取對數處理,并將控制變量做滯后1期處理。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財政干預政策對企業融資傾向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2
此處系數表示在財政干預政策的影響下,企業選擇不同融資方式的相對比率,并以自然對數為底的指數值直接表示。。其中,因變量表示在自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影響下,企業分別選擇股權融資、債務融資和混合融資的概率與企業選擇內部融資的概率之比。概率值之比越高,表明企業越傾向于選擇該融資模式。將上述概率比作為因變量與自變量進行分組回歸,當財政激勵政策的回歸系數大于0時,通過exp指數函數轉化后的影響大于1即表明財政激勵政策的推行使得企業更傾向于選擇該融資模式,當三組融資選擇概率值之比與財政激勵政策的回歸系數均大于0時,表明在財政政策的激勵下,企業將外部融資作為比內部融資優先級更高的形式,內部融資不再是企業最青睞的融資形式。同時,還可以根據財政激勵針對不同融資選擇的回歸系數值進行橫向比較,得到企業在財政激勵下最傾向選擇的融資方式。可以發現,各項財政干預系數均為負數,表明財政干預推動了企業更傾向于內源融資。財政干預在緩解企業內部現金流方面有積極的意義,驅使企業減少外部融資、轉向內部融資,同時政府補貼包含的財政撥款、貼息等形式對金融市場釋放了政府政策關注的風向。但是,企業無法僅通過內部資金進行投資,仍需要外部融資進行補充。財政干預推動企業選擇股權融資作為外部融資活動的首選形式,當債務融資的抵稅效應因為財政激勵政策實施帶來企業內部現金流增加而減少時,股權融資的平均成本開始低于債務融資的平均成本,企業在選擇外部融資補充企業現金流時,將首選股權融資模式。對宏觀政策制定者而言,這個結果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在“去杠桿”的大背景下,除了債轉股、建立企業破產制度等主要針對金融企業的政策之外,針對實體經濟融資難問題,[JY]適當增加定向財政補貼、持續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將成為“結構性去杠桿”的一大利器。財政激勵政策的出臺,有效降低了企業的平均稅負,在增加企業現金流的同時,也客觀上對企業債務融資的動力產生消減作用。MM理論指出,企業外部融資結構在債務融資帶來的減稅效益與全部外部融資成本現值之和相等之時達到最優形式。在滿足上述條件后,由于債務融資的減稅效應和股權融資成本上升均邊際遞減,此時企業會增加股權融資的比重進而取代債務融資。財政激勵政策因其對債務融資減稅效應的抵消作用,而將這一臨界值降低,企業股權融資取代債務融資的可能性將提前出現。近年來,財政政策又對企業的股權融資采取了激勵性措施企業進行股權融資的成本包括股息紅利和發行費用等。針對股息紅利,財政部每年出臺多頻次文件公告,如《關于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101號)對投資者取得的股息紅利應繳個稅進行了有條件減免,這促進了企業股權融資成本的客觀降低。而發行費用和股權轉讓費用等成本的降低,主要依靠證監會不斷出臺的費用減免政策。,推動了企業在外部融資模式上向股權融資模式轉變。
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財務結構不同,企業的融資傾向也有相應變動。企業存量現金流越高,越傾向于選擇內源融資。企業上市越早,越傾向于選擇股權融資。企業上市年限越長,財務信息越公開透明,在金融市場上的融資政策越穩定,融資成本相對越低,因此會優先選擇股權融資。資產負債率越高,企業越傾向于選擇債務融資。鑒于本文的樣本中已剔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企業,因此樣本企業在風險可控的環境中更傾向于選擇既有的債務融資模式作為主要融資手段。資產收益率越高,企業越傾向于選擇內源融資,且外部融資首選方式為債務融資。資產收益率越高,說明企業的資產利用效果越好。對于債權方的銀行系統而言,從戰略管理風險角度來說,目標企業的資產收益率越高,越有利于銀行降低對其的貸款門檻,因此企業更傾向于選擇融資約束更低的債務融資模式。Tobin?Q與成長性作為從不同角度反映企業發展預期的指標,二者越高企業越傾向于選擇混合融資模式。這說明企業發展越健康、預期越樂觀,就會越注重在融資領域的政策綜合性,以保障企業投資所必須的資金規模,最大限度規避因過于倚重某一融資模式帶來的潛在資金風險。
(二)異質性分析
通過基礎回歸的分析,本文初步得出財政干預政策與企業融資傾向間的關系。但上述結論對于財政干預的精準化來說沒有太多參考意義。基于此,本文將實體企業樣本按照其異質性進行分類,分別考察不同類型的企業在融資時對財政干預政策的響應模式。
1.企業所有制
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融資傾向受到財政干預政策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3。財政干預推動國有企業傾向選擇股權融資方式,國有企業因為其在市場中的絕對優勢地位,在金融市場上融資約束要低于非國有企業。而非國有企業則與之相反:財政干預推動非國有企業優先選擇債務融資方式作為其外部融資的主要手段。傳統研究認為,非國有企業在信貸市場上存在著所有制上的歧視,是信貸資金發放的弱勢方[20]。本文結論與此相反,主要原因在于,本文的樣本范圍是財務指標正常的大中型上市企業,很多民營企業既是地方政府的穩定稅源,也是金融市場上的“壓艙石”。因此,非國有企業在信貸市場上與國有企業相比并沒有明顯劣勢,加之近年來不斷出臺的民營企業扶持政策,銀行信貸市場對于大中型民營企業的偏重愈發明顯,這類企業的信貸融資約束得到緩解。
2.企業行業性質
不同行業的上市企業融資傾向受財政干預政策影響的回歸結果見表4。在財政干預下,工業企業與商業企業更傾向于選擇股權融資。財政干預越積極,企業對經濟環境改變后的自身經營預期越高,企業會出現越大的資金需求,金融市場也會隨之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公用事業企業與工業企業相類似:財政干預促使該類企業優先選擇股權融資作為外部融資的首選方式。不同的是,股權融資傾向的回歸系數為負,這表示公用事業企業主要以內部現金流作為資金使用來源,其次是股權融資模式。該類企業作為實體經濟企業的主要支柱,無論財政補貼是否到位、稅收負擔是否減輕,銀行信貸對于該類企業都要給予必要的份額支持,因此,財政干預政策施加給此類企業,帶動了金融市場對于實體經濟預期的樂觀情緒,進而降低企業進行股權融資的成本。
3.企業規模
不同規模的上市企業受財政干預政策影響的回歸結果見表5。財政干預政策推動小規模企業傾向于選擇股權融資形式,主要原因在于小規模企業在信貸市場上的弱勢地位。其體量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差,可供質押的資產規模較小,因此債務融資成本相對較高,在財政干預下優先選擇股權融資形式。大規模企業則因其規模優勢,抵押貸款能力較強和主營業務成熟,因此主要選擇債務融資。當前,“去杠桿”的施策目標集中為金融企業,如何在財政政策上避免對實體經濟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造成困難是重要課題。小規模企業加大股權融資規模,既可以保證資產負債率穩步下降,又可以避免加劇“融資難”問題。這就需要財政干預充分配合貨幣政策,加大稅收優惠與財政補貼的同時,減少小規模企業的股權融資約束。
(三)穩健性檢驗
財政干預與企業融資傾向均為本文的重要研究變量,為保證實證設計與回歸的可靠性,本文進行了多種穩健性檢驗,部分結果見表6。
首先,將財政干預指標的度量方式改變為政府補貼與凈利潤之比(Inta)。改變度量方式之后的回歸結果與原結果相比,財政干預政策仍推動上市企業選擇股權融資方式。
其次,將財政激勵政策的指標中政府補貼拆分為財政貼息和撥款與稅收優惠兩類,再分別計算作為財政激勵政策的穩健性檢驗指標(Intb與Intc)。通過對比Intb與Intc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用財政貼息和撥款度量的財政干預政策指標推動企業首先選擇股權融資,而非內部融資;用稅收優惠度量的財政激勵政策指標推動企業首選仍為內部融資,股權融資作為企業的次優選擇。
再次,放松因變量邊界約束。為了保證企業融資傾向的度量方式合理,本文在原指標的度量基礎之上,將指標閾值從5%調整為10%與15%。利用新指標(Fica和Ficb)進行穩健性檢驗的回歸結果見表7。回歸結果與原指標相比個別系數雖然發生了變化,但在多元面板logit模型中,更需關注不同選擇的影響系數值的相對高低。從新指標設定下的系數相對值來看,財政干預政策仍然表現為推動企業選擇股權融資形式。
最后,去除金融危機的影響。為了避免2008年金融危機對本文的結論產生影響,將樣本范圍縮至2011—2019年,回歸結果見表8。與原指標相比,財政干預政策仍然表現為推動企業選擇股權融資形式。
五、影響機制檢驗
為了進一步梳理傳導路徑并檢驗本文的假說H3,基于其中,Ecx表示微觀企業對于實體經濟的預期,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微觀研究中對經濟預期的研究均以與企業財務運營相關的指標來構建企業家對于經濟預期的判斷。徐捷等[22]在問卷調查研究中詢問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在下一年度的變化情況,通過判斷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擴張、收縮或者持平來定義虛擬變量,考察企業對經濟預期的信心。在企業年報中,每年新增固定資產數據是已經剔除固定資產清理之后的數據,因此不能準確反映企業真實新增固定資產的規模。本文選取國泰安數據庫中固定資產凈額與固定資產清理指標數據之和作為原始數據,并通過計算每年各企業的新增固定資產數據的變動情況作為經濟預期的代表變量。該數據可以較好反映企業新增長期持有資產的偏好。為了避免內生性問題,按企業所屬行業進行分類,分別計算歷年各行業的平均新增固定資產規模,將此平均值的增長率作為企業當年對經濟預期的數值。
機制檢驗回歸結果見表9。第(1)組為基礎回歸結果,第(2)組展示了財政干預對經濟預期的影響,結果顯示,財政干預政策對企業的經濟預期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財政干預政策提振了企業對實體經濟的發展預期,促使企業擴大生產。第(3)組檢驗了經濟預期對企業融資傾向的影響,可以發現,企業經濟預期與三種外部融資傾向進行回歸的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表明經濟預期的提高帶動了企業擴大經營的動機,發展所需資金規模增大,進而推動企業采用更多的外部融資彌補資金缺口。對比第(1)組與第(3)組中財政干預政策系數的符號方向與不同融資傾向的系數相對大小可以發現并沒有變化,因此這一機制檢驗的結果是可靠的。
六、進一步分析:金融化帶來的沖擊
十九大報告指出,金融領域要做到“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能力”。這一要求的深層次原因就在于企業從金融領域獲得的投資回報已超過實業投資獲得的回報。當實體經濟不景氣時,企業從銀行系統受到嚴格的融資約束,為此企業被迫尋求金融市場及影子銀行進行融資。金融化問題作為經濟社會的鮮明特征,其營造出的政策實施環境對于財政干預政策本身的影響仍不容忽視。金融發展程度越高,財政干預的政策環境也越復雜,從企業的角度來說不僅是發展機會,也是潛在的金融沖擊。為了厘清市場金融化環境對于財政干預政策效果的影響,本文建立以下模型做進一步的檢驗:
其中,Frit表示環境調節變量,即市場金融化程度指標。對市場金融化程度的刻畫,[WTBZ]Cournede等[1]定義、眾多學者發展了三種指標,分別是金融業增加值/GDP、銀行貸款總額/GDP、股票市場總值/GDP等。其中,金融業增加值/GDP主要衡量金融業企業,銀行貸款總額/GDP主要衡量企業貸款渠道的金融化程度。結合本文的研究需要,股票市場總值/GDP能夠較好地刻畫金融市場在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和實體企業對于金融市場的依賴程度。據此,本文將市場金融化率計算為股票總市值與當年GDP之比,并以每年金融化率的中位數作為分界點將其設定為虛擬變量。
市場金融化率檢驗的回歸結果見表10。對比交互項系數可以發現,財政干預對于企業融資傾向的影響因市場金融化環境的加入而發生變化,財政干預下企業以內源融資為主、以股權融資為輔的原有融資傾向因金融化率的外部環境存在而改變。市場金融化加入分析后,財政干預推動企業選擇股權融資為主,在基礎分析中企業將股權融資作為外部融資的首選項,市場金融化率加強了這一效應,推動企業將股權融資作為主要融資形式。交乘項系數值同樣顯示,市場金融化率提高,財政干預政策推動企業選擇融資方式的優先順序仍然以股權融資為首。這表明市場金融化程度提高,企業內部現金流已無法滿足企業主要投資需求,因此需增加外部融資比例以保障企業正常發展。財政干預對于企業最大的意義正是通過財政補貼的形式為企業進行“隱形擔保”。
七、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通過構建財政干預政策與企業融資傾向的指標,利用多元面板logit模型進行實證發現:財政干預政策鼓勵企業采取內部融資方式,在財政干預下,國有企業傾向于選擇股權融資,非國有企業傾向于選擇債務融資;工業企業與綜合企業傾向于選擇股權融資,商業企業傾向于選擇債務融資,公用事業企業則傾向于選擇內源融資形式;小規模企業傾向于選擇股權融資,大規模企業傾向于選擇債務融資。企業的異質性不同,其在財政干預政策下做出的融資方式選擇也各不相同。
進一步地,本文以企業對實體經濟的預期作為中介變量進行機制檢驗發現,財政干預政策顯著提升了企業對經濟預期的樂觀程度,這一經濟預期也帶動了企業對外部融資的正向需求。以市場金融化程度作為外部政策環境的沖擊,檢驗結果發現,市場金融化程度的提高推動企業從優先選擇內源融資轉變為以股權融資形式為主、以債務融資為輔的融資模式。這一檢驗結果說明,在金融化程度提高的大環境下,財政干預政策效果也出現了改變。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新常態下財政政策的轉型和精準化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首先,各級政府在針對不同微觀主體實施財政干預時,要切實注意企業的異質性,保證不同企業能以相對較低的外部融資方式獲取企業發展所必需的資金。對于具有體制、行業以及體量等優勢的企業,要適度控制財政補貼數量,鼓勵企業深入進行股份制改革,通過股權形式發動民間資本力量參與企業資金支持中。對于其他在外部融資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的企業,財政干預要以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形式將該類企業引導為政府政策重點扶持的地位,改變信貸市場對于這些企業的輕視現狀。其次,財政干預還應配合貨幣政策工具,建設金融市場秩序,保證實體企業在金融市場上可以獲取必要的發展資金,以此控制企業金融化程度在合理區間,保證實體經濟高速有序發展。最后,作為微觀企業,要充分利用政企間的信息優勢,發展企業自身特點,適應政策變化,爭取更多的財政補貼與稅收優惠,增加企業內部現金流,全面減緩融資約束。
參考文獻:
[1]?[ZK(#]COURNEDE?B,DENK?O.Finance?and?economic?growth?in?OECD?and?G20?Countries?[M].Paris: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2015:1112.
[2]?CHRISTIANO?L,MOTTO?R,ROSTAGNO?M.Financial?factors?in?economic?fluctuations?[R].Society?for?Economic?Dynamics?Working?Paper,2010:171.
[3]?FAZZARI?S,HUBBARD?R,PETERSEN?B.Investment,financing?decisions,and?tax?policy?[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8,78(2):200205.
[4]?MYERS?S,MAJLUF?N.Corporate?financing?decisions?when?firms?have?information?investors?do?not?have?[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84,13(2):187221.
[5]?VISWANATH?P.Strategic?considerations,the?pecking?order?hypothesis,and?market?reactions?to?equity?financing?[J].The?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1993,28(2):213234.
[6]?蘇冬蔚,曾海艦.宏觀經濟因素、企業家信心與公司融資選擇?[J].金融研究,2011(4):129142.
[7]?DEANGELO?H,MASULIS?R.Optimal?capital?structure?under?corporate?and?personal?taxation?[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80,8(1):329.
[8]?劉行,趙健宇,葉康濤.企業避稅、債務融資與債務融資來源:基于所得稅征管體制改革的斷點回歸分析?[J].管理世界,2017(10):113129.
[9]?于文超,殷華,梁平漢.稅收征管、財政壓力與企業融資約束?[J].中國工業經濟,2018(1):100118.
[10]孫雪嬌,翟淑萍,于蘇.柔性稅收征管能否緩解企業融資約束:來自納稅信用評級披露自然實驗的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9(3):8199.
[11]童錦治,黃克瓏,林迪珊.企業避稅、融資成本與資金配置效率:基于我國上市公司數據的檢驗?[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5(6):7481.
[12]THORSTEN?B,KLAPPER?L,MENDOZA?J.The?typology?of?partial?credit?guarantee?funds?around?the?world?[J].Journal?of?Financial?Stability,2010,6(1):1025.
[13]魏志華,趙悅如,吳育輝.財政補貼:“餡餅”還是“陷阱”??[J].財政研究,2015(12):1829.
[14]MODIGLIANI?F,MILLER?M.The?cost?of?capital,corporation?finance?and?the?theory?of?investment?[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58,48(3):261297.
[15]李建軍,張書瑤.稅收負擔、財政補貼與企業杠桿率?[J].財政研究,2018(5):88100.
[16]張西征.企業家經濟預期、融資約束與預防性現金管理?[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4(12):3346.
[17]HOVAKIMIAN?A,OPLER?T.The?debtequity?choice?[J].Journal?of?Financial?&?Quantitative?Analysis,2001,36(1):124.
[18]BECK?T,DEMIRGUCKUNT?A,LEVINE?R.Bank?supervision?and?corporate?finance?[M].Paris: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2003.
[19]柳光強.稅收優惠、財政補貼政策的激勵效應分析: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視角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6(10):6271.
[20]喻坤,李治國,張曉蓉,等.企業投資效率之謎:融資約束假說與貨幣政策沖擊?[J].經濟研究,2014(5):106120.
[21]溫忠麟,侯杰泰,張雷.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的比較和應用?[J].心理學報,2005(2):268274.
[22]徐捷,袁銘,郭紅.企業預期形成與預期偏誤:基于企業層面調查數據的經驗研究?[J].金融研究,2016(1):116129.
編輯: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