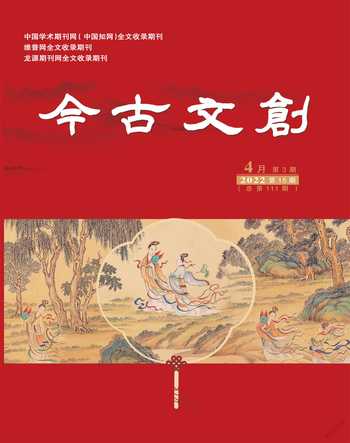《環形廢墟》引起讀者“震撼” 的技巧探究
【摘要】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作為幻想文學大師,其大多數重要作品的基礎是幻想,他的幻想作品中既體現了他的現實觀,也體現了他的幻想觀,其中“夢”與“時間”是作為他實現幻想的重要方式。在《環形廢墟》這一篇純屬虛構的哲學性短篇小說中,讀者接受反應批判下,本文擬從域限幻想小說中讀者的期待與感知的重建以及博爾赫斯的現實觀與幻想觀來探究博爾赫斯是如何利用現實與虛幻、夢與時間的哲學思想來引起讀者“震感”的寫作技巧,這有助于讀者了解博爾赫斯哲學作品中傳達出來的讀者對內在的意識與激勵的目標。
【關鍵詞】博爾赫斯;幻想與現實;域限幻想小說;夢;時間
【中圖分類號】I783?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2)15-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15.003
《環形廢墟》是博爾赫斯第二部小說集《虛構集》里的一篇,全篇純屬虛構,篇幅短小,卻傳達出博爾赫斯的“時間虛無”“自我虛幻”的哲學思想。
小說講述了一位魔法師來到一個環形廢墟,他在夢中造創造了一個虛構的少年并把少年當成兒子,他們朝夕相處,魔法師與他過著幸福的日子,他使那個少年逐漸熟悉現實。為了讓少年不察覺自己是虛幻的人,他想起世間只有“火”知道他的兒子是幻影,于是他決定朝著大火走去。然而當他走進大火時卻毫無知覺,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也是別人夢中的幻影。
國內學者對于《環形廢墟》的研究主要是從各個角度,如時間、空間上解讀博爾赫斯的虛無與荒誕觀。國外學者主要探尋其中的宗教、哲學和科學觀。
該短篇小說是典型的域限幻想小說,作者如何利用有限的篇幅精確傳達出自己的虛無和荒誕觀,利用讀者接受反應的能力,從而使讀者分不清是幻想還是現實,使讀者的感覺刺激量達到一定強度而引起“震撼”的手法值得探究。
一、期待與感知的重建
(一)讀者的期待視野的重建
幻想小說的分類標準非常多,根據題材可分為科幻小說、魔幻現實主義小說、漫畫幻想、童話等。想象是從形象到形象的過度,而幻想是把激情的情感轉化為直覺[1]。法拉·門德爾森從幻想和敘事的關系將幻想小說分為四類,即入口—探索幻想小說、擬真幻想小說、入侵幻想小說、預先幻想小說。在門德爾森的分類中,域限幻想小說達到的要求是最高的,是人們能對幻想事物預期理解與顛覆,與讀者接受反應的過程與程度相關,所以本文擬從門德爾森德分類出發,探究域限幻想小說對于讀者反映的技巧。
《環形廢墟》是典型的域限幻想小說(liminal fantasy),域限(Liminality)一詞源于拉丁文“limen”,指“有間隙性的或模棱兩可的狀態”。作為心理學名詞,指外界引起有機體感覺的最小刺激量。這個定義揭示了人感覺系統的一種特性,那就是只有刺激達到一定量的時候才會引起感覺[1]。在《環形廢墟》一開篇以《鏡中奇遇》中的“假如他再夢不到你”作為小說的題記,作者將讀者帶入一個似真似幻、帶有夢的色彩的場所——被焚毀的廟宇,魔法師便開始在這個廟宇中授課,撰夢造人。在這個特定的場所中,外界對于讀者的刺激并沒有起到作用,反而將讀者拉進一個局限的“廢墟”,而這個“廢墟”是宇宙的一個小小的角落。“環形廢墟”的標題讓讀者在進入接受過程之前,根據自身的閱讀經驗和審美趣味等,在進入閱讀前形成一定的思維定式,對于《環形廢墟》中接受客體有了預先估計與期盼——魔法師就是真實存在的那個造夢的人。這種期望在一定程度上使讀者對文章中“魔法師與夢”這兩種意象形成了在自己經驗上的規范化。此時的讀者的感覺并沒有達到任何刺激性。
進入閱讀時,讀者發現,文中魔法師的生活與我們無異,但他的特殊之處在于他的任務是“他要夢見一個人:要毫發不爽地夢見那個人,使之成為現實”。幻想事物進入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種域限幻想的敘述模式,但對主人公而言,這不能看作是入侵,而是被看作正常現象[1]。對于魔法師而言,使夢中的人成為現實并不是什么異想天開的事,也不會令人吃驚。但是對于讀者來說,讀者在閱讀時,本能地將魔法師預想成具有超能力的人,而隨著閱讀中魔法師的生活化,現實性形象占據主要地位,讀者將文本中主體的心理場帶入自己的心理場進行驗證,漸漸感到疏離和不安。此時的讀者不得不重構自己的期待視野使之與文本相適應。當讀者在這種修正、打破、重建、再修正、再打破、再重建的動態過程時,博爾赫斯將筆鋒一轉,借魔法師之口告訴大家,其實魔法師自己也是別人的夢中幻影。此時讀者的情感有個一定程度的積累,便感到奇妙,震驚與出乎意料。同時給讀者留下“空白”,并沒有繼續描寫魔法師進入火后的情況以及少年的情況,激發讀者的想象力,從而主動參與文本的建構,使哲學意義更加深刻。
同時域限幻想小說運用反諷、習以為常的語調,與其他大多數幻想小說的一本正經的模仿幻想世界相反。譬如在小說開篇作者并沒有花筆墨來介紹魔法師來到這座環形廢墟的魔幻過程,而是直接描寫魔法師來到這座環形廢墟時的狀態,平鋪直敘,就如一個普通人帶著遍體鱗傷的身體來到一個陌生地方,迷茫且無助。在平鋪直敘中暗示魔法師對這座廢墟有一定記憶,將讀者固定在一個空間的同時又引起讀者不安。幻想引發讀者的緊張與不安,這種感覺是域限幻想小說的核心[2]。開篇將幻想事物帶入現實加之平鋪直敘,讀者沒有感受到推理的跌宕起伏感,所以會發生對主人公的積極的“移情”,讀者在知覺中把自己的人格和感情投射到(或轉移到)對象中,與對象融為一體,結尾的筆鋒斗轉的手法頓時打破讀者閱讀初期的期待視野和共情感,刺激量頓時達到讀者的感受強度,在結尾造成“震撼”,引發讀者深思,傳達出作者內在的意識與對讀者的激勵,人生仿佛一個環形廢墟,人不在夢中生死夢中。
(二)讀者的感知與思維的重建
人類感知主體其本質與感覺主體相同,根本區別在于,人類感知主體是自己能意識到的。人類具有“思維”能力,具有利用抽象符號把握無形或內在事物的能力,是一種自我意識的體現,思維反映事物共同的、本質的屬性和內部規律性。在《環形廢墟》中作者利用讀者作為感知主體性,引導讀者去感受與反思文章中的魔法師作為感知主體與自我的關系——魔法師做夢成為少年的感知,少年做夢成為魔法師的感知,二者是否是自我與本我的關系。 在《杜撰集》的《博聞強記的富內斯》中,博爾赫斯強調“思維是忘卻差異,是歸納,是抽象化”。對比《環形廢墟》中的魔法師和少年,在讀者閱讀過程中感知到的是二者作為夢與被夢的關系,是現實與非現實的對立。當少年出現后,讀者對于魔法師和少年人物形象的感知力開始抽象。感知主體本質是“自覺”,讀者一直在作者的引導下利用時間、空間的概念來感知魔法師的“自我”狀態。在魔法師撰夢造出少年前,讀者可以明顯感知到魔法師人物形象是一個被上帝賜予特殊力量的“人”,但魔法師造出少年后,少年與魔法師的關系變得微妙,二者的關系不似做夢與被夢的關系,反而像一對生活在現實中的人。此時讀者對于二者關系的感知趨于抽象,魔法師使“少年逐漸熟悉現實”,少年就是他的兒子,二者的形象逐漸在讀者腦中變得抽象,分不清二者到底是誰的現實。黑格爾認為人的意識與自然世界的事物包括人的身體是彼此外在的,各自有著截然不同的本質和作為,由此二者通過感覺和知覺達到的統一也只能是一種外在的統一。[3]他將這種思維方式描述為“自然意識”。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自然意識”來自博爾赫斯在時間和空間上、現實與虛幻上營造出來的對魔法師與少年“自我”的意識的模糊,此刻讀者的思維方式還處于自然狀態。
文章最后作者揭示了魔法師也是“另一個人夢中的幻影”,“自然意識”上升到哲學意識。人們開始警惕地對熟知的東西的態度,如主體和客體、上帝和自然、知性和感性等。[3]從“自然意識”到“哲學意識”這一思維方式的轉變,要求讀者放棄經驗論而不是對“無限”與“循環”意識的追求。而作者在《環形廢墟》的哲學主題便是傳達出自我虛幻本質,在結尾讀者的思維方式的陡然轉變也是引起震撼的一大因素。
二、臨界點模糊讀者心理效應
(一)“夢”與“現實”的臨界點
博爾赫斯在其許多幻想作品中總是在現實與非現實的二元對立中尋求突破,他開頭總是佯裝正在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時間、地點、人物都十分明確,頗具現實主義風格,但是他又將非現實因素插入其中,如從方位、光線、氣味、聲音、視覺等多方面展現細節的真實,又將“夢”“時間”等虛幻性插入現實,使現實與非現實水乳交融,真偽難辨[4]。在《環形廢墟》中,現實與幻想的界限在“夢”和“時間”的延伸中變得模糊。法拉·門德爾森也說域限幻想小說高度依敘述技巧[5]。《環形廢墟》中,故事由現實的層面進入非現實的層面這個過程博爾赫斯采取的是否是通過“夢”來轉換?在文中雖然在開始便交代了魔法師有一個將夢變為現實的任務,看上去是引導讀者,這是由現實變為非現實的“臨界點”的轉換,實際上讀者已經掉進了博爾赫斯設的圈套,作者加入“夢”這一特征以后,讀者自然而然認為魔法師所做的夢便是該篇小說中的“虛幻”。《環形廢墟》并沒有真正的“臨界點”,而是作者在描寫真實的事物的同時,加入大量的暗示性語言,在讀者產生強烈的真實感后提醒讀者這一切有可能只是幻覺。這類句子在小說中比比皆是,常常出現在對人物、環境的描寫過程中,它們使真實的事件、情境顯得模棱兩可,時刻引起讀者警覺。如,“在那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誰也沒有看到他上岸,誰也沒有看到那條竹扎的小劃子沉入神圣的沼澤。”“一天,那人仿佛從黏糊糊的沙漠里醒來,發現朦朧的暮色突然和晨曦沒有什么區別,他明白自己不在做夢。”“那天下午,他夢見了塑像,夢見它有了生氣,在顫動。”如這類句子有以下幾點特征:第一,這些句子是充滿詩意的,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含混和模糊。肖徐彧[1]說過博爾赫斯的“夢”是一種具有高度美學形式的夢,是一種探索某種哲學思想的文學可能性的夢;第二,“做夢”與“未做夢”穿插敘述使事物模糊對應的關系變得似是而非;第三,似乎、仿佛等表示不確定性的副詞的大量使用,也增加了意義的模糊性。由于無法確定小說中真實與虛構的因素,讀者在閱讀時往往會產生猶豫和遲疑的閱讀感受。
(二)“空間”與“時間”的模糊性
博爾赫斯經常在小說中討論時間、空間、存在、自我等形而上學的哲學問題,他的小說被稱為“形而上學小說”,這篇文章依舊貫穿著他的這些小說主題。在《環形廢墟》中所營造的虛幻感并不僅僅依靠人的空間感,同時依靠人的時間感。開篇營造的環形廢墟宇宙空間感,萬物的生長、發展和滅亡過程構成了宇宙的全貌,人們在空間上感受宇宙虛幻。但是在《環形廢墟》里,博爾赫斯通過“分有”形成層次,宇宙是魔法師是少年的“上帝”,少年是魔法師分有出的下層[6]。由此向上向下延伸,魔法師的上層是魔法師的“上帝”,少年的下層是少年的幻影。宇宙萬物都處于變化之中,時間看似在文章中在流逝,但實際在循環發展。由于魔法師本身自帶虛幻色彩,博爾赫斯反其道而行之,僅把他當成一個“帶有特殊技能的人”來營造其形象,可以看到在魔法師的生活中,他的生活同常人無異,他的日常就如現實中學生與老師之間的關系——老師授課,學生聽課并考試,同時寫出了學生因擔心考試而“專心致志”的狀態。博爾赫斯將讀者拉入日常生活狀態,讓讀者忽視了魔法師這一本身自帶的虛幻性,從而忽視了作者會在時間上做文章。雖然從表面看,時間似乎在不斷向前推移或變化魔法師每天都按時開始在夢中完成他的任務,但是漸漸的魔法師做夢的時間和次數漸漸變得沒有規律,“現在下午也用來做夢了,除了一天清醒一兩個小時以外,他整天睡覺”此時的時間感開始變得模糊,而就在這個階段,他夢見了那個少年,夢見了那個他想讓他變成現實的少年,此時的讀者似乎感覺到了時間在發生變化,但是并沒有刺激到他們的感覺。對于讀者而言,閱讀時從整個空間感而言是虛幻,但從時間上看讀者仿佛置身于現實,當讀者在結尾發現其實是“夢中夢”時,感覺達到一定刺激強度,讀者的內心便大受震撼,縱使把注意力移至身外,伸展到宇宙盡頭,也超不出感知范圍之外,想象出一種感知不到的存在。博爾赫斯帶動讀者的時間感來增強虛幻性,揭示其哲學主題——萬物從開始,經歷各個階段后有返回到虛無,萬物的歷程皆是循環。
三、總結
“夢”帶有神秘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色彩,博爾赫斯利用域限幻想小說的特點在開篇召喚出讀者的期待視野,在敘述過程中模糊現實與非現實的界限,打破現實像非現實轉換的臨界點,在結尾筆鋒一轉,戛然而止,巧妙地將個人的虛幻與“無限”的主題結合起來,因為夢到魔法師的人也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夢,少年長大后也會撰夢造人,無限循環下去,以此將讀者的“自然意思”轉向“哲學意識”。博爾赫斯利用讀者對于文本在閱讀前,閱讀中,閱讀后期待視野的建構、打破重組、再建構等循環過程,刺激讀者的感受,加上文章客體的虛幻性,使讀者對文本的反應接受能力逐漸加強同時使刺激量達到一定程度,達到作者想要的閱讀效果。循環時間與夢包含著博爾赫斯的哲學主題,引起讀者震撼的同時讓讀者聯系到自我,形而上學的思想——自我虛幻的本質得以升華。
參考文獻:
[1]肖徐彧.博爾赫斯與中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22,26,65.
[2]張漢行.博爾赫斯與中國[J].外國文學評論,1999,(04):46-52.
[3]唐清濤.思維、感知與世界[J].江漢論壇,2006,(02):89-92.
[4]張學軍.博爾赫斯與中國當代先鋒寫作[J].文學評論,2004,(6):146-152.
[5]M Farah.Rhetorics of Fantasy[M].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08.
[6]陳玉清.虛無與死亡:解讀《環形廢墟》[J].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09,19(4):64-66.
作者簡介:
杜海蘭,女,漢族,四川遂寧人,西南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