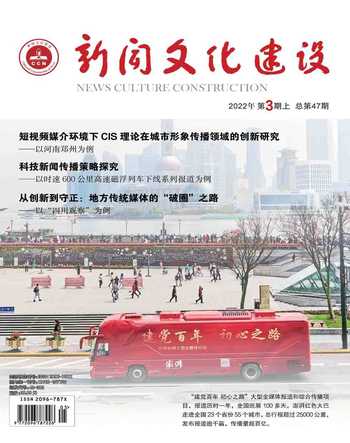跨學科視野下的社會工作在新媒體平臺中的運用
沈孟帆
摘要:在新媒體平臺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中,社會工作的形式也有了更多的轉變和豐富。如何融合社會工作與新媒體,在扶貧、慈善、消除數字鴻溝等方面加以運用,是亟待突破的新議題,倫理、收益透明度、信息真實性等問題亦是運用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痛點。
關鍵詞:新媒體;社會工作;弱勢群體;美好生活
當今社會正處于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引領之下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新媒體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指出,伴隨著5G商業化時代的開啟新媒體發展迎來了技術與內容的雙維爆發式發展,成為社會治理智能化和專業化的重要幫手,保持著生機勃勃的行業活力。智能化通信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世界無時不刻不在進行著信息的交流、碰撞、共享,為人們的美好生活帶來了無限的可能。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11億,我國網絡視頻(含短視頻)用戶規模達9.44億,較2020年12月增長1707萬,占網民整體的93.4%;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達8.88億,較2020年12月增長1440萬,占網民整體的87.8%。新媒體和我們的生活已經密不可分。
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指出:“信息技術的發展將變革人類的學習方式、工作方式、娛樂方式,一句話,人們的生存方式。”而在各個產業中,如何謀求發展,亦是如何跟上時代,將它們的未來和數字化對接。社會工作亦是如此。
在信息飽和的今天,弱勢群體如老年群體、貧困人口如何運用智能化的新媒體傳播滿足精神需求、實現自我人生價值,展現個人風采?如何運用新媒體技術更好地助推社會工作的運行?社會工作應如何對待社交媒體帶來的新機會?社會的發展迎來的是機遇更是挑戰。
一、新媒體與社會工作
新媒體是相較于傳統媒體而言的一個相對概念,“新”可以從支持技術、視覺表現和創作思維層面來理解[1]。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熊澄宇教授認為,新媒體是“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基礎之上出現和影響的媒體形態”。它不再局限于傳統媒體,我們通常將互聯網和移動網絡劃歸到新媒體的范疇[2],它是利用數字技術,通過計算機網絡、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服務的傳播形態。
而社會工作則是指秉持利他主義價值觀,運用科學的專業的方法,幫助弱勢群體解決其生活困境問題,協助個人融入其社會環境的職業活動。它幫助社會上的貧困者、老弱者、身心殘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預防和解決部分經濟困難或因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會問題。而脆弱群體恰恰是社會上心理承受力較弱的群體,是社會結構的薄弱帶,社會矛盾將首先從這一最脆弱的群體身上爆發。因而,社會工作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職業化的幫助脆弱群體的活動。這幾年,在國家層面的不斷扶持下,大量社會工作機構不斷涌現,社會工作正朝著多元化、專業化的趨勢不斷蓬勃發展。但與此同時,國家、社會、人民對于社會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需求、期望。新媒體有傳播速度快、傳播成本低、互動性強、信息展現形式豐富等種種優點。因此,利用新媒體技術開展社會工作是大勢所趨。
二、社會工作在新媒體平臺中的運用
(一)“扶貧+新媒體”
“精準扶貧”是對傳統扶貧觀念的創新,而“扶貧+新媒體”不僅是一項對于傳統扶貧的創新,亦能助力精準扶貧。而媒體思維要緊跟國家政策、主流思想。
近年來,個人微紀錄片和短視頻等媒介的傳播已在扶貧領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它結合了國家的扶貧政策和新興的網絡信息技術,幫助貧困地區的產品、群眾走入大眾視野。一部分社會工作者和鄉村工作者甚至是一些網紅明星,利用新媒體平臺吸引流量,通過農產品銷售、旅游業推廣等助力脫貧。
目前“扶貧+新媒體”從主體出發可以概括為三個類型:一是來自貧困地區的自媒體工作者,自發性地分享個人生活、家鄉美景、農產品,從而幫助村民脫貧。這樣的扶貧下沉到底層,信息傳遞更為個性化,但通常無組織,扶貧效率低;二是當地政府、媒體邀請網紅、明星主動性地為當地宣傳。這種宣傳扶貧效率高、扶貧力度大。對于公眾的影響更為深遠,但是成本高、具有一定的時效性;三是在外務工人員,通過短視頻看到家鄉發展后自發性返鄉建設,同時也促進了扶貧工作的進一步推行。這樣的融合和治標不治本的物質補貼不同,它讓貧困地區的人民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財富,是更為徹底的社會服務工作。讓粉絲變顧客,拓寬銷售渠道、提供新的銷售渠道,增加就業機會、宣傳文化,促進文旅發展、走向美好生活。
社會工作者在利用新媒體扶貧時必須緊跟國家戰略政策,“以人為本”“為民服務”。利用新媒體手段搭建農業、產業、旅游業、服務業等平臺,讓貧困地區“走出去”,大眾視野“走進來”打破信息“剪刀差”。信息匱乏是貧困的一大表現,也是導致貧困的一大重要原因,所以“扶貧+新媒體”需暢通信息交流渠道,打破信息“剪刀差”,讓貧困地區也成為新媒體的重要發展和覆蓋的區域,實時與外界交互。
扶貧先扶智,社會工作者們還可以利用新媒體,幫助貧困地區的孩子們接受更優質的教育。如定期開授網課、線上答疑等。
(二)“慈善+新媒體”
與傳統慈善以政府、國家為主體不同,新媒體慈善的主體下沉到廣大老百姓中,讓其更有發聲權、參與感。在傳播方式上,傳統慈善更多的在報紙、雜志、電視上進行宣傳,宣傳成本高且見效慢。而新媒體更多的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上發布,宣傳成本低、見效快。在社會監督方面,傳統媒體慈善互動性差,行業不透明,主要依靠公眾對慈善機構的信任進行,以記者、社會工作者自身監督為主。而新媒體慈善互動性強,在工作過程中雙向回饋明顯,更為透明。主要以廣大的網民、媒體、平臺監督為主。“新媒體+慈善”的優勢不言而喻。
因此,對于一些無法進行勞動罹患病癥的特殊群體,利用好新媒體能起到重大的作用。不同于公益視頻,慈善在短視頻領域已經有了廣泛的應用,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對弱勢群體進行拍攝、記錄,希望通過大眾的關注,給被記錄者提供幫助,利用大眾的同理心,為他們提供物質、精神層面的救助、幫扶。新媒體通過延伸受眾的視覺、聽覺,多方面的展現形式,使受眾感同身受,展現弱勢群體生活的艱辛。利用大眾的同理心,為他們提供物質、精神層面的救助、幫扶,也能夠反映一些社會痛點、社會議題。
“慈善+新媒體”可以分為兩個類型,即瀏覽幫扶和持續幫扶。前者是拍攝者進行的一次性的拍攝過程,反饋活動較少。但設計幫扶對象多,具有代表性,以引發公眾關注為主;后者是拍攝者會持續跟蹤拍攝弱勢群體的生活,反饋活動較多。主要側重于幫扶被拍攝的主人公,多為了解被幫扶對象的鄰居、社會愛心人士等拍攝。從主體分類,可以將其分為“個體新媒體慈善”“組織新媒體慈善”“平臺新媒體慈善”“國家新媒體慈善”等。現如今,這種“慈善+新媒體”的傳播方式,已經使慈善活動很好地得到了推廣,愛心人士越來越多,讓弱勢群體獲得了幫助、尊嚴,也收獲了更多陽光。
(三)“老年群體+新媒體”
傳播學中的“數字鴻溝”,是指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中,不同國家、地區、行業、企業、社區之間,由于對信息、網絡技術的擁有程度、應用程度以及創新能力的差別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貧富進一步兩極分化的趨勢。“數字鴻溝”的本質就是以國際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在普及和應用方面的不平衡現象,這種不平衡不僅體現在不同地理區域、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同時也體現在一個國家內部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之間[3]。2020年11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在新時代數字媒體高速發展的進程中,老年人似乎是被時代遺忘的群體。而在如今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的背景下,保留傳統服務方式是一種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但更重要的是要幫助他們跟上時代跨越數字鴻溝,切實幫助老年人對于新媒體新技術的使用。
美國學者普林斯基依據人們的數字化生存模式劃分出兩類人——數字原住民和數字移民,前者是引領新媒體浪潮的年輕人,后者是亦步亦趨適應新媒體浪潮的中年人。這一劃分標準忽視了另一個被邊緣化的重要群體——老年數字弱勢群體[4]。在與老年群體的接觸過程中不難發現,其自我價值的追求可能比年輕人更為強烈。在網絡中,我們看到“阿木爺爺”“盧正義的雕刻時光”“敏慈不老”等老年人活躍在社交媒體中,他們自信地展現自我,傳授自己豐厚的人生經驗。但也不得不承認,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老年人是不太會使用電子產品、無法從中滿足精神需求,如老人無健康碼乘地鐵受阻、94歲老人被兒子抱起艱難“刷臉”、老奶奶冒雨交醫保被告知不收現金等新聞。新媒體具有兩面性,因而留給社會工作者、留給社會的難題就是怎樣更好地運用它,我們不希望看到老年群體被淘汰、代際差異拉大、“數字鴻溝”加深。我們希望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老年群體活躍在新媒體中、享受新媒體的紅利,融入新媒體社會,擁抱美好生活。
社會工作在新媒體中還可以有哪些方面的運用?“醫療+新媒體”“青少年+新媒體”“農民工+新媒體”等,都是社會工作與新媒體的融合。新媒體作為全新的傳播媒介在信息的傳播方式和傳播速度上有著傳統媒體無法相比的優勢。
三、社會工作在新媒體平臺中的運用可能出現的問題
(一)倫理問題
這是社會工作不論在哪個領域都會出現的問題,而在媒體平臺中更是如此。在進行倫理選擇時第一是生存需要,第二是能力需要,第三是尊重需要。但是每個人都存在三觀差異,對美好生活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期許。幫扶過程中與幫扶對象之間的差異、傳播者和受眾之間的差異、受眾個體之間的差異……因而在“新媒體+社會工作”中,產生倫理問題是不可避免的。
在利用新媒體平臺傳播的過程中,要注意對特殊群體如殘障人士、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的隱私保護,未經允許需要打碼、匿名化。但在生活中,還是會看到一些新媒體工作者將受助者甚至家庭地址等信息暴露,給受助者帶來很大困擾。
(二)收益透明度問題
收益透明度一直是社會工作中人們十分關注的問題。雖然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更為透明雙向,但新媒體平臺畢竟也不是面對面交流,難免會讓一些心懷不軌之人有可乘之機。公信力的構建過程中打著扶貧名號銷售不合格商品、打著做慈善的名號吸引流量變現、濫用慈善款等行為都會讓公眾喪失信任。這就需要在進行社會工作時做到收益透明化。這不僅需要社會工作者的自我監督,更需要新媒體發布者與公眾密切聯系,獲取反饋、落實收益并及時公布。
(三)信息真實性問題
隨著技術賦權,有些微信公眾號、視頻號將真實性拋于腦后,不惜通過策劃擺拍的方式營造戲劇效果以增強視覺沖擊力,以此欺騙受眾感情非法獲取受眾的熱心捐助,善款變成贓款。另外,慈善機構公信力不足、慈善活動缺乏戰略規劃、慈善資源動員不足以及對市場機制的不熟悉,構成了慈善事業發展的內在缺陷[5]。作為社會工作者要秉持公序良俗,客觀地傳遞信息,不夸張、不虛假宣傳。政府等監管部門也應加強對這類信息的篩選核實,增強社會公信力。作為受眾,要擦亮雙眼,獻愛心做好事固然沒錯,但要小心莫將善意付諸東流。
(四)新媒體的運用局限問題
在創新社會治理的背景下,我國社會工作正在不斷地向前發展,但在新媒體的融合上有所不足。
第一,多數社會工作者缺乏創新精神,運用新媒體意識薄弱。社會工作者多將重心放在進行務實的社會工作之中,而忽視了利用新媒體進行傳播的重要性。因此,新媒體的優勢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第二,在社會工作中投入新的媒體宣傳的人力、物力不足。在新媒體這樣一個需要快速高效獲得用戶反饋、發送及時消息、聽取用戶意見的雙向性的傳播模式中,需要專人負責運營。但是社工機構往往沒有設置專門的部門進行管理,從而造成發布消息不及時、反饋不到位、溝通交流效率低等問題;第三,對新媒體的功能使用不足。新媒體的眾多功能沒能充被分利用。
四、結語
當前,新媒體以不可阻擋的勢頭滲透到各行各業中,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推動著社會更快速地發展。社會工作與新媒體融合是大勢所趨,也是當前研究的熱點。社會工作者應轉變和豐富社會工作的形式,更好地利用新媒體這一平臺扎根基層、服務群眾,真誠地幫助弱勢群體走向美好生活。
參考文獻:
[1] 范玉潔,陳艷梅.新媒體時代設計藝術與文化研究[M].西安: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19:1.
[2] 陸地,高菲.新媒體的強制性傳播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胡鞍鋼,周紹杰.新的全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數字鴻溝”[J].中國社會科學,2002(3):34-48+205.
[4] 王萍,王斌.新媒體使用與積極老齡化:對老年人生活質量改善的分析[C]//第六屆亞太地區媒體與科技和社會發展研討會論文集,2008:98-102.
[5] 果佳,闞萍,馬夢溪.從“格桑花”危機透視中國網絡慈善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問題[J].中國行政管理,2012(11):6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