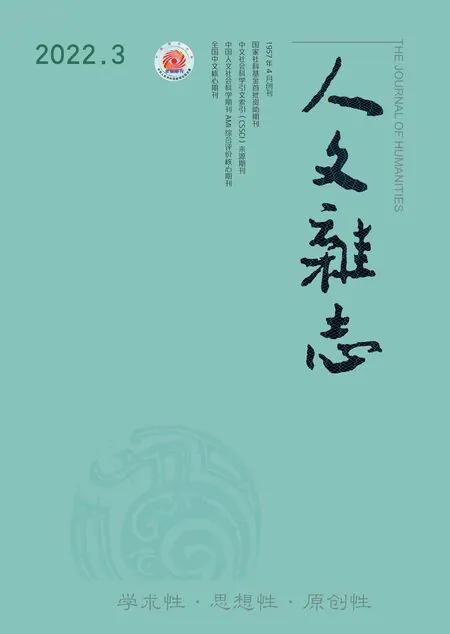區(qū)分與融合:論北宋審美趣味的變革
李昌舒
關(guān)鍵詞 北宋 身份 審美 趣味 范式
〔中圖分類號(hào)〕I206.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0447-662X(2022)03-0061-10
北宋是中國(guó)歷史上的一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也就是學(xué)界常說的唐宋變革論。其具體內(nèi)容包括很多因素,錢穆先生說:“論中國(guó)古今社會(huì)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guó)。宋以后,乃為后代中國(guó)。……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學(xué)術(shù)思想乃如藝術(shù),亦均隨時(shí)代而變。”①這種變化與士人身份密切相關(guān)。在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中,士人既是政治的主體,也是學(xué)術(shù)思想、藝術(shù)的主體。唐宋變革中,作為社會(huì)中堅(jiān)力量的門閥士族逐漸消退,庶族士人經(jīng)由科舉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這可以說是最為重要的一個(gè)變革。對(duì)于北宋審美的諸多新思想、新特點(diǎn),學(xué)界已有充分注意。本文嘗試從士人身份的角度,探討身份變革對(duì)審美趣味的影響,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的新的審美范式。
一、士人身份與審美趣味
科舉出身的士人大多是集文人、學(xué)者與官員于一身的“文—官”,“文”在其本義上并非今天學(xué)科劃分意義上的文學(xué),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從狹義的儒家禮樂到廣義的一切文化,都可以稱之為“文”。①美國(guó)漢學(xué)家包弼德的名著This Culture of Ours在被翻譯成中文時(shí),譯作《斯文》,就是一個(gè)十分精確的表述。不同于漢代的察舉征辟制和魏晉南朝的九品中正制,北宋繼承了唐代的科舉制,將其作為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但不同于唐代的主要以詩賦為考試內(nèi)容,北宋科舉的內(nèi)容雖然經(jīng)歷了多次變化,但范圍主要囊括了政治、經(jīng)義、詩賦,是一種廣泛的文化考察。這就是北宋科舉士人所具有的“文”。“文”作為北宋士人身份的一個(gè)突出特征,對(duì)于審美具有重要影響。②美國(guó)漢學(xué)家卜壽珊說:“封建世襲貴族在唐代仍強(qiáng)而有力,官員一般都出自名門望族。直到宋代,士人階層才第一次獲得社會(huì)權(quán)力,他們可以單憑功績(jī)得到高位。這個(gè)時(shí)代,科舉定期舉行,有才干的人常以此獲得官爵。……此時(shí)的高官往往是著名學(xué)者、作家、詩人,一種道德嚴(yán)肅性彌散到所有文化形式之中。宋代的士大夫形成了功勛卓著的顯貴集團(tuán),它和唐代的世襲貴族統(tǒng)治大相徑庭。正是這些文人確定了這個(gè)時(shí)代的文化基調(diào),創(chuàng)造了新的散文、詩歌、書法風(fēng)格。在這種氛圍下,蘇軾開始思考一種特殊類型的繪畫——文人畫,這并不足為奇。”③這段話的要點(diǎn)有四:一是唐宋變革中士人身份的變化,二是科舉制對(duì)士人身份的重要意義,三是北宋士人身份的特點(diǎn),四是身份變化對(duì)審美的影響。最重要的是“道德嚴(yán)肅性”確立了“時(shí)代的文化基調(diào)”,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的“新的散文、詩歌、書法風(fēng)格”。雖然這些觀點(diǎn)并非由卜壽珊第一次指出,但她的這段話簡(jiǎn)明扼要地概述了北宋審美變革的基本原因。這意味著北宋美學(xué)的一種新的考察路徑:在當(dāng)代精細(xì)的學(xué)科劃分的影響下,一般都是分門別類考察具體學(xué)科的美學(xué)思想,但在此之外,還可以從士人身份的角度觀照作為一個(gè)整體的北宋美學(xué)。④
身份的變化必然帶來審美趣味的變化。卜壽珊說:“從宏觀角度看,11世紀(jì)末,所有的藝術(shù)呈現(xiàn)出一種類似的趣味:新型的詩歌、書法、繪畫都是由同一群人,即蘇軾和他的朋友們所開創(chuàng)的。”⑤身份和趣味之間具有必然的關(guān)聯(lián)。北宋士人身份的基本屬性是富“文”而重“道”,由此帶來審美趣味的變化:一是富“文”。博學(xué)多識(shí)、學(xué)富五車的文化是士人身份的突出屬性,這使他們不同于唐代的科舉士人。由于唐代科舉重詩賦,如同元人所編的《唐才子傳》一書所揭示的,唐人多為“才子型”,而北宋科舉內(nèi)容轉(zhuǎn)向策論、經(jīng)義,士人多為學(xué)者型,王安石《答曾子固書》中自稱:“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jīng)》《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nóng)夫、女工,無所不問。”⑥南宋王十朋說:“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shí),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jīng)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jīng)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fēng)俗之消長(zhǎng),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jī)而貫其妙,積而為胸中之文,不啻如長(zhǎng)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狀。”⑦雄厚的文化素養(yǎng)必然溢出、擴(kuò)散到整個(gè)審美中,在宋人的各種文藝門類中,我們都能看到才學(xué)的影響。①二是重“道”。強(qiáng)烈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是北宋士人的突出特征,這使他們不同于魏晉門閥士族。魏晉名士高蹈浪漫,風(fēng)流絕俗,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對(duì)社會(huì)責(zé)任的摒棄、對(duì)道德約束的漠視。余英時(shí)說:“‘以天下為己任……可以看作宋代新儒家對(duì)自己的社會(huì)功能所下的一種規(guī)范性的定義(normative definition)。”②表現(xiàn)在審美上,也就是前引卜壽珊所說的“道德的嚴(yán)肅性”。程杰說:“宋代文學(xué)把對(duì)‘浮靡文風(fēng)的批判擴(kuò)大到個(gè)人情感的廣泛方面,從廣大庶族地主階級(jí)知識(shí)分子即士大夫階層人倫秩序建構(gòu)的現(xiàn)實(shí)責(zé)任和文化精神建構(gòu)的時(shí)代需要出發(fā),改革文學(xué)世界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建立新的審美理想,拓展藝術(shù)表現(xiàn)體式、技巧和風(fēng)格,從而創(chuàng)立了一些價(jià)值觀念、審美趣味和藝術(shù)技巧相統(tǒng)一的文學(xué)表現(xiàn)新范式、新類型,在漢唐文學(xué)的價(jià)值規(guī)范之外,為后世文學(xué)尤其是士大夫文學(xué)的繼續(xù)發(fā)展樹立了又一榜樣;因而我們可以這樣說,北宋詩文革新既是撥亂反正起衰復(fù)興的過程,又是革故鼎新、繼往開來的過程。”③這段話雖是針對(duì)文學(xué)而言,但“革故鼎新”顯然并不限于文學(xué)領(lǐng)域,而是整個(gè)美學(xué)思想的趨勢(shì),它意味著士人對(duì)新的審美范式的自覺建構(gòu)。
審美范式的自覺來自士人共同體的自覺。北宋士人出身普通,沒有門第可以依恃,所以無論是政治理想的實(shí)現(xiàn),還是審美范式的建構(gòu),都必須尋求同道。美國(guó)漢學(xué)家田安說:“從社會(huì)學(xué)的角度總體來看,8世紀(jì)末到唐代滅亡前的數(shù)十年間,擁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志向和趣味的精英共同體在社會(huì)階層的組成、地域分布以及文學(xué)品位方面都變得越來越多樣化。隨著群體的變化,其成員在其中不斷地維護(hù)個(gè)人和集體的立場(chǎng),好像他們是共同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而不僅僅是傳遞者。9世紀(jì)士人共同體中的友誼——既有士人之間的人際交往,也包括通過文本結(jié)成的友誼,業(yè)已成為宣稱和保持‘士之身份的一條強(qiáng)有力的途徑,也促進(jìn)了一種新文化的獨(dú)立。”④這段話是針對(duì)中唐科舉出身的士人而言,但如果考慮到科舉士人在北宋的數(shù)量和地位上遠(yuǎn)勝于中唐,則可以說這段話同樣、甚至更適合北宋士人。韓愈等人復(fù)興儒學(xué)的追求,經(jīng)過宋初的無人問津,到慶歷之后,則完全被北宋士人接受,歐陽修被時(shí)人視為當(dāng)世之韓愈,⑤他與同道者在韓愈、柳宗元等人開辟的道路走得更遠(yuǎn)。促成共同體的制度基礎(chǔ)是科舉制,維系共同體的思想基礎(chǔ)是儒學(xué),共同體“促進(jìn)了一種新文化的獨(dú)立”,這也就是當(dāng)代學(xué)界所概括的“宋型文化”。
共同體形成之后,對(duì)士人又產(chǎn)生重要影響。美國(guó)學(xué)者包華石注意到一個(gè)現(xiàn)象:“宋代的‘公論是一個(gè)被中國(guó)史學(xué)界學(xué)者很大程度上忽視的豐富議題。對(duì)《宋史》的快速檢索可以獲得大量奏折與個(gè)人書信,其中所包含的‘公論一詞被理解為考察政事的重要因素,如‘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自昔天下之患,莫大于舉朝無公論。”⑥政治上如此,審美上也是如此。歐陽修對(duì)自己文章的修改是學(xué)界熟知的,宋人的一段記載頗為生動(dòng):“歐公晚年,嘗自纂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dāng)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怕后生笑。”⑦再如,范仲淹為東漢著名隱士嚴(yán)光所寫的《嚴(yán)先生祠堂記》,結(jié)尾本為“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zhǎng)。”李覯讀后,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將“德”改為“風(fēng)”。雖然此時(shí)范仲淹已是名滿天下,為士人領(lǐng)袖,李覯只是一介布衣,但范仲淹“凝坐頷首,殆欲下拜”。①宋人書信中大量的關(guān)于審美的討論比比皆是,這同樣反映出審美上對(duì)“公論”的重視。北宋真宗、仁宗時(shí)期,京東士人頗為活躍,他們的遭遇頗能說明問題。其典型代表是石介,他在政治上推崇復(fù)興儒家之道,具有強(qiáng)烈的濟(jì)世熱情,與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的思想基本一致,但在審美上則存在尖銳沖突:文學(xué)上,石介主張的“太學(xué)體”受到歐陽修的貶斥,書法上,石介自覺的求“怪”之體同樣受到歐陽修的質(zhì)疑,歐陽修平易自然的文學(xué)和書法觀更適合“文”“道”并重的北宋士人,結(jié)果是歐陽修的審美趣味成為主流。雖然歐陽修和石介在出身上相同,在政治上也近乎同道,但由于石介代表的是后來理學(xué)家的審美趣味,重“道”而輕“文”,與作為“文壇盟主”的歐陽修代表的“文”“道”并重的審美思想并不相同,甚至頗多齟齬,從審美上講,歐陽修通過知貢舉使其審美觀成為北宋士人的主流。蘇軾在科舉及第后給主考官歐陽修的信中說:“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dāng),求深者或至于迂,務(wù)奇者怪僻而不可讀,余風(fēng)未殄,新弊復(fù)作。”②這里的“士大夫”就是石介等人,他們所倡導(dǎo)的“太學(xué)體”被蘇軾視作“新弊”,顯然,身居高位的歐陽修與初入京師的蘇軾構(gòu)建的審美共同體摒棄了石介代表的審美趣味,雖然“太學(xué)體”在當(dāng)時(shí)有很大影響,甚至放榜之后,主考官歐陽修受到考生的激烈攻擊,但這并未改變歐陽修的審美趣味成為審美共同體的經(jīng)典范式。③在給石介的第二封信的結(jié)尾,歐陽修特別提及:“凡仆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善,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后生也。”④這說明歐陽修之所以一再批評(píng)石介的書法,是擔(dān)心其“近怪自異”的趣味對(duì)于“后生”的不良影響,這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責(zé)任心在審美上的體現(xiàn),也是對(duì)與士人身份相一致的審美趣味的自覺維護(hù)。元人方回說:“近世之詩,莫盛于慶歷、元。”⑤也許可以說,不僅是詩,“宋型文化”都是發(fā)端于慶歷,成熟于元。這兩個(gè)階段的核心人物分別是歐陽修、蘇軾,他們都有建構(gòu)共同體的自覺。⑥
二、趣味區(qū)分與審美范式的建構(gòu)
士人的審美范式正是在與其他趣味(既有此前的趣味,也有同時(shí)代不同的趣味)的區(qū)分中逐漸清晰,得以明確。區(qū)分是北宋“文—官”士人的一個(gè)基本思維方式:政治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zhēng),思想的洛學(xué)、朔學(xué)、蜀學(xué)、新學(xué)之爭(zhēng),文學(xué)的駢文與散文之爭(zhēng),道德的君子、小人之辨,區(qū)分可以說是宋人的一個(gè)根本意識(shí)。原因還是在于“文—官”身份。“文”的身份使他們有能力對(duì)朝政方針提出質(zhì)疑,這也就是學(xué)界所說的宋人的懷疑精神和好議精神;“官”的身份使他們有條件施展自己“文”的理想,實(shí)踐自己的“文”,從政治上講,這是黨爭(zhēng),從更為宏大的視野看,這是區(qū)分。
就中西方美學(xué)而言,趣味是審美的核心范疇,或者說,審美的關(guān)鍵就在于趣味。就審美而言,區(qū)分同樣無處不在。對(duì)于歐陽修等慶歷士人來說,是與西昆體、太學(xué)體的區(qū)分;對(duì)于蘇軾等元士人來說,是與道學(xué)家程頤、政治家王安石等人的區(qū)分。布爾迪厄說:“趣味進(jìn)行分類,為實(shí)行分類的人分類:社會(huì)主體通過他們對(duì)美與丑、優(yōu)雅與粗俗所做的區(qū)分而區(qū)分開來。他們?cè)诳陀^分類中的位置便表達(dá)或體現(xiàn)在這些區(qū)分之中。”①就北宋士人而言,趣味的區(qū)分,不僅是士人與市民階層、商業(yè)意識(shí)進(jìn)行區(qū)分,也是和持有不同趣味的其他士人進(jìn)行區(qū)分。翻檢北宋士人文集,可以看到,區(qū)分的意識(shí)無處不在。例如,前文關(guān)于歐陽修與石介的書法觀是一種區(qū)分,關(guān)于雅俗之辨的區(qū)分更為典型地表現(xiàn)了這一思想。蘇軾說:“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yī)”(《于潛僧綠筠軒》)。黃庭堅(jiān)說:“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書繒卷后》)。在布爾迪厄看來,通過趣味的區(qū)分,不同習(xí)性的人擁有不同的審美配置,從而形成不同的團(tuán)體:“審美配置也是社會(huì)空間中的一個(gè)特權(quán)位置的一種區(qū)分表現(xiàn),而社會(huì)空間的區(qū)分價(jià)值客觀上在與從不同條件出發(fā)而產(chǎn)生的表現(xiàn)的關(guān)系中,確定自身。如同任何一種趣味,審美配置起聚集和分隔作用:作為與生活條件的一個(gè)特定等級(jí)相關(guān)的影響的產(chǎn)物,它將所有成為類似條件產(chǎn)物的人聚集在一起,但將他們按照他們擁有的最根本的東西與其他所有人分隔,因?yàn)槿の妒且粋€(gè)人的全部所有即人和物的原則,是一個(gè)人對(duì)別人而言之全部所是的原則,是一個(gè)人借以給自身分類被分類的東西的原則。”②趣味是一個(gè)人成為其所是,又與其他人區(qū)分的根本屬性。通過趣味的區(qū)分,審美一方面將相同趣味的聚集成一個(gè)共同體,另一方面又將不同趣味的人分隔。這段話可以說是北宋士人建構(gòu)新的審美范式的出發(fā)點(diǎn)。他們維護(hù)精英地位、或者說構(gòu)建起士人身份的基礎(chǔ)是“文”,審美則是“文”的集中體現(xiàn)。從這個(gè)意義上講,審美是士人保持身份的基本屬性。一方面,士人在政治、學(xué)術(shù)思想上有區(qū)分,但只要在審美趣味上是相同的,則仍然屬于同一個(gè)共同體,比如新黨中的很多人,如晚年的王安石、沈括等人,甚至后來的宋徽宗,在審美趣味上與歐陽修、蘇軾為代表的宋型文化是一致的,③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他們與歐、蘇等舊黨士人共同構(gòu)建了北宋士人的審美范式;另一方面,雖然石介與歐陽修同屬于慶歷新政的支持者,程頤和蘇軾同屬反對(duì)王安石變法的舊黨,但在審美趣味上差異太大,前文已論,石介對(duì)“險(xiǎn)怪”文風(fēng)的追求與歐陽修“平易”的趣味截然相反,而程頤則直接認(rèn)為“作文害道”,反對(duì)在文學(xué)上用功。因此,石介和程頤就被排斥在審美共同體之外。這是一個(gè)與以往研究者不同的劃分方法,其著眼點(diǎn)是審美趣味,是科舉出身的“文—官”士人所代表的審美趣味,也是被后世所接受、認(rèn)同的北宋審美范式。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與政治上朋黨之爭(zhēng)的界定范圍不一致,但一致的是審美共同體也是黨同伐異。雖然就北宋中后期的政治而言,朋黨之爭(zhēng)是最突出的問題,但就審美而言,審美通過黨同伐異,所建構(gòu)的趣味范式對(duì)后世的影響更為深遠(yuǎn)。布爾迪厄說:“趣味(也就是表現(xiàn)出來的偏好)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差別的實(shí)踐證明。當(dāng)趣味要為自己提供充足的理由時(shí),它就以全然否定的方式通過對(duì)其他趣味的拒絕表現(xiàn)出來,這并非偶然:在趣味方面,超過任何方面,一切決定都是否定性的;而且趣味無疑首先是對(duì)其他趣味、別人趣味的厭惡。……審美的排斥異己具有可怕的暴力。”④布爾迪厄在此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審美趣味的“全然否定”“拒絕”“厭惡”以及“可怕的暴力”,表面上看似乎過于激烈,但從北宋的實(shí)際來看,歐陽修和蘇軾等人在維護(hù)士人審美共同體的純粹性時(shí),確實(shí)是這樣做的。駙馬王詵的審美趣味與蘇軾等人相近,搜集了諸多珍奇字畫,將存放之地命名為“寶繪堂”,并向蘇軾“求文以為記”。雖然他貴為駙馬,但與蘇軾私交甚篤,“烏臺(tái)詩案”后,很多人選擇畏避、疏遠(yuǎn)蘇軾,王詵雖也受到牽連、遭到貶斥,卻仍主動(dòng)向蘇軾示好,這種人格與情誼是蘇軾后來屢屢致敬的。蘇軾在寫作《寶繪堂記》時(shí),當(dāng)然不會(huì)忘記這種情誼,但這篇記不僅不是稱頌之作,反而是嚴(yán)厲的“全然否定”,是“拒絕”與“厭惡”的態(tài)度:“凡物之可喜,足以悅?cè)硕蛔阋砸迫苏撸魰c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鐘繇至以此嘔血發(fā)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復(fù)壁,皆以兒戲害其國(guó),兇其身。此留意之禍也。”①將王詵搜羅字畫的風(fēng)雅行為與各種“害國(guó)兇身”的慘烈事例相聯(lián)系,對(duì)寬容豁達(dá)的蘇軾來說,這是罕見的苛刻之辭。喜歡書畫本是文人雅趣的表現(xiàn),遠(yuǎn)高于聲色犬馬之類,而且王詵并非嚴(yán)格意義上的科舉出身的士人,并且作為文人、學(xué)者式的官員,蘇軾以及其他北宋士人大多擅長(zhǎng)于此,喜好于此,那么他為何會(huì)有如此激烈的態(tài)度?美國(guó)漢學(xué)家艾朗諾的《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與追求》一書專門討論了北宋士人對(duì)美的追求與為官的責(zé)任之間的矛盾,在蘇軾看來,對(duì)美的過度沉迷會(huì)影響到士人作為官員兼濟(jì)天下的責(zé)任,從而對(duì)士人“文—官”的身份構(gòu)成威脅,因此,在游心于藝的同時(shí)需要與美保持距離。②這是一個(gè)在北宋頗具普遍性的問題,由于崇文抑武的基本國(guó)策,由于科舉制的展開,“文”是北宋一朝的突出特色,但作為“官”,應(yīng)該以社稷蒼生為念,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蘇軾對(duì)王詵的批評(píng)是針對(duì)所有士人、包括他自己而發(fā),是對(duì)士人審美范式的維護(hù)。也正是在這篇《寶繪堂記》中,蘇軾提出了影響深遠(yuǎn)的一個(gè)審美命題:“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③歷來論者對(duì)這段話已有充分關(guān)注,此處需要說明的是,作為科舉出身的“文—官”士人,他們要構(gòu)建一種儒家道德與個(gè)人興趣相兼容,或者說名教與自然相統(tǒng)一的審美范式:既不違背道德之中正,不影響為官的社會(huì)責(zé)任,也不走向王安石政治家、程頤道學(xué)家的極端,而是處于其中。④換句話說,他們要與魏晉風(fēng)流的“游乎方外”區(qū)分,也要與道德論、政治論的“游乎方內(nèi)”區(qū)分,審美需要在“方外”與“方內(nèi)”之間保持一種平衡,蘇軾的“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正是這種區(qū)分與平衡的表述。也正是從這一立場(chǎng)出發(fā),蘇軾在政治上反對(duì)王安石變法,卻又與晚年的王安石在詩歌討論中相見恨晚;在政治上與司馬光相互支持,卻又在元更化時(shí)期圍繞科舉改革中是否保留詩賦與司馬光針鋒相對(duì)。
從這個(gè)角度上講,元時(shí)期,程頤與蘇軾、也就是洛黨與蜀黨的斗爭(zhēng)就不僅是一種學(xué)術(shù)的爭(zhēng)執(zhí)或政治的分歧,更是一種由審美趣味而產(chǎn)生的生活方式的差異。布爾迪厄說:“對(duì)那些認(rèn)為自己是合法趣味的持有者的人來說,最無法忍受的,首先是趣味使之分開的各種趣味大逆不道地集合。這就是說藝術(shù)家和美學(xué)家的游戲以及他們?yōu)閴艛嗨囆g(shù)合法性而進(jìn)行的斗爭(zhēng)不如表面上那樣單純:沒有什么關(guān)于藝術(shù)的斗爭(zhēng)不以推行一種生活藝術(shù)也就是將一種隨意的生活方式轉(zhuǎn)化為合法的生存方式為賭注,這種轉(zhuǎn)化將其他一切生活方式拋入隨意之中。”⑤如果我們熟悉程頤和蘇軾交惡的爆發(fā)點(diǎn)是在司馬光的葬禮上因?yàn)閷?duì)禮的不同態(tài)度,①則可以說,這一偶然事件的背后是兩種不同的趣味而導(dǎo)致的對(duì)彼此的“生活方式”的“無法忍受”,他們視彼此為“大逆不道”。如果我們?cè)賹⒁曇胺诺阶鳛橐粋€(gè)整體的“共時(shí)”的北宋,翻檢宋人文集,會(huì)發(fā)現(xiàn)他們幾乎在各個(gè)領(lǐng)域都有爭(zhēng)論。所謂宋人好議,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就是一種區(qū)分,而審美,以及宋型文化其他各個(gè)門類的范式就是在與其他各種思想的區(qū)分與斗爭(zhēng)中逐漸清晰、定型的。
三、范式的形成與價(jià)值
區(qū)分不僅是同時(shí)代的士人彼此之間的,也是與前人的。北宋文學(xué)史上有名的一個(gè)典故是歐陽修與王安石的相識(shí),②在王安石回贈(zèng)的詩歌中,即使是以復(fù)興儒道為己任、備受歐陽修推崇的韓愈也不被認(rèn)可,以風(fēng)月詩酒聞名于世的李白更是未置一詞。進(jìn)而言之,王安石不僅對(duì)以文學(xué)立世的唐人不屑一顧,對(duì)于歐陽修本人也頗有微詞。這并非個(gè)別現(xiàn)象,雖然在年齡上二者只有十幾歲的差距,但正如陳植鍔指出的,二者之間已經(jīng)出現(xiàn)從義理和性理的轉(zhuǎn)變,歐陽修所代表的慶歷士人已經(jīng)是后生們超越的對(duì)象。一個(gè)有趣的現(xiàn)象是,蘇軾對(duì)于歐陽修、黃庭堅(jiān)對(duì)于蘇軾,都有自覺的超越意識(shí),一方面,他們對(duì)自己的老師和其他前輩充滿敬意;另一方面,他們又在內(nèi)容與形式、思想與文體等方面有意識(shí)地另辟蹊徑,別開生面。例如,蘇軾有意避開歐陽修擅長(zhǎng)的墓志銘和艷詞,以及黃庭堅(jiān)對(duì)蘇軾詩歌和書法的批評(píng)等。這方面的論述已經(jīng)很多,不做展開。
美國(guó)學(xué)者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中開篇即云:“本書的著眼點(diǎn)僅限于詩人中的強(qiáng)者。所謂詩人中的強(qiáng)者,就是以堅(jiān)忍不拔的毅力向威名顯赫的前代巨擘進(jìn)行至死不休的挑戰(zhàn)的詩壇主將們。”③這段話雖然是針對(duì)西方文學(xué)而言,但用來形容北宋士人,是十分形象的。身處中國(guó)古代數(shù)千年歷史上政治地位最高的時(shí)代,自身又是憑借雄厚的文化得以入仕,北宋士人普遍具有一種強(qiáng)烈的自信心和責(zé)任感,他們是當(dāng)仁不讓的“強(qiáng)者”,在政治、思想、文化以及審美的各個(gè)領(lǐng)域,他們都勇于有意識(shí)地“挑戰(zhàn)”前人。不妨繼續(xù)借用布魯姆的理論,下面兩段話是研究者經(jīng)常提及的:“詩的影響——當(dāng)它涉及到兩位強(qiáng)者詩人,兩位真正的詩人時(shí)——總是對(duì)前一位詩人的誤讀而進(jìn)行的。這種誤讀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校正”,④“閱讀,如我在標(biāo)題里所暗示的,是一種異延的、幾乎不可能的行為,如果更強(qiáng)調(diào)一下的話,那么,閱讀總是一種誤讀。”⑤在布魯姆看來,在前人影響的焦慮的驅(qū)動(dòng)下,后人會(huì)有俄狄浦斯式的挑戰(zhàn)和超越的沖動(dòng),誤讀的實(shí)質(zhì)是創(chuàng)新。北宋士人也有此焦慮,這不僅是北宋士人內(nèi)部代際之間的,更是來自北宋之前的影響的焦慮。蘇軾一段廣為引用的話可以視為這種焦慮的表露:“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⑥錢鍾書先生說:“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⑦面對(duì)這種影響的焦慮,北宋士人憑借其雄厚的文化素養(yǎng)和審美能力,在詩詞書畫等各個(gè)藝術(shù)門類,都有新的創(chuàng)造。一個(gè)典型的例子是蘇軾在繪畫史上對(duì)吳道子和王維的誤讀:一方面,他承認(rèn)吳道子是“畫圣”,在技法上無與倫比;另一方面,他又以詩論畫,將原本不受重視的王維畫構(gòu)建為經(jīng)典范式。其實(shí)質(zhì)是將自己所屬的士人階層上升為繪畫的主體,正如卜壽珊所說:“蘇軾第一個(gè)從社會(huì)身份上來劃分繪畫。”①這也就是一種接受美學(xué)中的“期待視野”:“‘期待視野是閱讀一部作品時(shí)讀者的文學(xué)閱讀經(jīng)驗(yàn)構(gòu)成的思維定向或先在結(jié)構(gòu)。”②對(duì)于蘇軾以及其他北宋士人而言,這種“思維定向或先在結(jié)構(gòu)”也就是他們的士人身份。在此意義上可以說,王維的畫、杜甫的詩、顏真卿的書法都是因?yàn)榉鲜咳松矸荻械摹捌诖曇啊倍唤邮埽蛘哒f,北宋士人是從自己的身份出發(fā),誤讀前人的作品,并在此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新的審美范式。
伽達(dá)默爾說:“每一時(shí)代都必須按照它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歷史流傳下來的本文,因?yàn)檫@本文是屬于整個(gè)傳統(tǒng)的一部分,而每一時(shí)代則是對(duì)這整個(gè)傳統(tǒng)有一種實(shí)際的興趣,并試圖在這傳統(tǒng)中理解自身。”③北宋是一個(gè)充滿矛盾的時(shí)代,振奮人心的理想與積弱積貧的現(xiàn)實(shí),文化的強(qiáng)大與國(guó)勢(shì)的衰弱,士人地位的高漲與黨爭(zhēng)的漩渦,在這樣的時(shí)代氛圍中,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思想上高揚(yáng)孔孟之道、嚴(yán)守夷夏之辨,在審美上推崇顏真卿的書法,杜甫、陶淵明的詩歌,王維的繪畫,等等,“試圖在這傳統(tǒng)中理解自身”。伽達(dá)默爾說:“真正的理解活動(dòng)在于:我們是這樣重新獲得一個(gè)歷史過去的概念,以致它同時(shí)包括我們自己的概念在內(nèi)。我在前面曾把這種活動(dòng)稱之為視界融合。”④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北宋士人對(duì)前人的接受概括為區(qū)分與融合。一方面,是對(duì)不同趣味的區(qū)分,是對(duì)前人的超越;另一方面,又是對(duì)其他趣味的融合,是對(duì)前人的繼承。
美國(guó)學(xué)者庫(kù)恩在《科學(xué)革命的結(jié)構(gòu)》認(rèn)為:“范式一改變,這世界本身也隨之改變了。科學(xué)家由一個(gè)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領(lǐng)域。甚至更為重要的是,在革命過程中科學(xué)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過的地方時(shí),他們會(huì)看到新的不同的東西。……范式改變的確使科學(xué)家對(duì)他們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變了。……在革命之后,科學(xué)家們所面對(duì)的是一個(gè)不同的世界。”⑤在北宋士人這里,一切皆可入詩,無物不可審美,審美對(duì)象泛化到無所不包,真正做到了莊子所說的“道在瓦礫”“道在屎溺”,蘇軾就曾以“牛矢”入詩。⑥清人葉燮說:“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比之銅鐵鉛錫,一經(jīng)其陶鑄,皆成精金。”⑦也許可以說,在審美范式改變之后,北宋士人“看到新的不同的東西”,他們“面對(duì)的是一個(gè)不同的世界”。較之于前代,宋代審美所呈現(xiàn)的并不是一種向外無限拓展的獵奇追新,而是在身邊瑣碎、平常事物中“以故為新”“以俗為雅”。不妨借用俄國(guó)形式主義的思想來說明:“在他們看來,詩學(xué)的重要目的是要回答,是什么因素使語言材料轉(zhuǎn)變成了文藝作品,語言藝術(shù)的藝術(shù)性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換言之,文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不是文學(xué),而是文學(xué)性,亦即使某一部書成為文學(xué)作品的那種東西。”⑧雖然北宋美學(xué)與俄國(guó)形式主義是針對(duì)不同的問題,但借用這個(gè)說法,北宋士人討論的是作品的審美屬性,使一切事物成為審美對(duì)象的屬性。“賦予某物以詩意的藝術(shù)性,乃是我們感受方式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而我們所指的有藝術(shù)性的作品,就其狹義而言,乃是指那些用特殊手法創(chuàng)造出來的作品,而這些手法的目的就是要使作品盡可能被感受為藝術(shù)作品。”①以此來解釋宋人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以俗為雅,以古為新,似乎是可行的。題材是否可以成為審美對(duì)象,并不在于題材本身,而在于“感受方式”的改變。這是強(qiáng)調(diào)審美主體的作用,主體的審美能力、審美態(tài)度決定了對(duì)象是否具有“藝術(shù)性”,以及是否為“藝術(shù)作品”。
作為博學(xué)多識(shí)的學(xué)者,北宋士人在哲學(xué)、文學(xué)、史學(xué)、藝術(shù)等多方面都有很高造詣,他們將自己的學(xué)識(shí)貫穿在各個(gè)藝術(shù)門類中,詩歌是“以才學(xué)為詩”(嚴(yán)羽《滄浪詩話》),書法是“尚意”,繪畫則進(jìn)入“文學(xué)化時(shí)期”(鄭午昌《中國(guó)畫學(xué)全史》)。憑借著“文”的文化素養(yǎng)和審美能力,他們將天地萬物、日常生活納入審美對(duì)象,一切皆可成為審美對(duì)象,審美態(tài)度貫穿于一切。宋末任長(zhǎng)慶評(píng)價(jià)蘇軾兄弟說:“淘汰之以詩酒詠歌、風(fēng)流諧謔與夫釋氏、老子之書,故風(fēng)節(jié)益峻整而不露,學(xué)問益醇深而不雜。天以斯文之任授二蘇,出之安樂,投之憂患,而二公旋即于憂患境中簸弄文字為安樂法,其以文為戲,直以造物為戲矣!”②“戲”是游戲的審美態(tài)度,從“以文為戲”到“以造物為戲”,必然有一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乎哀樂”的樂。“文”所賦予的審美趣味將“官”所帶來的貶謫之悲苦轉(zhuǎn)化為一種自得之樂。蘇軾的兩段話充分表現(xiàn)了這種思想:“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③“吾兄弟俱老矣,當(dāng)以時(shí)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nèi),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④這種“觀”是審美的觀照,是超越功利的觀照,前者作于“烏臺(tái)詩案”之前的密州任上,后者作于流放黃州時(shí)期。雖然其間有“世事萬端”的變化,但蘇軾通過天地萬物追求精神之“樂”的思想是一致的。正如學(xué)界多有指出的,“樂”并非蘇軾個(gè)人思想,而是北宋審美的一個(gè)基本追求,從范仲淹到王安石,從歐陽修到黃庭堅(jiān),從周敦頤到程顥,莫不如此。范仲淹被貶江南后,作《瀟灑桐廬郡十詠》;周敦頤教二程尋“孔顏樂處”,作為道學(xué)的入手;司馬光反對(duì)新法,退居洛陽,建造園林,題名“獨(dú)樂園”,有記有詩,一時(shí)群賢,多有詩文題記。可見這是北宋士人的一個(gè)共同理想,它典型體現(xiàn)了“文—官”士人因?yàn)殡p重身份帶來的審美趣味。
散文上,北宋古文運(yùn)動(dòng)臻于成熟,成為此后科舉考試的基本范本;詩歌上,宋詩在唐詩之外,開辟出另一條路徑,成為后世效仿的對(duì)象;宋詞作為一個(gè)新的文學(xué)體裁,與唐詩、元曲、明清小說一道,成為中國(guó)文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內(nèi)容;繪畫上,士人畫在元代發(fā)展為文人畫,成為明清繪畫的主流;書法上,蘇、黃、米、蔡奠定了率性自然的審美風(fēng)格,繼晉人和唐人之后,成為中國(guó)書法史的又一座高峰。歐陽修所創(chuàng)立的金石學(xué),不僅保存了諸多前代古物,而且影響后世,成為中國(guó)文化史上的一個(gè)重要內(nèi)容。諸如此類,不一而論。⑤王國(guó)維先生在詳細(xì)列舉北宋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之后,總結(jié)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dòng)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⑥誠(chéng)如當(dāng)代學(xué)者王毅所概括的:“華夏民族之文化中的許多部分都是在宋代達(dá)到了最高境界,其中尤以士大夫文化藝術(shù)之完善精美更為空前絕后,哲學(xué)、史學(xué)、文學(xué)、繪畫、園林建筑等等概莫能外。”⑦如果我們聯(lián)系陳寅恪和柳詒徵的相關(guān)論述,更可以見出士人與北宋審美范式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①
美國(guó)漢學(xué)家列文森在分析中國(guó)明代官員時(shí),說:“他們是全整意義上的‘業(yè)余愛好者,和人文文化的嫻雅的繼承者。他們對(duì)進(jìn)步?jīng)]有興趣,對(duì)科學(xué)沒有嗜好,對(duì)商業(yè)沒有同情,也缺乏對(duì)功利主義的偏愛。他們之所以能參政,原因就在于他們有學(xué)問,但他們對(duì)學(xué)問本身則有一種‘非職業(yè)的偏見,因?yàn)樗麄兊穆氊?zé)是統(tǒng)治。”②這典型概括了科舉士人“文—官”身份的審美趣味:作為“官”,他們必須承擔(dān)治理國(guó)家的責(zé)任,因此,他們必須以業(yè)余者的態(tài)度對(duì)待審美;作為“文”,他們擁有雄厚的文化素養(yǎng),并且憑借這種身份獲得官員資格,因此,他們不屑于只是行政管理的俗吏,而是要時(shí)時(shí)彰顯自己“文”的身份,審美正是這種身份最突出的標(biāo)識(shí)。“文—官”雙重身份由科舉制促成,科舉制成熟、定型于北宋。科舉制是此后古代社會(huì)的官員選拔的基本制度,在此意義上,北宋士人的審美范式也就自然成為此后美學(xué)的基本范式。陳望衡說:“我們前面談到陽修美學(xué)思想是封建士大夫美學(xué)的突出代表,蘇軾亦是,而且更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說,蘇軾是封建士大夫美學(xué)的集大成者。”③學(xué)界已經(jīng)注意到士人美學(xué)的重要性。張法認(rèn)為:“就整體一部分關(guān)系中強(qiáng)調(diào)整體來說,只有一個(gè)美學(xué),即由士人來思考的中國(guó)美學(xué)。在這一意義上,中國(guó)美學(xué)就是士人美學(xué)。”④但從已有的研究現(xiàn)狀來看,士人美學(xué)的研究并未受到充分重視,主要原因應(yīng)該是涉及古代政治、哲學(xué)、歷史等多學(xué)科的研究,而日趨精細(xì)的分門別類的學(xué)科劃分使得當(dāng)代學(xué)者很難有全面的知識(shí)背景去深入研究這一問題。隨著近年來身份、心態(tài)話題日益受到重視,尤其是當(dāng)前強(qiáng)調(diào)跨學(xué)科的新文科的研究路徑,士人美學(xué)勢(shì)必將會(huì)受到更多關(guān)注。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xué)文學(xué)院
責(zé)任編輯: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