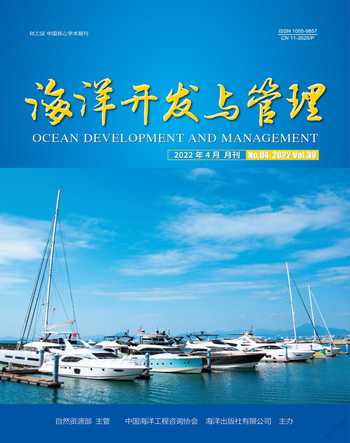海洋文化的學科主體性困境與建構
寧波 金童欣

摘要:中國對于海洋文化的理論探索與建構已有數十年的積淀,然而目前學術界對其學科主體性依然缺乏共識。為增強中國海洋強國建設的文化軟實力,文章解答海洋文化學科主體性的基本問題,分析海洋文化學科主體性建構面臨的挑戰,并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建議。研究結果表明:海洋文化屬于知識門類意義上的學科,是獨特的知識集合和自成系統的理論體系;由于傳統學術思維的慣性、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研究對象范疇模糊和研究方法特性缺失等因素,海洋文化的學科主體性尚未真正確立;海洋文化的學科主體性建構應堅持“人-海主體”的理論建構、“人-海和諧”的價值取向、“人-海依存”的研究范疇和“人-海互動”的研究方法。
關鍵詞:海洋文化;學科主體性;研究方法;理論體系;文化軟實力
中圖分類號: G12;P74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10059857(2022)04005005
The Dilemma and Construction of Ocean Culture as a Discipline
NING Bo12,JIN Tongxin'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2.Research Center for Ocean Culture,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Abstract:The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ocean culture theory system have been constructed for years in China, but as a specialized theoretical system, it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by the aca- demic communit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marine power construction of China, the paper answered the basic questions of the subjectivity of ocean culture, analyze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ocean culture,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cean culture was a unique subject of knowledge category and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ystem.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academic thinking and the theory construc- tion,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etical subjectivity of ocean culture had not yet been really estab- lished.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ubjectivity of ocean culture, it should adhere to the construction idea of “human and ocean subjec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human and ocean har- mony”, the research principle of “human and ocean dependence”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of “hu-man and ocean interaction”.
Keywords:Ocean culture,Theoretical subjectivity,Research method,Theoretical system,Cultural soft power
1海洋文化的學科主體性問題
中國對于海洋文化的理論探索與建構已有數十年的積淀,然而目前學術界對其學科主體性依然缺乏共識。截至2021年,海洋文化的學科主體性建構若從1953年楊鴻烈出版《海洋文學》算起已有68年歷史,若從1999年曲金良出版《海洋文化概論》算起也已有22年歷史,但海洋文化作為專門理論體系即學科主體性的存在迄今仍未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同。
1.1海洋文化是學科還是領域
學科是某種知識門類或知識形式[1],其英文單詞“discipline”源自希臘文的“didasko”(教)和拉丁文的“disco”(學),古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兼有知識(知識體系)和權力(孩童紀律和軍紀)之義[2]。根據學科的定義,中國的海洋文化經過數十年的研究積累,已逐步形成獨立的知識系統即成為學科,然而海洋文化作為獨立學科迄今未在國內學術界形成共識。一方面,囿于傳統學術思維慣性,人們對海洋文化這一新事物缺乏認識和了解;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海洋文化概念的走熱,其不斷吸引文藝學、歷史學、政治學、軍事學、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旅游學和傳播學等學科的關注,以致影響海洋文化自身理論體系的主體性建構。海洋文化是作為歷史學、社會學和民俗學等學科的研究對象而存在,還是有其自身獨特的學科屬性、理論體系、知識系統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說,海洋文化是學科還是領域?
海洋文化面臨的尷尬學術處境,與教育學長期以來面臨的學科主體性質疑頗為相似。拉格曼曾在其著作中指出:“許多人認為教育本身不是一門學科。的確,教育既沒有獨特的研究方法,也沒有明確劃定的專業知識內容,且從來沒有被視為是一種分析其他科目的工具。但是,我把教育看做是受到其他許多學科和跨學科影響的一個研究領域與一門專業領域”[3]。自陳炎、楊國楨和曲金良等學者接續努力至今,海洋文化作為知識門類意義上的學科已不言自明[4]。因此,與其質疑海洋文化的學科主體性,不如反思傳統學術思維的局限性、涵納性和創新性。
1.2海洋文化是知識集合還是理論體系
本研究于2021年5月1日以“海洋文化”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總庫進行主題檢索,檢索時間范圍為1915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1日。檢索到學術期刊論文3615篇、學位論文553篇和專著14部,以《海洋文化概論》《海洋與中國》叢書、《海洋中國與世界》叢書、《中國海洋文化》叢書和《中國海洋生態文化》為代表(表1)。這一略顯簡單的檢索佐證海洋文化作為學科已有數十年和數千篇(部)的學術研究積累,顯示其作為知識集合的形成過程以及作為理論體系的建構過程。
在海洋文化的理論體系建構方面,宋臻[5]和曲金良[6]從歷史文化遺產中挖掘海洋文化遺產,重新審視中國海洋文化的發展軌跡,從而確立其應有的歷史地位,即中國五千年歷史并非與海洋文化隔絕,而是擁有悠長而厚重的積累,有力駁斥以黑格爾為代表的中國海洋文化虛無主義[7];劉淑珍等[8]和唐夢雪等[9]通過田野調查梳理中國海洋文化發展現狀,提出民族志式的“照相式”記錄和類型提煉,推進對中國海洋文化的認識和了解,并成為海洋文化田野調查的研究范式;很多文獻結合國家大政方針提出海洋文化方面的政策解讀、概念新詞或真知灼見[10-11],同時提出其他視點的研究結論。
盡管海洋文化已形成理論體系且不失厚重的學術積累,但其究竟作為知識集合還是理論體系迄今仍存在爭議。2014年曲金良等出版的《中國海洋文化基礎理論研究》試圖宣示海洋文化基本理論體系的建立,并較系統地闡述中國海洋文化在世界海洋文化體系中的地位及其基本內涵、特性、歷史積淀、價值、功能和發展現狀等問題[12],但遺憾的是未得到學術界的普遍接受和認可。與之較類似的是高等教育學,高等教育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合理身份在學術共同體內部一直存在分歧且爭議不斷[13],即理論體系建構和身份認同存在很大張力。其實,海洋文化不僅是獨特的知識集合,而且是或許不盡成熟但已自成系統的理論體系,所謂的分歧和爭議也許來自自古以來人們對海洋文化的陌生感和疏離感。因此,與其繼續論爭海洋文化的學科主體性地位,不如努力做好海洋文化的推廣和普及。
2海洋文化學科主體性建構面臨的挑戰
2.1傳統學術思維的慣性
西方的學術傳統來自古希臘哲學,而中國的學術傳統則來自歷史學。中國的歷史學研究比較重視訓詁和引經據典,受此影響,中國的海洋文化被賦予較濃厚的歷史學色彩,且現實中歷史學者確乎是海洋文化研究的主要群體之一, 因此海洋文化作為歷史學研究對象的意義遠遠超過其作為獨立學科的意義。即使有眾多學者試圖對海洋文化給出明晰、簡潔和易懂的定義,但終究限于海洋文化的小范圍學術圈,且受制于厚重的學術傳統而未得到普遍認同。
除歷史學外,在近代以來引入中國的西方哲學、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和人文地理學等學科中,海洋文化也多作為研究對象而存在。丁希凌[14]提出海洋文化學是綜合性學科,涵蓋哲學、社會、自然和科技等方面,包括社會、自然和技術科學三大門類,而其中每個門類又可形成多層次學科群;這一定性分析試圖闡釋海洋文化的學科屬性,遺憾的是這使海洋文化看上去更像“大雜燴”,反而弱化了其獨立的學科屬性。因此,受傳統學術思維的影響,海洋文化儼然成為各學科理論體系的補充和延伸,即海洋文化研究僅為眾多學科圍繞海洋文化的百家爭鳴。
2.2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
中國學術界多沿襲儒家經世致用思想,海洋文化研究亦然,即理論為服務實踐而生以及理論為指導實踐而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因時而生。北京大學的陳炎于1982年發表《略論海上“絲綢之路”》, 吹響“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號角:“一條連接亞、非、歐、美的海上大動脈連匯而成。這條海上大動脈的流動使得這些古代文明互相交流并綻放異彩”[15]。不論自覺還是不自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從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遺產中為改革開放提供歷史、思想和理論參照,深刻闡釋“海洋-開放-交流-發展”的意義。
隨著21世紀“海洋世紀”的到來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和“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海洋文化研究興起熱潮,彰顯學者們為治國理政獻計獻策的強烈意愿。然而受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人們對直面實踐的概念創新情有獨鐘,而對海洋文化等形而上的理論探索相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海洋文化自身理論體系的建構和完善。“無用之用,方為大用”,海洋文化迫切需要形而上的超然、淡定、獨立和深刻的理論思考和體系建構。
2.3研究對象范疇模糊
海洋文化的學科主體性模糊與其研究對象范疇過于寬泛有很大關系。縱覽海洋文化研究,有不少成果借海洋文化之名而行對外交流之實,還有不少成果言海洋文化而實為漁文化,不一而足。曲金良[16]提出海洋文化研究的5個方向,包括海洋文化基礎理論,海洋文化史,中外海洋文化的互相傳播、影響及其比較,海洋文化田野作業以及海洋文化與社會發展;陳國棟[17]認為海洋文化研究可分為七大范疇,包括漁場和漁撈,船舶和船運,海上貿易和移民,海岸管理、海岸防御和海軍,海盜和走私,海洋環境和生態(海洋利用和關懷)以及海洋人文和藝術。從上述探討中可以發現,海洋文化的研究對象在認識上存在頗大彈性,即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和因地而異。這恰恰凸顯當下海洋文化研究對象的模糊性和主觀性,從而影響海洋文化學科主體性的建構。
2.4研究方法特性缺失
海洋文化研究多借用歷史學研究方法、社會學研究方法、民俗學和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文化比較法以及數據分析法等,而缺少自身獨特的研究方法。如同教育學和高等教育學過于依賴心理學和社會學等研究方法,其學科主體性至今受到質疑[18]。海洋文化缺少獨特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海洋文化的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另一方面,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都在研究海洋文化,而眾多學者缺少海洋實踐背景,使海洋文化的研究方法呈現多元化。海洋文化的特色格外鮮明,意味著海洋文化也應具有獨特的研究方法,但受限于研究經費或研究條件等因素,其特征性研究方法尚未出現且未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和認同。
3海洋文化的學科主體性建構
3.1堅持“人-海主體”的理論建構
海洋文化確立學科主體性須堅持“人-海主體”的理論建構,即理論建構應基于人與海之間的關系以及由此所創造的物質與財富的總和。人因為海而形成獨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是海洋文化有別于其他學科的典型特點。2018年江澤慧等[19]主編的《中國海洋生態文化》創造性地探討中國海洋生態文化主題,是海洋文化理論建構的重要成果,且開辟中國海洋生態文化研究的新領域。顯然,只有首先樹立“人-海主體”理念,才能確立海洋文化的學科主體性;如僅將海洋文化作為一時的研究對象,卻并無對“人-海主體”的認識和理解,也就談不上海洋文化的學科主體性,海洋文化研究充其量僅是某學科就海洋文化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和學術文獻。3.2堅持“人-海和諧”的價值取向
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通常都具有獨特的價值取向,即“百家爭鳴,爭在價值”。正如儒家追求經世致用以及哲學追尋“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往哪里去”的價值取向和終極關懷,海洋文化研究須堅持“人-海和諧”的價值取向。只有堅持“人-海和諧”的價值取向,才能避免海權功利的片面價值取向,才能視海洋為“命運共同體”,才能使理論創新助力海洋可持續發展以及助力人類實現面向海洋的價值追求和生活方式,否則可能產生理論建構異化,導致錯誤地開發利用海洋,最終危害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3.3堅持“人-海依存”的研究范疇
對于海洋文化的研究對象迄今缺少普遍認識,其實海洋文化本身已給出明確答案。“文化是一種養成了習慣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余秋雨),因此海洋文化是海洋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獨特存在,其來源于“人-海依存”的歷史實踐,發展于“人-海依存”的實踐創新。因此,海洋文化研究須緊緊把握“人-海依存”的研究范疇,“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接觸海洋而非僅從書本等媒介認識海洋,深入海洋而非僅從濱海旅游等活動體認海洋,這樣才能發現有意義的學術問題和得到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值得關注的是,不能以大陸思維研究海洋文化現象,而應以海洋思維[20]調查和分析海洋文化現象背后的規律和本質。
3.4堅持“人-海互動”的研究方法
海洋文化的研究方法誠然可以采納和借鑒歷史學、民俗學、社會學、經濟學和人文地理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但須始終堅持自身獨特的“人-海互動”研究方法。所謂“人-海互動”就是除研究對象外,在研究時還應體驗“人-海互動”的方法和途徑。例如: 某日本學者為研究福建疍民文化,除學習和梳理以往文獻外,還特地赴福建開展田野調查,認一對疍民夫婦為義父母,在船上共同生活2年,從而親身體味原汁原味的福建疍民文化。當然,受限于時間、精力和經費等因素,如此深度的調查研究無法簡單復制;然而在調查研究中,除調查者和被調查者外,海洋作為第三者的存在不可或缺。以往有些文獻梳理廣泛、論證縝密且數據分析嚴謹,但唯獨缺少海洋體驗,以致在一些具體細節上凸顯“實踐經驗不足”,即因不了解海洋而影響總體說服力。例如: 對慣于歷史學研究的學者而言,很容易通過歷史文獻簡單得出有失偏頗的結論,而有些歷史文獻的記載與實際情況存在錯位。這樣的例子為數不少,比較典型的是不少研究依據明清文獻,從字面上夸張放大明清海禁;而實際上當時雖行海禁,但民間海洋貿易一直禁而不絕,否則就無法解釋茶葉和瓷器等出口之巨;近年來的海洋考古發現沿海明清海商沉船數量眾多,亦反證海禁的間歇性和局部性。因此,有些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或可在書齋里冥思頓悟,但海洋文化研究則須體驗海洋、了解海洋和理解海洋。
4結語
在當前中國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踐行“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背景下,海洋文化亟須加強學科主體性建設,通過增強研究內容的“海洋味”、凸顯研究方法的獨特性以及提升理論體系的顯示度,逐步確立和強化海洋文化作為學科的理論體系主體性,使海洋文化真正成為助推“海洋強國夢”實現的文化軟實力,同時成為建設海洋強國的思想基礎、理論自覺和行動方向。
參考文獻
[1]曹永國.何謂學科:一個整體性的考量[J].蘇州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8(4):43-51.
[2] HOSKIN K W,MACVE R H. Acounting andtheexamination: agenealogyofdisciplinary power[J]. Acounting, Organization andSociety,1986,11(2):107.
[3]拉格曼.一門捉摸不定的科學:困擾不斷的教育研究的歷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
[4]寧波,郭靖.中國海洋文化發展報告[A].崔鳳,宋寧而.中國海洋社會發展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130-148.
[5]宋臻.以考古發掘來解碼寧波海洋文化基因[N].寧波日報,2021-04-16(3).
[6]曲金良.我國海洋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與對策[J].中共青島市委黨校青島行政學院學報,2011(5):96-101.
[7]寧波.關于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比較的再認識[A].崔鳳.中國海洋社會學研究(2013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52-60.
[8]劉淑珍,李春霞.中國海洋文化產業發展研究現狀綜述[J].經濟研究導刊,2016(33):31-32.
[9]唐夢雪,譚春蘭.海洋文化資源開發現狀與發展對策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13,41(13):6106-6107.
[10]張杰.加強海洋文化遺產保護政策與路徑研究[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01-18(6).
[11]寧波.海洋文化產業及其發展策略芻議[A].上海海洋大學,上海市歐美同學會.第三屆海洋文化與社會發展研討會論文集[C].上海:上海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中心,2012:7.
[12]趙娟.追尋藍色海洋文化的深厚底蘊:評《中國海洋文化基礎理論研究》[J].海洋世界,2015(10):76-77.
[13]付八軍,龔放.學科標準的審思與學科政策的突圍:化解高等教育學學科危機的兩個向度[J].高等教育研究,2021, 42(3):54-59.
[14]丁希凌.海洋文化學芻議[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3):61-62.
[15]陳炎.略論海上“絲綢之路”[J].歷史研究,1982(3):161-177.
[16] 曲金良.海洋文化與社會[ M].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3.
[17]陳國棟.海洋文化研究的多元特色[J].海洋文化學刊,2017,12(3):17.
[18]丁鋼.教育學學科問題的可能性解釋[J].教育研究,2008(2):3-6,32.
[19]江澤慧,王宏.中國海洋生態文化(上、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0]寧波,郭新麗.海洋教育重在傳習海洋思維[J].寧波大學學報
(教育科學版),2021,43(2):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