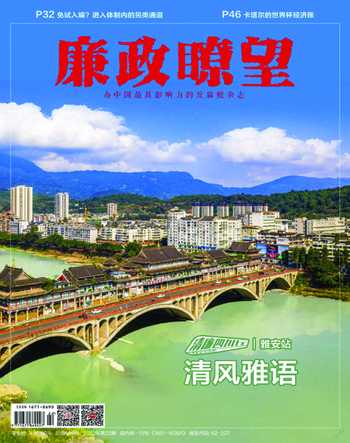對話青年舞蹈家黎星:“不知者”無畏
李浩瑄
千紅一窟,萬艷同杯。帷幕撤下,十二金釵褪去華裳,各著一色舞衣在狀似墓碑的椅子上起舞,地面鋪散開來的花朵“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這是11月18日晚,在四川大劇院上演的舞劇《紅樓夢》的末章中的場景。十二金釵拖著象征束縛的披風緩步退下,“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劇場燈亮,40余名演員依次返場謝幕。當飾演賈寶玉的黎星撥開白色紗幕走向臺前,場內觀眾掌聲雷動,有人在呼喊他的名字。大幕降下,又升起,黎星和伙伴們手牽手反復奔往臺前,向久久不愿離場的觀眾致謝。
黎星不僅是舞劇《紅樓夢》的參演者,作為國內首位獲得國際六項舞蹈大獎的青年舞蹈家,他還是這部舞劇的導演及編舞。“或許是不知者無畏吧,當初江蘇大劇院找到我做《紅樓夢》,我沒有猶豫就接下了。”黎星向廉政瞭望·官察室記者回憶當時的心態時,眼神中流露出興奮和滿足,他很清楚這部鴻篇巨制在中國人心中的分量。
“演員們穿練功服上臺了!先把昨天改的部分走一遍。”11月20日晚七點半,在德陽市演藝中心劇場內,黎星拿著話筒站在觀眾席中央,招呼著20余名專業舞者回到臺上繼續排練。
就在這天早上,他還自己驅車返回成都為新劇《火車站》錄音。“凌晨5點,他還在給我發信息溝通戲服修改的事。”因受疫情影響,從廣州訂購的布料延遲了3天才發出,《火車站》的服裝設計李昆連日來感到壓力巨大。“導演會在劇場合成階段,對戲服提出修改意見。”
李昆已與黎星合作多次,從《大飯店》到《紅樓夢》再到《火車站》,不過兩人最早的合作可以追溯到黎星2006年第一次獲得國際大獎首爾國際舞蹈比賽金獎的作品《蒲公英》,那時的黎星15歲。
黎星平均每年要演出上百場,在他的人生經歷里,酒店和車站占據著相當大的比重。《火車站》和黎星之前的作品《大飯店》被他歸為“城市空間系列”,“飯店、火車站,它們都是文明世界的建筑,這個建筑會與人產生關系。我想要探尋空間與人之間的無限可能。”如果說《紅樓夢》是黎星從男性視角對女性之美的詮釋,那么“城市空間系列”則是黎星從自我出發對人性的探尋。
表達作品的內核力量
廉政瞭望·官察室:我們能夠很明顯地感覺到《紅樓夢》的最后兩個章節《花葬》和《歸彼大荒》是完全屬于您的表達方式,以現代舞的形式來描繪十二金釵或者說是封建社會中女性被壓抑多年的釋放。但有一部分人可能不太接受這樣的表現形式,您怎么看?當初提出這樣的構思后有沒有被出品方否決過?
黎星:首先出品方從頭到尾沒有干涉過我的創作。他們剛開始找到我做《紅樓夢》的初衷是做一個民族樂劇,而我是做舞劇的,我的腦海中對它的畫面處理都是舞劇的概念,就這樣做著做著,我們就決定,好好地打造一部舞劇出來。
舞劇《紅樓夢》算是我們這群90后對這部作品的解讀,如果只是單純地把文字變成了舞蹈,讓舞蹈成為翻譯名著和文學的工具,對于我個人而言,我不滿足。
創作戲劇文本的目的是要去表達那個文學,體現名著核心的思想,和戲劇邏輯里面的內核。無疑,《紅樓夢》中有非常豐富的內核力量,我們選取了女性力量來作為我們這版《紅樓夢》的核心。《紅樓夢》里的女孩們都像花兒一樣燦爛,但是她們又像煙花一樣,凋零于最燦爛的時節。花是這些女孩的命運。
有很多觀眾覺得我們的舞劇《紅樓夢》很好看,但我希望能做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感觀審美的刺激。我希望五年、十年后,大家再看舞劇《紅樓夢》,最起碼能找到我們90后這一代人在創作《紅樓夢》時的動機。每個時代都會有大家覺得很好看的演繹,別人在演繹《紅樓夢》的時候,可能選擇十二金釵為主體,也可能選擇寶黛釵為主體,還可能做一個全家福,但是還會有其他人做《花葬》嗎?我覺得不會。
《花葬》這段由12名優秀女舞蹈藝術家演繹的現代舞群舞,即使離開《紅樓夢》也是一段好看的舞蹈,但是它一旦離開《紅樓夢》就失去了內核力量,那種蓬勃的生命力。
廉政瞭望·官察室:當初有沒有想過拒絕,畢竟我們都知道一旦涉及與《紅樓夢》相關的作品,都會面臨較大的爭議,這對創作者來說往往是個巨大的挑戰。
黎星:沒有哎,可能就是不知者無畏吧。其實我做完這個作品接受觀眾審閱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哎喲,還挺不怕死的。做的時候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些情況,不然會畏手畏腳。
中國人對《紅樓夢》太熟悉了,作為一個創作者會對它產生景仰之情。我找來了中國12個特別頂尖的女舞者扮演十二金釵,這中間當然有困難,光是協調和統籌就花了相當大的精力。但是當這個事做成了,觀眾認可了,我覺得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們來到成都,看到在這樣的大環境里,臺下座無虛席,掌聲無比熱烈,會沉浸在感動中。
突破自我局限
廉政瞭望·官察室:這次《火車站》的演員中,大多數是街舞舞者,但是目前國內還沒有其他劇目以街舞的形式在劇場呈現一個完整劇目的先例,是如何想到要做這樣的創新?在編排上會不會相對困難?
黎星:我做這個事情的初衷不是在創新,而是在新鮮和好玩。兩年前,我在參加湖南衛視《舞蹈風暴》時,認識了黃瀟、馬曉龍他們這一撥人。他們跳的街舞和現代舞、芭蕾舞、中國舞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但是卻能傳遞出巨大的能量,這個能量到了舞臺上更能被放大。我希望通過舞蹈劇場這樣的形式,讓更多觀眾感受到這股能量。
《火車站》的主演中也有現代舞演員,比如和黃瀟扮演的小站長有很多對手戲的賣花姑娘,他們一個是街舞舞者,一個是現代舞舞者,兩種不同的舞蹈形式結合的雙人舞,依然是成立的。當然,不同的劇目有不同的難點,但是搞創作的本質就是不停追尋完美,再創造遺憾。對我來說,這個過程中的困難都是不值得被提及的。
雖然我已經有了很多做舞蹈劇場的經驗,但是我不想用我過去的經驗來框住現在做的東西,這樣會形成局限,我更愿意去傾聽街舞舞者的表達,再消化,這對我來說也是一次學習的機會,在突破我的局限。
廉政瞭望·官察室:李昆老師提到您凌晨5點還在給她發消息,提出服裝的修改意見。對你們來說,一個劇目首演前工作到凌晨是一種常態嗎?
黎星:應該說每天都是這樣,而不僅是一種常態。特別是進入劇場合成階段,不是把每個舞段編好了就直接上舞臺,舞美燈光一打,跳就行了。一部舞臺劇好看,好看在氣口的銜接。在現階段,我對舞臺的把控主要還是靠感受,純靠理論是不行的。這是觀眾看不見的部分,但它會影響全劇的節奏,一個劇是被拉垮還是被拎起來,就在這些細節上。一塊璞玉,要雕刻成藝術品,關鍵就在于細節。
渴望冒險,順其自然
廉政瞭望·官察室:您從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后就進入了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友文工團,對大多數專業舞者來說,有一個院團是最好的歸宿,而且您在文工團里也一直挑大梁擔任男主演,為什么會選擇離開呢?
黎星:我不是一個喜歡穩定的人,不然我不會花自己的錢干那么多的事情。我覺得人生一定要酷一次,就像我喜歡極限運動、喜歡自駕,我骨子里就是喜歡冒險的。
放棄每個月一萬塊的固定工資,以及各種待遇,確實也屬于一種冒險。除了小時候被送去學舞蹈不是我自己在拿主意,上大學以后,我的所有決定都由自己做,我會告訴父母,但不再是商量。
廉政瞭望·官察室:你獲得過很多國內外大獎,它們對您來說有著怎樣的意義?
黎星:毋庸置疑,那些獎項對那個階段的我來說是一種認可,它們給我帶來了信心,并且促進我快速成長。但是對現在這個階段的我來說,我沒必要再專門告訴大家我獲得了哪些獎項,如果我現在還能獲獎,當然還會感到開心,只是和過往的心態不同了。
廉政瞭望·官察室:大家常說三十而立,您今年31歲了,步入新的階段有哪些不一樣的感悟?
黎星:我對年齡感覺特別強烈的時候是在29歲的最后幾個月和30歲剛開始的那半年。中國人每到一個十歲都會有一些儀式感,但我其實對這個階段的劃分不太明晰。我那段時間拼命在問自己30歲應該做什么?但是想著想著,好像就忘了這件事。回過頭發現,我可以把當時經歷的某件事刻意地放到這個節點。
比如正好在我步入30歲的過程中,做了《紅樓夢》,我覺得它就是我送給自己的30歲禮物。那么我現在正在做的《火車站》,則是真正表達了30+的黎星的心態,是完全屬于我自己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