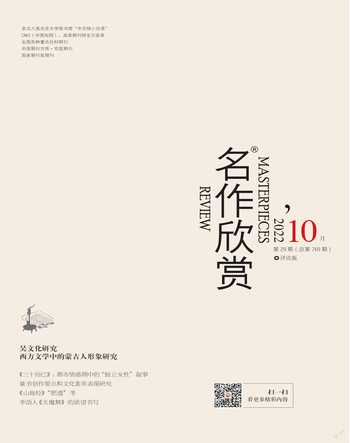21世紀前二十年(2001—2020)李清照《詞論》研究綜述
關鍵詞:《詞論》 李清照 研究綜述 文本研究 價值研究
《詞論》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關于詞學創作的文章。21世紀以來,學界對其研究層出不窮。經統計與整理,近二十年(2001—2020)對《詞論》的研究范圍涵蓋作者作年研究、寫作成因探析、文本細節研究和價值研究四個方面,總體呈現出不斷深化、細化的趨勢。通過全面、綜合的梳理和反思21世紀前二十年的李清照《詞論》研究,有助于下一步研究的深入和拓展。綜合來看,21世紀以來,對李清照《詞論》的價值研究沿著20世紀的研究展開并不斷深入,仍是《詞論》研究的熱點,其研究主要從不同立場出發,不斷重衡《詞論》的價值,生發出充分肯定與辯證看待兩種研究方向。然而,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還比較薄弱,尤其是寫作成因等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
一、作者作年研究
《詞論》這一文本“最早見于宋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三·題作李易安云云,《詞論》一名是今人所加”。鄧子勉認為,胡仔并未明確指出李易安就是李清照,而李格非也曾自號“易安居士”,在此基礎上,他對《詞論》的作者提出了質疑。從行文風格上,《詞論》更接近李格非“常有游戲筆墨之文,無事不說,無物不論,形容強嘲而評之”的創作心態;從詞學觀上,《詞論》創作與儒家的詩教觀聯系密切;從寫成時間與論及詞人上,《詞論》更似李格非的時代。從行文風格、寫成時間、論及詞人和所持詞學觀四個方面出發,鄧子勉提出了“《詞論》的作者李易安更可能指李格非”的觀點。同年,肖振華的論文則駁斥了鄧子勉的觀點。肖振華指出:“從現存關于李格非的記載來看,還找不到將其稱為‘李易安的材料。”肖振華同樣從行文風格、寫成時間、論及詞人和所持詞學觀四個方面出發,逐一推翻鄧子勉的觀點。基于孤證難立的研究思路,肖振華認為《詞論》仍應為李清照所作。
關于《詞論》的創作時間研究,多有北宋說和南渡說兩種觀點。朱崇才主張南渡說。他創作的《李清照〈詞論〉寫作年代辨》一文將《詞論》力斥“亡國之音”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相聯系,從語言風格、音律發展脈絡、《詞論》文本出處以及北宋后期蘇黃話題敏感等五個角度出發,闡釋了“《詞論》可能是針對南宋詞壇的現實而發”的觀點。鄧子勉則從《詞論》文本出發,以對“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余年”一句中“余”字的理解來推斷《詞論》的創作時間,認為《詞論》的創作時間下限在北宋哲宗元祐年間,這一觀點即為北宋說。
學者對《詞論》的作者作年研究雖存在爭議,但綜合各家學說,《詞論》為李清照所作的觀點似乎更加合理,而其創作時間還有待進一步論證。
二、寫作動因探析
從《詞論》文本出發,研究其寫作動因的成果共有學術論文八篇,其研究思路為《詞論》創作主要受到詞學發展過程中的繼承與創新以及李清照家庭與性格等方面的影響。
關于《詞論》創作的繼承與創新,黃寶華、李學軍、孫克強、程應嘉、劉雙等學者皆有著述。黃寶華和李學軍都是在宋代詞學視域下探析《詞論》的寫作成因。黃寶華認為《詞論》是宋詞雅化過程的產物,是李清照面對宋詞雅化這一趨勢提出的若干見解;李學軍則梳理了宋代詞學的歷史演進,對《詞論》的理論建構進行挖掘,認為《詞論》提倡文雅和音律并重是源于對宋代詞學“重文雅、輕音律的抨擊”。孫克強以《花間集敘》《詞論》《樂府指迷》為中心,分析了唐宋詞壇詞體觀的演進,認為“李清照所處的時代,詞壇的主要問題是詩詞之辨,也就是說應該怎樣處理詞與詩的關系。《詞論》主要即為此而發”。程應嘉同樣是從詞壇的發展演進出發,當時宋詞由俗變雅,“這種創作及評詞之風,在為建立比較系統的批評理論提供思想材料的同時,也提出了迫切的需要。李清照的《詞論》,便應運而生”。劉雙則指出,《詞論》不僅繼承了宋代及其以前詞論的觀點,還有李清照個人詞學觀點的闡述。這一研究不再局限于《詞論》創作的繼承性,更進一步挖掘其新變的一面。
認為《詞論》創作與李清照家庭、性格有關,主要有三篇研究成果。皇甫榮華認為,李清照從宏觀角度總結詞學的發展規律,分析其創作《詞論》所受到的影響。李清照灑脫自由、叛逆不羈的個性與從小接受有關詩詞創作的良好家庭教育以及父親忠貞正直的性格有關。梁懷超同樣從李清照的性格出發,認為其好強好勝的性格導致《詞論》這一具有爭議性的文章的出現。而魏向陽的研究則從李清照的歷史責任感、創新精神和詞學審美理想的張揚三方面探討《詞論》的寫作動因。這些研究皆以李清照的人生觀照為出發點,從知人論世的角度探討《詞論》的寫作成因。
綜合而看,學者對李清照《詞論》創作成因的探析不外乎時代與個人兩方面的原因。宋代詞學的發展與李清照家庭環境及其性格特征共同促進了《詞論》的產生。
三、文本細節研究
《詞論》文本細節研究的相關成果較多,約有學術論文和學位論文十八篇,主要涉及首句標點與解讀,引用李八郎故事,以及未提周邦彥等問題。
對首句的標點與解讀關系到對《詞論》全文的理解,學界對此存在頗多爭議。經統計整理,21世紀以來,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多圍繞任半塘《唐聲詩》展開。任半塘認為“樂府”指長短句詞,“聲詩”指唐代歌詩。余恕誠先生對此觀點進行了批評,他認為《詞論》首句“樂府、聲詩并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所闡釋的是《詞論》的發論點,即它是立足于聲詩與詞之間的淵源關系而發論的。孫尚勇則指出,“余恕誠的研究以批評任半塘《唐聲詩》作為立論前提未盡妥當,其結論可能未必確當。”李定廣同樣認為余恕誠先生的觀點“甚至強為其牽解”,他的《“聲詩”概念與李清照〈詞論〉“樂府聲詩并著”之解讀》一文,概況了學界對此問題的不同觀點,指出任半塘“唐聲詩”的概念是其自設的概念,并非唐人觀念,“唐代‘樂府‘聲詩‘歌詩在配樂歌詞意義上是同義互換的關系”。吉林大學李春明的碩士論文對現存李清照《詞論》首句標點解讀進行了疏證,有利于系統地理解各家學說的分歧。張海明的研究同樣是探討各家學說,對各家分歧進行了梳理,他更進一步指出了當今學界的三個共識,即“李清照以此作為《詞論》的開頭語,意在彰顯詞與音樂的血緣關系,強調詞須配樂演唱的音樂屬性;李清照《詞論》意在主張詞、詩有別,其落腳點乃在提出‘詞別是一家;詞體之成熟且形成與詩并行之勢,是晚唐以后的事,中唐以前,‘詞主要為文人創作之齊言近體。”張海明先生的研究拓寬了《詞論》首句解讀的思路,學術研究不必拘泥于爭議性問題,發掘爭議背后的共識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李清照《詞論》引用了李八郎故事,學者對此故事進行考證,力求重釋《詞論》思想。柏紅秀結合唐宋史料,考證李八郎進京賽唱一事發生在中唐初期,姜榮剛則認為李八郎的故事經過李清照的大幅度改寫,對其原故事發生時間的考證并無意義。柏、姜二人都是以李八郎之例的解讀為基礎,對李清照《詞論》思想進行解讀,二人觀點的不同源于其研究角度的差異,柏紅秀認為,李清照以此例旨在強調杰出人士在歌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姜榮剛則認為,李清照“有意將李八郎的故事放到盛唐的歷史語境中,是為說明詞在新聲中產生,其創作自應首先適合歌唱”。美國學者艾朗諾則從女權主義批評理論的視角出發,用文本細讀法和歷史還原法,來重新建構李清照的歷史語境,他指出《詞論》開頭引用李八郎的故事體現了李清照作為一個女性,正試圖撼動當時的男性精英階層的傾向。
關于《詞論》并未涉及周邦彥的問題,主要有三篇學術論文,分別是徐小茹、吳思、張曉東三人所作。徐、吳、張三人皆認為周邦彥的詞符合李清照“詞別是一家”的要求,所以無需評論,只是三人的研究角度不同。徐小茹以《碧雞漫志》為證,分析了周邦彥在宋代的接受情況,并以《詞論》并未回避在世之人為依據,側面論證周邦彥的詞作符合《詞論》的詞作規范;吳思和張曉東都是對周邦彥的詞加以考證,發現“不論《詞論》中提到的鋪敘、故實、典重還是音樂性,在美成詞中都有著極好的體現”。對《詞論》并未涉及周邦彥的問題,學者從正反兩個方面加以論證,皆認為《詞論》未涉周邦彥是因為周詞符合李清照的詞學規范,可謂殊途同歸。
綜上可得,21世紀以來對《詞論》研究不僅涉及作者作年研究和寫作動因探析,還關乎文本細節研究。這些研究或達成共識,或存在爭議,但從創新性而言,關于文本細節的研究新見最多,值得仔細研讀。
四、價值研究
價值研究一直是李清照《詞論》研究的重點課題。20世紀的研究呈現三個階段:五六十年代否定意見居多;七八十年代從否定到肯定;90年代充分肯定。21世紀以來,學者對李清照《詞論》的價值研究沿著總體肯定的方向進行,不斷重衡《詞論》的價值,形成充分肯定與辯證看待兩種評價態度。
(一)充分肯定
21世紀以來,學者充分肯定李清照《詞論》的價值,主要從詞學發展和女性意識兩方面展開,約有四十二篇研究成果。
一方面,《詞論》為宋代詞學發展奠定理論價值,在我國詞學史上占有一席之位。顧易生是反思《詞論》“片面強調音律”、反對“以詩為詞”等舊說的第一人。吳瑞霞則指出,“別是一家”說代表了北宋詞論的最高水平,起到了規范并引導宋代詞學發展方向的作用。申煥以詩詞關系為切入點,提出《詞論》涉及“詞與詩的關系和詞的特質問題”,這在詞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余苓的研究從《詞論》要求的“協音律”和“詞體形式”兩個方面出發,發掘李清照《詞論》在詞史發展演進過程中的重要價值。此后,其他學者多沿詞“別是一家”的觀點進行研究,從李清照提出詞論創作具體要求出發,對《詞論》的詞學價值加以肯定。
另一方面,《詞論》作為女性所作的第一篇詞學專論,提高了女性在文學批評史的地位。王昊首先看到了李清照《詞論》中的女性主義話語立場,提出了“以女性主義批評的視角來闡釋以往女作家的理論批評和創作”這一新的研究視角。袁梅則從詞學本體精神出發,認為李清照對詞體的準確把握源于她作為女性的領悟與直覺,將其《詞論》置于詞學史、女性史乃至社會史的高度。饒迎的研究另辟蹊徑,選擇以《詞論》為文本,探討其中體現的李清照人文判斷、理性思考、知識體系,以及雅士情懷等文化人格,以此論證《詞論》的獨特價值。彭玉平指出,李清照《詞論》“融入了女性的冷靜細密和恢復詞體本原之尊的使命意識”,施劍南將其歸納為一種“神駿”之氣。此后,李晴、王高宇、孫奕菲、姜杉、劉韻智等學者對《詞論》中暗含的女性意識多加關注,從這一角度對《詞論》價值進行了充分肯定,谷卿更是直接指出:“詞作為一種合乎女性表達的文體,對李清照的意義顯然要超過其他男性作者。”
由此可見,學者對《詞論》的價值判斷往往從文學發展與性別意識兩方面展開,充分肯定了李清照所創作的《詞論》。
(二)辯證看待
除了單方面肯定李清照《詞論》的價值,還有一部分研究認為,對待《詞論》要采取辯證的態度,對其中合理之處充分肯定,但同樣不能忽視其不合理的一面。
21世紀始,高春燕是第一位采取辯證態度的學者,她通過分析《詞論》的創作背景和內容,肯定了作詞要重視音律,應有審美特點等主張,同時也看到其音律要求過嚴、過細,對蘇軾、王安石等人評價有失公允等片面性的一面。張海明先生的研究從音樂與詩的結合以及詞體的發展演變出發,梳理了歷代有關李清照《詞論》的評論,看到以往研究的不公允之處,并提出了一個新的主張,即不必強調對李清照《詞論》評價的“公正性”,更應關注其評價的“科學性”。彭國忠則從語源、學源、文本等角度展開研究,在肯定《詞論》價值的同時,指出《詞論》評論詞人的標準,對詞體的稱名,對聲律的認識和論述,也有許多混亂和錯誤。此后,劉倩、顧晶晶、王萬祥、鄭學識、劉明宇等學者多從音樂、審美和文體三個方面重衡李清照《詞論》的價值,既肯定了《詞論》對音律的追求,也看到其在詩與詞兩種文體劃分上的片面性,主張采取辯證的研究態度。
由此可見,21世紀前二十年的研究對李清照《詞論》的價值總體達成一致的肯定態度,但研究重點的不同導致出現了充分肯定與辯證看待兩種不同的研究主張。
《詞論》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女性創作的關于詞學創作的文章。自20世紀起,《詞論》研究進入現代學者的視野,至今仍不斷有研究成果出現。綜上可得,21世紀以來對《詞論》的研究涉及作者作年研究、寫作動因探析、文本細節研究和價值研究等方面,其中作者研究與寫作動因研究雖存在部分爭議,但基本認定《詞論》為李清照所作,其創作時間還有待進一步考證,這些研究中,關于文本細節的研究新見最多,值得仔細研讀。對李清照《詞論》的價值研究沿著20世紀的研究展開并不斷深入,仍是《詞論》研究的熱點,然而,寫作成因方面的研究成果還比較薄弱,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
作者:李夢露,寶雞文理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兩漢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