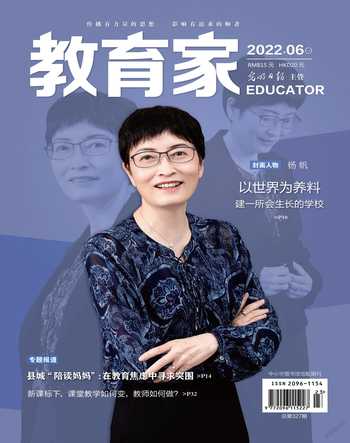馮果川:我們不培養未來的建筑師
周麗


馮果川
建筑師,兒童建筑教育推廣者、“童筑文化”創始人;現任筑博設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首席建筑師、筑博設計建筑工作室總負責人、海口經濟學院雅和人居工程學院副院長;著有系列兒童建筑讀物《一住一萬年》等。
兒童、建筑、教育,這三個平常的詞匯,組合到一起卻帶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并和“美”“創造”產生強關聯。實際上,在歐美一些國家,特別是以教育聞名于世的芬蘭,兒童建筑教育很早就被作為一種重要的藝術教育,用來培養孩子的審美力、創造力等。在中國,亦不乏有識之士在建筑與兒童之間搭建起素質教育的一隅天地——建筑師、“童筑文化”創始人馮果川便是其中的探路人。
從2012年至今,馮果川致力于推廣兒童建筑教育已整整十個年頭。盡管這一路上,作為“舶來品”的兒童建筑教育在國內的發展始終“叫好不叫座”,馮果川依然帶領團隊篤定前行,希望用建筑這種途徑,幫助孩子們收獲成長路上那些包括但不限于審美力、創造力的“更重要的東西”。
從建筑師到“教育家”
“建筑學最基本的就是在討論人與空間的關系,實際上建筑是人的生活狀態的一個反映,不僅僅是空間,還有時間。”保持對人、社會和時代的觀照,是一名優秀建筑師應有的職業修養,也是馮果川長期游走于建筑與兒童教育領域的重要動因。
多年職業生涯中,馮果川主要從事公共建筑的設計建造。作為頗高產的建筑師,馮果川擔任過國內多個大型重點項目的設計負責人。“海螺般的海南史志館、漂浮在呆萌綠島上的深圳光明區公共服務平臺、像果凍一樣Q彈的喜之郎集團總部大廈”,以及南方科技大學、深圳自然博物館、國銀民生雙塔、微軟科通總部、黃金交易中心、西麗文體中心等建筑作品,都是馮果川智慧和創意的結晶。
以專業技能積極影響城市空間的同時,馮果川也跨界整合城市設計、景觀設計、燈光設計、公共藝術等不同領域,推動城市整體藝術水準的提高,并通過寫作、研究等方式,保持對中國城市、建筑的反思與批判……無論是作為建筑師、藝術家還是“野生學者”,馮果川的成就都可圈可點。但這些“光環”,近年來越來越被“兒童建筑教育推廣者”的高光所遮蓋。
2012年,兩位女建筑師趙星和黃靜杰發起NGO組織“觀筑”,希望在建筑和大眾之間搭起一座橋梁,增進建筑師跟非建筑師之間的交流,其中也包括兒童。一貫主張“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建筑這種途徑來認識自己”的馮果川受邀出任理事,并作為主要擔綱者,同幾位建筑師共同開發了一套兒童建筑課程。
最初,這一課程被命名為“小小建筑師”。馮果川對此并不十分贊同:“兒童建筑教育并非培養未來的建筑師。”不久后,為了更忠實地實踐自己的兒童建筑教育理念和理想,馮果川創立了公共教育項目“童筑文化”,專注于以建筑學為媒介,引導和幫助孩子成長。
對于兒童建筑教育,馮果川總結道,其至少具備創造性、社會性、身體性和綜合性四個維度。在創造性維度上,由于建筑學自帶“人類無中生有的一種創造力”和“話題的開放性”等特點,兒童建筑教育可以對現在的“主旋律教育”進行調整,在其之外,給孩子們一個空間,釋放他們另一部分的想象與認識,培養他們的創新創造、獨立思考能力;在社會性維度上,兒童建筑教育可以引導孩子們嘗試團隊合作,同時關注社會,樹立社會責任感;在身體性維度上,兒童建筑教育可以把孩子們的身體帶回真實的世界,感受木頭的溫暖、鋼鐵的冰冷……更好地激活“身體的思維”,教會孩子們用身體去思考、學習;在綜合性維度上,建筑學作為一個“綜合了諸多學科、沒有清晰知識邊界”的專業,可以像線索一樣,串起不同的領域,開闊孩子們的視野,讓身處信息碎片化時代的孩子們學會鏈接和運用大量知識去討論、解決問題。
兒童建筑課要教什么?怎么教?
在馮果川看來,建筑師的一大工作就是虛構生活場景,其內核實質上跟小朋友玩過家家沒有多大區別,只不過建筑師玩的“過家家”更有知識含量。因此,建筑課完全可以變成一種游戲。
在架構課程時,考慮到傳統的建筑教育比較抽象,依賴圖面的表達,而圖上的建筑往往與現實中的建筑脫節,再加上兒童掌握精確的繪圖技術比較困難,不易理解功能之類的概念,馮果川和團隊確立了“讓建筑回歸現實”的原則,引導孩子盡量直接呈現建筑或場景本身,同時圍繞對生活的觀察和理解去討論建筑。
基于這些維度和對兒童教育不斷深入的思考,馮果川帶領團隊在兒童建筑教育領域進行了持續而珍貴的探索。
在“建筑游戲”中體認現實世界
馮果川介紹,當前“童筑文化”的課程大致可以分為基礎性課程和項目式課程兩大類。
基礎性課程包括觀察課、感知課、構成課、建構課等,主要是對孩子們身體、身體感覺及基礎能力的訓練,讓孩子們通過“玩”、通過身體的參與去學習。在這些課程里,孩子們感知色彩、認識圖形,接觸并運用真實的木頭、磚塊、水泥等材料,理解不同材料的力學特點,處理不同構件的搭接方式,等等。
“比如我們會給孩子們一把筷子,讓他們用這把筷子搭一個屋頂,唯一的要求是不會垮,而不設定這個屋頂下要有什么功能,是一個圖書館或是什么。然后讓他們先自己嘗試、探索,如果嘗試不出來,老師可以提供一些建議,教授一些結構知識和搭建技術。通過這樣反復的訓練,孩子們自己就可能找到一些方法,玩出自己的花樣。”
搭建課上,孩子們用充氣枕蓋拱,用水管做鞋柜、椅子,用竹篾編“籠屋”,用聚丙烯板建“帳篷”……玩出了各種各樣有趣的創意,并在自由的探索中識記了建筑學相關知識。
項目式課程則側重綜合性的訓練。以“童筑文化”正在實施的“理想之家”課程為例,馮果川和團隊會先讓孩子們回憶、講述家的樣子并默繪出來,再教授一些測繪方法,讓他們把家現實的樣子原原本本測繪一遍,然后讓孩子們對比默繪與測繪的家之間有什么不同,討論為什么情感記憶會帶來這些差異。之后讓孩子們在測繪的基礎上制作出家的模型,并引導孩子們從情感體驗出發,描述家庭的生活場景,審視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方式,去發現當下家庭生活的美好與不足,進而追問更理想的家庭生活,重構一個屬于自己的“理想的家”。
“學建筑實際上是為了理解‘我’是誰,‘我’怎樣在這個世界中生活、存在。”除了“反觀自省”,馮果川還希望通過兒童建筑教育,讓孩子們對所生活的城市、社會有不一樣的認識,并對其產生積極的影響。
“在深圳生活的孩子對這座城市的認知其實是很窄的。前幾年,深圳約有2/3的人生活在城中村,但中產階級的孩子可能從來沒去過。”為此,馮果川帶著孩子們到深圳的城中村行走,去看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特色的古建和民居,并在此過程中引導孩子們發現城市的另一面。
在深圳龍崗區,有一棟“像是從宮崎駿的動畫里走出來”、被稱為“龍崗怪樓”的建筑。這棟樓不僅外觀奇特,而且布局設計精巧,最特別的是,里面的家具都是用清水混凝土澆筑而成。馮果川曾多次帶孩子們去參觀這個片區和這座房子。當房子面臨拆除時,他們找到開發商,闡明這座建筑的價值,并做了很多研究,四處去宣傳。最終,這棟房子被列為保護建筑保留了下來,參觀“龍崗怪樓”也成了“童筑文化”的保留節目。
一個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馮果川和團隊帶著孩子們改造了社區的一塊公共區域。這塊區域此前被用來堆放垃圾和雜物,為了美化環境,也是為了給居民增加一個休閑的角落,孩子們搭建了一張圍樹椅,把一棵樹保護起來,同時形成了一個休息區。擔心還會有人往這個地方亂扔亂放,孩子們又繪制了漂亮的馬賽克畫,把畫嵌在地板上。“他們當然不會允許別人來堆垃圾蓋住自己的畫,所以這些孩子會關注這里。這些畫就像一道一道的符,鎮住了這個區域。”
不同于一般的培訓,兒童建筑教育對老師的專業性有較高的要求。“童筑文化”的授課老師基本上都具有建筑專業背景。馮果川堅持不去培訓“對建筑沒有多少理解、僅僅是照本宣科”的標準化老師,并要求老師本身要帶著很鮮活的個性色彩去跟孩子們互動。
“90后”的周慧星,2019年從深圳大學建筑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加入“童筑文化”。在他眼里,馮果川是一個“特別能跟小朋友玩到一塊兒的人”;而在孩子口中,他則被形容為如鄰家大哥哥般“既幽默又威嚴”。在馮果川的影響下,他被帶進兒童建筑教育這個“坑”里,越陷越深。為了打磨好“設計褶學”這門有別于傳統手工折紙課的DBL(基于設計的學習)課程,近半年,周慧星一頭扎進折紙這門“精深的科學”中,時時刻刻都拿著紙把玩、研究……
學員量大、課程標準化、老師成本低,是傳統兒童教育“做大做強”的三要素,這三個缺哪一個都不掙錢,而“童筑文化”似乎一個都不占。馮果川坦言,作為“非剛需”類的素質教育,“童筑文化”多年來都是投入性的項目。盡管“叫好不叫座”,他仍確信兒童建筑教育的需求是有的,建筑課對孩子們有一定幫助,并希望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吸引更多“同道中人”,把這件事做得再好一點。
目前,除了自主招生,“童筑文化”也與深圳的百仕達小學、香山里小學、南山外國語學校等建立了課程合作關系,為學校的課后服務和素質教育注入了新鮮活力。
陪孩子成長,重識建筑與自我
“建筑是嵌在人類本能里的,就跟老鼠打洞、鳥要筑巢一樣。應該把這種本能保護起來,同時也利用這種本能幫助我們成長。”
近十年來,除了投身兒童建筑教育,馮果川的身影也活躍在線下線上的公共平臺,向大眾分享建筑知識。至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馮果川每個月都會雷打不動地在深圳市中心書城開設一場公益講座,講授建筑歷史、建筑常識、城市認知和美學賞析等內容。
2016年年底,馮果川“突發奇想”——編繪一套“入門級”建筑專業知識圖本。他和長期的工作搭檔——建筑師、作家張莉反復討論后,最終決定從講述一萬多年來人類居所的變化入手。
“孕育”這套書的艱難遠超設想。前期,馮果川和團隊做了大量資料搜集和整理等工作,后又因具備建筑知識的插畫師很少,而且工作速度跟不上出書的節奏,馮果川“舍我其誰”地承擔起了大部分插圖繪制工作。張莉記述這套繪本的出爐過程時寫道:“在梳理了住宅的三冊內容后,大大小小的插圖量已經達到百張之多,而且許多古代建筑形式都沒有現成圖樣,需要從大量資料信息中分析提取,參考已有的圖文,還原出在建筑學上沒有錯誤的形式。這已經不僅僅是繪畫,而近乎建筑創作了……老馮決定豁出半年時間,用每天深夜處理完工作后的一兩個小時,把這些插圖慢慢畫出來。”
苦心醞釀三年,《一住一萬年》終得問世。這套圖本包羅了萬年間不同時空地域的人類居所案例,其間穿插著歷史文化知識點、專業名詞解析和著名建筑大師的趣聞軼事,不僅為孩子們提供了一把看世界的鑰匙,還因為文字有趣、插圖豐富而又不失專業性,引得很多家長,包括建筑師,看得津津有味。
11歲的丁丁向記者強烈推薦了這套書。丁丁是“童筑文化”最資深的學員。4歲時,他在書城聽了馮果川的一場公益講座,“就像磁鐵一樣,自然而然地被吸引”,此后便成了馮果川的忠實粉絲,每個月都來聽講,并加入了建筑課的學習——這只是丁丁此前報的十余個興趣班、輔導班中的一個,即使后來不斷縮減,丁丁始終堅定地保留了這門課。七年間,丁丁的媽媽張芮瑄明顯感覺到建筑課對于孩子的改變,這種改變不僅體現在身體協調能力、動手能力的提高上,更體現在邏輯思維、抽象思維及STEAM思維等的進步上。
問及未來的職業理想,丁丁作出了“肯定不做建筑師”的回答。在他看來,建筑課增加了他看社會、看世界的視角,教會了他把想法付諸實踐,這些才是最重要的——這正符合了馮果川辦兒童建筑教育的本心和追求。當然,馮果川也“失望”地看到,一些孩子受他們的影響選擇了建筑學專業,成了他們的“準同行”……
實踐兒童建筑教育多年,馮果川被稱為最懂兒童教育的建筑師。但他認為,教育是一種互動,是教學相長,把建筑學知識普及出去的同時,建筑師也通過教育活動收獲了孩子的天真和看問題的視角。在這種反哺下,馮果川在工作中慢慢向兒童傾斜,越來越多地承接幼兒園一類的設計。“因為有接觸孩子們的機會,更了解他們,我就更愿意為他們去創造一個建筑的空間。”
馮果川也希望這種反哺能傳遞到建筑學上:“與未來的主人翁聯合起來,共同分享我們對建筑、空間的感受和知識,共同面對和對抗現有空間對我們生活的異化。這樣,建筑學或許可以煥發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