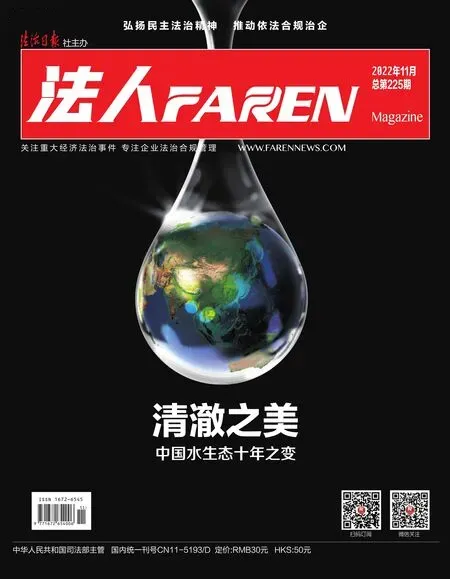長江“蝶變”
《法人》全媒體記者 李遼

“十年禁漁”令長江煥發生機
雪山格拉丹東的尾部,延續著一段5000米長的冰塔林,冰塔融化的淙淙細流,兩米多寬,20厘米深……這是長江西源——姜根迪如冰川,從這里開始,它化作亞洲第一長河,流經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在中華大地蔓延6300多公里。
近幾十年,人類活動的影響使長江流域生態環境急劇惡化,長江生物完整性指數曾到了最差的“無魚”等級。為治“長江之病”,黨中央多次開展長江生態大保護,1998年在長江上游等地區實施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黨的十八大以來重點布局長江經濟帶戰略,2021年長江“十年禁漁”和長江保護法幾乎同時實施。長江再現“一江清水、兩岸蔥綠”,實現了生態環境的綠色“蝶變”。
護源
長江源頭位于青海省西南部三江源國家公園,長江大保護從這里開始。
因為發源了長江、黃河、瀾滄江等大江大河,三江源地區因水而得名,被譽為“中華水塔”。每年,這里要為中國以及東南亞的5個國家輸送600多億立方米的清潔水源。
上世紀8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三江源地區受氣候變化和過度放牧影響,導致雪線上升、冰川退縮、土地沙化、災害頻發,給當地群眾生產生活及下游的發展帶來了嚴重威脅。進入新世紀,三江源地區建起了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累計投入244億元,實施了生態保護修復這一長時間、大規模的系統性工程。
2016年6月,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掛牌成立。為保護水源地,青海省對地處三江源地區的全部49處礦業權和水電站進行了注銷,其中涉及長江源的有19處礦點。“玉樹曲麻萊大場金礦,黃金資源儲量超過300噸,屬于超大型金礦。為保護好長江源頭,我們也毫不猶豫將其關閉,進行財政補償,并做生態修復。”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副局長孫立軍11月1日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稱,“如今遠遠望去,昔日人聲鼎沸的工地,綠油油一片,基本看不出開礦痕跡。”
三江源國家公園6年內累計投入62億元,先后實施了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保護修復項目,提升草地生態系統,修復荒漠生態系統,保護湖河生態系統,加強雪山冰川系統保護,強化濕地的保護與恢復。如今,長江源頭重現千湖美景。
舉全省乃至全國之力的保護力度,加上近些年受氣候暖濕化的影響,長江源過去5年年均自產水資源總量達到266.17億立方米,較1956年至2000年的多年平均值增加48.4%,這標志著長江源當前水生態和水資源整體向好,能持續穩定向下游地區輸送大量淡水。
三江源國家公園面積龐大,是美國黃石國家公園的21倍。如果把它算作一個省,它排在河北之前,位列全國第12位。“這么大的面積,光靠我們409個在編職工是保護不過來的。”孫立軍介紹,長江源有50多種珍稀野生魚類,大多是高原特有種類,“‘十年禁漁’政策實施之后,我們要落實各項‘硬措施’,確保源頭水的安全。”好在三江源國家公園設立了生態管護員制度,一戶一崗。這些生態管護員同時也是國家公園的信息宣傳員、監測員、治安員和攝影人員。
收網
雅礱江是長江上游金沙江的最大支流,落差大、峽谷深、水流湍急,是中國水能資源最富集的河流之一。
溫繼棻是四川省雅礱江木材水運局的退休職工。11月2日,他告訴記者,20多年前,站在雅礱江邊,看到的只有荒山禿嶺和滿江漂浮的木頭。
1998年夏天,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洪災,引起國家高度重視。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下,當年9月1日起,四川省六地共計57個縣460萬公頃的原始森林全面停止采伐,實行長年管護,這標志著中國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在四川率先啟動。溫繼棻回憶說:“當年10月,四川省雅礱江木材水運局掛起了‘四川省長江造林局’的牌子。從此,雅礱江趕漂人變身為長江造林人。”
“荒山造林改善了長江上游嚴重的水土流失問題。”如今,住在四川省攀枝花市雅礱江畔的他感慨,“近10年來,國家更是加大了對長江沿岸生態的保護。肉眼可見,江邊的山更青了,水更綠了,就連常年干旱少雨的攀枝花如今也時常出現云霧,濕度明顯增加。”
長江乃多魚之水,沿江老百姓對品食江鮮歷來有特殊情懷。“退休前,我常年在長江沿岸城市出差,從攀枝花到宜賓、瀘州、重慶、宜昌,處處都是吃魚的餐館,有的直接將餐館修到大船上,現場捕撈,捕魚網也在江面上常年撒開。”但在前些年,他明顯感覺到菜場里很難買到正宗的江魚,能售賣正宗江魚的飯館也是少之又少。
從事濕地生態與生態修復的重慶大學教授袁興中常年在長江、嘉陵江考察調研,他觀察到,“十年禁漁”之前,很多釣魚者釣完魚后,會將餌料包放入水中,誘魚聚集,方便第二天再去垂釣,“這種俗稱‘打魚窩子’的釣魚方式,不僅對魚類的生存構成威脅,對河湖生態系統產生的污染和破壞也是驚人的。”
袁興中稱:“重慶地區河湖岸線漫長,‘十年禁漁’之后,仍有偷偷打魚的人,但好在執法非常嚴格,監控手段也能跟上,那些被列入了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國家濕地公園、水利風景名勝區等自然保護地的水庫,建起了24小時自動監控系統。”
說到成效,他頗感欣慰:“過去少見的一些珍稀特有魚類,種群數量明顯恢復,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長江江豚的遇見率明顯提高。如今,國家水利部、農業農村部、生態環境部都從各自渠道開展了長江流域水生生物資源監測。”
“在河湖生態體系中,鳥類的生存依賴于健康的魚類種群,浮游生物又維持著魚類的健康生存,整個生命網絡緊密關聯。擁有完整的生物群落、復雜的食物網結構,才能保證河流的生物自凈能力的有效發揮,維持整個水生態系統的健康。”袁興中表示,實施“十年禁漁”絕不是因為我們沒有魚吃了,而是因為魚類多樣性減少,影響了整個水生態系統的長久維持:“這個政策不僅僅是在保護整個河流生態系統中最為重要的生物成分之一,實質上也是在維持對于河湖生態系統健康至關重要的水生食物網結構。”
放魚
“十年禁漁”政策雖實施時間不長,但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收效明顯。前不久,江蘇鎮江環境監測中心在豚類保護區水生態監測工作中,意外觀測到五六頭長江江豚在江面追逐嬉戲。
長江江豚是長江中僅有的水生哺乳動物,也是極度瀕危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是整個長江生態系統穩定性的重要標志。根據最新數據,在江蘇南京、鎮江、馬鞍山三市所轄的長江江段,生活著約100頭長江江豚,約占長江干流江豚數量的22%。近年來,得益于長江大保護,長江江豚出現頻率明顯增加。
去年6月5日,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淡水漁業研究中心工作人員在長江海門段監測到了野生河豚魚苗,這是20年來的首次,說明河豚已經形成了種群,而刀魚資源密度相比2015年至2018年的平均指標也增加了一倍多。
1995年出生的江蘇江陰女孩鄭冰清自5歲起,便跟隨爺爺鄭金良養魚、放魚,對水產養殖、生態保護產生了濃厚興趣。“爺爺告訴我,他小時候長江里的河豚、鰣魚、刀魚數量繁多,小伙伴們經常拿鰣魚去換大米。但在我出生的那年,野生鰣魚的價格已經漲到了10元一斤。”
1999年,鄭金良拿出6萬元積蓄尋找江上漁民幫他捕撈可以繁殖后代的河豚親本(動植物雜交時所選用的母本或父本),3個月后才捕到一雄一雌兩條,終于在第二年成功繁殖出40萬尾魚苗。他留下幾百尾用于之后的繁殖,剩下的全部放歸長江。
受爺爺影響,鄭冰清主修生物工程,與項目團隊成員一道對長江珍稀魚類的繁育機制開展了深入研究,陸續突破了長江瀕危魚類養殖、淡水大黃魚全人工繁育、瀕危淡水貝類繁殖等課題。
工作后,愛美的她常年穿著下水褲摸爬在鰣魚養殖溫棚,每天衣服、鞋子不知要干濕幾回,她便帶著三套換洗衣服上班。在團隊共同努力下,鰣魚養殖技術與品質獲得明顯突破。
多年來,鄭冰清累計向長江放流河豚等珍稀魚類和四大家魚魚苗1.7億余尾。她回憶,以前去長江放流,不僅參與的人不多,桶里還未放歸的小魚苗也經常被偷走。“但現在,很多愛心人士專程咨詢我們如何購買魚苗,想要一起放流,就連很多學生也自愿加入進來,每次放流工作不到30分鐘就能完成。”她指著江面對記者說。“爺爺常說,如果魚活得好,江面上看起來就像泛著一層油光。看,如今就是這樣的。”鄭冰清感慨,“‘十年禁漁’從呼聲到鐵律,是一件利在千秋、造福萬代的大事。如今,長江的魚真的變多了,這只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