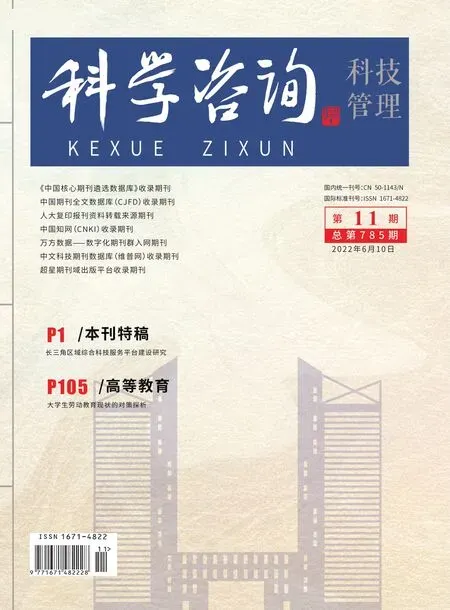接受美學視域下中國文化典籍的翻譯
張玲娟
(蘭州工商學院,甘肅蘭州 730100)
接受美學是以讀者為中心的文藝美學理論,強調作者通過自我創造,從讀者的角度考慮文學作品的創作,使讀者在閱讀中能積極、主動參與作品創造。這時,文學作品不再是毫無生命的客觀存在,讀者的參與賦予了作品生命力。文學作品能夠喚醒讀者的記憶,構建讀者的視野。由此可見,一部好的作品是在作者和讀者的良性互動中,共同創造出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進入新時代,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想、人文智慧和文化內涵。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在中國與世界的對話和互動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意義重要。在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中,以文學為載體、以翻譯為媒介的文學英譯發揮著重要作用。最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傳統典籍是中華文明精髓,內容豐富,數量眾多。中國傳統典籍的英譯是讓世界了解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重要途徑[1]。因此,中國文化典籍的英譯研究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十分必要。但如何讓外國讀者理解典籍中的人文智慧和文化內涵,即對中國文化美學視野的接受,是文化典籍翻譯不可回避的問題。
一、接受美學
接受美學的理論源于文學批評理論,以現象學美學和闡釋學美學為理論基礎,主要研究外國讀者對他國文學作品接受的變異。接受美學理論為比較文學研究開辟新模式,將作品與讀者的關系放在研究的首位,強調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和理解的意義[2]。接受美學實現了以文本為中心向以讀者為中心的研究方向轉移,成為西方文學研究的新方法。
姚斯從文學史的角度探討文學的接受問題,伊瑟爾從心理學角度提出文學接受的主要觀點,主要讀者期待視野、讀者接受方式、讀者的主體與能動地位、效果與接受史、審美經驗和文學解釋學等六個方面。雖然研究出發點不同,但各有側重,并相互補充。
起初,接受美學是一種以作者為中心,以文學作品為基礎的文學理論傾向。然而,隨著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與發展,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讀者的理解,這說明在文學作品的意義闡釋過程中,讀者的作用不可忽視。因此,審美接受逐漸從作者轉向讀者,演變成以讀者為中心的文學理論思潮。讀者的閱讀行為是讀者與作品之間的對話過程,是不斷生成、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過程。作家在進行寫作時,從讀者的角度思考文學作品的自我創造,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情感與思想。因此被讀者認可和接受的創作才可以被稱為文學作品,否則只是文本,換言之,一部作品只有在與讀者的良性互動過程中,使讀者將自己的視覺與作品的視覺結合起來,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才能有所體現。由此可見,文本意義的實現主要取決于原文作者、譯文譯者和讀者的主觀能動性[3]。三者相輔相成,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文學作品必須與讀者產生共鳴,才能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形成讀者積極的心理誘導,并逐漸接受作者的觀點和主張,這對文學作品的意義和價值起著關鍵作用。
二、接受美學對文化典籍翻譯的啟示
文化需要在不斷加深的交流和借鑒中得以傳播。好的文學作品不僅需要大量的讀者,更依賴于讀者的知識和大眾的接受。20世紀80年代,接受美學理論傳入我國,進入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之后,接受美學理論與翻譯研究的“聯姻”隨之開始。接受美學視野下的翻譯研究應運而生。與此同時,“戴著鐐銬跳舞”的譯者面臨著更大的挑戰。譯者不僅要理解作品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情感,還要將作品的翻譯放置在異域文化中的背景下,考慮譯文讀者對翻譯作品的認可和接受,最終接受作品和譯者的美學思想。在這個過程中,譯者具有多重身份,他們既是文學作品的讀者,又是文學作品的譯者兼創作者。積極澄清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是譯者的首要任務[4]。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必須充分考慮異域文化中,讀者的視域體驗,滿足讀者的審美需求,讓作品被讀者接受和認可。在讀者和譯者的雙重作用下,實現文本意義的價值,進而推動思想和文學的對外傳播。
中國古典文學體量龐雜,涵蓋古代的文學、史學、哲學等不同領域,是中國古代先人智慧的結晶,具有非常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文化自信”提出進一步促進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并通過不同形式的宣傳,進行對外傳播,得到國際認同。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學對外傳播的諸多方式中,典籍翻譯是直接面向國外讀者的傳播形式。中國傳統典籍擁有深厚的歷史沉淀、豐富的文化內涵、深刻的思想情感和獨具特色的語言表達形式,對譯者而言,挑戰不言而喻。因此,譯者深入探索傳統典籍的歷史、文化及語言,把握作品思想和情感。同時,還需要考慮外國讀者的意識形態、文化內涵、審美習慣和表達語言習慣等因素,最終才能將中國經典文學翻譯成英文作品[5]。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充分調動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不僅要讓外國讀者理解經典作品所表達的意思,還要積極創造出能被大多數讀者認可和接受的原文,真正實現文學經典的意義和價值。
(一)譯者的主體地位
伊瑟爾認為藝術作品中的多層次結構構成包含了意義的空白。讀者對文學文本的接受是一種闡釋活動,讀者通過反復閱讀和理解文本,闡釋文學作品的意義。文本意義的實現是一個漸進、循環和上升的過程。一部好的文學作品不僅具有靜態特征,而且具有動態效應。文本相對穩定,但對于譯者而言,要反復閱讀,理解作者的真實意思,不斷分析和總結審美經驗,不斷地與原作者的思想發生碰撞,直到實現與作者的視野融合。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積極參與對潛在意義的解讀,不斷做出期待、預測和判斷,填補文本中的“空白”。所以,文本意義的實現不是指原作者想要表達的意義,也不是譯者隨意曲解的意義,而是通過譯者的反復閱讀,在閱讀過程中實現譯者作為讀者的身份,不斷與原作者溝通對話,產生思想碰撞的產物[6]。因此,接受美學的研究者基本上接受了以讀者為中心的觀點。文學作品為讀者服務。當讀者閱讀時,其思想極其重要,占據著中心領導地位。但面對不同的讀者群體,他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思想觀念和教育水平。因此,文學文本的理解沒有明確答案。不同時代,閱讀同一篇文章,往往會形成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的理解[7]。
翻譯活動是一個由原作、譯者、譯作、讀者組成的翻譯—作品—接受的雙向互動過程。譯者是原作的讀者,即接受者,又是原文的闡釋者,即二度創作者。所以,在翻譯典籍時,譯者面臨的主要困難是應對歷史、文化、語言、哲學思想、意識形態等諸多差異,同時,在自身審美經驗的基礎上,充分考慮譯文讀者的美學經驗,對原文做出闡釋,做出最大限度地實現原文的意義,此時,兼具原文讀者和譯文譯者的雙重身份的譯者在翻譯中處于主體地位[8]。
(二)譯文讀者的期待視野
姚斯指出讀者閱讀作品時往往具有一種期待視野。“期待視野”是指閱讀一部作品時,讀者的文學閱讀經驗構成的思維定式或先在結構。當讀者閱讀的作品與自己的審美經驗和期待視野一致的時候,更容易接受作品的內涵,也能豐富讀者的審美經驗,但同時也很可能失去閱讀的興趣。但當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發現作品與自己的審美不一致,超過了期待視野的時候,讀者在積極參與理解和闡釋的過程中,豐富審美經驗,擴展期待視野,從而建立新的審美標準。
在翻譯典籍過程中,譯者既是原作品的讀者,又是譯文的作者。譯者身份具有雙重屬性。從接受美學角度出發,好的文本翻譯體現在以讀者為中心的主體層面,也體現在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層面。因此,譯者必須仔細閱讀和研究作者的古籍,以提高對原文的理解和接受。當譯者在翻譯前,從自身的審美經驗出發,積極參與原文文本的闡釋,以讀者的身份來理解作者的意圖。此時,譯者呈現出了讀者的期待視野。譯者的雙重身份決定了翻譯中必須考慮讀者的接受,這對文本翻譯具有重要意義[9]。譯者需要在充分了解決定譯文讀者的接受視域的知識水平、意識形態、文化特點及語言表達習慣等因素,結合翻譯目的和翻譯背景,在對原文充分理解的基礎上,做出適當調整,判斷文本內容的選擇,刪除一些不符合讀者需要的內容,并對具有中國文化內涵的內容進行解釋。所以,對文本內容進行必要的修改和審查,是基于譯者對文本的深入理解,是以讀者為中心的本質體現,也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必然要求[10]。
(三)接受美學中的審美距離
接受美學家認為讀者的審美經驗與作品之間存在審美距離。當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發現作品與自己的審美經驗一致時,不存在接受問題;但當作品與讀者的審美經驗存在不一致時,美學接受成為可能。讀者的視角是嬗變而不可預測的。典籍翻譯的國外讀者缺乏對中國文化的系統學習和認識,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大都停留表層文化,無法深入到中層文化和深層文化。由于讀者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差異,譯文讀者和譯文作者的期待視野是不一致的,因此,讀者對文本的理解相應存在差異,對中國文化的接受和理解都會受限,進而重建讀者的期待視野是相對復雜甚至困難的。也就是說,譯文讀者和譯文之間存在較大的審美距離。通常,審美距離能夠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對提升讀者審美經驗大有益處,但審美距離太大,讀者接受就很難實現。適中的審美距離是最佳選擇[11]。因此,為更好地構建讀者期待視野,譯者在翻譯文本時,應結合讀者的文化背景、社會環境、宗教信仰、藝術素養等因素,積極構建以讀者為中心的接受視野,探索適合讀者閱讀習慣和表現形式,調整或補充原文信息,達到讀者理解原文思想和文化的目的,進而在閱讀中實現讀者和譯者的視域融合。讀者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理解,有助于中國文化“走出去”。可見,譯者不僅是文本的創造者,也是文化的傳播者[12]。
三、結束語
中國是擁有五千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孕育了豐富而深刻的詩詞歌賦及文學作品。中國典籍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塊瑰寶,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中輸出文學作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典籍翻譯是外國讀者了解中國文化、領略中國智慧的嚴肅渠道。因此,譯者肩負傳播中國文化的使命和責任。美學理論為典籍翻譯提出了一個新的視角。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反復思考和探索文化,結合外國讀者的時代背景和語言習慣進行翻譯,以確保他們更好地接受譯文審美,進而能夠通過文本,更好地傳播和樹立中國優秀文化的形象,體現文本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