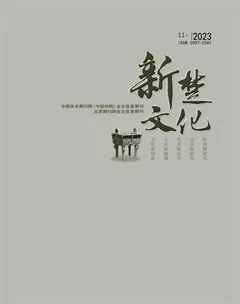《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消費性解讀
萬連增
【摘要】《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美國小說家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從讓·鮑德里亞的消費符號差異的視角分析,小說中的豪宅、華裳、名車等突出的消費符號,并不能反映擁有者真正的社會地位。蓋茨比終其一生實現了物質上的極大富有,并想通過物的符號意義實現他社會階層的跨越,因而其悲劇命運也終不可避免。
【關鍵詞】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讓·鮑德里亞;消費符號
【中圖分類號】I106.4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33-0028-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3.33.009
一、引言
美國小說家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美國現代主義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他的杰作《了不起的蓋茨比》(以下簡稱《了》)一經出版就在評論界備受稱贊。美國評論家理查德·利罕認為菲茨杰拉德在《了》中“以高超的技巧講述了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1]265。馬里厄斯·比利則稱贊這部杰作是“在美國最偉大的小說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品”[2]216。一眾評論家們不僅對小說藝術手法、語言特征、意象進行了分析,還著重分析了蓋茨比夢滅的原因與必然。
從讓·鮑德里亞的消費符號差異視角出發,《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描述的豪宅、名車、賽馬、游艇、美酒、華裳等均為典型的消費符號,具有超出其使用價值的符號意義。由于符號所標識的社會地位只不過是符號化的社會地位,是一種幻想,它并不能反映人們真正的社會地位,而蓋茨比想要在消費意識形態中利用物的符號意義來實現他的社會階層跨越是不可能的,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的悲劇命運。
二、瘋狂消費的時代
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是一個生產倫理讓位于消費倫理的時代”[3]16,一戰后的美國沒有像其他參戰國家一樣遭受戰爭的創傷,反而借機發了軍火財,進而美國的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使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類消費品涌入市場;傳統清教主義提倡的勤儉、節約、清潔與禁欲被極端享樂、鋪張奢華的各種聚會及炫目的消費所取代。因此,正如鮑德里亞所言:“我們處在‘消費控制著整個生活的這樣一種境地。”[4]5
羅納德·伯曼認為《了》中運用了“大量篇幅描寫工業產品和形式”[5]206。有商業主街、通宵餐館、如蛛網的高架鐵路和川流不息的車輛及專門報道百老匯丑聞的諸多雜志,也有大且豪華的電影院、五光十色的廣告牌和櫥窗,時時刻刻都在宣示著消費的喧囂,同樣也刺激著人們消費的欲望,“它們俯瞰小說的情節發展并提供了某些意義”[5]206,這些復雜的商品使消費者產生了更為復雜的動機。
湯姆的瘋狂消費僅從他的英王喬治殖民統治時期建筑風格的別墅就可見一斑,別墅面向大海,草坪從海灘一直延伸到門口,竟然有四分之一英里。他異常富裕的家境支撐著他在大學時代就備受指責的“揮金如土”,從芝加哥往東部搬家能夠把打馬球的全部馬匹都運過去,這種排場令人咋舌,也令人難以置信。這種上層社會引領的消費狂潮悄無聲息地席卷著整個社會,所有人都被裹挾著在時代的旋渦中掙扎,迷失了自我。在這種物欲橫流的搏擊中,人們看似搏擊奮進了,卻“好比逆水行舟,不停地被水浪沖退,回到了過去”[7]152,甚至連蓋茨比那個看上去并不完美的夢想也成了“人類最后的也是最偉大的夢想”[7]152的象征,但終歸于了破滅。
三、物的符號化消費
在消費社會,商品不再局限于使用價值,除了商品功能性的作用,消費由原始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轉換,變成了如今的消費社會中交換價值向符號價值的轉變,消費由物的消費成為一種符號化的轉換,從而轉為對符號的消費,對符號的追求遠遠超過對物的功能需求。鮑德里亞斷言:“消費就建立在符號/價值的交換模式上。”[6]149人本身就是一種符號化的存在,在消費與對消費的追求中,人也在被符號化與物化。
小說中不斷反復出現了一系列的消費符號——巨幅的眼睛廣告、豪華汽車、電影院和各類休閑雜志,這些消費符號深刻影響著蓋茨比,他選擇豪宅、名車、華裳、盛宴來彰顯自己作為成功人士的地位。故而,更吸引人們的已經不再是物品本身和物品的功能,而是被賦予某種象征性的符號意義或者說是具有社會價值的符號。菲茨杰拉德在《了》中對蓋茨比宛如市府大廈的豪宅給予了非常細致的描述,比如說他那棟別墅,無論用什么標準都算得上是龐然大物,像是諾曼底公爵領地內的古建筑,聳立著的塔樓,還有大理石砌的游泳池,草坪和花園就占地四十多英畝。蓋茨比的豪宅此時已經不再僅僅體現它的使用價值——可以供人棲身、遮風擋雨之所,更多的則是為了彰顯他的財富、身份與社會地位。擁有這樣宮殿似的豪宅對蓋茨比而言,其符號的象征意義則遠遠超越了房子本身的居住價值。除此之外,作為區分符號,它還被完全賦予了社會文化價值,蓋茨比希冀借助豪宅以及他在那里舉辦的豪華盛宴顯示他已順利擠入上層社會,成為其中一員,他已經不再是當年的窮小子。“既然物扮演著社會地位的體現者角色,并且既然這種地位已經具有了潛在的可變性,那么物也將總是在彰顯一種既有地位的同時,還要彰顯這一社會地位潛在的變動性。”[6]36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消費結構中,“物充分地展現了其主人的社會地位”[6]13。換句話說,“人們可以將物自身以及他們的總和視為某種社會成員身份的象征”[6]13。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除了豪宅,蓋茨比還對華裳和高檔汽車近乎癡迷。多年之后,蓋茨比與黛西的見面,他穿著“一身白法蘭絨西裝,銀色襯衫,金色領帶”[7]72,并當著黛西的面“打開了兩個名牌廠家制造的特大衣櫥,里面裝滿了他的西裝、晨衣和領帶,還有許許多多的襯衣,一摞一摞像磚頭一樣碼得十幾層高”[7]78-79。服裝所代表的社會身份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這個超級衣柜中,裝滿的襯衫已經不再是蓋茨比消費的真實目的,其真正的含義則是這些衣服所指涉的階層和身份,因為這些服裝暗示了一種社會身份、一種實際地位。
蓋茨比所擁有的高檔汽車有很多輛,有羅爾斯—羅伊斯轎車、黃色甲殼蟲旅行車,還有一輛彰顯主人地位與身份的加長豪華汽車。“車子是濃重的乳白色,鍍鎳部分閃閃發亮,長長的車身上這兒、那兒的鼓突出來,是內設的放置帽子、食品和工具的暗箱,別具一格。”[7]55這輛超出普通交通工具范疇的名車是“一種符號性的凸狀炫示”[8]25,通過購買這種超級酷炫的汽車,蓋茨比極力想凸顯自己已達到所期望高度的社會地位,自己已然躋身所謂上層人的行列。如鮑德里亞的所言:“某個體屬于某團體,因為他消費某財富;他消費某財富,因為他屬于某團體。”[4]51
顯然,蓋茨比的豪宅、華裳和名車不再是單純的商品,而是具有了社會價值的符號。蓋茨比期望這些所有物能證明自身的成就或證明社會地位變動的可能性。因為“物總是圍繞在他所隸屬的那個階層的周圍”[6]36。蓋茨比對豪宅、華裳和名車所暗示的符號價值深信不疑,并希望通過對這些符號的運用喚回黛西的芳心,最主要的原因是,最初處于更高團體的黛西首先吸引著默默無聞、一文不名的蓋茨比的,正是她漂亮的住宅、靚麗的服裝和雪亮的汽車。黛西的家使蓋茨比驚奇不已,從未進過如此漂亮房子的蓋茨比被深深吸引了,“這所房子帶有一種引人入勝的神秘感……使人聯想到今年雪亮的汽車,聯想到鮮花還沒凋謝的舞會”[7]125。窮小子蓋茨比“深切地體會到財富怎樣幫助人們擁有和保存青春與神秘,體會到一套套服裝怎樣使人保持清新靚麗,體會到財富怎樣使黛西像白銀一樣熠熠發光,安然高踞于窮苦人激烈的生存斗爭之上。”[7]126甚至黛西剛結婚后,痛苦的蓋茨比還重溫了他和黛西當年開著黛西那輛白色跑車所去過的地方。黛西漂亮的房子、香車與時尚的服裝直指黛西高貴的身份地位,處于社會下層的蓋茨比對擁有這些物品的黛西很是著迷,對她所代表的階層也是心生敬仰。黛西是蓋茨比所認識的“第一個‘大家閨秀”[7]125,這也就可以解釋多年之后,蓋茨比總是凝視著自己豪宅對岸的綠色燈火,并窮其一生想到達彼岸的原因。他癡迷于黛西,更多的是源于與黛西所匹配的大家閨秀身份以及被他不可企及但逐步描摹并符號化了的圣潔女神形象。
四、階層跨越的虛幻
社會分層不可能“僅僅根據一個物的清單就被界定了出來”[6]11。在傳統社會中,人們的地位和身份通常以擁有和占有物的總和來象征。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分層雖然不再有天生的貴族與平民的等級,但也并不是以是否擁有財物進行階層劃界。
鮑德里亞認為“借助于物,每個人以及每個群體都在某種序列中尋找他/她的位置,同時根據個人的發展努力擠入這一序列中。通過物,一個分層的社會出現了……它試圖將每個人放置到某個特定的位置上”[6]17。在消費文化的激勵下,蓋茨比開始竭盡全力要擠入黛西所在的那個序列,并試圖把自己放在想要抵達的位置。窮小子蓋茨比的父母是老實本分的鄉下莊稼人出身,但蓋茨比卻不愿承認自己低微的出身。為了擺脫窮困的境地,這個中西部的年輕人開始了他的宏偉計劃,從各個方面對自己嚴格要求,并與《富蘭克林》自傳中所提到的十三美德相比較。他拼命練習咬文嚼字,重塑自己的談吐,“說話字斟句酌,謹小慎微”[7]44;他舍棄精神上、內在品質的提升,轉而選擇丹·科迪快捷而實際的物的操控。為了能夠很快地擠入富人行列,17歲的他來到明尼蘇達州南部路德教的圣奧拉夫學院,希望在此能夠改變命運。然而他卻很快離開,因為學院不屑于窮學生不切實際的夢想,也因為他自己不屑困于學費而疲于勞作。后來蓋茨比在蘇必利爾湖干雜活時遇到了丹·科迪,這位靠采金礦銀礦、做銅的生意發大財的大人物。聰明伶俐且雄心勃勃的蓋茨比很快便追隨在科迪左右。科迪的揮金如土,各種奸詐伎倆讓蓋茨比成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了”[7]86。科迪的引領為蓋茨比后來與邁爾·沃爾夫山姆的合作做了鋪墊。他們買了很多小街上的藥房,并且不用處方就把酒精賣給人家以牟取暴利,蓋茨比就通過這種方式一夜暴富。
然而,“消費符號蘊含著的意識形態,給人一種虛假的承諾,讓人信以為真”[9]142,消費者被嚴重異化,“在符號系統的異化中……符號所標識的社會地位只不過是符號化的社會地位,是一種幻象,它并不能反映人們真正的社會地位和主體的個性”[9]142。
擁有豪宅、華裳、名車甚至水上飛機和數不清財富的蓋茨比舉辦奢華喧囂的酒會,揮灑重金,希望用最短的時間結識上流社會的人士,并希望通過這些派對,讓大家接受他為其中的一員,進而把自己塑造成上流社會的人,實現自己地位向上流動的目的。小說中的富家子弟湯姆·布坎南——黛西的丈夫,也喜歡在同類人中扎堆,“他們在法國待了一年,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然后來回游蕩,居無定所,只要哪里有玩馬球的,有富人,他們就往哪兒去”[7]7。但來參加蓋茨比狂歡宴會的“上層人士”并不認可蓋茨比的暴富身份,關于他的謠傳與污蔑也層出不窮,“有人告訴我說他殺過人”[7]38“多半他在大戰時當過德國間諜”[7]39“我敢打賭他殺過人”[7]39“他是個販賣私酒的……有一回他殺了一個人……他是興登堡的侄子,惡魔的表兄弟。”[7]53可見蓋茨比借助消費狂歡拉升自己社會地位的想法,顯然沒有實現。湯姆直接質疑蓋茨比的身份,他突然質問尼克,“這個姓蓋茨比的究竟是誰?”“一個大私酒販子?”“你知道這樣的暴發戶中很多人是大私酒販子。”[7]91甚至,連帶參加宴會的這些人的身份也受到了質疑和鄙視,“我說,他一定費了很大的工夫才搜羅到這么一大幫牛頭馬面”[7]91。當發現蓋茨比要和他搶黛西,對他的地位產生威脅時,湯姆則毫不猶豫地深入調查蓋茨比,并一招制勝。“我早已發現你那些‘藥房是搞什么名堂的。”[7]114湯姆對蓋茨比水火不容,揭其老底,直接讓本已投入蓋茨比懷抱的黛西選擇退縮與回避。盡管蓋茨比竭盡全力在黛西面前為自己辯護,“但是他說的越多,她就越往后縮,置身事外,不理不睬”[7]114。
蓋茨比本指望借喧囂的酒會,依賴物的消費狂歡來實現自己的階層跨越和人生夢想,豈不知這是已固化的統治階層制造的消費幻想,“消費建立在對個人需求的滿足之上,所以消費看上去曾經是一種普適的價值體系,但實際上它不過是一種制度、一種道德而已”[6]55-56。換言之,消費成為民主的借口,并被偽裝成“一種民主社會功能”,“如同一種階級制度一樣發揮著作用”[6]49。美國社會宣揚平等、自由、民主,并對民眾宣稱只要在美國經過堅持不懈地奮斗,就可以獲得更好的生活,實現物質上的成功。這白手起家、走向成功的階梯的美國夢已然猶如這個消費夢魘。消費的秘密“在它的虛假的社會外衣之下,掩蓋了真實的政治策略”[6]54。事實上,這種作為普遍價值體系的消費不過是統治階層遮蓋階級對抗和控制社會的另一種手段而已,消費“在過去和未來都曾經或者將會是任何社會中權利策略的一個要素”[6]56。
五、結語
“人們依賴物,而物充其量不過是顯現了他們無法實現的社會期望。”[6]36-37蓋茨比在這種消費幻想下,企圖借助物的消費來抵達新的階層,其悲劇性不可避免。祥和的普遍性消費幻想之下,隱匿了一層更深、更強的控制意圖,物的消費掩蓋了真正的社會分層和對抗性階級結構,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遮蔽。蓋茨比借助豪宅、華裳、名車和流光溢彩的酒會來提升自己,追求階層提升,卻終無奈穿、住、行這些看似沒有價值取向的消費,這不過是上層統治階層為掩蓋階級對抗和控制社會而采取的手段。這種消費力的幻想,實則是社會區分的真實力量,奢侈品的消費或者說物質層面的優越并不能視為階層的躍升,而只是較低階層表達階級的社會預期和愿望的一種虛幻參與。
參考文獻:
[1]程錫麟,編選.菲茨杰拉德研究文集[C]//理查德·利罕.《了不起的蓋茨比》——文本作為建構:敘事情節與展開.陳愛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2]程錫麟,編選.菲茨杰拉德研究文集[C]//馬里厄斯·比利.菲茨杰拉德對美國的批判.陳愛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3]程錫麟,編選.菲茨杰拉德研究文集[C]//馬爾科姆·考利.菲茨杰拉德:金錢的羅曼史.孫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4]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
[5]程錫麟,編選.菲茨杰拉德研究文集[C]//羅納德·伯曼.《〈了不起的蓋茨比〉與現代時期》導論.程錫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6]讓·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M].夏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7]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姚乃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8]張一兵.消費意識形態:符碼操控中的真實之死——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解讀[J].江漢論壇,2008(09):23-29.
[9]李輝.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的符號批判[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01):14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