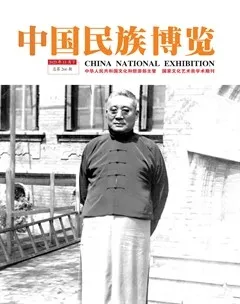音樂期待,一種音樂美學觀點:人們對音樂風格的敏感從何而來?
【摘 要】近代以降,關于自律論與他律論的爭端逐漸走向雙方均無法自竭的困境,與此同時一種新的美學觀點——音樂期待逐漸走進人們的視野。通過討論邁爾音樂期待理論中,期待的產生、依據和結果,探討其在大眾型音樂教育中的啟示作用是本文主要的討論內容。
【關鍵詞】音樂美學;邁爾期待論;音樂教育
【中圖分類號】J6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3)22—091—03
談及音樂風格,總會有人將其形容為一種屬于“內行人”的游戲,通過音樂片段的只言片語就能夠判斷這部作品的風格年代、作曲家甚至能夠說出該片段的準確名稱。然而,音樂風格的建立真的這樣神秘嗎?換言之,是否可以對音樂風格的建立“有意為之”呢?這一問題也或許可以在美國音樂美學家倫納德·B·邁爾的論著中得到答案和幫助。他提出了這樣一個有別于20世紀“自律論”于“他律論”的新概念——音樂期待。這一概念一經提出就轟動一時,以至于影響美國五十年的音樂教育審美主義哲學的奠基者貝內特·雷默也深受其啟發。
事實上,邁爾作為“自律論”與“他律論”爭辯的親歷者,難免會發現被前人有意無意所遮蔽的一些事實,對于音樂之意義的理解到底應當從何而起,是邁爾集中討論的問題,并將其研究主要分為音樂期待與音樂風格兩個部分。如果需要僅僅用一句話來概括邁爾的理論即是:音樂期待通過沖突產生,累計的音樂期待經驗會形成音樂風格。盡管解決大眾音樂教育的問題并非邁爾的初衷,但作為帶有音樂教育思維的后來研究者,當以何種眼光來看待這一問題,并將其運用到課堂之中,是筆者接下來要討論的問題。
一、期待的產生:“刺激”“沖突”心理過程的統一
“沖突”是一個心理學范疇的名詞,由杜威提出的刺激——反應發展而來。杜威認為刺激與反應、感覺與運動這兩組關系各自的意義只能在運動回路(即感覺)中的位置和作用中得以實現,這套完整的行為——感覺—運動的協調永遠先于刺激,刺激再顯現于這個協調:“感覺或意識到的刺激本身并不是一個事物或存在,它是在一個協調中由于協調內部發生了沖突而不能確定如何去完成協調,因而引起注意的那個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追尋結果就是刺激。刺激就是對于可能作為刺激的運動的反應。”[1]
米德在進一步的討論中,將“姿態”這一概念加入到這一過程之中,姿態意味著態度。其中有聲的姿態對人的行為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憑借作為表意符號的姿態,心靈或智能的存在才是可能的。”[2]借由這種思考方式,米德補充發展了“刺激”的觀點,提出了“沖突”這一概念,即行為與人們的歸類發生沖突時,偏離產生,由此引發主體的情緒變化。需要辨析的一點是,“刺激”是一個物理概念,是違背習慣而產生的客觀行為;“沖突”是當下的感覺與之前的經驗產生相左的內容,因此,“沖突”是人心理上加工過的“刺激”。
這些觀點對邁爾對音樂期待的產生過程的論述有極大的幫助,也導致了其音樂美學充滿了心理學的意味。邁爾沿用了杜威關于“刺激”的觀點以及米德對“沖突”的重新定義。在《音樂的情感與意義》中,邁爾這樣解釋:“當一種趨向反應被抑制或者被阻止,情感或感情就會被喚起”[3]。放入音樂中即是說,簡要言之:當我們聽到的音樂屬于我們掌握的音樂經驗時,音樂期待不會產生;而當我們聽到的音樂超出我們所掌握的音樂經驗,習慣被打破成為刺激,從而心理上的沖突產生,引發人們去尋求接下來發生的有聲姿態的意義。
二、期待的依據:實用主義哲學——經驗與學習
首先,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斯將思想的根本特點規定在時間之中,因此,實用主義的許多觀點都包含著“過程”的意味:每個思想都通過其周邊與其他思想的接觸,構成在過程中發展的思想流,由此一切的哲學概念都可以放入經驗的范疇進行討論。關于習慣的論述在詹姆斯的思想體系中占有很大比重,詹姆斯認為,習慣是物體受外力作用而產生的適應性變化過程,甚至可以說,每個動物都是由習慣造就的。人的習慣分為兩個部分,一種是本能的,它發生于一定的結果但未預見到結果的行為之中,而且無需經過教育,是一種無意識的習慣;而另一種是后天習得的,強調主體學習的作用,這種習慣較前一種更加準確,且發生于有意識的情況之下。
邁爾首先將“過程”的觀點放入音樂期待的理論中,由此提出了音樂事件連續不斷的認知模式作為基礎,在此之上才有可能(期待不是一定會發生的)產生對音樂的期待,因此,審美經驗的實現也不是一件一勞永逸的事件,它只是在人的認知水平和復雜環境中得以短暫的平衡。其次,邁爾同杜威一樣,認為思維的經驗具有它自身的審美性質,經驗本身就具有相對系統的情感性質,因為它可以通過內部自竭的,和系統的運動而實現完整性。邁爾在《音樂的情感與意義》中也有類似的表述:“這些來自人類心理過程性質的期待,總是被那些在特定的音樂風格中所呈現的材料和它的組織的內在的可能性和或然性所制約。”[4]而風格,這一存在于音樂之中的框架,取決于集體的文化經驗。
或許正如杜威在《藝術即經驗》中說的那樣,“為了理解藝術產品的意義,我們不得不暫時忘記它們,將它們放在一邊,而求助于我們一般不看成是從屬于審美的普通的力量與經驗的條件”,從本質上說,藝術的萌芽就孕于經驗之中,而人類經驗本身也包含著審美知覺的允諾。
三、期待的結果:音樂的內涵
(一)席勒:審美教育論
首先,邁爾認為,期待的結果和最終目的是通往審美的自由。關于此種的論述,可以從席勒的教育審美論中找到依據。席勒首先從時代背景出發,回答了“美是什么”這一問題:“理想的藝術必須脫開現實,必須堂堂正正地大膽超越需要;因為藝術是自由的女兒,她只能從精神的必然而不能從物質的最低需求中接受規條。”[5]
席勒認為,進行審美教育的出發點是尋求一種讓道德社會存在于自然社會之中的支柱,讓人兼具生存能力和人性與道德,而這種第三性格、這種“支柱”就是“有教養的、全面的人”,就是高尚化的性格:“這種性格(所謂的‘支柱)和那兩種都有連帶關系,它開辟了從純粹是力的支配過渡到法則支配的道路,它不會妨礙道德性格的發展,反倒會為目所不能見的倫理提供一種感性的保證。”[6]而通往這一目的的道路,就是通過比古希臘更高的藝術即審美教育來恢復人們天性中的完整性。然而,席勒在寄給奧古斯滕堡公爵的第十封信中這樣說:“這就有必要預先提出一個美的概念,它的淵源不是經驗,因為通過它應當認清,經驗中所說的美是否有理由用這個名稱。”如此看來,席勒雖認為審美教育的最終目的不在“美”之內,但也同樣肯定“美”的概念應當從人的純粹理性概念中得出,完全是產生在“感性”之內的:“我們甚至樂意讓想象力更勝一籌,因為在這里,歸根到底,只是一種感性力量戰勝了另一種感性力量。”[7]
同席勒一道,邁爾也沒有在音樂意義存在于何處的問題上作出非黑即白的選擇。一方面,邁爾盡力規避談論音樂以外的音樂藝術的價值,另一方面,邁爾又因風格的介入承認藝術的價值在于選擇性的創造,即在風格結構內一定程度的偏離,從而引起特定人群的期待,而這類“特定人群”又有文化信念所規范。正如羅格·斯庫頓所說:“雖然音樂需要個人的理解和聆聽,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將它作為一種社會的姿勢去聆聽的話,我們就會感到全然的失落。”
(二)文化相對論
其次,邁爾以此作為依據進一步闡述,期待的結果在于實現音樂的內涵,“音樂內涵是聽者感到某音樂事件所具有的概率在起作用”[8],而音樂事件發生的概率又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文化信念與態度,即生長在同一文化模式(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相互聯系的各種現象以及受其制約的形成的一個綜合體[9])中的人群所共有的,聯想的生成物就是內涵,所以對音樂內涵的理解,應立足于不同文化信念和態度之上。例如,對于“死亡”這一命題,西方國家偏向將其描繪為緩慢的音樂,伴以音域低沉的銅管樂器,而在中國,人們偏向于使用相對中速的音樂,并伴以音域高亢的樂器(如嗩吶)。對于這一命題的不同反應,來自于不同文化對“死亡”的態度,而非個體聯想差異的結果,也非個體對音樂理解差異的反應。由此,邁爾將音樂內涵的文化屬性作為情緒走向情感的轉折點,認為“情感體驗正是比情緒體驗具有更多認識和思想成分的高一層次的感受”[10]。進言之,音樂內涵必須滿足文化的“共性”,從而期待的結果才會由私人化的想象邁向集體審美的風格范式。
四、新的路徑:對于音樂教育的啟發
由于國內鮮少有關于音樂期待理論下沉至本國音樂教育理論體系的先例,筆者僅從上述期待的產生、依據、結果與價值對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第一,善用“偏離”的練習。需要說明的是,此處所說的“偏離”是具有要求的。教師需要通過對音樂的分析,運用具有特點的音樂要素進行該內容的練習。教師要找到適合做“偏離”內容的素材,通過挑戰學生既有的音樂經驗,以獲得音樂風格的豐富。
第二,不要懼怕重復的練習。這里所說的重復,并非一直使用同樣的教學環節、教學步驟甚至教學素材。而是通過同樣的心理路徑讓學生將這一回路變成習慣,從而釋放一部分注意力至音樂本身。
第三,從文化本身提出要求。如前文所述,人是存在于文化背景當中的,因此在設計課堂教學的過程中,應當關注學生本民族的音樂習慣、音樂語匯與音樂表達方式。不能強求學生一瞬間敞開心扉,這一特性并不在中國傳統的音樂文化信念當中。因此,找對方法循循善誘才能讓學生保持對音樂課堂的興趣,從而搭建起其今后直面音樂的橋梁。
第四,遵從音樂意義發展的客觀規律,切勿拔苗助長。音樂意義的發展是具有階段性的,是一個從模糊到清晰的過程,教師應當順應這一規律,而不是將音樂情感與語言的表述簡單對應起來。例如,跳躍的音樂就是“歡快的”,小調的音樂就是“悲傷的”,這種標簽化的表達和對應只適用于簡單的音樂情感,并不適用于復合型情感的音樂(如馬勒《第一交響曲》第三樂章),在培養學生完整的音樂欣賞習慣和系統的音樂經驗等方面同樣不樂觀。一方面容易使學生的音樂體驗高度標簽化,另一方面容易走入機械主義的困境。
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這樣說,“偉大藝術中的烏托邦從來不是現實原則的簡單否定,而是它的超越的持存。在這持存中,過去和現在都把它們的影子投射到滿足之中。”筆者由衷希望,音樂教師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尋求更多的方法,使學生的音樂生活從碎片變得完整,并可以使一生的精神生活都在這“持存”中受益。不管是歌唱、聽賞還是任何音樂活動,都不能將其進行簡單化的處理。一方面,使得普通音樂教育能夠盡量消除與專業音樂教育之間的壁壘,另一方面在野心勃勃的精英主義面前表現出一種謙卑——順從文明的再造,才能走向審美的自由。
參考文獻:
[1] Dewey J.The reflex arc concept in psychology[J].Psychological Review,1896(4).
[2](美)喬治·H·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M].趙月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3][4](美)倫納德·B·邁爾.音樂的情感與意義[M].何乾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5][6](德)弗里德里希·席勒.審美教育書簡[M].馮至,范大燦,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德)弗里德里希·席勒.秀美與尊嚴[M].張玉能,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
[8]Leonard B Meyer.music,the art,and ideas:patterns and predi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culture[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9](蘇)尼·切博克薩羅夫,伊·切博克薩羅娃.民族、種族、文化[M].趙俊智,金天明,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5.
[10]高拂曉.期待與風格:邁爾音樂美學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劉垚佳,女,漢族,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音樂教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