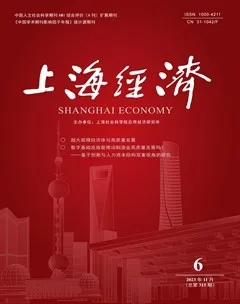上海新經濟企業發展現狀與成長因素研究
余麗甜 張延人



[摘要]促進新經濟企業成長以全方位激活新經濟產業是頂住經濟下行壓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區域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產業大數據庫,首先利用文本挖掘技術對上海新經濟企業進行識別。在此基礎上,對上海新經濟企業發展狀況以及成長能力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本文發現,上海新經濟企業數量連年高速增長且疫情防控期間仍保持快速增長之勢;企業平均年齡為7.02年;行業分布高集中度特征明顯;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區,且在靠近江蘇一側的西北方向的企業密度要遠高于靠近浙江一側的西南方向的企業密度。從經營質量來看,實現新經濟的長遠穩健發展仍充滿挑戰,主要體現為新經濟企業以小微企業為主、約20%企業資產負債率超過100%,有近五成的企業處于虧損狀態。進一步回歸分析發現,盈利能力、良好的債務與股權融資環境能顯著促進新經濟企業的成長,并且對發展初期的企業作用更強。最后,本文對推進上海新經濟企業發展提出針對性意見。
[關鍵詞] 新經濟企業;發展現狀;成長
[中圖分類號] F062.5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0-4211(2023)06-0091-16
一、引言
發展新經濟已成為世界各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提升核心競爭力的戰略重點(鈔小靜等,2021)。我國在2011年“十二五”規劃中就提出重點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由此新經濟在中國開始了快速發展的勢頭。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了中國特色的新經濟涵義。2017年,十九大報告則提出要在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新動能。十九大以來,在高質量發展的引領下,新經濟在國內迅速發展,逐漸發展形成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主要特征的“三新”經濟。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三新”經濟占GDP總量約16.3%,在經濟受新冠疫情嚴重沖擊下,“三新”經濟依然呈現逆勢正增長態勢。可見,新經濟已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不容忽視的力量。
相比于傳統企業,新經濟企業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通用數字技術為核心基礎設施,具有成長迅速、能快速適應行業變革和新的市場形勢、企業經營和管理依賴于數據資產等特點(許憲春等,2020)。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新經濟企業形成了知識密集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經濟結構的優化以及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目前,各省市均在積極部署和推進新經濟產業布局和發展,對沖疫情的不利影響(王克強等,2021)。上海作為我國經濟中心城市,是我國數字化轉型發展的排頭兵,也是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的關鍵節點城市,具備發展新經濟的堅實基礎和比較優勢。上海市“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了強化高端產業引領功能,加快釋放發展新動能的發展要求:到2025年底,上海數字經濟占全市GDP比重要大于60%,產業集聚度和顯示度明顯提高。為了落實這一要求,上海將在新型網絡、智能計算、工業軟件、區塊鏈、數據要素市場、數字醫療、智能制造、低碳能源、數字城市、智能出行等10個領域,推進建設重大新賽道支撐工程,為相關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提供基礎設施支撐。
新經濟企業是新經濟組成的最基本單元。目前學界對微觀層面新經濟企業的發展狀況與特征以及更為重要的新經濟企業成長問題關注尚少。因此,本文以大數據分析技術為基礎,利用文本挖掘技術對上海新經濟企業進行識別。在此基礎上,從“量”和“質”兩個方面對上海新經濟企業發展狀況和特征進行分析,并進一步研究影響上海新經濟企業成長的因素,從而為推動上海新經濟發展、提升城市能級與核心競爭力,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提供可靠的實證依據并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新經濟”一詞最早出現于1996 年美國《商業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指的是在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下產生的以高經濟增長、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失業率為特征的新經濟形態。伴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及其與實體經濟活動的不斷深入融合,衍生出了更多新型經濟業態,目前新經濟的內涵已經遠遠超出最初的狹隘定義。新經濟是信息技術引領的以創新為發展驅動力的新經濟形態在學界已經達成共識,但對于新經濟具體內涵的界定,學術界尚處于百家爭鳴的狀態。2016年我國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經濟涵義:不僅包括三產中的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電子商務等新興產業和業態,也包括工業制造當中的智能制造、大規模的定制化生產等。Scott(2016)提出新經濟是在知識經濟的基礎上,由電子計算機、電子通信等新技術革命引起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以及經濟運行規則等的變化。戚聿東和李穎(2018)認為新經濟是相對于傳統經濟提出來的概念,因此與信息技術及其應用相關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均可歸到新經濟范疇內。任保平(2020)也提出相類似觀點,認為新經濟是一種以信息化和互聯網技術創新及其應用為內核的新型經濟形態。李曉華(2018)認為新經濟以新一代互聯網技術群、新一代信息技術等重大技術創新為核心驅動力,以數據作為重要生產要素,通過與其他產業深度融合對傳統產業產生了變革性影響。由此可見,新經濟是信息技術發展不斷滲透和應用到經濟活動中所衍生的各種新型經濟形態,并隨著技術發展過程的演進,新經濟呈現出更加豐富多維的業態。
還有一系列文獻聚焦于探索新經濟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轉型的作用機制和理論。陳維濤(2017)指出創新驅動是新經濟的核心內涵,這是新經濟得以長期穩定增長的重要因素。荊文君和孫寶文(2018)基于索洛模型,指出數字經濟可以通過三條路徑促進經濟增長, 即增加要素投入或調整要素比重、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并且數字經濟還具有一種類似斯密提出的自增長模式。姜江(2018)認為新經濟是以技術進步、需求升級和資源要素條件變化為動力,對支撐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具有重要作用。許憲春等(2020)指出,新經濟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可以通過降成本、降能耗和碳排放、增加就業以及依賴于數據資產打破以往自然資源有限供給對增長的制約等方式促進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汪連杰(2017)認為新經濟的發展體現了我國以創新為主的新發展理念,與以往的經濟增長模式相比,新經濟有著不一樣的增長動力,優化了資源配置以及經濟結構。
新經濟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并正衍生出以往所未出現的全新業態。雖然許多學者意識到新經濟的運行在技術特征、組織結構、產業組織等方面都迥然異于傳統經濟,新經濟的發展對政府規制、產業政策、制度和市場環境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李曉華,2018;戚聿東和李穎,2018),但國內對如何促進新經濟發展的問題關注依然較少,從微觀新經濟企業成長視角的研究更少。許憲春等(2020)基于對全國九省市29家新經濟企業的調研情況,對新經濟企業的特征以及發展中所存在的困難進行分析,指出稅負過重、政策掣肘、人才和數字基礎設施不足等因素是我國新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杭敬等(2016)基于上海普查數據,對上海新經濟總量規模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測算和研究,發現2013年新經濟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為21.8%,所屬大類行業的增加值、從業人員數量和資產規模是影響新經濟規模的重要因素。前者樣本數量有限,所得結論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后者雖然基于微觀企業數據,但也只是從行業層面上對新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缺乏企業微觀的視角。
可見,現有文獻對新經濟內涵與新經濟的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有益探討,但依然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其一是,對新經濟內涵和界定尚未達成共識,因此新經濟范圍與分類缺乏明確的界定。同時,由于新經濟在一、二、三產中跨界共生、滲透融和,現行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不能明確找到它們所屬的門類,直接使用宏觀統計數據較難準確反映新經濟的規模和發展狀況;其二是缺乏微觀企業視角的研究,新經濟企業是新經濟組成的最基本單元,新經濟企業發展狀況和成長的研究亟須深化。
三、上海市新經濟企業發展狀況分析
(一)新經濟企業的識別
新經濟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并正衍生出以往所未出現的全新業態,新經濟產業的統計口徑難以確定下來。本文參考了杭敬等(2016)所使用的方法,對新經濟企業進行篩選,具體步驟如下:(1)以國家統計局《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統計監測制度(2021年)》與《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統計分類(2018)》為基礎,提取擴充構成包含957個關鍵詞的“新經濟詞典”;(2)以復旦產業大數據庫為數據源,獲取各企業“經營范圍”字段作為文本挖掘對象;(3)基于步驟1構建的“新經濟詞典”,使用Python軟件內的jieba分詞組件將各企業“經營范圍”所對應的文本切分成詞語;(4)遍歷各企業“經營范圍”的分詞結果中是否包含“新經濟詞典”中出現的特征詞語,包含的則被認定為新經濟企業。
通過文本挖掘篩選出具有新經濟特征的企業后,我們剔除了無繳納社保記錄的企業,根據分析目的做了進一步的篩選后形成了3個樣本組:
樣本組1。組內企業具有完整的經緯度與成立時間信息,2021年含36.37萬家新經濟企業,該樣本組主要用于繪制上海市新經濟企業年齡分布圖。
樣本組2。組內企業具有完整的行政區劃代碼、所有制類別與行業類別信息,截至2021年含28.27萬家新經濟企業,該樣本組用于分年份、行業、所有制與行政區分析新經濟企業特征。
樣本組3。組內企業具有完整的經緯度、所有制類別、行業類別與財務信息,截至2021年含8596家新經濟企業,該樣本組主要用于上海新經濟企業經營特征分析與新經濟企業成長驅動因素的實證計量分析。
(二)上海市新經濟企業基本情況——“量”的角度
根據年份來看,2010—2021年間上海新經濟企業數量保持高增長態勢,增速基本保持在20%以上。2014年受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啟動影響,上海新經濟企業數量漲幅大增至63.3%。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釋放重點培育新經濟的信號后,上海新經濟企業增速駛入快車道,2017年以來數量始終保持20%~30%的高增速。2020年后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響,增速略有下降,但依然維持在20%以上的水平。到2021年,上海新經濟企業總量超28萬,為2017年的近3倍。
根據行業來看,2010—2021年間上海市新經濟企業中超七成集中于“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2021年這三大行業中的新經濟企業數量分別為8.05萬、7.14萬、5.68萬,占比分別為28.48%、25.25%、20.1%。“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中的新經濟企業數量長期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存量份額從2010年的16.11%提升到了2021年的28.48%;“批發和零售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與“制造業”中的新經濟企業數量則從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的第一年)開始逆勢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新經濟企業數量經歷了“倒U型”變化:2019—2021年數量分別為1128戶、9317戶、4886戶。
上海新經濟企業集中于服務業體現了上海市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領跑者,位列最早進入工業化的一批城市,同時也是最早跨入后工業化階段的城市之一。近年數據顯示,上海第一產業對全市經濟發展的貢獻較弱,第二產業占比不斷下降,第三產業飛速發展,占比已超過七成。
圖2 2010—2021年上海市各行業新經濟企業數量變化
圖3 2010—2021年上海市新經濟企業行業分布變化
根據所有制屬性來看,民營企業始終是新經濟企業的最主要活力來源。2010年以來,新經濟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比始終高于95%,且呈現繼續上升趨勢。相比之下,港澳臺及外商參營企業、國有和集體企業新經濟企業所占份額在觀察期內呈明顯的下降趨勢,2021年所占份額分別為1.98%、0.04%。這一方面是因為在推進新經濟企業發展的過程中強調了市場導向的原則,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新經濟行業中,外資企業在技術和管理上的優勢正在逐漸削弱,而國內企業通過學習模仿和自我創新已經具有了相當的市場競爭力。
根據企業年齡來看,新經濟企業平均年齡為7.02年,其主體為新成立企業,也有部分老企業的經營范圍呈現出了新經濟業務活動特征。樣本中年齡在2年以內的新經濟企業占比高達21.85%,即在受疫情影響的2020、2021年間新經濟仍保持著極強的生機,體現出創業者對新經濟的青睞與信心,同時年齡在20年以上的新經濟企業占4.67%的份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部分傳統企業正通過業務轉型向新經濟方向發展。上海新經濟企業7.02年的平均年齡一方面顯著高于全國民營企業3.7年的平均壽命,但平均僅僅存活七年的現實也反映了在新經濟領域內創業的高風險——這類企業面臨著壓力空前的市場競爭壓力。如何激勵有才能的個體在這樣的競爭壓力下創立新經濟企業,并在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時候用有效的金融與法律制度來保護好這些創業個體,發揮其創造力,是一個事關保持上海社會經濟長期競爭力的問題,是推動上海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發展的關鍵。
從新經濟企業在各區的分布密度來看,中心城區仍然是新經濟企業最為密集的區域,這也與新經濟企業所在的三大核心行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對人員密集度、基礎設施完備程度的高要求與租金成本敏感度較低等特性相吻合。與上海所有企業在上海地區的分布熱力圖相比,新經濟企業在選址上的決定因素基本與非新經濟企業一致,并沒有明顯的新的考量。
根據調研數據,無論是否新經濟企業,在靠近江蘇一側的西北方向的企業密度要遠遠高于靠近浙江一側的西南方向的企業密度。我們認為,有三個可能的因素導致上海企業在選址上偏向于江蘇。第一個是歷史因素。在近代以前,上海地區在行政上歸屬江蘇,因此近代之后形成的行政邊界對上海企業選址的影響相對較小。第二個是產業結構因素。上海在產業結構上和蘇南地區有較強的互補性:一方面蘇南地域的企業有賴于上海的高端服務業與交通運輸業;另一方面,上海接入國際外循環以及產業轉移有賴于蘇南地區較好的制造業基礎。而浙江在產業鏈上有較強的獨立性,在新興的互聯網產業領域和上海更多是競爭關系。第三個是土地政策因素。浙江更多地把建設用地指標配置在靠近行政中心附近的區域,而由與上海相鄰的嘉興和湖州等地區來滿足耕地紅線,這使得浙江難以在靠近上海的區域發展配套產業。但蘇南地區可以把配套產業配置在接近上海的區域,而由蘇北來承擔中央對耕地紅線的要求。因此,上海的企業也更愿意將企業設立在靠近配套更完善的江蘇的區域,而不是靠近浙江的區域。
從各區新經濟企業數量占全上海新經濟企業總數量的份額與變動趨勢來看,奉賢區、崇明區對新經濟企業的吸引力在顯著增強,而外環以內各區對新經濟企業的相對吸引力有所下降。近年來,奉賢區、崇明區新經濟企業數量占上海新經濟企業總數的份額不斷提高,兩區新經濟企業份額已從2010年的12.8%、4.25%提升至2021年的24.11%、9.44%。這反映出,兩區對新經濟企業的相對吸引力逐漸增強,但不可否認,新經濟企業密度依舊較低。未來兩區在吸引新經濟企業、發展新經濟方面有較大潛力。而嘉定、徐匯、虹口、楊浦、黃埔、靜安區新經濟總數量所占份額則整體呈下降趨勢,或與當地企業密度過高、企業間競爭強度增強以及相關經營成本的上升相關。
圖6 ?2010—2021年上海各區新經濟企業數量占上海市新經濟企業數量份額變化
(三)上海市新經濟企業基本情況——“質”的角度
從新經濟企業規模角度來看,上海新經濟企業仍以小微企業為主,青浦區與徐匯區新經濟企業中超三成資產總額在25萬以下。2021年上海市新經濟企業資產總額分布顯示,資產總額小于25萬的新經濟企業占近四分之一,這類企業在青浦區密度最高(34.36%),徐匯區次之(30.69%),黃浦新區最低(12.88%);資產總額在25萬~125萬之間的新經濟企業份額近三分之一;資產總額在125萬~225萬的企業占比不到十分之一;資產總額超過225萬的新經濟企業占比僅為15.96%,這類企業在靜安區密度最高(21.04%)、閔行區次之(19.41%)、青浦區最低(11.68%)。從融資角度來看,新經濟企業資產負債率低于10%的占比超四分之一,這類企業在松江區密度最高(69.85%)、崇明區次之(54.28%)、寶山區密度最低(32.29%),而資產負債率超過100%的新經濟企業占比超五分之一,青浦區密度最高(23.64%)、閔行區次之(23.45%)、松江區密度最低(14.25%)。
圖7 2021年上海市新經濟企業財務數據分布
從企業盈利能力角度,2021年上海新經濟企業超四成處于虧損狀態。2021年上海市新經濟企業中,44.58%的企業凈利潤小于0,松江區密度最高(51.16%)、閔行區次之(49.91%)、崇明區最低(34.13%),23.19%的企業凈利潤僅處于0~10萬元之間,而凈利潤超100萬的新經濟企業占比為11.10%,金山區密度最高(21.38%)、長寧區次之(15.18%)、楊浦區最低(7.8%)。
圖8 ?2021年上海市新經濟企業凈利潤分布
本文認為存在以下幾個原因造成新經濟企業凈利潤較低:首先,可能存在企業樣本選擇的問題。本文所運用的數據中,企業的財務數據是自愿披露的,如果企業選擇性披露財務數據,那么就會造成本文對凈利潤的核算不準確。其次是企業的年齡問題。新經濟企業以新成立企業為主,往往面臨著更大的市場競爭壓力,在經營管理上通常也不夠成熟。第三是新經濟企業的前期研發投入較大。新經濟企業往往會在起始階段進行大量的研發投資,而研發成果商業價值的最終實現往往需要等待較長的時間。因此,單純從財務上看,此類企業在發展早期往往處于虧損狀態。
四、 上海市新經濟企業成長的驅動因素分析
從以上對新經濟企業“量”與“質”的分析可以看出,新經濟企業正蓬勃發展,但仍以小微企業為主,且盈利能力仍有較大改善空間。因此,下文將基于最新2021年企業數據進一步聚焦驅動新經濟企業成長的主要因素,以為助力新經濟企業的成長提供參考。
(一)企業成長衡量指標
已有文獻主要使用銷售額、從業人員、資產等指標來測度企業成長。在這些關于企業成長的文獻中,30.1%和29.8%的文獻分別使用了銷售額和從業人員測度企業成長 (Delmar,1997)。可見,銷售額和從業人員是最常用的測度企業成長的指標。除了上述兩大絕對指標,慕靜等(2005)進一步總結了可用于衡量企業成長性的幾類相對指標,包括成長速度(營收總額成長速度、凈利潤成長速度)、盈利能力(銷售凈利率、總資產凈利率、凈資產報酬率)和營運能力(總資產周轉率、凈資產周轉率、人均營收額)三大類。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擇了企業銷售總額與利潤率(凈利潤與銷售總額的比值)兩類指標來衡量企業發展成長狀況。
(二)影響企業成長的因素
1.企業盈利能力
企業盈利能力往往決定著企業的長期增長趨勢,具有獲利能力的企業更有動力實現增長,因為持續的利潤獲得不僅使企業能夠維系既有的增長水平,也具有了實現擴張的資本(Nelson和Winter,1982)。與此觀點相一致的是,Glancey(1998)發現盈利能力和企業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Mendelson (2000)和Cowling(2004)等研究也發現企業銷量增速和利潤顯著正相關。基于此,本文選擇以企業ROE(企業凈利潤與所有者權益之比)衡量的盈利能力作為企業成長性的解釋變量之一。
2.企業杠桿水平
由Donaldson(1961)首先提出的融資順位理論認為在企業發展的初始階段通常選擇內部融資,隨著企業的成長,將更多采用債務融資、股權融資等對外融資方式。Durinck 等(1997)基于比利時中小企業樣本,發現企業增長越快外部融資份額越高,其中債務融資的增加較股權融資的增加更為顯著。Heshmati(2001)、Honjo 和 Harada(2006)等人的研究也為企業杠桿率與企業成長正相關提供了證據。基于上述學者的研究,本文采用企業杠桿率作為企業成長性的影響因素之一。
3.企業償付能力
企業自有資本比率往往通過企業所有者權益與總資產之比來衡量,該比率越高,通常企業經營狀況更加健康。Myers和Majluf(1984)認為經理人往往偏好先利用企業內部留存收益進行投資,其次是使用借款,這意味著在企業成長早期,企業留存收益會不斷減少,企業自有資本比率降低。不過企業自有資本比率的變動模式會隨企業所處階段而變化,如Durinck 等(1997)等人發現,企業增長越快,將越多采用外部融資,即隨著企業不斷成長,自有資本比率會經歷先下降后上升的過程,因此處于成長早期的企業其成長性與自有資本比率往往負相關,而處于成長后期的企業,其成長性往往與自有資本比率正相關。由于企業所處階段的界定沒有明確的標準,企業自有資本比率與成長性的相關關系需要視實際情況而定。
(三)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章節所用數據來自復旦產業大數據庫,該數據庫包含了企業的詳細財務信息,以及與企業經濟類型、所在位置、所在行業與成立時間相關的信息。為了在保證樣本量的同時捕捉到新經濟企業運行的最新特征,我們使用了上海新經濟企業2021年的相關信息,剔除了不披露財務數據、沒有社保繳納記錄、實際地理位置不在上海的企業。此外,由于金融行業企業的財務特征與其他行業具有顯著不同,本文剔除了在金融行業的企業,得到包含8342家企業的樣本。由于企業財務信息可能存在部分極值,為保證數據整體的平穩性,在1%水平上對企業財務數據做了縮尾處理。
(四)變量定義
1. 被解釋變量
本文采用企業銷售總額(加1后取對數)與利潤率兩個指標作為企業成長性的衡量。企業利潤率,用企業凈利潤與銷售總額之比來表示。
2. 解釋變量
(1)企業盈利能力的衡量:本文以ROE衡量企業盈利能力,定義為企業凈利潤與所有者權益之比。
(2)企業杠桿水平的衡量:本文使用企業凈資產負債率指標來表示企業杠桿水平,定義為企業負債總額與企業所有者權益之比。
(3)企業償付能力:本文使用企業自有資本比率來反映企業償付能力,以所有者權益與企業總資產之比來表示。
3. 控制變量
除了上述主要關注的解釋變量,可能還有其他潛在的因素影響著企業的成長性,本文在回歸中還控制了企業年齡、企業所在區域(浦東新區、外環以內與外環以外),企業所有制(國家/集體所有企業、民營企業和港澳臺外商參營企業)、大類行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
(五)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表1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樣本企業銷售總額的均值為915.470萬,利潤率均值為-11.3%,平均凈資產回報率ROE為27.1%,平均凈資產負債率為27.1%,意味著企業負債總額平均為企業所有者權益的三分之一左右,企業自有資本比率均值為-40%(股東權益比由于資不抵債為負值),樣本中企業平均年齡為9.082年。樣本中有1.1%的企業為國有或集體所有、95.6%的企業為民營企業,52%的企業位于外環、15.5%的企業位于浦東新區,15.2%的企業屬于第二產業、84.6%的企業屬于第三產業。
(六)實證分析結果
表2呈現了以銷售總額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OLS和Tobit回歸結果基本一致。實證結果顯示,新經濟企業ROE和銷售總額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性,盈利能力越強的新經濟企業更有可能做大規模實現成長;凈資產負債率與企業銷量總額也成顯著正相關,當新經濟企業具有更好的融資環境、更易獲得融資時,將可以有更大空間按照企業規劃實現發展;企業自有資本比率與企業銷售總額也成顯著正相關關系,基于上文,企業往往會在發展后期選擇股權融資,而樣本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樣本中上海市新經濟企業的平均壽命為9.082年,已經過一定的發展,內部資金與債務融資或無法完全滿足企業發展需要,股權融資已成為企業實現進一步成長的重要資金來源。在其他控制變量方面,新經濟企業年齡與銷售額正相關,存活時間越長、越有市場經驗的企業市場表現越好;國有/集體企業與民營企業以銷售總額衡量的發展能力不如港澳及臺外商參營企業,其中國有/集體新經濟企業差距更大;位于外環以外的新經濟企業發展能力較外環以內的新經濟企業稍有不足。
表3呈現了以利潤率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實證結果顯示:盈利能力與企業利潤率成顯著正相關;新經濟企業自有資本比率與企業利潤率成顯著正相關,而凈資產負債率與新經濟企業利潤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不再穩定顯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國有/集體新經濟企業與民營企業較港澳臺外商參營企業具有更好的盈利能力,其中國有/集體新經濟企業表現更優。
為進一步分析各影響因素對不同成長性企業影響的差異,本文進一步采用分位數回歸法進行了分析,觀察不同解釋變量對銷售總額與利潤率位于25分位、50分位與75分位的新經濟企業的影響有何不同。由表4可以看出,當以新經濟企業的銷售總額衡量企業成長時,ROE、凈資產負債率、自有資本比率等主要解釋變量的影響結果均具有統計顯著性;當以利潤率衡量企業成長時,僅部分分位回歸中的結果具有統計意義,無法考察變量系數在不同分位時的變化,因此下文主要圍繞被解釋變量為銷售總額的分位數回歸結果進行分析。
圖9以折線圖形式刻畫了不同解釋變量對用企業銷售總額衡量的企業成長性的影響程度,各圖橫軸表示企業銷售總額的不同分位,縱軸則表示不同解釋變量與企業銷售總額之間的相關系數。由圖9可以看出:(1)新經濟企業盈利能力、凈資產負債率、企業年齡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程度呈現出“倒U形”特征,即三者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首先隨著企業成長能力的增長而增強,當企業成長到一定高度之后,這三個因素對企業成長的影響逐漸降低。(2)新經濟企業自有資本比率對企業成長的帶動作用隨著企業成長能力的增強而增強,當企業成長能力到達一定階段后,自有資本比率的影響將保持不變。(3)新經濟企業性質與所處位置中具有統計意義的幾個變量,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變化則呈現“U形”,即民營企業、國有/集體企業與港澳臺外商參營企業相比,隨著企業不斷成長,差距越來越大,而當企業成長到一定高度之后,開始實現追趕。位于外環的企業相較位于內環的企業也表現出類似的特征。
圖9 ?銷售總額作被解釋變量進行分位數回歸時各變量系數變化
三、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產業大數據庫,本文首先利用文本挖掘技術對上海新經濟企業進行了識別,并在此基礎上,對上海新經濟企業發展狀況以及成長能力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本文主要發現為:(一)2010—2021年間上海新經濟企業數量年均增速超過20%,且在疫情防控期間依然呈現快速增長之勢。(二)上海新經濟企業高度集中在商業服務,零售批發與科技服務行業,制造業占比偏低。(三)在地理分布上,新經濟企業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區,近些年崇明和奉賢兩區對新經濟企業吸引力顯著上升;上海新經濟企業與江蘇的關聯要明顯強于與浙江的關聯,在靠近江蘇一側的密度要遠高于靠近浙江一側的密度。(四)上海新經濟企業以小微企業為主、約20%企業資產負債率超過100%、有近五成的企業處于虧損狀態。(五)盈利能力、良好的債務與股權融資環境能顯著促進新經濟企業的成長,并且對發展初期的企業作用更強。
本文對于推進上海新經濟企業蓬勃發展提出以下建議:(一)上海應加強培育制造業領域的新經濟企業,穩定制造業占比。上海應結合自身的制造業產業優勢,加強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通用技術與傳統制造業全產業鏈的融合和發展,形成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相互促進的高端產業集群。(二)上海應加強與浙江的協調,把實現上海與浙江的新經濟產業鏈融合作為推進長三角一體化進程的重點方向,做到新經濟產業在長三角區域內合理布局、有序分工、協同創新、差異化發展。(三)結合新經濟企業以小微企業為主,且成立初期創新投入大的特點,創新新經濟發展產業扶持和融資支持政策;協助新經濟企業技術轉移和科技成果推廣,加快新經濟企業研發成果轉化;以解決新企業成立初期融資約束問題,促進新企業成長以及壯大。
參考文獻:
[1]Cowling M. The growth–profit nexu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4, 22(1), 1-9.
[2]Delmar F, Davidsson P, Gartner W B. Arriving at the high-growth firm[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2): 189-216.
[3]Donaldson G. Corporate debt capacity: A study of corporate debt policy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corporate debt capacity[M]. Beard Books, 2000.
[4]Durinck E, Laveren E, Lybaert N. The impact of sales growth above a sustainable level on the financing choice of Belgian industrial SMEs[J]. Business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 1997.
[5]Glancey K. Determinants of growth and profitability in small entrepreneurial fir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1998, 4(1): 18-27.
[6]Heshmati A. On the growth of micro and small firms: evidence from Sweden[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1, 17: 213-228.
[7]Honjo Y, Harada N. SME policy,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firm growth: Evidence from Japan[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6, 27: 289-300.
[8]Mendelson, H. Organizational architecture and success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Management science, 2000, 46(4): 513-529.
[9]Myers S C, Majluf N S.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 13(2): 187-221.
[10]Nelson R R, Winter. S G.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1]Scott W L. The ‘New Economy: Outcomes, Perspectives, and Public Policy[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6.
[12]鈔小靜,薛志欣,王宸威.中國新經濟的邏輯、綜合測度及區域差異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1,38(10):3-23.
[13]陳維濤.“新經濟”的核心內涵及其統計測度評析[J].南京社會科學,2017(11):23-30.
[14]姜江.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機理、思路、對策——基于新經濟、新動能培育的視角[J].宏觀經濟研究,2018(11):54-63.
[15]荊文君,孫寶文.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個理論分析框架[J].經濟學家,2019(02):66-73.
[16]杭敬,苑立波,張志遠.基于經濟普查大數據的上海“三新”經濟發展態勢研究[J].統計科學與實踐,2016(11):9-13.
[17]李曉華.“新經濟”與產業的顛覆性變革[J].財經問題研究,2018(03):3-13.
[18]慕靜,韓文秀,李全生.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小企業成長性評價模型及其應用[J].系統工程理論方法應用,2005(04):369-371.
[19]戚聿東,李穎.新經濟與規制改革[J].中國工業經濟,2018(03):5-23.
[20]任保平,豆淵博.近年來國內關于新經濟研究的文獻述評[J].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21,36(04):55-62.
[21]王克強,梁紹連,路江林等.上海發展新經濟新業態的優劣勢分析與對策建議[J].科學發展,2021(07):17-26.
[22]汪連杰.經濟新常態下對中國“新經濟”的考察研究[J].求實,2017(05):34-43.
[23]許憲春,張鐘文,關會娟.中國新經濟:作用、特征與挑戰[J].財貿經濟,2020,41(01):5—20.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Growth Factors of Shanghai's New Economy Enterprises
Yu Tianli1, Zhang Yanren2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Fuda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new economy enterprises and comprehensively activating the new economy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withstand the downward pressure of the economy,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database, this article uses text mining technology to identify Shanghai's new economy enterprises and then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owth capacity of Shanghai's new economy enterprises. We find that the number of new economy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for several years and has maintained a rapid growth trend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The average age of the enterprise is 7.02 years;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 distribution is obvious; Geographically, it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and the density of enterprises in the northwest direction near Jiangsu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outhwest direction near Zheji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quality, the long-term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conomy is still full of challenge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new economy enterprises are mainly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with an asset liability ratio of about 20% exceeding 100%, and nearly 50% of enterprises are in a loss state. Further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profitability, a favorable debt and equity financing environmen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new economy enterprises, and have a stronger impact on early-stage enterprises.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vides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s new economy enterprises.
Key words: New economy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status; Growth 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