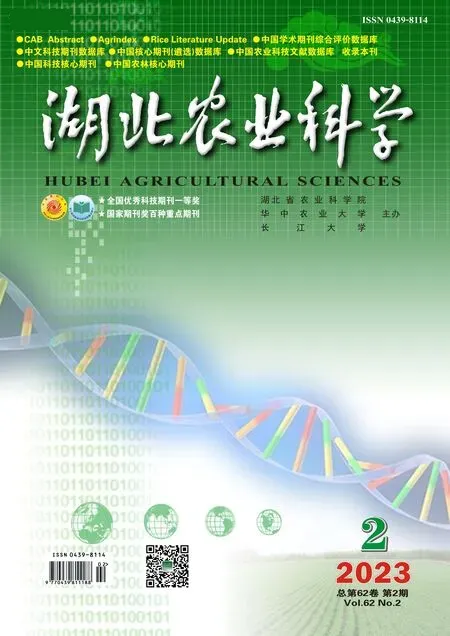鄉(xiāng)村振興背景下農(nóng)村“時間銀行”生發(fā)原理、藩籬與紓困之道
趙爽爽,李 靜
(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南京 211100)
目前,中國60 歲及以上老年人超2.6 億人,其中農(nóng)村老年人1.3 億人,農(nóng)村老齡化水平達22.5%,預測到2028 年,中國農(nóng)村老年人口比重將突破30%,高于城市老年人口的比重[1]。與英國、美國、日本等發(fā)達國家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不同,中國人口老齡化伴隨“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給家庭養(yǎng)老和社會養(yǎng)老帶來嚴峻挑戰(zhàn)。然而農(nóng)村家庭“多子多福”傳統(tǒng)觀念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和生育觀念轉變銷聲匿跡,2030 年中國家庭人口規(guī)模將降至 2.61[2],傳統(tǒng)家庭養(yǎng)老功能式微。2018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規(guī)劃(2018—2022 年)》強調要不斷提升農(nóng)村養(yǎng)老服務能力,加強農(nóng)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建立以居家為基礎、社區(qū)為依托、機構為補充的多層次農(nóng)村養(yǎng)老服務體系[3]。農(nóng)村“時間銀行”互助養(yǎng)老作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重要制度安排付諸實踐。
“時間銀行”最早由日本旭子水島女士提出,并經(jīng)由美國卡恩教授實踐推廣。卡恩教授倡導無差別的服務,彰顯志愿、愛心與奉獻。20 世紀末,“時間銀行”養(yǎng)老服務模式傳入中國并進行本土化改造,一種有別于傳統(tǒng)志愿服務的養(yǎng)老模式在全國推廣。實踐證明,“時間銀行”在農(nóng)村具有極大發(fā)展?jié)摿Γ渥鳛橐环N“抱團取暖”能夠調動農(nóng)村老年人“自我養(yǎng)老”積極性,排遣因年老帶來的孤寂感和無用感,實現(xiàn)“老有所為”,增強老年生活安全感。同時,“時間銀行”將服務人群擴展至年輕群體,鼓勵青年人積極參與志愿服務,形成全社會、全生命周期、全領域的志愿共同體,在社會營造愛心奉獻的良好氛圍。為此,本研究基于哈貝馬斯交往共同體理論,探究農(nóng)村“時間銀行”互助養(yǎng)老的生發(fā)原理、獨特優(yōu)勢與藩籬,以實現(xiàn)鄉(xiāng)村振興背景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及推動農(nóng)村養(yǎng)老服務健康發(fā)展。
1 交往共同體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共同體是指特定社會主體通過特定互動行為結成的穩(wěn)定社會關系的總體[4]。在價值視域里,共同體是指“擁有共同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背景或共同信仰、價值目標、規(guī)范體系,關系穩(wěn)定而持久的社會群體”[5]。這與哈貝馬斯的共同體觀念不謀而合。本研究的交往共同體是以生活世界為背景和前提,交往共同體不能脫離生活世界而獨立存在。其中,生活世界由文化、社會和個性三部分組成(圖1)。文化、社會和個性為交往共同體的形成提供前提條件。首先,共有的文化傳統(tǒng)既為交往共同體提供總體意義源泉,又為其單個成員提供行動背景和內涵。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通過歷史長焦鏡的沉淀歷久彌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價值意蘊深刻影響人們行為選擇。其二,共同遵守的社會規(guī)范為共同體提供必要的行動邊界和意義邊界。這種規(guī)范又分為道德和法律,它們?yōu)樯钍澜绱_定秩序。在生活世界中,這些道德和法律為交往主體確定共同的視野和邊界,在一定程度上不用質疑和批判就可以理解對方。其三,生活世界的個體是共同體最基本的要素,對其個性的承認與尊重構成交往共同體形成的前提。農(nóng)村“時間銀行”養(yǎng)老模式將老年人和志愿者組成養(yǎng)老共同體,在彰顯傳統(tǒng)互助文化和倫理文化的基礎上,承認老年人的社會價值,充分開發(fā)老年人人力資源,培育社區(qū)社會資本,可極大地促進農(nóng)村互助養(yǎng)老服務發(fā)展。

圖1 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共同體邏輯機理
2 中國農(nóng)村發(fā)展“時間銀行”的獨特優(yōu)勢
2.1 傳統(tǒng)儒家文化熏陶漸染
中國自古以來提倡“孝文化”,孝敬父母,尊重長輩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家庭養(yǎng)老是中國主要養(yǎng)老模式。由于儒家文化對孝的強調,贍養(yǎng)老人已經(jīng)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成為約束人們的內在責任和自主意識,是其人格的一部分。同時,農(nóng)村有優(yōu)先城市發(fā)展“時間銀行”的根基。一方面,在農(nóng)村人們祖祖輩輩生活在一起,彼此信任,農(nóng)忙時節(jié)互幫互助,閑暇時間聊天解悶,人際關系非常緊密,積攢了大量社會資本;另一方面,中國人普遍重“面子”,講誠信,害怕因不好的名聲遭遇鄰里鄉(xiāng)親詰難,使得農(nóng)村“時間銀行”信度和效度大大提升。
2.2 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季節(jié)性和土地規(guī)模的狹小
在中國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遵循自然規(guī)律,具有季節(jié)性和周期性。農(nóng)閑時間遠多于農(nóng)忙時間,農(nóng)村勞動力閑暇時間較為充足,將這部分人的閑暇時間集中起來納入農(nóng)村“時間銀行”以為老年人提供養(yǎng)老服務具有可行性。同時,家戶土地經(jīng)營規(guī)模較為狹小,種植結構單一[6],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上所付出的勞動時間較少、勞動強度較低。近年來,伴隨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農(nóng)村掀起土地承包浪潮,村民通過租賃土地收取相應租金,既解決農(nóng)民“靠天吃飯”的風險又解放了勞動力。由之,很多村民由于上了年紀以及照顧孫輩留在農(nóng)村,這一部分人有大量時間可以參與農(nóng)村“時間銀行”養(yǎng)老服務,既能夠為自己積攢年老時所需服務時間、緩解孤獨感,又能夠為自己贏得“好名聲”,得到社會承認和大家尊重。
3 交往共同體理論視域下農(nóng)村“時間銀行”中的藩籬
3.1 信任問題侵蝕“生活世界”
農(nóng)村“時間銀行”互助養(yǎng)老是將親屬、鄰里互助社會化,吸納低齡、健康老人為高齡、獨居、失能老人提供養(yǎng)老服務[7],并擴展至中青年群體,主要依托農(nóng)村社區(qū)為實現(xiàn)場域。這種低償甚至無償?shù)幕ブ绞揭欢ǔ潭壬夏軌蚓徑怵B(yǎng)老壓力,然而在實際運行中存在諸多問題。一是這種勞動成果延期支付方式,帶有明顯的信用產(chǎn)品性質[8],養(yǎng)老服務儲存的時間往往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后支取,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加之人口老齡化加劇,未來支取時間遠多于存儲時間。二是中國早期很多“時間銀行”試點由于領導班子換屆、賬本丟失、資金鏈斷裂等難以為繼,使得社會對“時間銀行”信任度堪憂。現(xiàn)在存儲的時間,未來能否兌換服務還未可知。三是在服務過程中老人可能會遇到摔倒、突發(fā)疾病、服務糾紛等風險,作為風險規(guī)避者,農(nóng)村“時間銀行”互助養(yǎng)老服務提供者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考慮,也會減少甚至不愿參與“時間銀行”助老活動。基于以上問題,農(nóng)村“時間銀行”互助養(yǎng)老難以擴大規(guī)模,服務提供者和服務需求者缺乏交往時間和空間,交往行動所必須的“生活世界”因信任問題而被侵蝕。
3.2 工具理性湮沒價值理性
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中國傳統(tǒng)“互助倫理”和“孝文化”道德標準被經(jīng)濟理性侵蝕[9]。加之維系傳統(tǒng)關系的公共力量被削弱,人們彼此疏離,傳統(tǒng)“熟人社會”被解構,單純依靠家庭的養(yǎng)老模式難以為繼。“時間銀行”互助養(yǎng)老以時間為計量標準,對于服務類型、勞動強度、技術含量等并未進行有效區(qū)分,出于理性“經(jīng)濟人”考量,多數(shù)“時間銀行”服務提供者傾向于為老人提供助餐、打掃衛(wèi)生、清洗衣物等簡單勞動,而對于喂食、助浴、失禁護理、安寧療護等專業(yè)性強、勞動強度大的服務項目避之不及。可見,由于“時間貨幣”缺乏統(tǒng)一規(guī)范的計量標準,使得工具理性湮沒價值理性。加之農(nóng)村“時間銀行”養(yǎng)老服務提供者多為當?shù)氐妄g、健康老人,為高齡、失能老人提供服務也僅停留在生活照料層面。究其根本是農(nóng)村“時間銀行”服務提供者專業(yè)技能較低,老年人養(yǎng)老服務供需不匹配。再加之農(nóng)村“時間銀行”多由社區(qū)組織,其本身專業(yè)技能不足,對老年志愿者養(yǎng)老業(yè)務培訓不夠,使得“時間銀行”服務提供者難以定期接受專業(yè)化技能培訓,對于難度大、專業(yè)性強、技巧高的服務內容難以勝任,而僅能提供生活照料層面的服務和簡單的日常護理服務。因此,農(nóng)村“時間銀行”服務提供者均傾向輕松簡單的服務項目,不利于“時間銀行”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
3.3 “時間銀行”供需雙方交往缺乏有效性
社會認知度不高是桎梏農(nóng)村“時間銀行”養(yǎng)老服務發(fā)展的關鍵。“時間銀行”養(yǎng)老服務作為志愿服務范疇[10],需要社會組織多措并舉提高社會知曉度。然而在很多農(nóng)村“時間銀行”養(yǎng)老服務推行地區(qū),大部分人對此并不了解。目前參與農(nóng)村“時間銀行”養(yǎng)老服務的志愿者多為低齡、健康老人,社會力量參與不足。相較大城市而言,農(nóng)村“時間銀行”養(yǎng)老服務發(fā)展相對緩慢,社會認知度更低。對于大部分農(nóng)村地區(qū),尤其是偏遠落后地區(qū),“時間銀行”知曉度知之甚少。同時,作為新生事物,在社會層面“時間銀行”尚處于認知階段[11],由于缺乏交往有效性,人們對“時間銀行”互助養(yǎng)老模式存在認知偏差,很多人將“時間銀行”理解為社區(qū)居民之間的互幫互助、是一種固定的“一對一”服務交換,而這些認知偏差直接降低“時間銀行”對公眾的吸引力。同時,在農(nóng)村“時間銀行”互助實踐中,志愿服務時長的換算標準、兌換機制等缺乏規(guī)范文件指導,隨意性和無序性較強,嚴重影響“時間銀行”參與者的熱情和服務質量[10]。多數(shù)人對“時間銀行”概念、性質、作用、意義并不了解,“時間銀行”作為互助養(yǎng)老模式效果甚微。盡管民政部門出臺相應養(yǎng)老服務“時間銀行”項目工作指引以及具體實施細則,但這些文件對管理者、服務提供者和服務對象之間的權利義務依舊缺乏明確界定,影響規(guī)范執(zhí)行效果[12]。良好的政策環(huán)境是實現(xiàn)“時間銀行”養(yǎng)老服務有序發(fā)展的根本[13],“時間銀行”缺乏規(guī)范、統(tǒng)一的法律政策文本,信任問題成為阻礙“時間銀行”發(fā)展的關鍵,基于通存通兌、持續(xù)性、意外事故等的處理,成為阻礙“時間銀行”供需雙方交往有效性的藩籬。
4 交往共同體理論視域下農(nóng)村“時間銀行”的紓困之道
4.1 使“時間銀行”主體實現(xiàn)平等對話和互動
從社會學視角看,社會弱者是一個在社會性資源分配上具有經(jīng)濟利益的貧困性、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會群體[14]。老年人是弱勢群體成為社會主流觀念。然而“時間銀行”打破這一固有觀念,凸顯老年人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老年人通過參與“時間銀行”積攢將來被服務時間,是一種自我主動養(yǎng)老的積極舉措。老年人將互助服務量化存儲,在彰顯志愿愛心奉獻的同時也是對勞動價值的認可。因此,一是“時間銀行”要彰顯老年人主體意識,鼓勵老年人積極老化,轉變“老而無用”傳統(tǒng)觀念,在增權理論及延續(xù)理論視域下,激發(fā)老年人自身潛能,使其利用自身資源參與農(nóng)村“時間銀行”互助養(yǎng)老服務,提升自養(yǎng)能力以滿足自身養(yǎng)老需求。二是明確“時間銀行”志愿者“身份福利”。要充分肯定老年人自養(yǎng)能力,以平等、尊重的態(tài)度對待老年志愿者。可以每年定期評選優(yōu)秀“時間銀行”老年志愿者并給予適當?shù)奈镔|和精神獎勵,如積分兌換商品、積分兌換景區(qū)門票等,以此提升農(nóng)村“時間銀行”志愿者參與熱情,保障“時間銀行”持續(xù)運營。
4.2 創(chuàng)設“生活世界”以促進農(nóng)村時間銀行主體間交往行動
哈貝馬斯所論及的生活世界由文化、社會和個性三部分組成。傳統(tǒng)互助文化是農(nóng)村發(fā)展時間銀行的根基,因此,“時間銀行”要結合傳統(tǒng)互助思想和“孝文化”,利用社區(qū)地緣平臺,強化鄰里互惠,鼓勵老年人自發(fā)參與互助養(yǎng)老服務,提升“時間銀行”各主體間的有效交往。
社會由道德和法律組成,在哈貝馬斯看來,道德只有在一定類型的社會中才能夠得到應用和實現(xiàn),道德規(guī)范和法律規(guī)范相互補充,從而使道德轉變?yōu)橐环N現(xiàn)實的制度[15]。農(nóng)村“時間銀行”在實質上屬于志愿范疇,然而單純依靠民間組織自發(fā)力量顯然不足以彌補養(yǎng)老需求,“時間銀行”健康發(fā)展需要政府政策引領。首先,加大頂層設計,出臺正式文件推動農(nóng)村“時間銀行”發(fā)展,逐步建立區(qū)—市—省—國家層面梯級“時間銀行”管理系統(tǒng),解決“時間銀行”志愿者的后顧之憂。其次,在老齡工作委員會下設農(nóng)村“時間銀行”獨立部門,專門負責全國農(nóng)村“時間銀行”政策實施、資金扶持、監(jiān)督管理等,保障“時間銀行”持續(xù)運營。最后,在法律層面上加強對“時間銀行”志愿者的保障。“時間銀行”是具有公益志愿性質的養(yǎng)老服務,為其提供相應法律保護符合志愿服務相關要求。如南京市“時間銀行”為志愿者購買“上門責任險”,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志愿者的風險,從而提高志愿服務積極性。
對農(nóng)村老年人個性的承認與尊重一方面體現(xiàn)在對老年人社會價值的認可,另一方面則是滿足老年人多樣化養(yǎng)老需求。首先,“老有所為”是農(nóng)村發(fā)展“時間銀行”的精神內核,農(nóng)村低齡健康老人是“時間銀行”的供給主體。其次,伴隨醫(yī)療技術進步以及身體素質增強,大量低齡老人在退休年紀身體健康并有強烈的繼續(xù)服務社會的意愿,老年人在長期職業(yè)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技能,而“時間銀行”為老人提供了“積極老化”的平臺。同時,老年人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輩子,彼此之間感情較為深厚,出于信任、互惠、親近促使低齡老人能夠并且愿意為社區(qū)內失能、失智、高齡老人等提供生活幫助。最后,對老年人個性的尊重需要承認其社會價值,老年人辛苦了大半輩子,在年老后有獲得國家、社會、家庭養(yǎng)老的權力。滿足老年人多層次養(yǎng)老需求符合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農(nóng)村老年人作為社會特殊群體,在滿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時[16],由于身體機能漸衰,老年人對醫(yī)療護理等方面的需求隨年齡增長而不斷凸顯。因此,“時間銀行”要在滿足老年人日常休閑娛樂的同時幫助其實現(xiàn)多樣化的養(yǎng)老需求。
4.3 推進“時間銀行”重塑價值理性
在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基于親緣、地緣基礎上的鄰里關系是現(xiàn)代農(nóng)村人際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鄰里關系能夠鏈接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補充農(nóng)村社會資本,培育社區(qū)共同體意識。然而伴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以及“打工潮”的快速推進,人們彼此間聯(lián)系逐漸松散、鄰里關系日漸淡漠。因此,要充分發(fā)揮“時間銀行”互助養(yǎng)老平臺作用,通過老年人社會交換積累社區(qū)資本,加強老年人及家庭的社區(qū)歸屬感和認同感,形成社區(qū)互助網(wǎng)絡,培育社區(qū)共同體意識[17]。
家庭結構核心化,促使傳統(tǒng)家庭養(yǎng)老功能式微[18]。而農(nóng)村“時間銀行”互助養(yǎng)老作為代內互助與代際互助相結合的互助模式,易于獲得農(nóng)村老年人及家庭的信任。因此,一方面“時間銀行”必須大力弘揚傳統(tǒng)尊老敬老孝老文化、強化互幫互助美德、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資源,在倡導價值理性的基礎上滿足農(nóng)村老年人的養(yǎng)老需求,實現(xiàn)互助養(yǎng)老。另一方面要充分肯定老年人的社會價值,鼓勵老年人“自我養(yǎng)老”“積極養(yǎng)老”“在地養(yǎng)老”,鼓勵時間充裕、身體健康的老年人積攢養(yǎng)老時間的同時幫助他人,體現(xiàn)社會價值。
養(yǎng)老企業(yè)具有逐利性,大多數(shù)養(yǎng)老企業(yè)主要在城鎮(zhèn)開展養(yǎng)老服務,容易造成養(yǎng)老市場城鄉(xiāng)區(qū)域供給失衡。因此,農(nóng)村“時間銀行”養(yǎng)老模式要立足公益價值目標,擺脫養(yǎng)老市場“利益本位”的束縛[19],以志愿互助為原則開展各項養(yǎng)老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