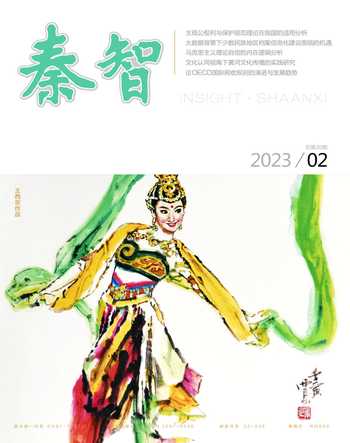對清末法律移植的思考與反思
[摘要]20世紀初,清政府為維護統治,推行法律改革,法律移植是其重要組成部分。這場有關法律移植的有益實踐使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發生了歷史性變革。本文以清末修律之刑律修訂為視角,分析修律過程中法律移植的原因、內容,探討清末修律對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所帶來的啟示。
[關鍵詞]清末修律;法律移植;啟示
1940年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炮火打開了中國國門,自此中國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社會性質和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導致原有的法律體系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加上西方近代法學的沖擊與西方人人平等、契約自由等先進思想的傳播,清政府被迫變法,這也拉開了中國近代法學的序幕。這一法律變革從實質上是以西方資本主義法律為藍本進行的全面法律移植。
一、清末法律移植的特點
法律移植,通常指的是將從一種文化土壤發展出的法律秩序及相關因素相對完整地向另一種文化土壤遷徙并盡可能發揮實效的現象[1]。古今中外很多國家地區都發生過法律移植現象,最早記錄是《漢穆拉比法典》《埃什南法令》中有關牛觸人的規定。較為世人所熟知的是古羅馬法的移植,古羅馬法伴隨著古羅馬帝國的鐵騎移植到那些被征服的土地。日本大化維新,以唐代法律制度為藍本進行大規模的法律移植。由此可見,世界范圍內法律移植并不少見。法律移植是清末修律的重要內容,通過對國外法律的翻譯,模仿借鑒,使中國法律制度發生歷史性變革,是中國近代法學的開端。在清末修律移植西方法律過程中,主要移植德、法、日等尤其是日本的法律體系,呈現出如下特點:
(一)清末法律移植具有明確的目標
清末修律的直接目的就是通過修律收回外國在中國的法外治權。鴉片戰爭之后,取得軍事勝利的西方列強為在政治經濟上謀得更大利益,紛紛與腐朽的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其中關于領事裁判權受到侵蝕更是舉國震驚,清政府在內部壓力下不得不考慮收回其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另一方面,隨著《辛丑條約》的簽訂,中國完全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成為西方列強的“傀儡”,西方列強也因此改變了對華政策,轉而扶持清政府,并許諾在清政府修改律法與西方律例一致時,放棄其法外治權。可以說收回領事裁判權可以說是清末修律的直接誘因和目的。
(二)清末法律移植以大陸法系模式為藍本
清末修律以大陸法系模式為藍本進行法律移植,這一選擇并不是偶然,其中有諸多因素的考量。首先,大陸法系模式具有法典化傳統,移植一部法典相比于移植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移植成本更低且可操作性更強,而且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一直將制定一部統一的法典作為中央集權的標志,這也為移植大陸法系法典提供了基礎。第二,大陸法系國家奉行國家主義,主張立法一元化,這與中國古代專制的中央集權不謀而合。第三,日本明治維新的示范作用,中日兩國的傳統文化背景相似,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向富強,極大刺激了清政府,在出國考察大臣的極力推薦下,清政府做出了“近采日本,遠法德國”的決定。
(三)清末法律移植受到較多政治方面的干涉。
法律移植需要一個相對自由的外部環境,政治因素的影響就顯得極為重要,這直接影響了法律移植的效果。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傳播,清政府的政治體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清政府為了維護其統治,宣布“變法”,想通過法律移植擺脫政治危機。而然“變法”,本身就意味著對政府權利的限制和削弱,這是腐朽的清政府絕對不允許的,因此采取各種方法阻礙法律變革的進行。這就造成清政府一方面高舉“變法”的旗幟,又用實際行動阻礙變法的,這一矛盾貫穿了整個法律移植的過程,直接影響了清末法律移植的效果。
二、清末修律中刑律修訂的內容
我國古代傳統法律體系一直都是“諸法合體以刑為主”,因此,清末政府進行法律改革時,首先就是著手準備新刑律的修訂,工作初期主要是翻譯國外刑法典。直至1907年,法律修訂館已翻譯完日本、德國、俄羅斯等12國家的刑法,還有美國等10個國家的刑法尚未譯完。此外,一些民間組織開展了一定的翻譯工作,其中以日本法律為主。這些對國外刑法的翻譯是為清末修律做準備,奠定了法律移植的基礎,其特點也初步指明了外國法律在刑法領域的移植方向。
(一)清末修律立法初期的法律移植
在清末修律的立法初期采用單行法的方式對舊律進行修改,例如在1905年上奏的《刪除律例內重法摺》中指出,舊律相比于外國刑法,雖然罪名體例不相同,但是刑罰過于殘酷,應當改重為輕,應當刪除戮尸、凌遲、斬梟三種酷刑,并將舊刑律中有關凌遲斬梟的條款改為斬決。刑律中緣坐入罪標準限制為知情者,不知情不為罪,并將刺字這一刑罰刪除。同時指出,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以修改法律為基礎,新律未公布就將梟首、墨刑等過于殘酷的刑罰刪除,最后民俗大變,國力日益強悍,現如今成為東亞強國。中日兩國風俗習慣國家制度相似,可借鑒而觀。這些建議得到清政府準許[2]。
1906年沈家本再次上奏《虛擬死罪改為流徒摺》,從中指出日美等國家死刑條款較少,少則數項,多不過二三十項,建議將刑律中有死罪之名但不實際執行死刑的條目改為徒流之刑,總刑期應當參照外國歐美日本之刑法,由重就輕確定刑罰。同年再次上奏《變通行刑舊制議》,提出秘密執行死刑建議,認為不僅可以節省開支,防止意外出現,也可以彰顯仁愛之心,彰顯人道。這些建議也得到批準頒行。
對國外刑事立法進行翻譯,并采用單行立法的方式進行法律移植,展現出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清末法律改革者對國外刑法學習借鑒和移植,也表明一些國外的刑法制度被中國刑律所接受,但是不難發現,其改革大多都是一些刑罰程度的減輕或者是一些細枝末節的修改,并沒有對封建制度或者是法律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也未觸動皇權乃至是封建貴族的利益,所以遇到阻力較小,真正對外國刑事立法進行系統性的移植是在《大清新刑律》中,無論是具體內容還是法律體例,都對進行了大范圍的法律移植,拉開了近代法學的序幕。
(二)《大清新刑律》中的法律移植
1907《大清新刑律》第一份草案起草完畢,共53章,387條。在各省征求意見時,因較舊律具有較大改動,遭受到“禮教派”的激烈抨擊,被要求重新修訂,此后又經歷數稿,最終于1911年頒布了《大清新刑律》。雖然《大清新刑律》的頒布歷經曲折,內容也是多次修改,但是清末修律目的就是為了制定一部西方列強相似的新律例,所以必將大范圍移植西方刑法。筆者從體例、內容兩個方面對其法律移植進行分析。
1.體例
中國古代傳統法律體系一直都是“諸法合體、以刑為主”,從奴隸制社會的第一部法典《法經》到封建社會最后一部法典的《大清律例》,內容雖不斷變化,但體例卻未曾變過。這也成為了中華法系的特征。而《大清新刑律》采用西方近代刑法體例,不光將民法商法等部門法從刑律中分離出去,單獨立法,而且將刑律分為總則和分則兩編,“總則為全編之綱領,分則為各項之事例”[3]。總則綱領性地規定了刑法典的原則制度,分則規定了各種犯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并規定成立犯罪,必須同時具備總則規定的普通要件和分則規定的具體要件。罪名也從原先的若干大類罪名改為具體的罪名。《大清新刑律》采用全新的體例使其具有了近代刑法的形式,這是對西方刑法進行法律移植的結果,具體而言,由于日本與中國地理、國情上更為接近,其形式與日本刑法典更為接近。
2.內容
《大清新刑律》移植了罪刑法定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西方近代刑法通用的立法原則。《大清新刑律》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由此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此外,《大清新刑律》貫徹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廢除了“減”、“請”等封建等級特權制度,使“刑不上大夫”成為了歷史。在刑罰方面,《大清新刑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移植了西方近代刑罰體系,并大量減少了死刑條款,由《大清律例》的400余條刪減到《大清新刑律》的40條,并刪除斬刑,統一改為監獄內執行絞刑。此外《大清新刑律》還移植了緩刑、假釋、訴訟時效與對數罪并罰限制加重等西方近代刑法制度和術語。
三、清末修律中法律移植所帶來的啟示
毫無疑問,清末在修律過程中移植西方先進的法律制度在當時是正確的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不僅為之后的法律移植積累了經驗,也開辟了中國現代化法律的道路。但是,清末進行的法律移植未能挽救清政府滅亡的命運,筆者認為清末法律移植的實踐有以下三點值得我們深思。
(一)法律移植要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法律作為上層建筑,其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進行法律移植首先要考慮到要符合被移植國家的經濟發展規律。清末修律時,中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剛剛興起,在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夾縫中發展緩慢。法律移植適當超前于當前的社會發展階段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是如果移植的法律脫離了現實的經濟條件,與民眾觀念相差過大的話,法律這一上層建筑就失去了其根植的土壤,變成一種脫離社會之外的法律文本,難以發揮法律移植的作用。
(二)法律移植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業,需要長遠的規劃和長期的準備,需要與社會的整體發展狀況同步。清末修律時,大部分中國人對西方文化制度帶有較為深厚的感情色彩,過于美化推崇西方法律制度,認為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當下的社會問題,具體表現為,迅速地以大陸法系為藍本照搬照抄,忽視了中國社會對異質法律文化的承受能力。其次,一個社會的法律制度應與社會的整體發展狀況同步,它的價值也只有在與其他社會因素相互呼應和相互協調中才能充分顯現[4]。考察清末法制改革運動不難發現,清末法律移植主要立法移植,那個時代的人們總試圖通過移植西方法典推動法律制度的改革,忽略了法律制度的變革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司法、執法、守法等配套因素的同步發展。這樣進行單一的立法移植導致了所移植的法律難以獲得普遍認同,喪失了法律社會運行的基礎,被社會拋棄遺忘。
(三)法律移植應當立足于本國實際,深入考察本國國情,重視法的本土化問題。清政府在修律時,未能深刻地考慮到中國國情,忽略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劇大差異,大刀闊斧地推動法律變革,時間倉促且充滿了功利色彩。清末法律移植的實踐告訴我們,全盤西化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法律移植也不是照抄照搬,法律移植應當要重視移植法的本土化,突出本土法制文化的民族特色,可以說移植法只有經過本土化后才具有生命力,這也是法律移植成功的關鍵。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的實踐,都是建立在本地經濟文化的基礎上,也必然受到它們的影響,所以在移植法律制度的同時,必須注重本地法對所移植法律的同化吸收,使所移植的法律真正成為本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5]。
四、結語
清末修律隨著清政府的滅亡戛然而止。然而,中國法制近代化的進程并未結束。清末修律的成果被之后的北洋政府所吸收,乃至現在我們仍能從當時的法律移植中獲益,這也是我們難以用法律移植的成敗去評價清末修律,現代中國仍處于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依然要借鑒他國文明成果,加以改造本土化后為我們所用。百年前的修律,可謂是這個過程的開始,無論得失都堪稱后世之殷鑒[6]。
參考文獻:
[1]黃金蘭.論法律移植[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1(6):6.
[2]佚名.寄簃文存[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3]唐自斌.沈家本與清末的法律修訂[J].求索,1992(5):3.
[4]楊曉莉.對清末法律移植的思考與借鑒[J].理論導刊,2010(1):3.
[5]何勤華.法律移植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6]張生.中國法律近代化論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基金項目:青海民族大學創新項目,項目名稱:對清末法律移植的思考與反思---以刑律修訂為視角(項目編號:04M2022089)
作者簡介:何新超(1997.3-),男,漢族,河南登封人,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