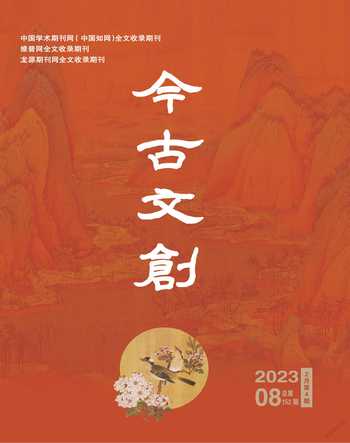《搖擺時光》中有色移民的 “ 他者 ” 形象解讀
【摘要】 《搖擺時光》圍繞扎迪史密斯成長的倫敦西北社區展開,講述了自幼就一起長大的兩個牙買加裔英國“有色移民”的故事。該書詳細描述了黑奴記憶給有色移民帶來的心靈創傷,揭露了英國社會種族歧視對人性的殘害。《搖擺時光》從不同的文學角度入手,把有色移民塑造成“他者”的形象,有色移民中的女性既是英國社會的“他者”,又是性別上的“他者”。本文通過有色移民女性的“他者”處境和“他者”的話語權兩個層面,探討了《搖擺時光》中有色移民的“他者”形象。
【關鍵詞】 《搖擺時光》;有色移民;他者;形象
【中圖分類號】I561?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08-002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8.008
扎迪·史密斯是一位在寫作中時刻帶有諷刺藝術的批判性作家。豐富多彩的人生閱歷讓她看到了種族與文化之間的碰撞與隔閡,也給予了她一種跨越種族沖突,立足于文化平等的廣博視野,讓她能夠從更廣闊的層面上來審視種族差異,并時刻關注那些被邊緣化的有色移民。《搖擺時光》是她在脫歐背景下最具影響力和感染力的一部新虛構作品,書中用兩個混血女孩成長歷程中的交流與碰撞來展開故事的情節,敘事空間跨越歐洲、北美和非洲。在這部小說中,扎迪·史密斯通過她獨特的幽默和巧妙的反諷手法,生動地刻畫了人與社會之間的微妙關系,尤其是那些被邊緣化的普通英國民眾和外來移民。她以女性特有的直覺和筆觸重塑了女性形象,而且以超脫女性的情感和視角關注多元世界中人的和諧人格的發展,同時對英國當下存在的諸多社會問題也進行了揭露與批判,也對作為“他者”形象存在的有色移民的生存困境給予了關照。
一、《搖擺時光》中的“他者”
他者,是相對于“自我”而言的。“他者”和“自我”這對截然相反的術語,是西方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的強烈表現。西方人常常將自己叫作主體性的“我”,而殖民地國家的人則是指“殖民地國家的他者”,或干脆指“他者”。“他者”即是主體的依附品,與主體是一種辯證存在的關系,“他者”和“自我”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搖擺時光》中表現在白人與有色移民之間,有色移民是作為白人的“他者”而存在的。
英格蘭公民和有色人種移民族群間存在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一方面,英格蘭的現代化和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都離不開跨境交易,然而跨境交易中有色人種移民起了關鍵性的角色。但是,由于一些英國公眾長期以來對有色移民的到來持批評態度,對外來者的不滿和不安與日俱增,對有色移民的刻板印象也是如此,有色移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他者”。有色移民在英國社會里始終處于邊緣地帶,處于被壓迫地位,沒有話語權。
在《搖擺時光》這部小說中,筆者認為有兩類“他者”存在,第一類是以特蕾西母親和敘述者母親為代表的牙買加黑人移民,他們受到種族歧視,處于英國社會的最底層,受到剝削壓迫。第二類是以我和特蕾西為代表的混血二代移民。她們既是性別上的“他者”,又是英國社會的“他者”。然而扎迪史密斯在小說中卻賦予了主人公“我”具有雙重他者身份的話語權,借著“我”的他者之口,對英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種族問題進行了深入剖析。如文章開頭寫道:“我總是依附于別人的光,我從未有過自己的光。我的生活是影子。①”敘述者用獨白來表現種族與影子之間的聯系,同時也對“非白人”移民和第二代移民進行了嘲諷,好像混血移民天生就是為了彰顯白人的高貴。
從敘述者“我”的表述中,隱約感覺到她們在“族屬認同”上的“他者”意識。扎迪·史密斯將目光鎖定在女性身上,通過她們的聲音去尋找歷史現實與社會現實,反映種族主義歧視的陰影對當代有色移民的影響,英美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對身份的不斷追尋。在這個“追尋”過程中,扎迪·史密斯將諷刺的矛頭指向脫歐大環境下英國社會現實中的種族歧視,揭示深刻而尖銳的混血移民身份歸屬該何去何從,也伴隨著作家本人對于社會結構的質疑,對個體生存困境和精神創傷的思考,以及從國家、民族等層面審視人性。
二、有色移民的“他者”處境
這里所說的有色移民的“他者”處境,即指根植于英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問題。種族歧視是把人按種族劃分為三六九等的社會階層,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做法的差異化看待,即種族歧視。小說中的種族歧視現象表明,絕大多數有色移民因膚色問題被剝奪了很多屬于自己的社會權利。種族主義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是對人性的蔑視,對人權的踐踏。在《搖擺時光》這部小說中,有色移民的“他者”處境分為兩類,第一代黑人移民與第二代混血移民。
(一)第一代黑人移民的“他者”處境
扎迪·史密斯在描寫他人處境時并沒有單刀直入,而是通過第一代黑人移民“兩位母親”的遭遇來體現。無論是徘徊于過去與現實之間的敘述者母親;還是因經濟問題等種種原因沉淪為男人附屬品,逆來順受的特蕾西母親,她們都無法真正走出身份的困境,一直作為“他者”的形象而存在。
1.迷失的敘述者母親
母親是敘述者生命中最為寶貴的人,作者對此進行了大量而又詳細的描繪。敘述者的媽媽是一名牙買加裔人,雖然她表面上成功地改寫了自己作為移民的“他者”形象,但實際上她內心卻一直無法從種族主義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她的一生都在不斷與現實抗爭,都在竭盡所能重塑她自己,而并非是一個一直處于社會邊緣地帶的“他者”形象。她告訴敘述者要在過去中學習并引以為戒,但她心目中的“過去”只是她無法擺脫種族主義陰影的一個縮影,一個只能被否定、抹去和拋棄的“過去”。敘述者母親的言行和思想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她標榜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卻總是依附于男人,她也強調工作的意義,但從未獲得一份固定的工作。她對資產階級的生活充滿了鄙夷和不屑,但是在離婚后,她卻成了資產階級生活的享樂者。她畢生追求的是種族的自由與平等,但卻從為此真正實踐和努力奮斗過,她把目標建立在空洞的演說和脫離現實的斗爭上。敘述者的母親雖然獲得了外人眼中的成功,實質上卻是一個“空想主義者”。她的政治演講可以隨時隨地進行,但缺乏對現實世界的關注和思考,在社區會場演講中,敘述者母親選擇的話題脫離現實、晦澀難懂,很少涉及現實生活中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社會環境決定了敘述者母親的身份認知和思想在清醒和迷茫中徘徊,她的內心充斥著躁動與不安,她從未找到過真正的自己。
作為第一代黑人移民,主人公的母親從內心里批判了西方在非洲的獨裁統治,但她被扭曲的思想依然覺得人們不應該懷舊,“過去”是不光彩的,她從未敢正視“過去”。她說英格蘭以外沒有祖國。生活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有色移民,有著黑奴的歷史記憶,常常陷入種族主義的成見中,把通俗意義上的自我重塑轉變為自我迷失的過程。處于自我迷失與精神幻滅中的有色移民又該何去何從呢?這是一個時代的命題,也是在扎迪·史密斯創作中一直思考的問題。有色移民女性的背后,是男性,是種族,是高高在上的上帝的眼,唯有打破這些牢籠與束縛,努力實現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才能完成自身的療愈,才能完成精神世界的重構。
2.被孤立的特蕾西母親。
特蕾西的母親在小說中是個無正經工作靠領取政府救助金生活的黑人移民形象。與白人結合后,生活并沒有好轉,特蕾西父親墮落、犯罪、出軌根本沒有盡到一點做丈夫的責任。特蕾西的母親作為獨立的個體并沒有獨立的意識,她還是處于依附地位,經濟和精神都依賴于丈夫路易,現實禁錮了她的自由。特蕾西的母親只能作為男人的消費品而存在,是父權下的奴隸。她扮演的是“忠誠的妻子”的角色,她生活的重心就是家庭,為自己的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身體和心靈都受到了巨大的摧殘卻完全沒有考慮自身的生存困境。特蕾西的母親對自身命運缺乏反思,從不考慮自己的訴求,甘愿淪為男人的附庸。由于自身意識的狹隘和女性意識的缺失,她最終也未能擺脫對婚姻和男人的依附,對于男權文化及其主導的英國社會秩序,她潛意識中體現的只有遵從與認同。女性由于缺乏女性意識導致無法清晰準確的認識自我,容易被男性的價值觀所引導。因經濟等多種原因,女性在男性主導的社會,總是以男性附屬的身份或者“他者”而存在。在白人眼里,黑人移民是沒有尊嚴的。白人把黑人視為劣等民族,黑人被有色化,被看成低賤的人,不被人尊重的人。在種族主義陰影的籠罩下,特蕾西的母親受到了男權和種族的雙重壓迫,這一類有色移民要實現生命意識的覺醒,作為個體重新回歸自身,需要打破外在思想的控制與束縛,關注自身的生命意義和價值。
(二)第二代混血移民的“他者”處境
《搖擺時光》中的敘述者和特蕾西雖然都有著復雜的移民背景,但特蕾西有著較強的虛榮心,特蕾西是第二代混血移民中被摧殘的典型。扎迪·史密斯在這里用大量的筆觸描寫了種族奴役思想以及家庭環境的負面影響對特蕾西的殘害。她陷入“黑人身份”的刻板印象中,對其他有色人種持鄙視態度,特蕾西對白人和白人文化都表現出嫉妒和輕蔑的矛盾態度。當特蕾西發現她和敘述者作為僅有的兩個黑人女孩出現在白人同學莉莉舉辦的小學同學生日聚會時,她立即對其他白人同學產生了敵意。但又迫不及待地要引起白人同學的注意,她故意在白人同學面前利用種族歧視的態度,說著有關于種族歧視的話語,例如在班級中說一起類似于“巴基佬”的話語。特蕾西強烈的自尊心和勝負欲,她不斷地將自己皮膚的顏色與敘述者皮膚的顏色進行對比,來確認自己仍然比敘述者白一點,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實現在混血移民中的高人一等。特蕾西表面上看起來驕傲自滿,實則是用這些虛假的東西來掩飾她人生的種種不幸,她和母親長期生活在慈善事業的救助中,沒有父親的關愛和教導。特蕾西的父親路易不務正業,做的都是非法勾當,經常逃到牙買加躲避抓捕。盡管如此,好勝的特雷西仍然渴望父親的愛。小時候,她的母親向敘述者抱怨她父親的行為不端,她會為他洗白,像文中說的“可特蕾西卻堅定地忠誠于對他的記憶,她維護她從不現身的爸爸遠勝于我維護我全心全意的爸爸。每次特蕾西媽媽說他壞話,她肯定會把我帶進她的房間或其他私密的地方,迅速把她媽媽說的話整合成她自己的‘官方版本’……②”從舞蹈學校退學后,她很長一段時間從一個舞蹈團漂泊到另一個舞蹈團。盡管她很有才華,但她很少在芭蕾舞中扮演主角。最終,上天所給的才能并沒有幫助特蕾西擺脫種族主義的陰影,她放棄了高超的舞蹈天賦,成了生育的機器,美貌和才華盡失,生活充滿了陰霾。特蕾西的世界觀是絕對的,她堅持二元對立的思維,否認移民身份的中間性。
三、“他者”話語權的喪失
關于話語權,法國著名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其著作《話語的秩序》中指出,話語是人民斗爭的手段和目的。這個詞就是權力,人們被這個詞迷住了。所以,言論和權力是相互依存的。權力是通過言語實現的,言語是權力的表現,誰掌握了話語權,誰便掌握了一種強大的思想權力。《搖擺時光》中的混血移民喪失了話語權。
一開始“我”覺得我與艾米是親近的朋友,“那一刻我竟相信,其實我倆的生命有同樣的重量,同樣值得討論,同樣值得付出時間。” ③而通過與敘述者生日事件、艾米領養非洲孩子瞞著敘述者等的對比上。可以看出,艾米從未把敘述者視作一個值得信賴和依靠的朋友,僅僅把她當作是助手。艾米總是看不起敘述者,艾米有自己的事業和愛情,敘述者只是為她服務的工具,依附于主人,成了名人的傀儡。“我”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局外人,是被孤立的他者。
小說中的“扒女生短褲游戲”的橋段,在操場上時是所有女同學都參與進來的,然而后來演變成在教室玩的時候,“現在的游戲沒有隨機性了:只有起頭的三個男生玩,他們只選離他們課桌近、他們認為不會有意見的女生下手。特蕾西是其中之一,我也是,還有和我住在同一條樓道的叫薩沙·理查茲的女生。在操場上撒野時基本都有份的白人姑娘,此時神秘地退出了:仿佛她們一開始就沒參與似的。” ④這個游戲,表面看上去平凡無奇,最多算是青春期的悸動,但實則蘊含著更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尤其是性別和種族的差異。20世紀80年代初,英國學校的教室里存在著嚴重的變形和歧視,學校里的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都心知肚明,只有黑人女孩的內褲可以被他們扯掉,黑人女孩既是白人男孩的“他者”,又是黑人男孩的“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童年游戲呈現出豐富、多維的文化內涵,暗指了“種族主義的逐步制度化、法制化和大眾化”。另一個例子是“丟錢事件”,當敘述者和特蕾西被邀請參加一個社區募捐節目,演出結束后,老師發現通過捐款募集的錢不見了。敘述者從一開始就被認定無罪,但特蕾西從一開始就是嫌疑人。特蕾西是所有女孩的敵人,黑的,白的,棕色的。在這里階級差別、種族歧視被表現得淋漓盡致,作為“他者”的混血移民從不具備為自己辯解的機會和權力,徹底喪失了話語權。扎迪·史密斯通過女性的視角來揭露種族歧視不為人知的一面,并沒有像以往一樣對于種族問題做善惡的評價,而是更聚焦于人的自我認知本身,彰顯了黑奴記憶對英美有色移民造成的隱性創傷,體現出英美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無法擺脫的種族主義陰影。
四、結語
人類一次次為拒絕“非我族類”而筑起高墻鐵籬,《搖擺時光》通過塑造眾多有色移民在英國社會的“他者”形象,真實地再現了她們在英國喪失話語權、備受歧視、迷失自我的悲慘遭遇,深刻揭露了英國社會中存在的種族歧視現象。體現了作者扎迪·史密斯對作為“他者”的有色移民問題的廣泛關注和深刻思索。解讀《搖擺時光》中的“他者”形象,對理解作品的內涵與價值意義深遠。
注釋:
①②③④(英)扎迪·史密斯著,趙舒靜譯:《搖擺時光》,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頁,第29頁,第137頁,第55-56頁。
參考文獻:
[1]童佳.淺論“他者”思想及其形象學意義[D].四川師范大學,2012.
[2]褚蓓娟,徐絳雪.“他者”在注視中變異——論比較文學中的“形象”[J].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11(03):282-286.
[3]孟雁超.他者身份的建構、淡化到消弭[D].南昌大學,2018.
[4]王卓.論扎迪·史密斯新作《搖擺時光》的敘事倫理和身份政治——兼談史密斯小說創作美學[J].當代外國文學,2019,40(02):45-53.
[5]王卓.論扎迪·史密斯新作《搖擺時光》中舞蹈的多重隱喻功能[J].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20,(01):64-72.
[6](英)扎迪·史密斯.搖擺時光[M].趙舒靜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7]許寶強,袁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作者簡介:
楊倩,女,漢族,云南騰沖人,云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比較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