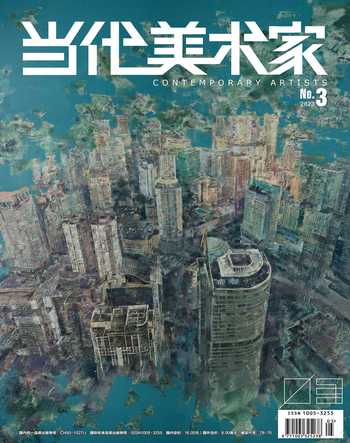以媒介研究為基

摘要:列夫·曼諾維奇從“新媒體”研究出發,以勾連現代藝術與計算機科技為研究路徑,揭示了新媒體藝術的歷史源流與內在機制。在歷史源流方面,新媒體與現代藝術,尤其先鋒藝術異質同構,新媒體以挪用拼貼的程序化、空間蒙太奇的日常化、構成主義的自動化繼承先鋒派的藝術實踐、實現先鋒派的藝術觀念;新媒體藝術則揭示乃至預言新媒體的發展。從內在機制來看,基于新媒體的運作機制,尤其是文化界面與數據界面的轉碼機制,新媒體藝術成為“文化習俗”與“軟件習俗”的“混合體”。從新媒體研究到新媒體藝術研究,曼諾維奇建構出獨特的“新媒體-藝術”的研究邏輯與理論話語,為新媒體藝術研究拓展出新維度。
關鍵詞:曼諾維奇,新媒體,新媒體藝術,先鋒藝術
Abstract: Lev Manovich, starting from the study of "new media" and taking the link between modern art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path, reveals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new media art. In terms of historical origins, new media and modern art, especially avant-garde art, are heterogeneous and isomorphic. New media inherits avant-garde artistic practices and realizes avant-garde artistic concepts through the procedural use of collages, the daily use of spatial montages, and the automation of constructivism; new media art reveals and even predict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mechanism, based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new media, especially the transcoding mechanism of cultural interface and data interface, new media art has become a "hybrid" of "cultural customs" and "software customs". From new media research to new media art research, Manovich constructed a unique research logic and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new media art", expanding a new dimension for new media art research.
Keywords: Manovich, new media, new media art, Avant-garde art
近年來,新媒體藝術成為當代藝術的熱點現象。在國內,互動裝置、沉浸式藝術乃至元宇宙藝術,成為粉絲爭相“打卡”和資本追捧的對象。然而,西方的新媒體藝術并非只是眾聲喧嘩中的奇觀,而是有其發展脈絡、前沿探索和人文深度。而在藝術實踐背后,是西方新媒體藝術理論的支撐。對此,國內學界尚缺乏系統關注。由于相當數量的國外新媒體藝術理論家也兼具藝術家身份,其理論觀點對于新媒體藝術實踐有直接的導向作用,因此國外新媒體藝術理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在國外的新媒體藝術研究領域,理論家兼藝術家列夫·曼諾維奇(Lev Manovich)無疑是其中的代表,其所提出的新媒體藝術理論在藝術界和理論界均引發熱議。有別于傳統的藝術史和美學研究,曼諾維奇基于新媒體的媒介研究,將現代藝術史與計算機技術、媒介變革勾連起來,以此揭示新媒體藝術的歷史源流與生成機制。
一、先鋒藝術的媒介化擴展:新媒體藝術的歷史源流
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的迅速發展,媒介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北美媒介環境學派則是其中的代表。媒介環境學派對于Media具體用法往往含混不清,它既指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也指一切能夠傳遞信息的材料、設備與介質。但從因尼斯到麥克盧漢,媒介環境學派開拓出相對清晰的“技術—媒介”研究路徑。如在麥克盧漢看來,由于電子技術取代了印刷術,形成新的電子媒介信息傳播體系,這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媒介感知和經驗[1]。
與麥克盧漢相似,曼諾維奇以“技術—媒介”的研思路,將第三次技術革命之后出現的“新媒體”視為計算機技術建構的媒介形態。在他看來,新媒體是計算機技術形成的界面、軟件與網絡,其運作機制區別于攝影機等20世紀初誕生的電子媒介。不過,麥克盧漢將技術視為形成新媒介的源動力,電子媒體的形成源于電氣技術的發展,而曼諾維奇試圖平等地兼顧技術與文化,把新媒體視為計算機技術進行傳播與展示的文化對象[2]。更為重要的是,他強調,技術與文化同為塑造新媒體的根源,新媒體實為先鋒藝術與計算機技術“類似思想”的交匯[3]。
曼諾維奇首先從現代藝術史的維度加以溯源,將先鋒藝術視為上世紀初“技術——媒介”變遷的成果。自20世紀10年代開始,伴隨現代工業技術的發展,攝影術、印刷技術、新建筑及工業產品等“新媒體”逐漸興起,印象派、立體主義、抽象主義、超現實主義等先鋒藝術流派紛沓而至,而受到照相機、攝影機等彼時新媒體的刺激,攝影藝術、實驗電影、現成品藝術也開始興起。杜尚在1912年開始嘗試用自行車等工業產品作為現成品材料進行藝術創作;而在社會主義的蘇聯,維爾托夫的影像實驗“擴展”著電影媒介的邊界。[4]在曼諾維奇看來,先鋒藝術伴生“技術-媒介”的革新形成了突破既有范式的實踐路徑和文化觀念。這一觀念區別于藝術史或哲學領域對于先鋒派的解讀。這些領域的學者,通常將先鋒派與社會語境聯系起來:現代主義繪畫被描述為對于學院派及其藝術體制的反叛;達達主義被闡釋為對于藝術體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反叛和嘗試介入大眾的范本。[5]曼諾維奇并沒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意識形態的角度審視先鋒藝術,而是繼承麥克盧漢的“技術—媒介”研究理路。事實上,在麥克盧漢那里,藝術家被視為能夠超前感知新的技術與媒介的人群,他們通常將對媒介的幽微感知,通過新的視覺形式傳達出來。麥氏以畢加索的立體主義繪畫為例指出,電氣時代的電子媒介以多樣和多向性區別于印刷媒介的單向閱讀,而立體主義正是源于藝術家對電子媒介“多向性”的感知[6]。與之相似,曼諾維奇也認為電氣時代“技術—媒介”的發展引發了藝術的革新。兩者的區別在于,麥克盧漢認為“技術—媒介”刺激藝術家形成新的藝術作品,而曼諾維奇將先鋒藝術的實驗視為“技術—媒介”從機械設備到電子文化界面的關鍵過程,其中,藝術家對于媒介的超前想象和實驗為新媒體(計算機媒介)的發展埋下伏筆。
自20世紀60年代末,隨著計算機技術的迅速發展,先鋒藝術的實踐方法和文化觀念在技術媒介中得以重現和超越。這種重現首先表征于挪用拼貼的程序化。對于現成品的挪用是先鋒藝術的重要特征之一,也被藝術史家和哲學家反復討論過。但鮮有研究關注到這些“后現代主義”的表達方式在計算機技術中的重現。然而,在Finalcut、Photoshop等人們日常使用的計算機軟件中,挪用現成素材進行創作已經非常廣泛。這種泛用不僅存在于專業人士的圖像處理和電影剪輯,更存在于草根自媒體發布的鬼畜、Flash動畫等視頻形式。可以說,先鋒藝術發明的挪用藉由計算機軟件技術已經被普羅大眾所使用。相同的是,拼貼同樣被運用到Photoshop等軟件中[7]。在先鋒藝術中,拼貼通常被視為藝術家解構現代主義“元敘事”的一種方式。隨機性、碎片化的拼貼見于現代藝術諸家:畢加索畫作中非洲面具和少女、雜志圖像與畫布的組合、基里科等超現實主義畫家的夢境表達、達達主義杜尚的現成品拼貼。在計算機中,這種打破理性邏輯的實驗性嘗試成為一種日常操作,通過軟件圖層的分離和組合即可實現。在曼諾維奇看來,計算機軟件不僅實現還超越了先鋒藝術,成為新的藝術品。他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計算機技術幾乎同時發展了現代藝術的某些關鍵項目[8]:前沿技術將先鋒藝術“物質化”,并最終超越了先鋒藝術。曼諾維奇所謂的“物質化”并非計算機代替藝術家進行拼貼創作,而是機制層面的“程序化”。無論專業人士還是非專業人群,均可根據軟件規則進行拼貼創作,這套規則背后是計算機軟件所建立的一套操作程序。隨著當下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機制的程序化甚至變為運行的自動化,如短視頻平臺內置了修圖軟件,人們只需打開程序即可實現置換背景等“一鍵修圖”。
亟須強調,曼諾維奇所說的拼貼不僅包括畫家和藝術家的實踐路徑,還意指維爾托夫等實驗電影者的“空間蒙太奇”。在維爾托夫《手持攝像機》的著作中,他構想了一種區別于愛森斯坦“時間蒙太奇”的電影創作路徑,并付諸實踐。維爾托夫通過剪切和疊加不同情境的膠片,呈現出“疊影”的視覺效果,從而實現不同場景的共時拼貼[9]。曼諾維奇認為,“空間蒙太奇”的原理體現和運用在Photoshop等軟件中,通過圖層的區分與疊加實現這一效果。空間蒙太奇不僅顯現于制圖軟件中,更成為日常化的界面操作形式。無論Windows、蘋果還是安卓操作系統,人們在計算機界面的操作均通過“空間蒙太奇”的方式展開:人們通過操作選擇不同的軟件,或者運行多個軟件來回切換。這些軟件實際是不同的窗口和界面的并行與疊加。此外,在曼諾維奇看來,當下人工智能的運用同樣與“構成主義”的先鋒派觀念相關。[10]構成主義的藝術家力圖通過繪畫的抽象化和視覺心理學的研究,建立人類通行的共感機制。構成主義需要畫家對圖式心理反應的反復研究,以此提煉出最簡單的形和色塊。這涉及素材的大量積累和反復實驗,進而建立一定的圖像范型。與之相似,人工智能技術以素材的大量學習為基礎,以此建立信息的處理模式。更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同樣尋找最為普遍的規律和模型,以便更多的人能夠適用和溝通。
可以說,在曼諾維奇那里,先鋒藝術與前沿技術兩個看似彼此無甚交集的領域,卻構成了一種跨時間代際的互文關系,這揭示出“新媒體”與藝術的隱形關聯。需要補充的是,這種判斷之所以成立,基于兩個重要的邏輯起點。其一是藝術家對于電子媒體的超前感知。正如科幻作家曾經想象的科技成果已經逐漸實現,藝術家的實驗求索在計算機技術中得以落地。其二是新媒體對于舊媒介的融合。曼諾維奇認為,計算機媒介融合了舊媒介衍生的一切文化信息和藝術實踐,并未產生多少新的文化形式。但正是得益于以新融舊的融合力,先鋒藝術才能夠在新媒體中重現和發展。
如果說20世紀初先鋒藝術與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處于彼此平行的狀態,那么自20世紀60年代,新媒體開始與先鋒藝術交匯,其所形成的新媒體藝術揭示,甚至預言了媒體的發展。事實上,藝術家對于變化的媒介具有一種超前的敏感性。激浪派藝術家約翰·凱奇創作的《想象的風景》系列作品,利用收音機和廣播媒體作為創作的材料。其中,《想象的風景第4號》由24位演奏者在舞臺上操縱12臺收音機,按照“作曲家”的規定控制每臺收音機的音量變化,調諧波段頻道,發出的聲音則是各電臺此時正在播出的各種節目聲音。意大利藝術家豐塔納則受到電視媒介的影響,電視信號跨地域的傳播力啟發其“空間主義”的觀念藝術實踐。而激浪派的另一位藝術家白南準以《磁鐵電視》等電視裝置構建了一種受眾與電子媒介的互動機制,他以磁鐵干擾電視中的抽象圖像,預言著互聯網的產生與傳播。隨著計算機技術的不斷發展,藝術家紛紛開始挪用“新媒體”進行創作,逐漸形成遠程通信藝術、網絡藝術等新媒體藝術門類,而“新媒體”的媒介特質在藝術家的創作中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多維呈現。在20世紀80年代,阿斯科特等藝術家的通訊藝術作品通過遠程觀眾的參與,呈現新媒體互動機制。20世紀90年代中期,互聯網開始普及,藝術家以互聯網作為材料和平臺,其形成的網絡藝術同樣揭示了互聯網的媒介特質。俄羅斯藝術家利亞利娜(Lialina)創作了早期的網絡藝術作品《我的男友從戰場上歸來》。該作品是網頁中展開的超鏈接小說,制造出徹底打破線性閱讀秩序的文本,而在此之前,喬伊斯等后現代小說家和德勒茲等哲學家分別從文字書寫和哲學理論的維度打破線性思維,但這種打破依然無法擺脫紙質媒介的約束。另一位東歐藝術家武科·柯西克(Vuk Cosic)則致力于探索計算機代碼的流動美學,試圖建立一種技術美學的審美范式。總之,如果從“技術—媒介”視角來看,先鋒藝術并非只是對體制的反叛,還包含對新媒介和新技術的前瞻性感知。這種前瞻性感知體現在新媒體對于上世紀初先鋒藝術的技術擴展,以及新媒體藝術的前沿性、探索性。
二、“文化習俗”與“軟件習俗”的轉碼:新媒體藝術的機制
除了歷史維度分析新媒體藝術的源流之外,曼諾維奇還通過分析新媒體的機制,解讀新媒體藝術的運作機制。
曼諾維奇認為,新媒體基于代碼編程的基本屬性,形成自身獨特的運作法則,包括數值化呈現、模塊化、自動化、多變性、轉碼性等。數值化呈現是指,無論是計算機創建的新媒體對象還是信息資源的數字化,其本質上都是數字代碼,計算機界面的聲音、圖像都是代碼的表征;模塊化是指新媒體的各個元素彼此獨立又協作運行的組織規制,如超文本結構,其中各個層次的窗口獨立存在,通過人機互動操作中彼此聯系;自動化是計算機具備的自主運算能力,從游戲引擎到人工智能,計算機不斷模仿、追逐甚至超越人類智能的自主意識;多變性是指計算機互動的個性化以及人機交互中的可生成性,“新媒體對象絕非一成不變,而是有著不同版本,而且版本數量具有無限的潛質” [11];轉碼性是指文化符號與代碼符號的相互轉換。簡言之,從計算機技術出發,曼諾維奇對于“新媒體”做出了全面剖析。一方面是代碼與文化符號的縱向結構,其中“數值化呈現”揭示文化符號的本質,而“轉碼性”是這一結構的具體運作機制;一方面是新媒體內部的橫向組織,模仿化、自動化和多變性構成其組織方式。
對于文化生產而言,基于新媒體的轉碼性尤為關鍵:新媒體所形成的文化界面與數據界面的彼此轉換,形成了新媒體文化。曼諾維奇認為,如果說攝影術等20世紀初的“新媒體”包含一種“紀實性”,即對于外部世界的記錄,那么計算機技術支撐的新媒體則包含“檔案性”,是對于“舊文化”和外部世界的“轉碼”。前者是“外向性”,后者是“內向性”。計算機將外在的、既有的文化信息內化為數據代碼,這構成了新媒體的“數據界面”。但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數據界面重新變為可識讀的文字、圖像與影像,變為融合和傳播各類文化信息的“文化界面”。因此,新媒體存在文化界面與數據界面的切換機制。
由于新媒體藝術家需要運用新媒體進行藝術實踐,“文化界面”與“數據界面”塑造了新媒體藝術獨特的“文化習俗”與“軟件習俗”結構,新媒體藝術也成為“文化習俗”與“軟件習俗”的“混合體”[12]。曼諾維奇所說的“習俗”實為一種規則、習慣與傳統。一方面,新媒體藝術家需要呈現“文化習俗”,包括審美形式的建構、人文觀念的思考和材料語法的設置。這需要藝術家在藝術史維度實現突破,即延續和突破既有藝術創作范式。而其作品同樣需要經受藝術批評家的評判和藝術體制的淘選。另一方面,新媒體藝術依然需要“軟件習俗”的支持,需要代碼的編寫和程序化。只不過軟件成為統領數據界面的機制支持。在此,作為先鋒藝術的軟件成為“數據界面”。軟件的數據界面制造了藝術家的文化表達,換言之,藝術家需要遵循軟件的規則,才能自如地呈現其“文化習俗”。
盡管曼諾維奇一再強調藝術史與科技史的并行,但當談及“文化習俗”與“軟件習俗”的混合,他依然將“軟件習俗”視為根源。在此,曼諾維奇實際重返了麥克盧漢設置的“技術—媒介”框架中。曼諾維奇將計算機視為一種“元媒介”,因為計算機能夠將一切舊媒介和文化融合其中。從“元媒介”出發,新媒體藝術不僅是“跨媒介”或者“多媒介”,而是以“元媒介”為根本的“混合媒介”。[13]這揭示了新媒體藝術的運作根本。元媒介成了計算機時代的“數據唯物主義”。在新媒體藝術家池田亮司的作品中,這種“數據唯物主義”得以展示,當流動代碼成為影像裝置,這形成了新的景觀和聲音,以此揭示了代碼的“元媒介”地位。可以說,新媒體藝術貌似由影像、裝置、繪畫等跨媒介的藝術形式構成,但媒介之間的關系均由計算機作為“元媒介”加以串聯與組合,“元媒介”成為裝置的核心要素。
不過,曼諾維奇依然強調“文化習俗”,這讓新媒體藝術的“混合體”理論呈現出一種內在矛盾。沿著曼諾維奇的思路,如果沒有藝術家的藝術化創造,軟件僅僅是一堆無意義的程序而已,正是由于藝術化的創構,軟件才從數據界面轉換為文化界面。但問題在于,軟件本身又被視為一種“先鋒藝術”:曼諾維奇認為計算機技術是信息時代的先鋒藝術繼承者,甚至斷言,軟件本身就是計算機生成的藝術品。既然如此,藝術家的“藝術化”究竟有什么存在價值呢?進而言之,如果軟件已經是藝術品,那么“文化習俗”與“軟件習俗”的二元劃分顯得不是那么必要,這樣的結構性張力是曼諾維奇不曾解決的理論矛盾。
對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擴展曼諾維奇的說法,“文化習俗”“軟件習俗”并非二元分化,而是被視為一種“褶皺”的動態關系,軟件因其對先鋒藝術的擴展,本身具有藝術轉化的潛能與優勢,而藝術家的作品激活了這樣的潛能。
事實上,新媒體藝術不僅僅是新媒體結構和規則的視覺呈現,還是“文化習俗”與“軟件習俗”的雙向突破。這種突破凸顯于對所謂“轉碼性”的先鋒性呈現。在1990年代的網絡藝術中,荷蘭藝術家組合JODI將二進制代碼作為創作材料,他們的作品將氫彈說明書“反向”轉換為代碼,形成互動式的超鏈接作品。當觀眾持續點擊代碼之后,氫彈說明書才逐漸顯現出來。人們日常瀏覽網頁中,代碼早已轉化可識讀的圖文符號,人們甚至忘記了代碼的存在。柯西克的作品則將代碼置于人們面前,讓人們通過互動將之變得可識讀。在這樣的互動中,人們參與和親自制造了轉碼的過程,所謂的“軟件習俗”悄然轉變為一種藝術實踐和“文化習俗”。籍此,軟件與文化已經變成了一體兩面。如果說柯西克的作品還停留在“界面”層面,那么加拿大藝術家查爾斯·戴維斯(Chars Davies)的虛擬現實作品則是將“習俗”的突破延伸到身體與感知層面。在她的作品《滲透》中,人們借助可虛擬現實設備進到一個打破笛卡爾坐標的虛擬世界。戴維斯通過軟件規則制造出一個超越真實空間的感官世界,而所謂“真實空間”其實是啟蒙運動以來建構出來的空間經驗,比如“地平線”的概念便是社會性的經驗建構。在戴維斯創造的虛擬世界中,地平線、邊界線均不存在,藝術家用軟件生成了突破“文化習俗”的空間形態,而這種突破同樣通過人們的體驗得以實現。另外,從“文化習俗”來講,大眾參與是先鋒派一直以來的實踐導向和文化傳統,1960年代的激浪派、偶發藝術等均繼承了這一傳統,而大眾基于計算機通訊的遠程操控延續了大眾參與的文化傳統,又將這種傳統拓展到新媒體維度。在“軟件習俗”層面,藝術家運用了互動編程的軟件技術,卻突破了技術的日常功能和既有“習俗”,賦予其藝術觀念和人文內涵。
三、從新媒體到新媒體藝術
綜上,無論歷史源流還是結構分析,曼諾維奇均以新媒體研究為起點,觀照新媒體藝術的形態與機制,建構出獨特的“新媒體—藝術”理論。他從藝術史和科技史的歷史維度梳理了新媒體與現代藝術尤其先鋒藝術的潛在聯系以及最終的連接樣態;與此同時,他從橫向維度剖析新媒體的內生機制,進而將新媒體藝術視為以新媒體為“元媒介”的文化習俗與軟件習俗的“混合體”。這種混合體充滿了內部的張力與矛盾。可以說,曼諾維奇理論中的新媒體藝術是“新媒體”的藝術:歷史維度的梳理確立了新媒體與新媒體藝術的必然聯結,橫向結構則揭示了新媒體藝術的生產機制。這顯著區別于奧利弗·格勞等新媒體藝術理論家書寫的“新-媒體藝術”:在沉浸式藝術的研究中,格勞將古羅馬時期的全景畫視為一種舊媒介的沉浸式藝術,計算機技術生成的虛擬現實藝術,則是這種古老的媒體藝術的延續。然而,曼諾維奇也存在將藝術邏輯與媒體邏輯簡單比附的缺陷。先鋒藝術的挪用拼貼有其特殊的社會語境,其內涵和其觀念顯然不只是新媒體軟件的操作規則。或言之,先鋒藝術家的創造并非簡單的方法“套路”的形成,而是包含文化想象和感知表達。對此,曼諾維奇試圖將計算機創造視為一種藝術化的想象,但科學家的想象更多屬于一種技術想象而非人文批判。進而言之,新媒體藝術應該是文化習俗與軟件習俗“復合”的第三空間,是一種超越文化習俗和軟件習俗二元分野的“超媒體藝術”。
作者簡介:楊光影,四川美術學院實驗藝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媒體與藝術傳播、視覺文化、新媒體藝術理論。
注釋:
[1]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Massachusetts: M I T Press ,1964,1994,pp.1-2.
[2] Lev Manovich,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1,p.41.
[3] Lev Manovich,“New Media from Borges to HTML”,in Noah Wardrip-Fruin and Nick Montfort,eds. The New Media Reader,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3,p.7.
[4] Lev Manovich,“New Media from Borges to HTML”,p.21.
[5] [德]比格爾:《先鋒派理論》,高建平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43頁。
[6] Marshall Mcluhan ,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 p.18.
[7] Lev Manovich,Avant-garde as Software,http://manovich.net/content/04-projects/027-avant-garde-as-software/24_article_1999.
[8] Lev Manovich.,“New Media from Borges to HTML”, pp.23-24.
[9] Lev Ma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p.18.
[10] Lev Manovich,Defining AI Arts: Three Proposals.AI and Dialog of Cultures, exhibition catalog, Hermitage Museum, Saint-Petersburg, 2019. http://manovich.net/content/04-projects/107-defining-ai-arts-three-proposals/manovich.defining-ai-arts.2019.
[11] Lev Manovich,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p36.
[12] Lev Manovich,“New Media from Borges to HTML”,p.8.
[13] Lev Manovich,software takes command. Bloomsbury Academic.https://library.oapen.org/handle/20.500.12657/58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