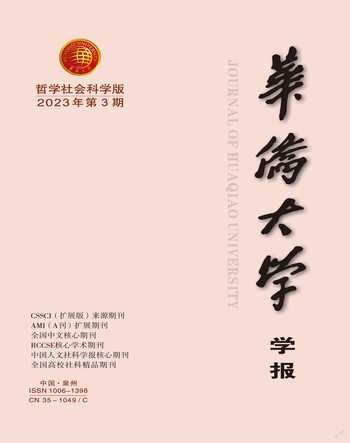智慧城市建設的空間邏輯及正義保障
秦鋒礪
摘要:智慧城市建設對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至關重要。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將空間視為人類活動的場所,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亨利·列斐伏爾推動了城市空間的認知轉向,認為城市的社會空間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是一種內含階級意志的社會關系。社會空間具有抽象的本質,并通過產品等物質實體得以體現。城市空間的非正義源于社會空間所內在的階級意志并通過物質實體得以感知。城市數字化轉型產生的城市數字空間是社會空間的新形態,其代碼邏輯在體現階級意識形態的同時卻沒有直觀可考的實體形式。要保證智慧城市建設的科學與民主,就要明確數字空間“使用”優先于“交換”的功能定位,既要保證數字空間內在代碼邏輯的科學性,又要在政府的主導下構建數字空間的監督機制。
關鍵詞:智慧城市;城市權利;空間邏輯;數字化城市;正義保障
中圖分類號:J6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398(2023)03-0005-09
一問題的提出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國未來五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主要目標任務之一。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智慧城市的建構邏輯等研究仍存在較大的理論探索與發展空間。自20世紀60年代起,以亨利·列斐伏爾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以空間作為研究視角和方法,對城市的發展邏輯進行了理論探索并提出“城市權利”的口號,以此作為人們在城市發展中所應享有的權利的理論基礎。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展開,城市已成為我國人民重要的生產生活場所。與此同時,隨著數字化、信息化技術的日臻完善,相關技術也開始運用到城市治理中,推動著城市的“智慧”發展。“智慧城市是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之后產生的一種更為高級的社會形態,新一輪科技革命是推動智慧社會產生的技術動力,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則是其根本特征。”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紛至沓來為人們建構了區別于以往物理空間的數字空間,城市發展具有了數字空間維度。但是,數字化技術在提升城市治理效率的同時也存在許多新的問題。習近平同志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亨利·列斐伏爾以空間為線索的城市權利理論在當今中國智慧城市發展的語境下,面臨著理論上的革新。
目前國內對列斐伏爾城市理論的研究主要以“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間生產”兩種理論為基石,面向不同的社會具體問題而展開:既涉及上述理論的整體性研究,又涉及對思想脈絡發展史、人類解放、都市規劃更新、世界化進程等具體主題的研究。盡管從列斐伏爾的理論出發,對城市問題進行研究的作品已經較為豐富且體系繁雜,但卻鮮見以此為基礎對數字空間這一新的空間形態展開的著述與討論。事實上,列斐伏爾在其20世紀的作品中就已經對信息技術形成了初步論述,將其作為審視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的理論落腳點,既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延伸,又能夠為我國的智慧城市建設提供理論借鑒,推動數字化城市建設的科學化與民主化。
二城市空間的雙重樣態:從物理空間到社會空間
城市權利研究源于20世紀6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空間轉向,亨利·列斐伏爾作為城市權利的倡導者之一提出了“社會空間”的概念,改變了空間在傳統理論研究中所處的弱勢地位。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對空間的理解也由此具有了物理和社會的雙重維度。
(一)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城市空間理念
列斐伏爾雖然是城市問題研究空間轉向的倡導者之一,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他卻并非首個關注城市空間問題的學者。馬恩二人雖然未就城市空間問題展開專題討論,但其著述中早已存在城市空間問題的萌芽。恩格斯在對英國曼徹斯特的工人階級生存狀況考察時發現了該城市存在的空間割裂問題,階級身份的不同決定了不同群體的地理方位和居住環境。“純粹的工人區,像一條平均一英里半寬的帶子把商業區圍繞起來。在這個帶形地區外面,住著高等的和中等的資產階級。中等的資產階級住在離工人區不遠的整齊的街道上,……高等的資產階級就住得更遠……在新鮮的對健康有益的鄉村空氣里,在華麗舒適的住宅里。”在《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指出了工人階級的住宅匱乏現象。其語境下的住宅匱乏具體表現為“本來就很惡劣的工人的居住條件因為人口突然涌進大城市而特別尖銳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一所房屋里的住戶愈加擁擠,有些人簡直無法找到住所”;等等。馬恩對城市空間問題的關注主要側重于對工人階級生存空間的考察,在二者筆下,資本主義城市的空間割裂往往體現出階級的特性,資產階級往往集中居住在空間寬敞、環境優異的地區,而無產階級則聚居在空間狹小且環境惡劣的空間中。
在馬恩看來,城市空間的割裂現象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密切相關。在恩格斯的理念中,空間同時間一樣,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這種空間體現為一種自然空間。因此大到城市,小到工人個人,其存在和生存都占據了相應的自然空間,這種空間是不可再生的。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下,大量勞動力從農村進入城市,勢必會造成城市生存空間的擠壓,不同的階級群體因不同的經濟基礎而生活在不同的區域。但這種城市空間的擠壓并不是造成工人階級居住空間狹小的根本原因。在恩格斯看來,現代大城市的發展往往會大幅度提升城市街區尤其是市中心的地皮價值,原本地皮上的房屋不能提升甚至反而會拉低地皮的潛在經濟價值,因此這些房屋會被拆毀而改建其他房屋,工人的住宅會變得更加稀少,因為昂貴的住宅能夠提供更為有利的投機場所,工人住宅只是一種例外。因此,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榨和剝削并不僅僅體現在剩余價值上,還體現在作為人們生存基礎的城市空間中。空間為資本生產提供了場所,也決定了生產規模的大小,資本生產占據的空間越大,便能容納更大規模的資本生產,資產階級所獲得的利潤也更多。而自然空間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非人造資源,對其占有具有功能上的排他性,機器等生產資料與工人不可能同時占據一處空間。因此,經濟效益便與空間產生了聯系,工人生活空間因較低的經濟效益而被壓縮。
馬恩對城市空間的關注揭露了資本主義工業城市發展及其空間規劃的規律,其形成并非各種要素自然聚集的結果,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人口、生產資料、交通設施等各種要素在自然空間聚集的結果,而資產階級對剩余價值的追求也決定了城市空間的布局和分配。因此,資本主義城市空間作為人們生產生活和資源分配的場所,城市建設與規劃的內在邏輯是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在此邏輯下,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工人階級居住狀況的改善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甚至隨著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聚集與生產規模的擴大,工人階級還存在被趕出城市尤其是核心功能區的可能。到了20世紀6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列斐伏爾注意到階級矛盾與空間之間的聯系,通過對空間概念進行重構,試圖探尋一條城市科學民主化的發展之路。
(二)城市空間的社會轉向
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雖然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但在對空間的理解和界定上卻與之存在質的不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生產理論認為,“生產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結果,首先表現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本身的,資本家和工人的關系本身的再生產和新生產。這種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實際上是這個過程的比其物質結果更為重要的結果。”在列斐伏爾看來,社會空間的本質就是一種社會關系。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張在提高物質商品生產效率的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建構或生產的過程。一方面,這種生產的社會空間蘊含在生產的物質商品之中,商店中的各種商品在更深層次上都內含一種生產者建構消費關系的目的性,生產者不僅生產了可供消費的商品,但同時也創造了新的消費欲望。另一方面,社會空間體現在人與人關系的建構中,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關系具體體現為以資本家和工人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傳統馬克思主義以時間為側重點,注重資本循環的時間維度。而列斐伏爾倡導的社會空間理念改變了傳統理念中空間的機械性和空洞性。正如城市社會關系發生的主要場所是街道一樣,自然空間在為社會生產提供場所的同時具有了交換價值,并作為一種生產資料參與社會空間的生產中。因此在審視資本主義城市發展問題上,社會空間的提出使“空間中的生產”轉變為了“空間的生產”。
社會空間的提出必然要審視其與自然空間的關系,盡管列斐伏爾提出了“社會空間”的理念并主導了其理論建構,但并不代表他對自然空間的存在及其對人類社會的作用持否定態度。自然空間與社會空間雖然都采用“空間”的表述,但并不存在本質上的共通性。列斐伏爾明確指出,雖然自然空間已經無可挽回地正在消逝,但它仍是社會過程的起源,是社會生產力所操弄的物質。社會空間并不是由自然空間轉化而來,前者是社會的產物,它“既不是實體性的實在,也不是精神性的實在,它不能被分解為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空間中事物的集合,也不是被占據的空間的集合”,“社會空間最初的基礎是自然——自然或物理空間”,“理論表明,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沒有一個空間會完全消失或者被完全廢除——即使是作為這個過程開端的自然空間”。在列斐伏爾眼中,“空間”一詞既指涉實體,表現為物質性的客觀實在,又指涉抽象,是與生產有關的社會關系的集束。從其構成而言,空間是“三元式”的存在,是個別、特殊和普遍的統一體,其中,社會空間體現了空間的特殊性,而自然空間或“場所”則體現出空間的普遍性。
因此,社會空間并非作為自然空間的替代品出現,二者是列斐伏爾空間理念的兩種維度。“社會空間和自然空間的位置存在很大的不同,因為它們并不是簡單并列的:它們可能會互相穿插、互相結合或者互相疊加——它們有時甚至互相碰撞。”社會空間和自然空間是列斐伏爾的城市空間理論的重要內容,自然空間作為先驗的絕對存在,為社會空間的生產提供了場所,是社會空間生產的起點。總之,從列斐伏爾的理論出發,城市工人階級生存狀況惡劣的原因實則也存在自然空間與社會空間兩個維度的原因:自然空間是生產要素的一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當交換與經濟價值產生關聯,對利潤的無限追求會使自然空間的交換價值優先于使用價值;社會空間的生產是一種內含目的性的社會關系建構的過程。
三城市的數字化建設及其空間特征
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及其在城市建設管理中的運用為城市空間帶來了新的內涵,我國城市數字化建設的推進數字空間作為新的空間形式與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存在聯系但又有區別。對數字城市時代城市權利保障措施的完善需要對數字城市的本質有清晰認知。
(一)我國數字化城市的構建及其影響
自2008年開始,我國的數字化城市發展經歷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被稱為概念導入期,此階段的重點技術以光纖寬帶、無線通信和超文本傳輸協議等為代表,是以單個部門、系統獨立建設而成的信息系統,產生了大量的信息孤島;第二階段始于2012年由住建部推動的試點探索期,體現為3/4G、云計算、射頻識別技術等的全面運用,此階段的信息共享以共享交換平臺為基礎,體現出系統建設縱橫分割等特征;第三階段始于2016年新型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物聯網、5G、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是此階段的重點技術,信息系統也開始向橫縱聯合的大系統演進,體現為以人文本、為人民服務等特征,并逐步形成了政府指導、市場主導的特征。由此觀之,數字化城市并不是被憑空創造出的全新城市形態,正如近代工業城市是在古代城市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來的一樣,數字城市是在現有工業城市設施網絡的基礎上進行技術改進而發展出的新型城市樣態,這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大致可以歸納為城市整體治理和居民個體生活兩個方面。
中科院發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指出,數字化城市是“在城市‘自然—社會—經濟系統的范疇中,能夠有效獲取、分類存儲、自動處理和智能識別海量數據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智能化的、既能虛擬現實又可直接參與城市管理和服務的一項綜合工程”。從城市整體層面而言,這意味著數字化城市的特點更多地體現為信息網絡技術對物質城市整體發展的介入,這一過程實則是運用信息網絡技術在原有城市結點之間進行的關系重構,主要依賴于數字孿生技術的使用。所謂數字孿生,是指通過對物理世界的各種要素數字化,在網絡空間再造一個與之對應的虛擬世界,這一技術已經成為當前數字化發展的必由之路。大到城市整體、產業園區、工廠建筑,小到具體的個人或某種具體設備,均可實現“萬物孿生”,數字城市從整體而言是物質城市的數字虛擬映射。通過將城市整體及其具體細節映射為數字信息,再通過大數據統計分析、計算機運算等技術手段,便可以為人們展示出被精確量化的城市構成及其運行規律:例如交通部門可以掌握每周、每天不同時段甚至是即時的交通信息,及時進行交通規制以避免道路擁堵;城市規劃部門可以精確掌握城市不同區域的人口密度、消費能力等信息,對城市進行更加詳細和科學的規劃。在城市整體層面而言,城市的數字化能更加精確直觀地呈現城市的運行規律,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推動城市的智慧化建設。
城市的數字化除了通過信息技術孿生出數字化城市整體,為城市治理推波助力外,還體現在個人的日常生活上。一方面,數字空間的出現重構了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在工業化乃至更早的城市中,各種資源的流通依賴于管道、電線、道路等設施的鋪建,社會關系的生產則依賴于物質的空間和場所,例如工業時代城市的生產和消費依賴于工廠和商場、教學活動的正常進行依賴于學校等。而在數字化時代,資源則可以通過互聯網等數字信息途徑進行互相傳遞,網絡消費平臺在不以物質場所為基礎的情況下就具有了與商場相同的社會功效;數字會議、辦公平臺等軟件的推廣使足不出戶但不影響正常辦公成為可能;老師和學生甚至在不進學校、不面對面交流的情況下就可以按時完成教學任務;等等。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使用使“人”這一主體更容易被識別、感知和更加“透明化”。在數字空間到來之前,無論是生物學意義上的“有機物說”,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關系說”,對個人的了解均依賴于對物理意義上的人的行為的考察與規律總結。而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的使用及其對人們生活的主導和更進一步滲透,使數字化生活已經成為人們基本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人的衣食住行均被數據化并留下相應痕跡,在非接觸情況下,對種種數據進行整體分析便能刻畫出人物的數字肖像,甚至做到大數據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在當今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最廣泛體現為對數字科技的需要。”總之,當今中國數字化技術已經深入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城市的高效治理以及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都依賴于數字化技術的推廣與使用,這種趨勢成為中國城市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數字化空間的特征及其本質
數字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空間形態:數字空間。數字空間與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相比,既存在功能等方面的相似性,但也表現出自身的獨特性。與自然空間相比,數字信息技術創造了一個新的與前者功能類似的“場所”,它容納了傳統人類社會活動的各種主客體,為人類數字維度層面的社會活動提供了載體。但它數字化的特征又消解了自然空間的時空特性,傳統物理意義上的距離、速度以及時間等概念對人類社會生產生活效率的影響已不復存在。這意味著在數字空間邏輯中,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就資本周轉的時間與空間特性進行的討論已不具備了現實基礎。在大衛·哈維的“三次循環”理論看來,在馬克思筆下,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剩余價值而對交通設施、廠房建筑等固定資產進行的擴大投資推動了城市物理空間的擴張,而這些固定資產的規劃布局則是通過“空間消滅時間”的方式保證資本循環效率的最大化,資本便以此種目的和方式介入城市的空間規劃之中。與自然空間相比,數字空間具有自身特有的代碼邏輯,代碼的運算規則決定了以數字空間為依托的社會空間的構建。因此,數字空間及其算法邏輯特征將與自然空間內產生的城市實體規劃邏輯存在質的區別,算法構建的邏輯考量取代了原本的時間、空間考量并決定了數字空間的運行邏輯。
數字空間與自然空間的另一區別在于其產生方式上,這主要體現為數字空間的人造屬性,即它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因此接下來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它與同樣由人類生產出的社會空間的關系問題。根據列斐伏爾的理論,社會空間是被生產出來的一系列社會關系。從數字空間的產生而言,數字空間無論是網線、無線電或是終端設備等基礎設施的鋪設,抑或是由這些設施傳遞承載的代碼邏輯,均是某種社會關系的體現。數字空間既是一種新型的人類產物,更是一種新型社會空間的表現形式。盡管數字空間是社會空間的一種,但與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空間相比,又表現出技術上的獨特性,即數字空間并不以自然實體為依托。在列斐伏爾的理論中,社會空間的出現并不代表傳統自然空間的消亡,二者存在互相糾纏的關系。對社會空間而言,“用來生產它們的‘原料是自然的”,其“‘現實性既是形式的,也是實體的”。“社會空間既不是一種物,也不是一種產品:相反,它包含了被生產出來的事物,也包含了這些物共存和共時時的相互關系。”就我們購買來的某種商品而言,商品本身的生產依賴于自然,其成品是實體性的自然存在,而社會空間則是這件商品自身所創造的生產、消費等各種關系。可以說,社會空間總是寓居于某項實體的背后,表現為一種抽象的形式。但數字空間并不存在其所寓居的實體,即便是其底層表現為“0”“1”的代碼邏輯,本身仍具有虛擬性。當社會空間寓居于實體時,人們可以直接感知空間規劃的內容及其科學性。而數字空間的虛擬性隱藏了社會資源分配的可感知性,人們無法直接感知數字資源的分布是否失衡,這意味著對數字空間的邏輯建構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可感知的監督方式。
四我國智慧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其保障
在列斐伏爾看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一樣,也存在自身社會空間的生產行為。但是二者對社會空間建構所遵循的深層邏輯有所不同,即不同社會制度下對社會空間的功能定位。在數字化城市時代,這種定位貫徹在數字化空間的建構中。與此同時,從數字空間的本質及其特征出發,其自身邏輯及其非實體形式特征決定了要從兩方面對城市數字空間的科學運行進行制度建構,即既要保證數字空間自身代碼邏輯的科學性,又要針對其不具有可被直接感知的實體形式這一特征建構一種有效可察的監督方式,通過“內”“外”兩種路徑的建構,才能保證城市數字空間的正義性。
(一)數字空間“使用價值”的功能定位
雖然我國城市的數字化轉型在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便利人們日常生活等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在這一過程中也面臨著矛盾。例如新冠疫情初期部分老年人因無法出示健康碼而出現出行難問題,因移動電子支付普及而在一些店鋪出現的拒收現金問題等,都表明了數字化的普及與推進往往需要面臨與傳統生活方式存在的沖突,這是不可避免同時也是不能回避的現實問題。加快推動傳統空間的數字化轉型還是尊重多種空間生活方式共存?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實則就是要回答好數字空間的功能定位問題。
企業或國家對空間的探索是存在目的的,對于信息空間而言同樣如此。明確中國城市數字空間的功能定位,就是要回答數字空間的建構是為了實現何種目的這一問題。社會生產依賴于空間并創造了空間,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中,“空間作為一個整體,進入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它被利用來生產剩余價值”。因此城市空間不能被簡單理解為貨物生產和消費地方之總和,它是如同機器一般的生產資料,是一種各種元素都可以彼此交換的商業化空間,這意味著城市空間除了具有使用價值外,也同時具有交換價值。在消費社會,空間成為可供交換的資源,加入到商品交換的隊伍中。在資本逐利性的推動下,資本主義的社會空間“以生產之社會關系的再生產為取向,空間的生產發生了均質化的邏輯與重復策略”。在這個過程中,它否定了自然、歷史、年齡、性別和族群等各方面的差異,打造了同質化的可用于交換的商業空間,其背后遵循的則是交換價值優先于使用價值的資本原則。
信息作為社會空間的一種形式,同時兼具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在列斐伏爾看來,信息產品來自生產的活動并被消費,其生產需要物質與勞動成本,它是一種具有非物質性的超級商品,所以信息一旦被生產出來,就要參與到買賣之中。它同樣面臨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沖突與選擇。社會主義的空間生產與資本主義相比,區別之一就體現在兩種價值的優先定位上。社會主義的空間并不是資本主義的空間,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需要為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創造條件,這意味著“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個人有接近一個空間的權利,以及擁有作為社會生活與所謂的文化活動等之重心的都市生活的權利”。由此,社會主義的數字空間不能是以資本作為衡量標準的逐利性空間,而是使用優先于交換的差異化空間,社會主義的數字化轉型要以尊重不同群體的空間生存模式為基礎。
(二)數字空間正義性的內在保障:數字空間邏輯的正義性
數字空間與自然空間的區別在于其隱藏在數字代碼中的邏輯性。作為人造空間,數字空間的邏輯必然是其生產者主觀意向的體現。在數據運算邏輯上存在的非正義問題以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大數據殺熟”現象為代表。目前學界并未對“大數據殺熟”有權威的定義,但從其表現特征而言,可以概括為消費者在購買同款產品時存在的價格差異現象,這種現象又以在線旅游、網約車等領域為代表。這種價格區別對待既針對不同群體,例如Android和iOS兩種操作系統就同種商品存在價格差異;又針對同一主體,例如同一消費者在同一平臺形成消費習慣后,會存在價格上漲等情況等。
之所以存在這種差異,原因在于上述數字空間所內含的非正義邏輯。在我國城市的數字化轉型中,無論是城市宏觀還是居民個體生活的數字轉型,均離不開各類企業所發揮的主導作用,既表現為高新技術企業對各級人民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設,又表現為不同數字平臺對人們具體生活的參與。在列斐伏爾看來,信息技術雖然是一種科技,但其內含了一種被論述為實證知識的意識形態,掌握了數字信息生產的技術權威和技術官僚便可以讓世界按照他們的指令進行運轉。因此,并不存在一種純正的類似于自然空間的社會空間,與物理、化學等客觀中立性的技術不同,城市數字技術的邏輯蘊含了其建構主體的主觀意向,當這種主觀性成為其自身不可剝離的特征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階級意志應在數字空間邏輯的建構中發揮主導作用。在數字化時代,數字正義實現的根本依據是數字資源的合理分配。盡管當下的智慧城市建設表現為政企合作的模式,但同樣依賴于政府對數據主體在資源占有、使用等方面的平等,力圖保證數字空間的科學性并以此實現運算的結果正義。
(三)數字空間正義性的外在保障:數字監督制度的建構
當我們吃面包時,這塊面包的物質形式蘊含了與其相關的生產、消費等一系列社會關系。同樣地,城市發展及其社會空間生產的邏輯同樣體現在建筑、場地等一系列物質的外在形式中。只有當某種社會空間依附于實體存在時,實體的直觀可感知性才能為我們理解和把握社會空間邏輯提供觀察的視野和工具。信息作為一種產品同樣涉及勞動、生產成本、剩余價值等內容,作為一種商品,信息具有其他商品都具有的特征,但其表現形式是非物質的。這意味著人們對數字空間邏輯的感知缺乏了可考的直觀形式。前文已述,數字空間并非客觀中立,它內含其生產者的意識形態,因此,數字空間運算的正義性還需要外在的監督制度的建構。
一方面,城市數字空間監督制度的推行要使數字空間的算法邏輯適當公開透明化。算法決策的公開透明是數字正義實現的外在表征。例如在大數據殺熟中,消費者只能感知數據運算的最終結果——價格,并比較不同主體之間存在的價格差異,這是人們發現數字空間非正義邏輯的唯一渠道。但人們對這一結果的具體運算邏輯卻不得而知,相應的解釋權也被掌握在相關平臺手中。“算法平臺與個人的關系可以理解為一種契約關系,對于算法運用的知情與同意是構建個人與算法平臺之間契約正義的前提之一。”在當前市場力量參與數字城市化的過程中,政府、消費者對數字空間建構的邏輯進行監督就顯得尤為必要。與此同時,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算法存在自我學習和自我更新的可能,其邏輯建構在自動學習的過程中存在發展方向的隨機性,甚至會超出其生產者的認知范疇,數字算法的監督就顯得更為必要。因此,通過對算法的基本原理、主觀意圖和主要運行機制等以適當方式進行公示,能提高人們對算法服務的分享和監督并抑制算法的誤用和濫用。
另一方面,政府應在城市數字空間監督制度的落實中起主導作用。城市數字空間的建構依賴于數字技術的運用,而后者作為一門專業技能,對其理解和監督存在技術門檻。這意味著即便將城市空間的數字算法邏輯完全公開透明,普通城市居民也難以理解其具體內容,更談不上監督制度的落實,而為了監督的落實而讓居民都成為技術專家又不具備現實可行性。換言之,城市數字平臺和城市居民之間存在不可彌補的信息和技術差,而政府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具備彌補差距、落實監督的可操作性,由政府主導的數字空間監督同時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城市數字化轉型中“為什么人服務”等根本問題的回答。
智慧城市的轉型已經成為進行時。新事物的出現往往伴隨著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直面并解決這些問題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面對這些新的社會問題,對事物本質的正確認識以及對相關理論的建構和完善是對目前乃至未來世界可能發生的各種風險進行未雨綢繆的有效手段。近年來,智慧城市在穩步推進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現實問題,亨利·列斐伏爾在20世紀所提出的城市空間理論仍能為我們解讀城市數字化的本質提供一種研究視角和方法工具。數字空間作為社會空間的一種表現形式,同樣具備后者的階級意志性,在此基礎上,中國城市的數字化轉型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就是“誰主導”和“為了誰”。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明確數字空間的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在政府的主導下推動智慧城市建設,確保城市數字空間正義的實現。
The Spatial Logic and Justice Guarantee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Starting from Henri Lefebvres Spatial Theory
QIN Feng-li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itie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governance abilities. Traditional Marxism regards space as the place of human activities. Western Marxist scholar Henri Lefebvre promotes a cognitive turn of urban space, believing that urban social space is a product of human social activities and a kind of social relations with class will. Social space has an abstract essence and is embodied by physical entities such as products. The injustice of urban space originates from the inner class will of social space and is perceived through material entities. The urban digital space generated by the urb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new form of social space, and its code logic reflects the class ideology without intuitive physical form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digital,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use” of digital space over “exchange”,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code logic of digital space, and to build a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spa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smart city; urban rights; spatial logic; digital city; justice guarantee
【責任編輯:龔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