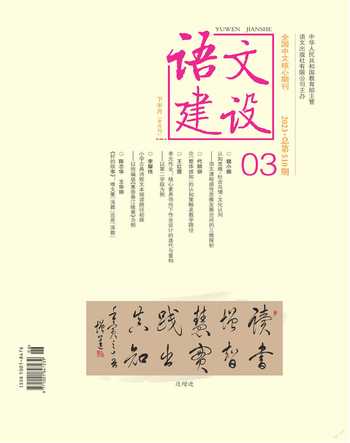《好的故事》:難文要“淺教”還是“深教”
陳志華 王華麗
【關鍵詞】魯迅;《好的故事》;小學語文;難文深教
魯迅《好的故事》曾出現在1958年、1959年、1960年及1963年的初、高中課本中,統編小學語文教材將其編入六年級上冊。將如此難讀的文章納入小學課本,勢必會引發魯迅作品選編格局的整體變動。盡管有魯迅研究專家認為把它編入小學語文教材“不大合適”…,但這是既成事實,當下要緊的是如何調整我們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最大限度地發揮這篇課文的教學價值。
目前學界普遍主張“難文淺教”,即主要教授詞匯、修辭、寫作背景等內容,不必過分注意學生的閱讀障礙。陳先云認為,可指導學生用“跳讀”的方法先跳過難懂詞語以降低學習目標的難度。作為教學方法,這是可行的,但若把它看作一種“類型教學”則明顯有待商榷。該課文中的難詞不僅因為“語言表達與現在不完全一樣”,而更多的是作者對“陌生化”效果的有意追求;長句、難句是為適應“似真幻境”的印象主義描繪創造出來的,非細讀難以體會其妙處。因此,深入分析難文何以為“難”,厘清教材對魯迅作品的整體內容選擇和價值定位,由此為語文閱讀教學的難點化解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就顯得十分必要。
一、價值追問:小學語文看重“魯迅選文”什么
這里的“魯迅選文”不僅指魯迅本人寫的文章,也包括那些塑造魯迅形象的回憶性、評論性作品。事實上,小學語文教材所選的文章后者居多。據統計,新時期以來選人小學課本的魯迅選文共24篇,魯迅所寫的文章僅有《少年閏土》《給顏黎明的信》《風箏》等寥寥數篇,其他文章要么是綜合各類事件、傳聞編寫的“魯迅故事”(如《三味書屋》《早》等),要么是以親身經歷述說“我心目中的魯迅”(如《我的伯父魯迅先生》《有的人》等),這些可統稱為魯迅“形象塑造”類課文。
教材如此密集地安排講述魯迅故事的文章,主要還是考慮到小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這一階段的小學生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可塑性極強,將魯迅樹立為榜樣式人物,能夠為其人生發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引。“魯迅選文”不僅承載著傳播知識、普及文學教育的功能,而且對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化及向普通民眾傳播起著重要的作用。小學階段的魯迅“形象塑造”類課文傾向于將魯迅還原為可親、可敬、可愛的、活生生的“人”。雖然某些歷史階段難免受到意識形態話語的影響,但學生的接受過程存在一種“過濾裝置”,它會篩除那些難以理解的部分,揀選、接納和同化一個與自我生活息息相關的可以接近的魯迅形象。
教材編者處理魯迅本人的文章時面臨的難題至少包括三個。第一,魯迅并非專門的兒童文學作家,不少文章雖寫的是兒時經歷,卻有意拓展了當時所涉及的社會歷史文化的內容,這不容易被小學生理解。第二,如何從篇幅長短和內容是否艱深兩個維度判斷作品閱讀難度。有的文章故事性較強,較容易讀懂,但其社會批判和自我批判傾向過于明顯,缺少閱歷的小學生會有閱讀障礙。第三,由于魯迅在政治文化領域具有特殊地位,教材選編其作品有不成文的規定,就是盡量不作語言及內容上的改動,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原作面貌。這樣,能夠進入小學語文教材中的魯迅作品只能向兩個方向分流:一是在保證閱讀整體性的前提下將原文“截短”,以《少年閏土》《在仙臺》為代表;二是全文選入貼近兒童生活的短篇作品,閱讀提示、注釋、習題等盡量降低難度,不過多涉及超出學生理解范圍的內容。就教學效果來看,第一類課文編選較為成功,第二類一直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難以成為小學教材魯迅選文的主流。
以此觀之,作為全文選入的《好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避免或消除了以上種種問題。
首先,文章篇幅短小,結構簡單,兒童視角與成人視角交織在一起,較好地融入了魯迅的童年經驗。作為蒙學讀物的《初學記》起到敘事線索的作用,在“我”的一“捏”一“拋”之間,對故鄉山陰道上風景的遐思和由迷思狀態回歸現實的驚醒都順理成章了。相對于“朝花夕拾”式的憶舊散文,本篇省去大量敘寫事件的筆墨,從而使文章內容更加集中。
其次,以農歷新年前后的一次“神游”為中心,不過多地涉及社會歷史內容,學生閱讀雖有難度,但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盡管有人主張深挖作品背后的精神、現實批判等主題,但那些畢竟是備選項,僅從學生閱讀感受和藝術感知出發,以“幻境尋蹤”等寫作手法為主組織教學也未嘗不可。學生閱讀時可能會遇到障礙,這正可以為提高經典誦讀能力、積累閱讀經驗加以系統訓練。
最后,因為簡短凝練,本篇適合作為接觸魯迅的入門讀物反復涵泳,以實現對現代文學經典的語言感知,受到文化熏陶。在當前流行“淺閱讀”的時代,我們應多花一些時間讓學生學會“慢讀”“深讀”,一些經典段落,如描寫“坐小船經過山陰道”的第五自然段,可以嘗試讓學生背誦下來,可能會對他們一生的閱歷產生影響。
二、內容追問:《好的故事》何以“難讀”
《好的故事》是散文集《野草》中公認的難讀篇目,過去一直出現在初、高中課本中。它究竟“難”在哪里?筆者擬從詞句的陌生化處理、印象主義及現代派寫作手法、思想意識流動不易捕捉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是詞句的陌生化處理。字詞是漢語閱讀中的基本單位,也是克服閱讀障礙要過的第一關。不少人認為《好的故事》難讀是因為“現代文學的初創時期”與現在語言習慣不同。其實,除了“石油”“蒙朧”等少數詞匯,大部分是作者對詞語進行藝術化處理的結果,如“膝髁”一詞是可以用“膝蓋”來代替的,選用書面詞匯,是與表現“幽雅”幻境相關的。另外一些則是極具地域色彩的方言、風物。例如,南方學生對“云錦”“烏桕”“茅屋”“一丈紅”等詞語可能并不陌生,但北方人若不借助相關資料很難知道這些詞語具體指什么。在《好的故事》中,二十余種事物不加任何修飾地出現在一起,共同組成視野開闊的長鏡頭。這時,任何一個無法還原作者心中意象的詞匯都可能破壞畫面,這是無法用“聯系上下文”的方法來解釋其詞義及表達效果的。
更大的困難來自拗口難讀的句子。這種“魯迅式”的表達或許是中小學生“怕周樹人”的重要原因。課文第七自然段中相互交織的錦帶、狗、白云、村女等,為讀者呈現了極具表現力和感染力的想象圖景。對小學生來說,這些詞語構成的意象組合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日常生活認知,特別是寫景部分有許多長句、復合句,需要拆解、細讀、聯想才能真正弄明白。
二是印象主義及現代派的藝術手法。嚴格來說,印象主義、象征主義、意識流等都是現代主義的分支,這些在《野草》各篇中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好的故事》運用了印象主義藝術手法,使光影、色彩、明暗、物象、視線、構圖、焦點轉換等融入瞬間感覺的捕捉,造成類似于莫奈《日出·印象》等畫作的既視感。很多人都認可《好的故事》寫的是夢境,但在筆者看來,它雖然有類似《死火》的潛意識狀態追攝,主體卻是不滿足于當下而產生的冥想遐思,這與不受意識控制的“做夢”是有本質區別的。由“在蒙眬欲睡的狀態中,看見一個美好的鄉村”而引發的“故事”,實是一次主動的、心理補償式的精神歷險之旅。
印象主義畫家竭力捕捉畫布上宇宙空間所凝結成的時間片段,通過并置不同的色彩顫動、物體運動和結構突然形成,將三維空間轉化為某個時間點的剎那印象。在他們這里,時間是靜止的,而空間是流動的,事物都以超越日常形態的扭曲、夸張、變形來暗示背后隱藏的深意。《好的故事》中各種意象都丟掉由遠近、高低、大小、岸邊、水中等命名的空間秩序,變成飄忽不定的“諸影諸物”。以這種充滿先鋒筆法的作品“喂養”習慣閱讀有頭有尾故事的小學生,難怪他們會讀不懂。
全篇雖不斷重復“好的故事”,但“無數美的人和美的事”僅僅是一些碎影,并沒有一個可稱之為“完整”的故事。這正符合印象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即沒有固定敘事順序、片段式印象記錄、“意識中心”的敘述方式、單一觀察視角,等等;敘事的動力主要來自對故鄉美好生活自然而然的追憶,這是厭倦了當前昏暗、陰沉、無聊之后的真情流露。在個人感覺統攝下,現實與回憶、當下與未來、昏暗與光明、單調與綺麗交織起來而難分彼此,這種打破常規的寫作思路要求讀者必須放下成見,從個人經歷、體驗出發才能真正感受文章的藝術魅力。
三是思想意識流動不易捕捉。若從“昏沉的夜——好的故事——回到暗夜”的結構看,全文行文思路比較清晰,但對文章有關主題及思想內容的提煉,目前學界的分歧仍然很大。單純從語文教育角度考慮,沒必要非得從一篇散文中挖掘太多微言大義,把它簡單處理成思鄉過程或是追憶游覽的經歷可能更好:《好的故事》的真實寫作時間并非文末所注的“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而是當年的一月二十八日。此時恰逢陰歷正月初五,民間有“破五”的習俗,正是“鞭爆的繁響”激發了魯迅對故鄉美好景物的遙想。
《好的故事》以中年人的視角書寫兒時記憶和青少年時期的感受,以對江南生活的追憶構筑起“他鄉一故鄉”的二維結構,本篇整體感情傾向是向往的、溫暖的、欣賞的、喜悅的。因此,解析重心不應過度向文本之外傾斜,而是要理順整篇的行文邏輯,以語言和藝術分析來探討溫馨畫面、深沉情感及和諧意境產生的原因與規律。
很多學生表示不理解為何文中多次提到《初學記》,詹丹對“好的故事”和此書的關系有精彩的論述。筆者想要強調的是,《初學記》作為中國傳統語文教育使用的蒙學讀物,大概讓魯迅想起了幼時在家庭和私塾接受教育的經歷。魯迅幼時曾在寺廟寄名并認有“師父”,以此觀之,文章羅列的“塔”“伽藍”“和尚”等不再是單純地營造典雅氛圍的景物,而是更多地浸潤著他的美好回憶和生命體驗。
三、教學細問:難文能否“深教”,如何“深教”
像《好的故事》這樣篇幅不長而深度、難度都極具挑戰性的篇目,如何組織教學確實非常棘手。從學生閱讀能力的長遠發展來看,教師需要弄清楚難文之“難”的真實原因,充分發揮經典篇目的語文教育價值,即所謂的“難文深教”。這樣主張有三層意思:其一,經典閱讀的重要方法是“涵泳”,學生不一定要理解原著全部奧妙,卻要能在不斷誦讀中受到語言文化的熏陶;其二,魯迅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個性,閱讀應該是“仰之彌高,鉆之彌堅”,學生接受過程“適度超前”是允許的也是必要的;其三,《好的故事》中現代主義的感知及表達方式或許正符合少年兒童以形象思維為主的思維形式。印象主義寫作方法不一定適合作為寫作練習進行模仿,卻可能對學生的認知、思維方式形成潛在而持久的影響。
鑒于此,筆者想從四個方面提出小學階段“難文深教”的教學策略,以就教于方家。
1.分化詞句難度,掃除學生閱讀障礙
《好的故事》適合定位為學生進行語言積累的范文,可以用畫出難詞、查工具書、給詞語歸類、畫圖列表鞏固所學等方法。《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在第二學段有“能用音序檢字法和部首檢字法查字典、詞典”的要求。因此,學生可通過查《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等弄懂“伽藍”等詞的詞義。字、詞典未給“鞭爆”等詞單獨列詞條,可先查每個字的意思,然后把兩個字合起來解釋。詞語分類方面,可處理成“表示事物的詞”“表示動作的詞”“表示色彩的詞”等,不必完全按詞性劃分。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鼓勵學生畫水彩畫、素描畫或連環畫,把自己心目中“好的故事”畫出來,將獲取的語言信息轉化為形象的圖畫。
文中句子難讀的另一個原因是長句拆分成了多個短句,主、謂、賓關系模糊或成分之間比例失衡,如第五自然段的“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卻又退縮,復近于原形”一句,須先弄懂“諸影諸物”究竟包括何“影”何“物”,其空間排列關系如何,以此為基礎,才能明白一連串的動詞都在描述它們的變化過程。須注意的是,此教學環節的語言材料積累和語言知識講解要同時進行,不能把過多的精力放在知識講授上,要讓學生自己讀、自己分析,教師只在必要的時候予以點撥。同時,可輔助使用旁批、注釋、做筆記、好句摘抄等閱讀標識手段。
2.深究文章細節,開闊學生視野
掃除語言障礙后,就可進入一些細節問題的探討。例如,作者將“好的故事”定性為“美麗”“幽雅”“有趣”,文中哪些地方能體現這些特征,沒有明確、具體的事件卻為何稱之為“故事”,它是否真的“有趣”,等等。這樣做的目的是帶領學生深入文本內部,在反復閱讀中將前后相關內容綜合起來看,養成對文章的結構化認知習慣。理解“云錦”“一丈紅”“虹霓”等詞可借助圖片、視頻或實物,也可讓學生描述觀看后的感受,說明作者為何借這些詞語來講述他的故事。
最難教學的是體會文章對瞬間印象的描摹,借助色彩、線條、物象變形等營造超現實場景,學生是不容易理解的。教師可從光線、色差角度設計教學,讓學生回憶或實地觀察室內室外、白天晚上、林中水邊等不同時間、空間的光影變化,再回頭品讀相關段落、語句,體會文章在描寫意象、畫面及感受方面的妙處。作為一本啟蒙讀物,《初學記》能讓我們見識古代少年兒童知識的寬廣,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敬畏之心。可以搜集相關資料、論文來介紹《初學記》,解釋《初學記》和文中“好的故事”的聯系,使學生開闊視野,對文章內涵、行文思路有更深的理解。
3.整合課程資源,有效聯結不同課文
首先要整合課內的課程資源。本單元主題是“認識魯迅”,四篇課文的文體有記敘文、散文、回憶錄和詩歌,從不同側面勾勒出了魯迅的真實生活和精神世界。因此不可孤立地看待每篇課文,要尋找它們之間的聯系,使教學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如《好的故事》涉及農夫、村婦等底層人物,與《少年閏土》中“忙月”屬同一類型,從對他們的贊揚和描寫中,可以看出魯迅“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有的人》)的高貴品格。《好的故事》課后“閱讀鏈接”能幫助學生理解課文,教師須注意引導;語文園地附有魯迅作品中的語段,最好是能夠摘抄、背誦。
此外,還應考慮課外資源對單元學習的重要性。教師應引入相關資料引導學生進行對比閱讀,以加深其對魯迅作品的理解。如《雪》描寫了北方和江南的冬景,《風箏》是對故鄉早春二月的書寫等,均能與《好的故事》相互補充,共同深化某些知識要點。既要考慮小學與初、高中語文教學的區別,更要把握它們的銜接關系。例如,《少年閏土》實際是從初中課文《故鄉》中節選的,前者的教學須找好“錨點”,與更高學段的學習形成難易適中的梯度關系。“難文深教”正是為學生學習魯迅經典作品打好基礎,促進學生后續對魯迅作品的理解,促進其能力的發展。
4.開展主題探究,促進學生思維發展
探究式學習難度相對大一些,但就思維發展和知識積累而言,在小學高年段完全有條件組織相關教學活動。探究活動可與跨學科主題學習、項目化學習、深度學習等新課改提倡的學習方法相結合,使課題研究過程真正轉化為學生做事的能力。可以從不同角度設計探究的主題,如“魯迅生活經歷梳理”“與魯迅有關的人和事”“江南水鄉風俗探究”“紹興地域風物歸類”“浙東地區動植物認知”“四時景物描寫與色彩運用”等。這能夠豐富課堂教學內容,使學生全面回顧、反思學過的魯迅作品,獲得高質量、綜合性的學習成果。
總之,魯迅作品教學的總體原則不是“淺教”,而是以課文核心特征分析為基礎,對其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進行深入挖掘,最終達到“深入淺出”的效果。在以學科核心素養培育為導向的課程改革中,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方式和教學手段,使學生的文化自信、語言運用、思維能力、審美創造等素養得到全面發展,是十分必要的。教師要尊重學生作為“閱讀者”的主體地位,俯下身子研究他們遇到的學習困難,利用各種條件、資源和手段幫他們解決知識發展與能力提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