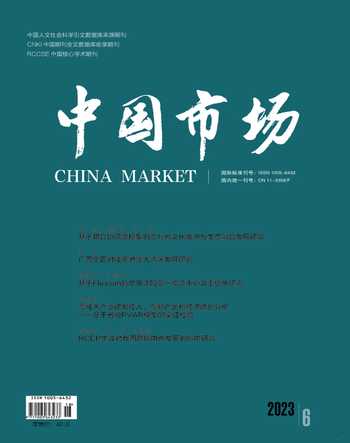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培養問題與對策
張建華 陳金源 溫可儀
摘?要: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推動“互聯網+”內涵與外延不斷豐富,國際貿易出現新的變化表征,為中國培養“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提出更高水平的新要求。當前中國培育“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存在系列問題,主要是針對貿易新業態與新模式的人才不足,特別是數字貿易高精尖人才欠缺,精通各類國際貿易協定規則人才匱乏,以互聯網為媒介的貿易安全人才缺少。有鑒于此,文章認為應強調國際貿易新業態新模式人才的培養、重視數字貿易專業人才的培育、完善國際貿易協定專業人才的培訓體系、建立以互聯網為媒介的貿易安全人才培養模式,為中國建設貿易強國提供更高質量的智力與人才支撐。
關鍵詞: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數字經濟;互聯網+
中圖分類號:?C961;F7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23)18-0000-00
引言
“互聯網+”是中國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國家頂層設計,自2015年李克強總理首次提出以來,“互聯網+”的內涵與外延就隨著實踐不斷演變,特別是2022年中共中央二十大首次將“高質量發展數字貿易”納入中央文件,為培養綜合性復合型國際貿易創新人才提出更高要求。不僅如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傳統的線下交易、見面式洽談等國際貿易運作方式發生改變,國際貿易線上化、無紙化與電子化成為主流趨勢,俄烏沖突疊加新一輪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國際貿易向區域化、短鏈化衍變,培育更高水平的“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勢在必行。不可否認,當前中國發展“互聯網+國際貿易”新業態已經取得系列成就,有推進貿易便利化發展的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有推進貿易無紙化的國際貿易“數字平臺”以及有效降低貿易成本的云計算、大數據、5G等物聯網技術,系列成就的取得為培養“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提供堅實基礎。然而,當前“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仍然停留在傳統貿易階段,數字貿易、貿易安全、市場采購等新型人才的培育較為欠缺,精通DEPA、RCEP與CPTPP等高標準貿易規則的制度型人才較少。因此,文章在剖析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國際貿易新變化下,深入分析當前“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培養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對完善我國國際貿易學科人才培養體系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1?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國際貿易的新變化
1.1新業態新模式成為國際貿易新增長點
第一,海外倉建設逐漸成為跨境電商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點。2015年5月中國商務部印發《“互聯網+流通”行動計劃》,倡議跨境電商出口企業建設海外倉布局國際貿易物流體系,截至2021年12月,中國海外倉在全球布局已超2000個,預計未來有關海外倉與跨境電商的貿易人才需求將更加旺盛。第二,新興市場采購貿易方式成為貿易新增長點。中共中央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培育市場采購貿易新業態。截至2022年9月,中國市場采購試點示范城市擴大至31個,市場采購貿易方式的改革紅利正不斷釋放。第三,綠色貿易新業態成為貿易新增長點。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歐盟是中國重要的綠色貿易進出口伙伴,2019年中國與歐盟雙邊綠色商品貿易、綠色服務貿易規模高達560億美元。“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促進貿易綠色發展,推動形成低碳經濟與循環經濟已經成為當今國人的普遍共識,培育貿易綠色化轉型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1.2數字經濟成為國際貿易新動能
第一,數字經濟催生數字貿易新業態。隨著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高速發展,數字經濟正在重塑貿易方式與貿易格局,已逐步成為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新式動能。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數字貿易發展與合作報告2022》,2021年中國數字貿易規模達2.33萬億元,數字貿易出口規模達1.26萬億元,同比增長18%。第二,數字經濟推動貿易數字化轉型。一方面,以數控機床、數字機器人為代表的數字新動能正逐漸推動傳統加工貿易向數字加工、智能加工與環保加工等方面升級,有助于加工貿易從低端鎖定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充分發揮其無紙化、便捷化與快速化的比較優勢,推動傳統一般貿易在生產、流通、銷售或售后等各個環節降低成本與提質增效,助力傳統貿易方式的數字化轉型。綜上所述,培養更優質的數字貿易專業人才是數字經濟時代下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高質量發展數字貿易與數字經濟的應有之義。
1.3系列國際貿易協定成為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新亮點
第一,更加關注《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的核心條款。DEPA以其深入的電子商務便利化條款、跨境數據移動自由化條款與數字安全條款,成為“互聯網+”或數字貿易的高標準條款。2022年8月中國已開啟申請加入DEPA的首輪談判,有望為數字貿易規則“中式模板”的形成提供平臺基礎。第二,更加關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高質量落實。中國加入RCEP是繼2001年加入WTO后再一次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如何高標準落實RCEP在數據要素跨境流動、數字貿易經濟合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成為當前人才培育的重要課題。第三,更加關注《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申請加入。統籌國內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是推進中國制度型開放的應有之義,充分對標CPTPP在知識產權、市場準入與技術壁壘等方面的高標準條款,有利于中國構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制。高水平的制度開放離不開高質量的人才支撐,培養高層次的國際貿易制度型人才成為當前教育體系的重要任務。
1.4貿易安全成為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第一,更加注重“互聯網+”關鍵技術與核心設備的貿易安全。互聯網能否順利聯動國際貿易,關鍵在于數據要素與因特網技術能否順暢流動與運用。然而,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多次援引“安全例外條款”倡導數據本土化與數據回流措施,在電子芯片、服務軟件等互聯網核心技術方面限制中國,而中國對于互聯網關鍵設施與技術的貿易依存度高達80%。第二,更加注重“互聯網+”核心國際貿易條款的制度安全。當前,國際各類型貿易條款與貿易協定顯現“意大利面碗”效應(Spaghetti?Bowl?Effect),針對中國互聯網貿易的“排外性”區域條款層出不窮,出現以《美墨加三國協議》(USMCA)為代表的“毒丸條款”,規制合圍中導致中國貿易安全處于不利地位。第三,更加注重“互聯網+”的供應鏈與價值鏈安全。俄烏沖突標志著國際貿易傳統安全回歸,“互聯網+糧食安全”、“互聯網+能源安全”等國際貿易安全新式命題亟待深入研究。因此,為了維護我國持續穩定的貿易安全局面,解決當前貿易安全面臨的新式問題,亟須培養更高質量的貿易安全專業人才。
2?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培養存在的問題
2.1新業態新模式國際貿易人才不足
第一,國際貿易課程設置停留在傳統階段。部分院校對于國際貿易學科教學的創新性不足,主要體現在教師知識固化嚴重,缺乏對貿易新業態與新模式的深刻理解,教學仍然停留在傳統的陸運、海運與空運貿易階段,對于跨境電子商務、政府市場采購、綠色貿易與數字貿易等新業態與新模式的授課內容較少。第二,授課軟件無法滿足“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新需求。高等院校普遍購入SIMTRADE、POCIB等教學軟件,該類軟件僅能模擬傳統貨物貿易全流程,無法仿真有關海外倉、市場采購、綠色貿易等新業態的運作過程,導致精通新模式的國際貿易人才稀少。第三,新業態新模式校企合作不到位。國際貿易新業態與新模式發端于騰訊、華為、TCL等互聯網大型企業,“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的培養理應對接新業態企業的具體項目與工作,校企合作不到位將大幅度降低“互聯網+”人才步入新業態企業實習實踐的機率,降低人才培養的實際效果。
2.2數字經濟數字貿易高精尖人才欠缺
第一,國際貿易專業教材滯后于數字貿易發展。當前,中國國際貿易學科專業的通用教材仍然集中于講授傳統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的進出口理論與實務,鮮少章節涉及數字貿易的前沿知識,甚至將數字貿易與跨境電子商務、服務貿易或互聯網技術等內容混淆,導致國際貿易人才培養偏離實際。第二,數字貿易專業“雙師型”人才不足。目前,中國經濟學學科門類下仍沒有將數字貿易設置為二級或三級學科,而是將數字貿易作為國際貿易學科的研究方向之一,勢必弱化了數字貿易專業屬性的同時,導致數字貿易教育型高端人才欠缺。第三,數字貿易理論與實踐教學分離。現階段,數字貿易的研究聚焦于前沿高端學術理論,與數字貿易有關的進出口貿易實訓、海關報關實操、數據跨境流動實踐、線上展會、線上商務禮儀等實務型研究關注較少,無法達到培養“互聯網+”實踐型人才的預期目標。
2.3精通各類國際貿易協定規則人才匱乏
第一,缺乏精通各類國際貿易協定的專業人才。國際上各類多邊貿易協定、雙邊貿易協定與區域貿易協定層出不窮,各類規則協定日新月異,同時精通CPTPP、DEPA與RCEP等高標準國際貿易協定深度規則的“互聯網+”人才較少,導致在具體貿易實操中出現貿易不合規的問題現象,能夠利用相關規則規避貿易風險人才更是少之又少。第二,缺乏到各類國際組織實習工作的國際貿易人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實力、國際社會影響力與日俱增,以WTO、WB與UN為代表的國際政府組織到各類非政府國際組織種類繁多,但是在國際組織中鮮少有中國學生參與實習或工作,減少了深入學習各類國際貿易組織或國際貿易協定的機會,導致精通各類國際貿易協定規則的“互聯網+”人才匱乏。第三,精通各類小語種的“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不足。CPTPP、DEPA與RCEP等國際貿易協定以英語通行語種為主,然而,隨著東南亞、非洲等國家日益成為中國簽訂貿易協定的重要合作伙伴,缺乏精通世界各國小語種的通識人才不符合“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培養要求。
2.4以互聯網為媒介的貿易安全人才較少
第一,課程理實一體化欠佳。部分院校教師大多將俄烏沖突、新冠肺炎疫情、臺海危機或中美貿易摩擦等貿易安全事件作為翻轉課堂或議題式課堂的興趣案例,并沒有深入探究此類貿易安全事件涉及的前沿知識,包括如何加強互聯網安全、如何維護貿易安全,無法在理論與實踐一體化中培養“互聯網+”專業型人才。第二,互聯網技術與貿易安全課程內容融合度較低。截至2022年11月,中國已然成為全球遭受“雙反調查”最多的國家,部分院校對于貿易安全的授課內容局限于過往的、已經發生的貿易安全事件,利用互聯網模擬仿真技術預警或演練未來可能發生的貿易安全內容涉及較少,不利于以互聯網為媒介的貿易安全人才培養。第三,貿易安全授課內容不全面。課程內容集中于“互聯網+”關鍵技術與核心設備的“卡脖子”問題,對于“互聯網+糧食安全”、“互聯網+能源安全”、“互聯網+產業鏈安全”等國際貿易安全新式議題關注較少,對于新式貿易壁壘的認識不足。
3?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培養的對策
3.1強調培養國際貿易新業態與新模式人才
第一,國際貿易課程設置需滿足“互聯網+貿易新業態”需求。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應結合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的新型增長點,在原有的國際貿易實務、國際貿易理論、國際商務研究等課程基礎上,設置更多有關海外倉、市場采購、綠色貿易或價值鏈貿易等貿易新業態與新模式的課程體系,拓展傳統貿易課程的內涵與外延。第二,設計或引入更多與貿易新業態有關的模擬仿真教學軟件。高等院校通過組建科研團隊重點關注跨境電商、海外倉、市場采購或綠色貿易的動態貿易全過程,攻關貿易新業態仿真軟件的研發與設計,為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提供更優質的授課工具與教學設備,在真正意義上實現教學相長。第三,形成“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的校企聯合培養機制。鼓勵高等院校與國際貿易新業態“領頭羊”企業開展深度的合作與交流,倡導形成校內導師負責理論教學、校外導師負責實踐運用的“雙導師”制度,院校與企業基于共同理念建立理論與實踐互補型培養體系,增加學生“面向企業”合作與實習的機會,提升國際貿易人才的綜合素質。
3.2重視數字貿易專業人才的培育
第一,撰寫或運用前沿的數字貿易專業教材。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的教材體系應與時俱進,在保有國際貿易學科核心章節內容的基礎上,新增更多高質量的數字貿易理論知識與實訓內容,拓展數字貿易在課程框架與課程內容的比列,區分電子商務、服務貿易與數字貿易授課內容的具體差異,強調個性化、全面化與差異化的數字貿易人才培養。第二,培養更多“雙師型”數字貿易專任教師人才。鼓勵更多中青年教師讀博深造、深耕教研與學科競賽,培養更多數字貿易專業相關的“雙素質型”教師或“雙職稱型”教師,優化教師職稱認定的評價體系,不斷完善“互聯網+”與數字貿易教師隊伍的人才建設。第三,將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融合。建議參考浙江大學中國數字貿易研究院有關數字貿易的課程設置體系,注重數字貿易實踐與數字貿易理念的聯動,強調數字貿易基本概念、理論模型與運行機理時,更注重數字貿易框架下跨境電子商務進出口的模擬練習與報關實務操作,形成“理論課堂—專業競賽—學科論文—社會實踐”四位一體的數字貿易專業人才培養架構。
3.3完善國際貿易協定專業人才的培訓體系
第一,培育國際貿易協定專精人才。從國際經濟與貿易、國際商務或國際治理專業入手,制定更高標準的考核體系與課程架構,著重培養更多精通各類國際貿易協定深度規則的專業人才。第二,鼓勵更多學生到國際組織機構實訓學習。建議參考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治理創新研究院培育國際組織人才的具體措施,與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形成緊密合作,搭建學生“走向國際組織”的重要平臺,實行“2+1+1”制度安排,即2年在國內高校開展國際貿易理論學習、1年在國外院校開展國際貿易實踐學習、1年到國際組織開展實訓實習活動,鼓勵更多學生培養國際勝任力,積極申報國際組織實習機會。第三,培養更多“互聯網+小語種”國際貿易復合型人才。鼓勵各個高校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高校開展密切合作,搭建國際貿易人才聯合培養實訓基地,探索“雙學位”培養制度,推動更多的學生到東盟、非盟或歐盟等國家院校開展交換生合作項目,接受不同語言環境下國際貿易規則制度的學習,培養“國際貿易+小語種”的復合型人才。
3.4建立以互聯網為媒介的貿易安全人才培養模式
第一,推進貿易安全課程體系的理實一體化建設。構建系統的國際貿易安全理論體系與知識架構,將熱點問題、具體案例與貿易理論相銜接,在培養學生對于貿易安全議題興趣的同時,結合國際貿易的有關理論,深度解讀貿易安全事件的來龍去脈與歷史價值。第二,推進互聯網技術與貿易安全授課體系的深度融合。強化情景式教學方法的運用,建立具備實踐性與操作性的貿易安全沙盤與仿真體系,探索貿易安全事件在事前預警、事中應對與事后反饋的處理全流程,在角色扮演或沙盤游戲中逐步建立以互聯網為媒介的貿易安全人才培養體系。第三,健全貿易安全人才培養授課體系。結合國際貿易熱點時事,延伸有關反傾銷、反補貼與保障措施等方面的授課深度,加強對新式數字貿易壁壘、綠色貿易壁壘與價值鏈貿易壁壘的授課學習,全方位關注“互聯網+糧食安全”、“互聯網+能源安全”“互聯網+關鍵技術”等國際貿易安全新式議題,明確貿易安全人才培養模式的核心內容。
4?結論
“互聯網+”驅動了中國國際貿易出現系列新的變化特征,適時開展“互聯網+”國際貿易人才培養方式改革,對標貿易新業態新模式,對接社會企業、國際組織或貿易協定的實際需求,建立以“互聯網+”為媒介的人才培訓體系與培養模式是國際貿易學科保有鮮活生命力的應有之義,為中國貿易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
參考文獻:
[1]李孟一.國際商務專業碩士人才培養初探[J].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5(2):154-160.
[2]趙曉俊.“一帶一路”框架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研究[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9,39(6):12-14.
[3]趙麗芳.應用型人才培養視角下“國際貿易實務”課程的教學改革研究——以山西為例[J].教育理論與實踐,2020,40(24):47-49.
[4]黃萍,錢曉英.國際貿易專業創新人才培養探究——評《國際貿易實務》[J].中國教育學刊,2017(4):130.
[5]杭言勇,嚴莉.協同創新視角下高校教學實訓平臺建設探討——以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國際貿易人才培養為例[J].中國高校科技,2016(8):63-65.
[6]趙龍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國際治理人才培養[J].太平洋學報,2020,28(1):28-35.
[作者簡介]張建華(1983—),男,漢族,甘肅慶陽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經濟貿易學院博士研究生,廣東食品藥品職業學院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國際物流;陳金源(1997—),男,漢族,廣東中山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經濟貿易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貿易政策;溫可儀(1998—),女,漢族,廣東惠州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經濟貿易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貿易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