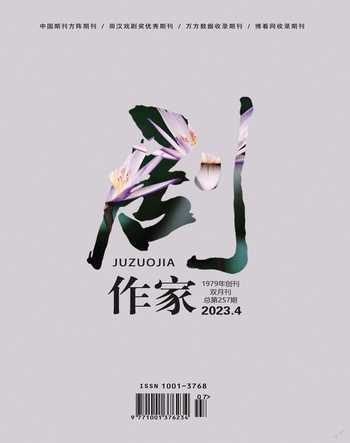當(dāng)代動畫創(chuàng)作在戲曲舞臺藝術(shù)上的應(yīng)用探析
黃小航 宋巖峰
摘 要:戲曲發(fā)展至今,面臨現(xiàn)代思潮的沖擊和數(shù)字媒體技術(shù)的挑戰(zhàn),迫切需要轉(zhuǎn)換創(chuàng)作策略。只有實(shí)現(xiàn)敘事與技術(shù)上的雙重“破圈”才能在新時代下蛻變,創(chuàng)作出符合時代需求和人民需要的作品,取得市場與口碑的雙贏。當(dāng)代動畫同樣在探索中進(jìn)化,動畫的創(chuàng)作與戲曲有共同的來源,而動畫在表達(dá)與技術(shù)應(yīng)用上又比戲曲多走了幾步,從動畫中學(xué)習(xí)經(jīng)驗(yàn)是舞臺藝術(shù)未來的發(fā)展方向。
關(guān)鍵詞:動畫創(chuàng)作;戲曲舞臺設(shè)計(jì);數(shù)字媒體
戲曲是具有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風(fēng)格的舞臺藝術(shù),借助舞臺的調(diào)度、演員的唱念做打再現(xiàn)劇本,在長久的發(fā)展中成為一部分人的偏愛。與戲曲相對的,數(shù)字媒體技術(shù)的崛起為動畫注入活力,動畫依靠自身所具備的幻想性與數(shù)字媒體技術(shù)結(jié)合得如魚得水,電影也借助二者的優(yōu)勢拓寬了銀幕的表達(dá)內(nèi)容和表現(xiàn)形式。
電影與戲劇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中國電影的開端也以戲曲電影《定軍山》吹響號角,開始了很長一段時間“影戲”的探索。由此可見,藝術(shù)的發(fā)展本就是互相學(xué)習(xí)交融結(jié)合的過程,而學(xué)習(xí)動畫之創(chuàng)新、揚(yáng)戲劇之所長可謂戲曲未來的發(fā)展之道。筆者試分析論述動畫敘事與戲曲舞臺藝術(shù)結(jié)合的可能性,提出戲曲舞臺藝術(shù)的創(chuàng)新可從動畫創(chuàng)作中吸取養(yǎng)分,在內(nèi)容上突出現(xiàn)代性,在形式上借助技術(shù)實(shí)現(xiàn)舞臺效果的飛躍。因戲曲自身的民族性特質(zhì),故本文所論述的“動畫”也相對應(yīng)特指中國動畫。
一、動畫創(chuàng)作應(yīng)用于戲曲的可能性
動畫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而著稱,戲曲則多是改編自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或民間故事,二者在表現(xiàn)形式上看似天差地別,究其實(shí)質(zhì)其實(shí)是同根同源開出的兩朵不一樣的花。回溯歷史,中國的第一部彩色動畫長片《大鬧天宮》就大量借用戲曲元素,臉譜化的角色設(shè)計(jì)、戲曲動作與戲曲配樂等,無論是內(nèi)容還是形式都能看出戲曲對其創(chuàng)作的影響,可見動畫與戲曲并不是相斥的關(guān)系,反而因它們自身的性質(zhì)、創(chuàng)作的要求,例如題材廣度、內(nèi)容深度等,而具備交融的可能性。
(一)民族美學(xué)的共同性質(zhì)
中國動畫和中國戲曲具有強(qiáng)烈的民族性。傳統(tǒng)戲曲經(jīng)過多年的積淀,早已擁有最能代表中國的、傳統(tǒng)的、民族的美學(xué)特征,其寫意的、留白的、概括的美學(xué)傾向,與中國動畫的創(chuàng)作不謀而合。
“美術(shù)片”是中國動畫的開端,初期的美術(shù)片借鑒中國傳統(tǒng)美術(shù)中的剪紙、水墨畫等,又吸收戲曲的表現(xiàn)經(jīng)驗(yàn),因而與美、日的動畫相比有明顯的去卡通化特征,表現(xiàn)出土生土長的中國民間美學(xué)氣質(zhì)[1]。在表現(xiàn)形式上,角色設(shè)計(jì)臉譜化,人物臺詞采用戲曲念白,人物動作參考戲曲的唱念做打,配音使用傳統(tǒng)戲曲配音;在表現(xiàn)內(nèi)容上,適當(dāng)留白,例如在《哪吒鬧海》里哪吒重生之后,結(jié)尾并未交代他的去處,而是以他乘坐仙鹿遠(yuǎn)去給觀眾以無限遐想,哪吒悲劇而孤獨(dú)的人物形象由此而生。
(二)家喻戶曉的敘事原型(民間傳說、神話傳說)
戲曲和動畫有著相似的敘事原型。戲曲的創(chuàng)作多來自于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白蛇傳》以白蛇與許仙的愛情故事為藍(lán)本,《霸王別姬》取材自秦末楚漢相爭時項(xiàng)羽虞姬的愛情故事,四大名著也皆被改編成戲曲劇本,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歷史積淀為戲曲藝術(shù)家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靈感。動畫的創(chuàng)作則更具靈活性,基于家喻戶曉的神話故事之上或補(bǔ)全敘事邏輯次序、或擴(kuò)大敘事范圍[2]。早期的動畫長片《大鬧天宮》截取《西游記》原著的片段,故事對觀眾的理解并不造成障礙,這得益于選取的題材來自觀眾熟悉的敘事原型。基于人人熟知的敘事原型,對神話原型的擴(kuò)充與重塑就成為動畫電影創(chuàng)作的常用手段,保留神話原型的再創(chuàng)作如《魔童降世》、“新神榜”系列,均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動畫的敘事拓展使家喻戶曉的傳說陌生化,賦予舊故事新的意義。戲曲保有中華民族最具民族性的藝術(shù)結(jié)晶與文化價(jià)值,想要邁向更廣闊的世界,從動畫的創(chuàng)作中汲取“新瓶裝舊酒”的經(jīng)驗(yàn)未嘗不是一條可行之道。
(三)戲曲推廣的需要
新媒體時代下,戲曲的推廣面臨挑戰(zhàn),市場呼喚年輕化的、現(xiàn)代化的戲曲走入年輕人的視線。粵劇電影《白蛇傳·情》為戲曲的“破圈”提供了很好的參照。這部影片保留了戲曲的古典詩意美學(xué),巧妙地把情與境、虛與實(shí)可視化,演員的唱念做打融于鏡頭語言中,場面調(diào)度下建構(gòu)出傳統(tǒng)之美,唱詞唱腔也經(jīng)過流行化的改編,降低觀眾欣賞門檻的同時又保留原有的藝術(shù)氣質(zhì),高質(zhì)量的成片配合多渠道的線上宣傳,使《白蛇傳·情》成為傳統(tǒng)戲曲走向世界的優(yōu)秀范式[3]。戲曲作為一門綜合性的藝術(shù),集詩歌、音樂、說唱、表演、舞蹈等于一體,具有很強(qiáng)的包容性。從外部環(huán)境來看,戲曲可以適應(yīng)時代的變化;從內(nèi)部特征來看,戲曲能夠包容其他藝術(shù)。與影像的聯(lián)姻正是戲曲推廣的手段之一,而動畫作為影像的一個分支,其敘事方式與美學(xué)建構(gòu)的演變也為戲曲的推廣提供了可靠的參考依據(jù)。
二、內(nèi)容的轉(zhuǎn)向: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
戲曲的傳統(tǒng)性既來自于長期演變中形成的表演的固定程式,又來自于自古至今的劇作。早已形成的程式性是戲曲的本體性特征,而劇作則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有不同的表達(dá)訴求。在新媒體時代要走近大眾,戲曲舞臺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動畫長片與時俱進(jìn)的內(nèi)容轉(zhuǎn)變?yōu)閼蚯膬?nèi)容轉(zhuǎn)變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從《大鬧天宮》到《大圣歸來》,從《哪吒鬧海》到《魔童降世》,“美術(shù)片”到“動畫電影”的路徑不僅是民族化的研習(xí)結(jié)果,更是市場化的轉(zhuǎn)型升級。
(一)流行性
具備流行性特征的內(nèi)容能在新媒體時代下被快速捕捉。動畫長片的創(chuàng)作在轉(zhuǎn)型過程中受到后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從而使近年來的動畫電影具有流行性的“國潮”色彩。在角色的形象設(shè)計(jì)上,同樣是神話人物哪吒,《新神榜:哪吒重生》把哪吒形象一分為二,現(xiàn)代與古代的形象兼容于主人公身上,以雙重身份為觀眾增添新鮮感;而《魔童降世》里的黑眼圈哪吒則以搞怪調(diào)皮的外貌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掀起模仿潮流;《羅小黑戰(zhàn)記》里的哪吒又是穿著時髦的青少年形象。三個不同形象的哪吒在傳統(tǒng)印象的基礎(chǔ)上融入“國潮”美學(xué),從而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哪吒新形象。在劇作的改編上,《魔童降世》采用雙男主的設(shè)定,從正反兩面表達(dá)少年人的內(nèi)在成長;《新神榜:楊戩》在敘事上更為年輕化,主人公楊戩的形象更符合當(dāng)代年輕人的審美喜好,楊戩也跳脫出傳統(tǒng)敘事中鐵板一塊的性格設(shè)定。動畫電影擺脫“低幼”標(biāo)簽,把消費(fèi)群體放大到青年群體當(dāng)中,敘事年輕化、角色偶像化就成為了必然的趨勢。戲曲在流行性上的挖掘可以參考戲曲電影《白蛇傳·情》的敘事新編。唱作為戲曲最主要的敘事手段,包含豐富的信息量。《白蛇傳·情》知曉其道而另辟蹊徑,新編通俗易懂的流行唱腔,并保留原有的粵劇唱腔,民樂與西洋樂的化學(xué)反應(yīng)兼顧了普通觀眾的品鑒趣味,大大降低了欣賞門檻,從而實(shí)現(xiàn)了戲曲的“破圈”[4]。戲曲在流行性上的突破不僅是內(nèi)容上的,還是形式上的。
(二)時代性
藝術(shù)既是民族的,也是時代的,在價(jià)值體系上回應(yīng)時代的訴求是作品時代性的體現(xiàn)。在這一點(diǎn)上,動畫電影提供了商業(yè)性與藝術(shù)性并存的典范。《魔童降世》在價(jià)值觀上回應(yīng)年輕人的心理訴求,讓哪吒發(fā)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吶喊;《白蛇:緣起》在劇作的改編上更是極盡巧思,糅合古典文本《白蛇傳》與《捕蛇者說》,加以前世今生的愛情書寫,頗具女性主義的劇本打造出青年化的動畫電影,白娘子的形象頗具反叛與主觀能動性,正緊跟了當(dāng)前時代對女性的關(guān)注。相同題材的《白蛇傳·情》在時代性上的建構(gòu)無疑也是成功的,戲曲影視化這一手段首先就是對戲曲的革新,把戲曲舞臺搬到銀幕上,化戲曲演員表演假定性之虛為實(shí),觀眾能通過影像實(shí)實(shí)在在地感受到戲曲唱詞之所指。其次在粵語歌詞上也做了通俗化改編,流行性的粵語小調(diào)和現(xiàn)代化的管弦配樂拓寬了粵劇唱腔的層次,也使得影片中的唱腔有著時代性的標(biāo)志。時代與藝術(shù)的雙向交流督促戲曲舞臺要擁抱時代,用傳統(tǒng)的根結(jié)出現(xiàn)代的果。
(三)奇觀性
奇觀能做到最直接的視覺沖擊。動畫始終沒有放棄對奇觀制造的追求。在早期的美術(shù)片中用二維動畫創(chuàng)造出東海龍宮、天庭、蟠桃園等奇觀景物,藝術(shù)家以高超的創(chuàng)作能力把人們對神話傳說的印象可視化,滿足觀眾對奇觀的好奇心理。隨著新媒體技術(shù)的成熟,近些年的國產(chǎn)動畫電影多以三維建模形式呈現(xiàn),三維效果極大地豐富了畫面質(zhì)感,也融入了更多新奇的場景設(shè)計(jì)。如“新神榜”系列的場景把賽博朋克美學(xué)與中國古典建筑結(jié)合起來,把神話人物放在霓虹燈下,擴(kuò)充原作的世界觀,使故事背景如游戲一般更具可讀性和探索性。粵劇電影《白蛇傳·情》發(fā)揮影像的優(yōu)勢,打破了演員假定表演的程式,化虛為實(shí),使用大量實(shí)景結(jié)合舞臺效果創(chuàng)造意境,一切景語皆情語,以奇觀景色襯托情意,其中利用特效制造的水漫金山令人嘆為觀止,成為經(jīng)典片段。奇觀化的舞臺效果使抽象的情境具象化,既展現(xiàn)了文本的表達(dá)層次,又豐富了觀眾的視聽享受,也有助于戲曲走向更年輕的群體。
三、技術(shù)的加持:從平面到縱深
數(shù)字媒體技術(shù)為傳統(tǒng)藝術(shù)帶來走出瓶頸的轉(zhuǎn)機(jī),使戲曲舞臺“活”起來。傳統(tǒng)的戲曲舞臺背景通常是靜止的、平面的,借LED屏幕塑造的“立體舞臺”使戲曲舞臺呈現(xiàn)出縱深的空間感,并能跟隨情節(jié)而發(fā)生相應(yīng)的變化,使情與景適時交融,虛實(shí)得當(dāng),傳統(tǒng)的平面詩意由此立體起來[5]。
數(shù)字媒體藝術(shù)的發(fā)展在動畫上表現(xiàn)為3D技術(shù)、動捕技術(shù)的應(yīng)用,逼真的場景與人物動態(tài)在銀幕上呈現(xiàn)出來的畫面是詩意化、藝術(shù)化后的真實(shí)。早期的美術(shù)片從戲曲中借鑒大量創(chuàng)造情境的方法,把戲曲技巧應(yīng)用于動畫中,除參考戲曲配樂與動作外,角色在平面上左右移動,彼此交互,仿佛戲曲表演中的演員你方唱罷我登臺的場面,也能看出戲曲對美術(shù)片的影響。這種平面上的表現(xiàn)形式來源于中國水墨畫散點(diǎn)透視的傳統(tǒng),如畫卷一般在平面上寫意,也符合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的觀賞邏輯。
戲曲舞臺的詩意代表中國傳統(tǒng)美學(xué)的氣韻特征,藏在假定性舞臺中的情與景,虛實(shí)交錯,營造出詩意。《白蛇傳·情》把戲曲的詩意影像化,把情融于景中,水袖舞、蛇仙斗法采用多機(jī)位多角度拍攝,鏡頭的運(yùn)動增強(qiáng)沉浸感,特效使戲曲舞臺躍升成為奇觀,觀眾仿佛置于煙霧繚繞的場景中,沉醉于白娘子與許仙真摯的愛情。
數(shù)字媒體與戲曲、動畫的結(jié)合使技術(shù)成為藝術(shù),戲曲和動畫由此跳出平面的交互,內(nèi)容與形式上都突破平面,走向更有縱深感的立體表達(dá)。從戲曲與動畫在數(shù)字媒體藝術(shù)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可以知道使詩意的美從平面拓展到縱深是大勢所趨,極為相似的特性與發(fā)展趨勢為二者向彼此參考學(xué)習(xí)奠定基礎(chǔ)。
中國傳統(tǒng)的欣賞趣味發(fā)展了幾千年,戲曲藝術(shù)集之大成,始終代表著最正統(tǒng)、最本土的中國之美。科技的發(fā)展為戲曲藝術(shù)帶來挑戰(zhàn),也帶來了機(jī)遇。挑戰(zhàn)在于面對市場化、商業(yè)化的趨勢,要如何保持自身的藝術(shù)特征又契合觀眾的觀賞愛好,實(shí)現(xiàn)“破圈”;機(jī)遇在于要利用科技的進(jìn)步走出瓶頸,探索并發(fā)展現(xiàn)代化的戲曲舞臺藝術(shù)。對此中國動畫的演變路徑提供了很好的參考經(jīng)驗(yàn)。近些年來我們見證了國產(chǎn)動畫電影的崛起,相信市場與科技也能為戲曲舞臺藝術(shù)帶來崛起的力量。
注釋:
[1]陶冶,馮穎倩:《試談中國動畫學(xué)派的價(jià)值系統(tǒng)重建——一種基于近年來國產(chǎn)動畫電影的題材偏好的觀察》,《當(dāng)代動畫》,2022年第1期
[2]尚文思琦:《精神胎記與靈感觸媒——中國神話原型在國產(chǎn)動畫中的應(yīng)用》,《當(dāng)代動畫》,2022年第2期
[3]葉瑩:《詩意表征、美學(xué)風(fēng)格與現(xiàn)代追求:4k粵劇電影〈白蛇傳·情〉的意義生成》,《劇作家》,2022年第5期
[4]劉婧,饒曙光:《共同體美學(xué)視域下的“國潮電影”》,《當(dāng)代電影》,2022年第6期
[5]蔡佳欣:《探究數(shù)字媒體技術(shù)在戲曲舞臺美術(shù)的應(yīng)用之美》,《中國文藝家》,2021年第1期
(作者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
責(zé)任編輯 姜藝藝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