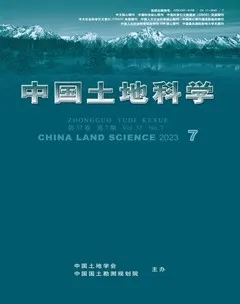綜合“同質等效—流補平衡”的耕地“進出平衡”管制:方法與實證
梁坤宇,金曉斌,3,王世磊,應蘇辰,祁 曌,周寅康,3
(1.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2.自然資源部海岸帶開發與保護重點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23;3.江蘇省土地開發整理技術工程中心,江蘇 南京 210023)
作為糧食生產的命脈和主要載體,耕地及其利用狀態直接影響著糧食安全[1-2]。中國人多地少,需要用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養活全球近20%的人口[3]。然而,隨著城市化的持續推進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較為普遍地出現了耕地轉為林地、草地、園地、養殖坑塘等其他農用地以及改種非糧食作物的耕地“非糧化”現象[4],威脅國家糧食生產的可持續供給[5]。2021 年11 月《關于嚴格耕地用途管制有關問題的通知》提出對耕地轉為其他農用地及農業設施建設用地實行年度“進出平衡”,嚴格管控一般耕地轉為其他農用地;2022 年《耕地保護法(草案)》設置耕地用途管制專章,進一步明確了耕地“進出平衡”的原則和范疇。面向新時期中國耕地保護形勢與問題,深化耕地“進出平衡”的學理解析并探索其用途管制路徑對穩定糧食生產、維護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學術界關于耕地用途管制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非農業建設占用耕地領域,以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總目標為基礎,重點從永久基本農田劃定和耕地“占補平衡”核算兩方面展開。在永久基本農田劃定方面,主要基于農用地分等[6]、LESA[7]、景觀生態格局[8]、貝葉斯網絡[9]、多目標粒子群[10]等評價方法和空間自相關[11]、空間聚類[12]、象限分析[13]等分區方法,在不同行政單元[14]及城市邊緣區[7]等特定區域開展了數量、質量、空間布局與建設時序等方面的用途管制研究[15];在耕地“占補平衡”方面,主要基于農用地分等和標準糧產量測算等級折算系數[16],探討了耕地“占補平衡”的時空特征與驅動機制[17]、實施成效與評價核算[18]、存在問題與對策建議[19],其用途管制內涵從“數量平衡”逐漸轉為“數量、質量平衡”再拓展到“數量、質量、生態平衡”[20]。然而,耕地“非糧化”背景下的農用地系統性治理研究尚不充分,現有研究多關注耕地“非糧化”的概念界定與測度、影響因素識別、綜合效應評估與管控路徑調控等問題,運用空間分析與計量回歸分析方法,主要使用非糧食作物面積占比或某一時間段內耕地用途改變面積占比等指標在宏觀、中觀、微觀等尺度刻畫耕地“非糧化”時空格局[4,21-22],探究自然稟賦、經濟社會、行為主體、制度政策等因素對耕地“非糧化”的影響與驅動機制[2,23-24],分析其在自然本底、糧食供需、利用主體等方面導致的生態安全、資源安全、生計安全[25-27],并從優化糧食生產布局、部門協同管控、加大補償機制、建立專項基金、推動產業升級、構建法律規制等角度提出防治對策[23,28-29]。尤其是在耕地“進出平衡”制度提出后,對一般耕地的管控進一步嚴格,從“占補平衡”到“進出平衡”的耕地用途管制邏輯予以重視[30],“進出平衡”管制需要遵循以適宜性評價為支撐和以糧食產能提高為目標的基本原則[31-32]。面向實現耕地利用空間配置優化以及細化耕地用途管制的現實需求[27],耕地“進出平衡”管制的認知體系和綜合治理框架仍有待進一步深入探索。
基于此,本文按照“體系認知—框架構建—案例實證”的邏輯主線,在明晰耕地“進出平衡”管制目標、對象、要求的基礎上,構建基于“同質等效”的耕作適宜性評價方法和基于“流補平衡”的管制分區方法,以江蘇省宜興市為研究區進行實證分析,以期為推動耕地“進出平衡”政策落實提供科學支撐,并為防治耕地“非糧化”難題提供有益借鑒。
1 耕地“進出平衡”管制體系
1.1 管制目標:通過優化農用地布局實現耕地長期穩定利用
耕地用途變化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一般而言,耕地用途變化后,耕地系統可在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的干預下實現自我調節,維系自身穩定[33]。然而,這種調節機制并不總是穩定的,特別是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的刺激與行為主體的響應共同導致耕地過度“非糧化”傾向,易造成耕地利用的結構失衡與功能紊亂。為保證耕地長期穩定利用,有必要通過規范耕地“進出平衡”的用途管制,約束農用地內各地類間隨意轉化用途的行為,使用公權力對私權進行約束以滿足公共利益最大化。在數量與質量雙控下,通過空間上的流轉置換以求緩解耕地單向流出造成的耕地“非糧化”問題,實現區域耕地保護及持續穩定的良田糧用。
1.2 管制對象:一般耕地與可恢復非耕農用地
耕地“進出平衡”轉出的是不穩定利用、質量較低、零星分散、不利于集中管理的耕地,轉入的是理論上適合整治恢復為耕地的所有非耕農用地。在耕地內,永久基本農田范圍內的地塊是依法劃定的優質耕地,重點用于糧食生產,原則上禁止轉用,故將其定義為穩定利用耕地;永久基本農田范圍外的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糧食和棉、油、糖、蔬菜等農產品及飼草飼料生產,但在管控不當時,可能出現過度種植其他農作物的情況,導致耕地質量下降或地類改變,故將其作為“進出平衡”管制中的潛在流出對象。在非耕農用地內,第二次土地調查(以下簡稱“二調”)中的既有耕地在第三次國土調查(以下簡稱“三調”)流出為非耕農用地的地塊,“三調”中根據耕作層破壞程度標注“即可恢復”或“工程恢復”,這部分農用地可通過相應措施恢復為耕地,是“非糧化”耕地整治的重要對象[22],故將其作為潛在耕地補入對象;對于種植屬性代碼未標注“即可恢復”或“工程恢復”的非耕農用地地塊,長期屬于非耕地且難以恢復為耕地,將其定義為穩定非耕地。
1.3 管制要求:“同質等效”與“流補平衡”
基于科學評價合理確定“進出平衡”的“平衡”閾值、明確“進出”數量,對保持農用地總量平衡、實現一般耕地與非耕農用地間的流量平衡甚為關鍵。本文提出“同質等效—流補平衡”的管制思路,即為明晰耕地“進出平衡”的管制依據和“進”“出”范圍、劃定農用地管控分區。囿于“三調”中的地類認定主要側重于地表覆被表面的種植屬性特征,難以直接體現調查地塊的耕作適宜性,故基于“同質等效”思路建立以適宜性為原則的管制依據,確保一般耕地空間置換后的“同質等效”乃至“優質增效”;而后,基于“流補平衡”思路,在明確耕作適宜性的基礎上,遵循合規性原則,在非耕農用地內將耕作適宜性較高的農用地作為“補入類”,在一般耕地內將耕作適宜性較低的耕地設為“流出類”,并保證“流出類”與“補入類”面積相當,以求優化調整過程中實現總量、流量的動態平衡及質量的優進劣出,實現良田糧用。綜上可知,“同質等效”是耕地“進出平衡”管控的評價準則,體現合理性與科學性;“流補平衡”是耕地“進出平衡”管控的約束準則與分區原則,是在明確管控評價準則的基礎上確定實際可流轉區域、完成管控分區劃定的思路指引,體現管制的合規性。綜合“同質等效—流補平衡”的管制思路,可為耕地“進出平衡”管制的推進落實提供具體思路,具體管制思路見圖1(a)。

圖1 耕地“進出平衡”管制思路與方法Fig.1 The idea and method of control of balancing cultivated land conversion
2 耕地“進出平衡”管制框架
2.1 基于“同質等效”的評價準則
耕地“進出平衡”管制的核心是對農用地用途的調整,而農用地用途調整的核心在于建立以評價為重點的技術方法。不同于以往基于自然質量、基礎設施條件對耕地適宜性的評價,“進出平衡”管制面向整個農用地系統,應綜合考慮可能的平衡關系,將產能、生態、經濟、社會等因素納入考量。因此,耕地“進出平衡”管制下的耕作適宜性評價,應注重自然、區位、景觀、產能、生態、經濟、社會多因素的協調平衡,以確保實現耕地數量足、位置穩、布局優、環境良、利用好。綜上所述,基于“同質等效”的評價思路,本文從“地塊—景觀—區域”對農用地進行多尺度量化評價。在地塊尺度以“同質”為導向,考慮耕地質量和立地條件對于耕地高產的保障能力;在景觀尺度以“穩態”為導向,考慮景觀格局對于耕地穩產的保障能力;在區域尺度以“等效”為導向,考慮糧食生產、經濟支撐、生態價值、社會意愿對于耕地效益的保障能力,將各因素對于耕作適宜性的影響機制顯化,測算農用地耕作適宜性,為耕地“進出平衡”落實提供管制依據(圖1(b))。
(1)耕地質量。指農用地的主體特征及其所處自然條件的優劣,包括土壤理化性質和自然環境。以生產功能為主的農用地對其自身屬性和自然條件具有適宜性需求。土壤理化性質和自然環境越優越,表明該地塊越適合進行糧食生產,開展管制的必要性越大。
(2)立地條件。指農用地的資源利用便捷性,包括區位條件和耕作條件。作為農用地的外部條件,立地條件限制著農業生產能力或農業活動的實現程度[7,34],其所包含的區位條件和耕作條件通過影響交通運輸和基礎設施等因素進而影響農用地糧食生產水平,應優先將與周邊現狀耕地布局集中連片、農田水利設施配套較好的地塊補入。
(3)景觀格局。代表著資源與環境的結構組成和時空特征,包括規模大小、集聚程度和穩定性。空間層面上,農用地的連片性與規模性決定著該區域農業生產的投入產出比[35],應優先考慮補入集中連片或自身規模較大的地塊以置換流出零星分散、不宜集中連片耕作管護的耕地;時間層面上,農用地在較長時間段內未發生地類轉換,表明該區域景觀結構穩定、抗干擾能力強,可穩定利用,故應優先將不穩定利用耕地流出。
(4)糧食生產。“進出平衡”管制即為保障并提升糧食生產能力[31],包括糧食產能和生產持續性。糧食產能直接反映農用地生產的效率與潛力[36],生產持續性則從時間尺度上對農用地的生產能力進行約束,確保農用地生產的穩定及可持續,應優先選擇糧食產能高、生產持續性強的地塊進行糧食生產。
(5)經濟支撐。指區域經濟水平對于開展“進出平衡”管制的可支撐能力,包括可投資能力和管制成本。國家和當地政府可投資能力的大小,以及在具體區域進行管制需要耗費的資金,決定著“進出平衡”能否實施及其實施的可持續性。一般來說,可投資能力越高、管制成本越低,開展管制的可能性越高。
(6)生態價值。指農田生態系統所形成和維持的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條件與效用,即農用地的生態系統服務。農田生態系統服務越好,表明農田生態質量和功能越好,生態系統整體越穩定,農田越不易受到破壞,更有利于農業生產。
(7)社會意愿。指政府和民眾對于開展“進出平衡”管制的期望程度或接受程度,包括政府意愿和農戶意愿。對于政府而言,由于所在區域農用地利用情況不同,耕地保護壓力大小不同,因此政策導向也不盡相同;農戶角度而言,作為理性經濟人,農戶會在比較利益的驅動下,選擇比較收益更高的種植方式,即比較利益較低區域的農用地,農戶對其的依賴性較低,開展管制的可能性較高。
2.2 基于“流補平衡”的管制分區劃定
由于一般耕地與非耕農用地所承載的生產功能、生態功能以及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不同,無論是將所有可恢復農用地恢復為耕地進行無差別糧食生產,還是將所有可轉出一般耕地全部種植經濟作物,都是難以實現的。因此,管控分區應在優先落實耕地保有量的基礎上,保障資源要素利用的總量平衡。在農用地范圍內,將耕作適宜性與累計面積掛鉤,優先將耕作適宜性較低的耕地轉出,同時補入面積相當且耕作適宜性較高的非耕農用地以優化耕地結構(圖1(c))。同時,將未流補的農用地依據其稟賦特征進行適地適用的分區管控,從而通過“流補平衡”實現“進”“出”的量質雙約束以及農用地用途管制分區的劃定。具體而言,本文將農用地用途管制分區方法擬定為:
(1)對可恢復耕作的非耕農用地圖斑按耕作適宜性(P補)由高到低進行排序,并對其面積進行累加(S補);對一般耕地圖斑按耕作適宜性(P流)由低到高進行排序,并對其面積進行累加(S流)。
(2)根據“流補平衡”原則,需在S補≥S流的基礎上滿足P補≥P流,滿足這一條件的閾值即為平衡點(S平衡,P平衡),即(S補=S流,P補=P流)。將符合P補>P平衡的潛在適宜耕作的非耕農用地圖斑納入備選補入區,并將P流<P平衡的潛在不適宜耕作的耕地圖斑納入備選流出區。
(3)對于P流>P平衡的一般耕地圖斑,因耕作適宜性高于流出標準,雖暫不流出,但需加強保護,故納入重點保護區,防止其“非糧化”或棄耕;對于P補<P平衡的非耕農用地圖斑,經評估后耕作適宜性尚未達到補入標準,暫時無法補入,納入特色發展區,因地制宜發展現代農業產業、種植特色經濟作物。
3 案例實證
3.1 研究區概況
耕地“進出平衡”以縣級行政管轄范圍為單元進行落實。宜興市是由無錫市代管的縣級市,地處江蘇省西南部,位于31°07’~31°37’N、119°31’~120°03’E,屬亞熱帶季風氣候,東連太湖與無錫市濱湖區,西、北接常州市金壇區、溧陽市、武進區,南鄰浙江省長興縣,西南鄰安徽省廣德市。全市總面積1 996.60 km2,下轄13個鎮、5個街道,常住人口128.70萬(2021年)。宜興地勢南高北低,西南部為低山丘陵,東部為太湖瀆區,北部為平原區,西部為低洼圩區。多元的地形促進了多樣性的特色種養,宜興市因地制宜發展了茶、竹、果、花卉苗木等特色經濟作物,是江蘇省最大的茶葉產區,陽羨雪芽、陽羨茶、百合等農產品入選國家地理標志產品。
近年來,宜興市通過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蟬聯江蘇省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績考核縣綜合排名第一等次,入選全國首批農業現代化示范區、全國首批農業科技現代化先行縣。然而,根據“二調”“三調”數據顯示,2009—2019年宜興市有15 439.96 hm2耕地凈流轉為林地、園地、草地或坑塘水域等其他農用地,耕地面積凈減少13 447.98 hm2,耕地“非糧化”形勢較為嚴峻。
3.2 評價指標與數據來源
3.2.1 評價指標體系與方法
基于研究區實際,參考相關政策要求和學術研究成果[13-14,22,37-40],遵循綜合性、科學性、代表性原則并結合可獲得性,面向同質、穩態、等效的目標導向,從地塊、景觀、區域三級尺度分別選取7個一級指標、14個二級指標、28個具體指標。各指標權重通過層次分析法獲得,權重結果均通過一致性檢驗。相關指標的含義、權重與量化方法詳見表1。
為消除量綱差異,對各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22,36],而后進行農用地耕作適宜性評價,綜合評價方法如式(1)所示:
式(1)中:Pi為第i個評價單元的耕作適宜性;wij為第i個評價單元的第j個評價指標的權重;pij為第i個評價單元的第j個評價指標值。
3.2.2 數據來源與預處理
本文使用的數據包括基礎地理信息數據、土地利用數據、社會經濟數據等,數據來源見表2。所有數據基于ArcGIS 對土地利用數據進行配準,統一為高斯—克呂格投影,CGCS2000坐標系。

表2 數據來源Tab.2 Data sources
3.3 耕地“進出平衡”管制對象
3.3.1 潛在流出對象
對現狀耕地扣除永久基本農田后,得到一般耕地5 910.76 hm2,為現狀耕地總量的14.55%。其中水田面積3 432.40 hm2,占一般耕地面積的58.07%;水澆地面積1 692.08 hm2,占一般耕地面積的28.63%;旱地面積786.28 hm2,占一般耕地面積的13.30%。從占現狀耕地比重上來看,潛在流失旱地占現狀旱地總量的比重較大,達到41.66%。空間格局上,呈現“東多西少”“北多南少”的分布格局,并集中分布于屺亭街道、丁蜀鎮、高塍鎮、新莊街道、新街街道等鄉鎮街道的城市建設用地外圍(圖2)。

圖2 宜興市耕地“進出平衡”管制評價對象空間分布Fig.2 The evaluation object location of the control of balancing cultivated land conversion in Yixing City
3.3.2 潛在補入對象
提取非耕農用地中種植屬性代碼標注“即可恢復”和“工程恢復”地塊,得到可恢復非耕農用地共計19 135.01 hm2,占農用地總量的24.28%。不同用地類型在“即可恢復”和“工程恢復”中的占比差異較大。其中占比比較高的地類包括坑塘水面、其他林地、灌木林地、其他園地,分別占比為35.35%、18.89%、18.07%、13.63%;喬木林地占比最少,不足0.40%。空間格局上,呈現出與一般耕地相異的“西多東少”分布格局,除中部新莊街道、屺亭街道、芳橋街道、宜城街道等區域分布較少外,其余區域廣泛分布(圖2)。
3.4 農用地耕作適宜性評價
基于上文確定的評價指標體系,通過綜合評價得到宜興市農用地耕作適宜性,分別基于一般耕地和非耕農用地提取相應的耕作適宜性,采用自然斷點法將耕作適宜性劃分為高、較高、中等、較低和低5個等級(表3和圖3)。

表3 宜興市農用地耕作適宜性結果統計Tab.3 Statistics of agricultural land suitability results in Yixing City

圖3 宜興市農用地耕作適宜性空間分布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ion suitabil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Yixing City
3.4.1 耕地耕作適宜性
耕作適宜性處于較高和高的面積為3 042.00 hm2,占一般耕地的51.47%,主要分布于屺亭街道中部和南部、丁蜀鎮北部、高塍鎮中部與南部、新莊街道西部、官林鎮中部、徐舍鎮,用地類型以水田為主,多為交通便捷區域、地塊規模大且形狀規整;耕作適宜性處于中等的區域面積為1 649.11 hm2,占一般耕地的27.90%,主要分布于高塍鎮東南部、丁蜀鎮中部和北部、徐舍鎮東部、屺亭街道中部和南部、官林鎮北部、宜城街道東南部,用地類型上以水田為主,多為區位條件較好且規整的地塊;耕地耕作適宜性處于低和較低的區域面積1 219.65 hm2,占一般耕地面積的20.63%,主要分布于張渚鎮、楊巷鎮北部、宜城街道西北部和東南部、高塍鎮、周鐵鎮中部、新街街道、湖?鎮,用地類型上以水田和水澆地為主,多位于中心城區邊緣或鄰近林地、坑塘零星分布。
3.4.2 非耕農用地耕作適宜性
耕作適宜性處于高和較高的面積為3 152.48 hm2,占非耕農用地面積的16.47%,主要分布于丁蜀鎮、徐舍鎮、官林鎮、新建鎮,用地類型上以喬木林地、其他林地、其他園地為主,地塊規模大且形狀規整;耕作適宜性處于中等的面積為5 094.30 hm2,占非耕農用地面積的26.62%,主要分布于徐舍鎮、丁蜀鎮、張渚鎮中部、官林鎮、高塍鎮北部和西部、新建鎮,用地類型上以坑塘水面、其他林地、喬木林地、其他園地為主,空間分布格局較為分散;耕作適宜性處于較低和低的區域面積10 888.23 hm2,占非耕農用地面積的56.91%,主要分布于高塍鎮北部與西部、楊巷鎮、張渚鎮、西渚鎮、徐舍鎮、和橋鎮、湖?鎮、太華鎮,用地類型上主要為坑塘水面、其他林地、其他園地、喬木林地,多為耕作不便、耕地質量較差的宜溧山地或滆湖水域沿岸。
3.5 宜興市耕地“進出平衡”管制用途分區
基于“同質等效—流補平衡”的思路,在測算農用地耕作適宜性的基礎上,進行農用地用途調控管制,對現狀一般耕地進行優化,最終確定備選補入圖斑8 233 塊,累計面積(S補)2 848.07 hm2;備選流出圖斑18 242 塊,累計面積(S流)2 847.70 hm2;重點保護27 543 塊圖斑,累計面積3 063.06 hm2;特色發展35 111塊圖斑,累計面積16 286.94 hm2,分區結果如表4、圖4所示。經計算,備選補入區耕作適宜性最低值P補= 0.62,備選流出區耕作適宜性最高值P流= 0.62,滿足“同質等效—流補平衡”所需的S補≥S流且P補≥P流。通過空間置換將現狀耕地耕作適宜性在P平衡之下的低質量斑塊流出,補入耕作適宜性在P平衡之上的高質量農用地。管制優化后,耕作適宜性最小值從0.43提升至0.62,耕作適宜性均值由0.60 提升至0.64,標準差由0.03降至0.01,一般耕地耕作適宜性得到提高且系統整體趨于穩定(表5);圖斑數量由45 785塊減少至35 776塊,在數量上表明地塊規模變大;對備選流出區與備選補入區分別選取3處不同規模下較為明顯的區域(圖4中的(a)、(b)、(c)、(d)、(e)、(f))進一步觀察,可發現備選補入農用地多為自身規模較大、與周邊現狀耕地布局集中連片的地塊,而備選流出耕地多為零星分散、不宜集中連片耕作管護地塊,即管制后實現了空間上的優化,有利于實現耕地的長期穩定利用。總的來看,基于“同質等效—流補平衡”的耕地“進出平衡”管制有利于實現耕地的量質并提、格局優化和功效改善。

表4 宜興市耕地“進出平衡”管控面積統計Tab.4 Statistics of the control areas of balancing cultivated land conversion in Yixing City

表5 耕地“進出平衡”管制前后對比Tab.5 Comparis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trol of balancing cultivated land conversion

圖4 宜興市耕地“進出平衡”管控分區空間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Yixing City under the control zoning of balancing cultivated land conversion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面向近年來的耕地“非糧化”傾向,科學合理地進行耕地“進出平衡”管制,對穩定糧食生產、維護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明晰耕地“進出平衡”管制思路的基礎上,構建了綜合“同質等效—流補平衡”的耕地“進出平衡”管制方法,并以宜興市進行案例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1)耕地“進出平衡”應將一般耕地和可恢復非耕農用地確定為潛在流出與補入對象,綜合“同質等效”與“流補平衡”的管制框架有助于明確耕地“進出平衡”落實中管制依據和“進”“出”范圍,通過優化農用地布局實現區域耕地保護及持續穩定利用的管制目標。
(2)“同質等效”為管制評價依據,從地塊、景觀、區域三級尺度統籌考慮耕地質量、立地條件、景觀格局、糧食生產、經濟支撐、生態價值、社會意愿等因素進行耕作適宜性評價;“流補平衡”為分區劃定原則,通過數量和質量規制將農用地用途劃分為備選補入區、備選流出區、重點保護區、特色發展區4種類型。
(3)基于“同質等效—流補平衡”的管制思路,可將宜興市永久基本農田外的農用地劃分為備選補入區、備選流出區、重點保護區、特色發展區4 種類型,面積分別為2 848.07 hm2、2 847.70 hm2、3 063.06 hm2、16 286.94 hm2。備選補入區斑塊自身規模大、與現狀耕地布局集中連片,備選流出區斑塊零星分散、不宜集中連片耕作管護,重點保護區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區邊緣區,特色發展區主要位于湖泊濕地沿岸的坑塘水域以及南部宜溧山地。通過落實耕地“進出平衡”,可使耕地耕作適宜性均值由0.60提升至0.64,并使耕地的空間格局得到優化。
4.2 討論
面向耕地保護實際情況,中國耕地用途管制制度不斷細化與完善,特別在耕地“進出平衡”制度提出后,對一般耕地的管控進一步嚴格,如何通過深化耕地用途管控,實現耕地利用空間配置優化的現實需求[27],亟待開展深入研究。明確耕地“進出平衡”管制的評價準則和約束準則,對緩解耕地“非糧化”、細化農用地用途管制規則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本文擬解決的科學問題。本文在明確耕地“進出平衡”管制目標、對象、要求的基礎上,提出了綜合“同質等效—流補平衡”的管制框架,以“同質等效”為思路進行耕作適宜性評價,并在此基礎上以“流補平衡”為置換規則實現耕地“優進劣出”和用途管制分區劃定,期望為科學確定耕地“進出平衡”管制要求提供參考借鑒。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1)管控思路上,本文主要面向發展糧食生產、維系糧食安全的目標進行農用地用途管制研究,對發展特色經濟作物關注不足,未來應權衡處理好發展糧食生產和發揮比較效益的關系。(2)指標選取上,本文以耕地生態質量表征耕地的生態價值,認為在生態保護紅線外生態質量越高的地區越宜進行耕作,但從土地整治的資源環境效應角度考慮,整治可能降低生態環境質量[45],造成耕地生態安全隱患,因此應結合具體目標判斷指標的正負向性質;同時,受限于時間等因素,未能通過訪談調查獲取一手數據,而是以相關指標進行替代表征社會意愿,可能影響計算結果準確性,未來應基于訪談調查獲取更加詳實的社會意愿數據。(3)數據選取上,受限于可獲得性,本文僅基于“三調”進行現狀分析,未能結合歷史數據進一步明晰農用地變化規律,未來可結合“二調”及變更調查數據納入更多時間節點,明晰農用地演變規律,更好地明確管控對象、核算識別“進”“出”范圍。以上問題有待于在后續進一步研究與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