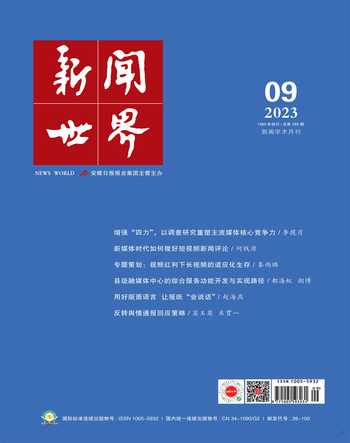抖音短視頻對(duì)小鎮(zhèn)青年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的影響
任卓琳
【摘? ?要】近年來,隨著短視頻平臺(tái)和移動(dòng)終端的興起,長(zhǎng)期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小鎮(zhèn)青年逐漸走入人們的視野,短視頻平臺(tái)的出現(xiàn),為小鎮(zhèn)青年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帶來新的方式。本文選擇抖音APP,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參與式觀察法,對(duì)小鎮(zhèn)青年在抖音短視頻平臺(tái)上的實(shí)踐及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和呈現(xiàn)進(jìn)行分析,探討小鎮(zhèn)青年在短視頻平臺(tái)的媒介形象及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的困境,并力求在此基礎(chǔ)上為小鎮(zhèn)青年的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議。
【關(guān)鍵詞】抖音APP;小鎮(zhèn)青年;身份認(rèn)同;短視頻
身份認(rèn)同是西方文化領(lǐng)域中的一個(gè)跨學(xué)科概念,其基本含義是指?jìng)€(gè)人與特定社會(huì)文化的認(rèn)同,包括以主體為中心的自我身份認(rèn)同以及以社會(huì)為中心的社會(huì)身份認(rèn)同,即“自我身份認(rèn)同”與“群體身份認(rèn)同”。當(dāng)下流行的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tái)是小鎮(zhèn)青年在網(wǎng)絡(luò)中最大的聚集地。小鎮(zhèn)青年通過網(wǎng)絡(luò)短視頻,尤其是抖音平臺(tái),進(jìn)行自我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及群體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
一、小鎮(zhèn)青年的定義
目前,學(xué)界有關(guān)小鎮(zhèn)青年的概念尚無統(tǒng)一定義,尹鴻在《2015年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備忘錄》中,將“小鎮(zhèn)青年”定義為“二三線城市及以下城市、縣城、鄉(xiāng)鎮(zhèn)觀眾”,其“年齡在19—30歲之間,多數(shù)為專科學(xué)歷,收入5000元以下”[1];魏翔則從消費(fèi)領(lǐng)域進(jìn)行界定,認(rèn)為小鎮(zhèn)青年是處在消費(fèi)成長(zhǎng)期和收入成長(zhǎng)期的普通新生代消費(fèi)者[2]。
在傳統(tǒng)媒體時(shí)代,大眾媒體致力于打造以城市精英為中心的話語體系,小鎮(zhèn)青年被置于話語體系的邊緣。由于長(zhǎng)期以來的“失語”,小鎮(zhèn)青年被貼上“精神小伙”“殺馬特”等非主流標(biāo)簽。移動(dòng)終端和短視頻的興起,為小鎮(zhèn)青年表達(dá)自我、進(jìn)行個(gè)人形象塑造帶來機(jī)遇與挑戰(zhàn)。
二、小鎮(zhèn)青年在抖音平臺(tái)上的媒介形象建構(gòu)
(一)自我認(rèn)同
吉登斯認(rèn)為,自我認(rèn)同通過兩種途徑得以實(shí)現(xiàn),一種是“個(gè)體反思活動(dòng)”,另一種是“參照他人”。“個(gè)體反思活動(dòng)”的核心是通過建構(gòu)“理想自我”來實(shí)現(xiàn)的,即塑造成為自己理想中的人,也可以說是在前臺(tái)塑造自己的社會(huì)完美形象;而“參照他人”則是指自我通過他人的反饋來獲得認(rèn)同感[3]。
1.塑造自我鏡像,形成“他者”幻象
戈夫曼在“擬劇論”中,把世界比作一個(gè)大舞臺(tái),人人都在舞臺(tái)上扮演自己的社會(huì)角色,這個(gè)舞臺(tái)分為“前臺(tái)”和“后臺(tái)”,人們?cè)凇扒芭_(tái)”塑造自己的形象,通過偽裝,隱藏真實(shí)形象,形成一種“他者”幻象。抖音短視頻平臺(tái)的出現(xiàn),為小鎮(zhèn)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臺(tái),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相對(duì)比較平凡普通的小鎮(zhèn)青年,得以在網(wǎng)絡(luò)中塑造一種理想化的、美好的“鏡中的自我”,形成“他者”形象。例如抖音ID“粽子粽子我是糯米”,是一位從農(nóng)村到上海工作的年輕女孩,她在抖音里記錄了自己工作之余的生活,包括日常穿搭、美食、感情、裝修等,塑造了一個(gè)精致、熱愛生活、健康向上的年輕女孩形象。
2.呈現(xiàn)理想自我,獲取他人認(rèn)同
除了塑造理想的自我,“自我認(rèn)同”還包括“參照他人”,即自我與他人的互動(dòng)。小鎮(zhèn)青年通過抖音進(jìn)行自我呈現(xiàn),打造理想化自我的同時(shí),也希望獲得他人的認(rèn)同。抖音的大數(shù)據(jù)精準(zhǔn)推送,有利于建立視頻發(fā)布者與觀看者之間的聯(lián)系,因此,當(dāng)小鎮(zhèn)青年利用抖音APP進(jìn)行理想自我的呈現(xiàn)時(shí),總能夠在評(píng)論區(qū)獲得他人的互動(dòng)和認(rèn)同。例如ID“路人甲成長(zhǎng)記”,是一位從東北小縣城到南京上學(xué)工作的青年,他的抖音賬號(hào)擁有73.5萬粉絲,共發(fā)布了71個(gè)作品,獲贊1184.9萬。他的作品標(biāo)題涉及高考、寒門子弟、公務(wù)員備考、畢業(yè)后的現(xiàn)實(shí)及出路、旅行、婚戀、育兒等話題,他的作品按照時(shí)間順序,展現(xiàn)了他剛上大學(xué)的懵懂、畢業(yè)后的迷茫以及為人父后的喜悅與無奈等,這些話題無不觸及大多數(shù)小鎮(zhèn)青年的痛點(diǎn),視頻評(píng)論也多為“說得太對(duì)了”“人間真實(shí)”等字眼。
(二)群體認(rèn)同
自我認(rèn)同與群體認(rèn)同并非割裂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聯(lián)系的。離開個(gè)體,群體認(rèn)同也就失去了主體,因此,二者的關(guān)系非常緊密。具體而言,小鎮(zhèn)青年在抖音APP中的群體認(rèn)同可概括為以下兩點(diǎn)。
1.網(wǎng)絡(luò)形成聚合,獲得群體歸屬
社交媒體及短視頻的發(fā)展,使得“人人都有麥克風(fēng)”成為現(xiàn)實(shí),用戶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表自己的觀點(diǎn),展示自己的個(gè)性,平臺(tái)同樣會(huì)通過自身算法和用戶畫像將有關(guān)內(nèi)容推送給類似喜好的用戶,這就驅(qū)使有共同愛好的人形成了聚合,找到了群體歸屬。例如ID“路人甲成長(zhǎng)記”,在其抖音賬號(hào)記錄了自己從求學(xué)到工作再到組建家庭的成長(zhǎng)歷程,在這一過程中,他也吸引了大批關(guān)注和點(diǎn)贊,并且聚集了很多經(jīng)歷相似的小鎮(zhèn)青年。
2.模仿城市青年,建立“他群”比較
個(gè)體在尋找群體認(rèn)同時(shí),通常還伴隨著“社會(huì)比較”,即將自己所在群體和其他群體在社會(huì)地位等方面進(jìn)行比較。并且,在實(shí)際生活中個(gè)體會(huì)更傾向于認(rèn)同其他擁有相同價(jià)值觀或者情感理念的個(gè)體。就小鎮(zhèn)青年在抖音APP發(fā)布的短視頻來看,其內(nèi)容通常是圍繞城市青年展開的,即傾向于模仿城市青年的穿著打扮、行為舉止等,形成與“他群”的比較。此類內(nèi)容中,小鎮(zhèn)青年多選擇“事業(yè)”“金錢”“愛情”等主題,衣著方面多是戴著夸張的首飾,穿著豹紋襯衫、貂皮大衣等,視頻中宣揚(yáng)成功的標(biāo)準(zhǔn)主要體現(xiàn)在房子、車子及金錢等方面。例如抖音ID“明哥不酷”,擁有粉絲457.1萬,發(fā)布了177條視頻,內(nèi)容多以“豪門”“逆襲”“總裁”“美女”“豪車”等要素展現(xiàn)都市生活,小鎮(zhèn)青年對(duì)城市青年的認(rèn)知多停留在媒介建構(gòu)的“現(xiàn)實(shí)”中,浮于表面。
三、短視頻時(shí)代小鎮(zhèn)青年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的困境
互聯(lián)網(wǎng)的快速發(fā)展在為小鎮(zhèn)青年提供了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場(chǎng)域的同時(shí),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小鎮(zhèn)青年長(zhǎng)期生活的環(huán)境相比大城市較為閉塞,文化素養(yǎng)和媒介素養(yǎng)大多不高,很多時(shí)候在互聯(lián)網(wǎng)中建構(gòu)和呈現(xiàn)的形象存在認(rèn)知偏差。我們?cè)诳吹缴缃幻浇闉樾℃?zhèn)青年提供場(chǎng)域進(jìn)行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的同時(shí),也不應(yīng)該忽視背后存在的隔閡。
(一)心理空間:對(duì)抗性敘事加劇割裂感,標(biāo)簽化刻板印象彌散
長(zhǎng)期以來,大批小鎮(zhèn)青年處于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的流動(dòng)中,身體的漂泊與內(nèi)心的迷茫使得小鎮(zhèn)青年很難連續(xù)性地對(duì)文化進(jìn)行傳承。小鎮(zhèn)生活的閉塞與經(jīng)濟(jì)的落后也使得小鎮(zhèn)青年難以樹立自身的自信,并且對(duì)自我進(jìn)行質(zhì)疑和否認(rèn)。這些都導(dǎo)致小鎮(zhèn)青年的群體內(nèi)部難以展示出統(tǒng)一的風(fēng)貌[4]。因此,在抖音APP中呈現(xiàn)出來的有關(guān)小鎮(zhèn)青年的內(nèi)容,出現(xiàn)了多種標(biāo)簽,有些用戶是以獵奇、扮丑來博眼球,有些是展示淳樸的鄉(xiāng)村生活,有些是通過對(duì)城市青年進(jìn)行模仿,以“土味霸總”的形象出現(xiàn)在人們的視野中。這些風(fēng)格迥異,帶有強(qiáng)烈對(duì)抗性敘事色彩的內(nèi)容加劇了小鎮(zhèn)青年群體內(nèi)部及群體與外部之間的割裂感,逐漸使得“土味”“精神小伙”“殺馬特”等標(biāo)簽化的刻板印象在網(wǎng)絡(luò)中彌散開來。
(二)文化區(qū)隔:地理空間加劇城鄉(xiāng)隔閡,對(duì)立化造就邊緣人群
長(zhǎng)期以來,城市傳播、鄉(xiāng)村傳播一直附著明顯的隔離主義的城鄉(xiāng)觀[5],城市傳播始終居于主流媒體話語中心,而農(nóng)村傳播則處于被動(dòng)地位,導(dǎo)致小鎮(zhèn)青年成為定位不清、邊界模糊且流動(dòng)性強(qiáng)的群體。“到不了的遠(yuǎn)方,回不去的故鄉(xiāng)”是大多數(shù)小鎮(zhèn)青年面臨的困境,這種特質(zhì)直觀地體現(xiàn)在他們的視頻作品中。例如抖音ID“史別別”,擁有粉絲328.8萬,共發(fā)布了182條視頻。她是一位北漂女孩,她的作品主要有兩大標(biāo)簽:“北漂日記”和“北漂生存圖鑒”,她在視頻中對(duì)比了北京和老家的巨大差異,也持續(xù)分享一些同樣是北漂人的經(jīng)歷,基本都在表達(dá)一個(gè)主題:繁華的都市即便工資高也很難過上有品質(zhì)的生活,而小縣城雖然安逸卻生活不便。這樣一種矛盾,不斷將小鎮(zhèn)青年推到一個(gè)尷尬位置,乃至成為城市與鄉(xiāng)村的邊緣群體。
(三)內(nèi)容層面:內(nèi)容生產(chǎn)淪為商業(yè)附庸,身份物化中失去自我
抖音平臺(tái)中,很大一部分小鎮(zhèn)青年的內(nèi)容生產(chǎn)都是以獲取流量為主要目的的,內(nèi)容成為了可售賣的商品。短視頻發(fā)布的低門檻和監(jiān)管不完善使得用戶可以隨時(shí)發(fā)布視頻,再加上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中的小鎮(zhèn)青年群體自身的學(xué)歷大多較低,文化素養(yǎng)和媒介素養(yǎng)不高,就導(dǎo)致其視頻內(nèi)容質(zhì)量良莠不齊,而抖音等短視頻平臺(tái)流量變現(xiàn)的規(guī)則,使得很多用戶在利益的驅(qū)使之下放棄對(duì)內(nèi)容質(zhì)量的把控,淪為商業(yè)附庸。
此外,在短視頻平臺(tái),鮮明的人物性格往往更能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因此,為了吸引眼球,很多小鎮(zhèn)青年都熱衷于給自己打造人設(shè),以滿足觀眾的獵奇心理。例如抖音ID“90后光頭強(qiáng)”,擁有粉絲92.1萬,共發(fā)布451條視頻,點(diǎn)贊量達(dá)382.9萬。在其發(fā)布的視頻中,他將自己打扮成光頭強(qiáng)的形象,利用夸張的語言和動(dòng)作來博取眼球,直播中也以光頭強(qiáng)的形象出鏡,甚至將線下真實(shí)的自我也以光頭強(qiáng)的形象進(jìn)行展現(xiàn),這種長(zhǎng)期對(duì)自我身份的物化呈現(xiàn)及對(duì)人設(shè)的過度追求,將會(huì)造成線上線下身份角色的錯(cuò)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人設(shè)的奴隸。
四、短視頻時(shí)代小鎮(zhèn)青年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的對(duì)策
探究短視頻平臺(tái)小鎮(zhèn)青年的身份認(rèn)同現(xiàn)象,是為了尋找更好的建構(gòu)小鎮(zhèn)青年身份認(rèn)同的路徑,從而推動(dòng)小鎮(zhèn)青年在網(wǎng)絡(luò)短視頻平臺(tái)破除“污名”,實(shí)現(xiàn)小鎮(zhèn)青年在網(wǎng)絡(luò)短視頻平臺(tái)的全面發(fā)展。
(一)文化層面:警惕數(shù)字鴻溝,提升小鎮(zhèn)青年媒介素養(yǎng)
互聯(lián)網(wǎng)的不斷發(fā)展,使得用戶在獲取更多信息的同時(shí)也讓不同圈層的人群獲取信息的能力差距拉大,導(dǎo)致“數(shù)字鴻溝”的出現(xiàn)。小鎮(zhèn)青年群體中,多是文化程度相對(duì)較低的用戶,文化素養(yǎng)和媒介素養(yǎng)不高,抖音等短視頻平臺(tái)內(nèi)容豐富,但受時(shí)長(zhǎng)和形式的限制,內(nèi)容淺顯,缺乏思想和深度,內(nèi)容同質(zhì)化現(xiàn)象嚴(yán)重。因此,小鎮(zhèn)青年主體作為媒介的使用者,必須不斷提高媒介素養(yǎng),嚴(yán)格遵守短視頻平臺(tái)的制度,提高對(duì)各種內(nèi)容的辨別能力,在觀看和發(fā)布相關(guān)視頻的過程中及時(shí)甄別。
(二)個(gè)體賦能:找準(zhǔn)自身定位,積極搭建良性社會(huì)互動(dòng)
除了努力提升自己的媒介素養(yǎng),破除“數(shù)字鴻溝”外,小鎮(zhèn)青年還應(yīng)該積極與他人進(jìn)行互動(dòng)交往,找準(zhǔn)自身的定位,搭建良性的社會(huì)互動(dòng)[6]。良好的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需要形成良性的社會(huì)互動(dòng),建立正向的人際互動(dòng)關(guān)系,摒棄媚粉、迎合低級(jí)趣味的做法,樹立積極向上的形象,并且要保持自身形象的一致性,杜絕出現(xiàn)前后矛盾的現(xiàn)象。例如抖音ID“南街壺娘”,是一位江蘇的年輕女孩,擁有粉絲136.9萬,共發(fā)布了1191條視頻,獲贊數(shù)高達(dá)3311萬。她發(fā)布的視頻中,主要有“小鎮(zhèn)的貓”“茶器茶料理”“南街茶壺”“江南小鎮(zhèn)的美食”等。整個(gè)作品風(fēng)格溫和幽靜,充滿濃郁的江南小鎮(zhèn)的氛圍,評(píng)論里的用戶對(duì)于自己感興趣并了解的茶器也會(huì)自動(dòng)進(jìn)行科普,大多數(shù)用戶的評(píng)論都為“治愈”“享受”“煙雨江南”等,形成了良性的互動(dòng),強(qiáng)化了“南街壺娘”的身份認(rèn)同。
(三)平臺(tái)把關(guān):破除刻板印象,推送多樣化的優(yōu)質(zhì)內(nèi)容
個(gè)人需要努力,平臺(tái)也需要改進(jìn)。觀眾對(duì)于抖音、快手這些短視頻平臺(tái)內(nèi)容質(zhì)量低的刻板印象,一定程度上也歸結(jié)為平臺(tái)方的流量導(dǎo)向和算法推送問題。在社交媒體時(shí)代,把關(guān)人變成各平臺(tái)方,這就對(duì)平臺(tái)方的監(jiān)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現(xiàn)實(shí)是,無論是抖音還是快手等短視頻平臺(tái),都曾發(fā)生許多主播低俗化的事件,且這些短視頻平臺(tái)為了博取眼球,刻意推送一些低俗內(nèi)容,這就導(dǎo)致大眾一度認(rèn)為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tái)“低俗”“土味”。因此,短視頻平臺(tái)應(yīng)加強(qiáng)監(jiān)管,破除刻板印象,打破流量至上和精準(zhǔn)推送的分發(fā)模式,為用戶推送多樣化的優(yōu)質(zhì)內(nèi)容;同時(shí)也要主動(dòng)發(fā)聲,打造更凸顯小鎮(zhèn)青年的正面標(biāo)簽。
(四)媒體引導(dǎo):聚焦邊緣群體,主流媒體進(jìn)行輿論引導(dǎo)
主流媒體應(yīng)積極進(jìn)行輿論引導(dǎo),改變傳統(tǒng)以城市傳播為主導(dǎo)的傳播模式,關(guān)注小鎮(zhèn)青年,聚焦邊緣群體。近年來,三農(nóng)題材的短視頻逐漸受到重視,小鎮(zhèn)青年的創(chuàng)作也越來越得到主流媒體的關(guān)注和報(bào)道。例如央視的專題節(jié)目中報(bào)道了一位帶動(dòng)藏區(qū)脫貧的女孩何瑜娟,何瑜娟的抖音ID為“嘉絨姐姐阿娟”,主要通過短視頻幫助當(dāng)?shù)氐霓r(nóng)產(chǎn)品銷售。主流媒體的報(bào)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大眾對(duì)小鎮(zhèn)青年的刻板印象,有效推動(dòng)鄉(xiāng)村振興。
五、結(jié)語
抖音短視頻以其短小精悍、碎片化以及易操作等特點(diǎn),為小鎮(zhèn)青年提供了一個(gè)展示自我的舞臺(tái)。然而,當(dāng)前小鎮(zhèn)青年群體在內(nèi)容傳播、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上還有很長(zhǎng)一段路要走,大眾對(duì)小鎮(zhèn)青年的刻板印象也需要時(shí)間來扭轉(zhuǎn),這些問題,靠單個(gè)自媒體的努力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還需要傳統(tǒng)主流媒體、社交平臺(tái)、小鎮(zhèn)青年群體以及社會(huì)各主體共同努力,了解小鎮(zhèn)青年群體背后真正的焦慮與隔閡,從制度到文化,多維度給予小鎮(zhèn)青年群體支持,從而更好地推動(dòng)小鎮(zhèn)青年群體的發(fā)展與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
注釋:
[1]尹鴻,孫儼斌.2015年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備忘錄[J].電影藝術(shù),2016(02):6.
[2]魏翔.小鎮(zhèn)青年、旅游經(jīng)和消費(fèi)動(dòng)向重審[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us/2019-03-26/doc-ihtxyzsm0
450947.shtml,2019-03-26.
[3]安東尼·吉登斯. 現(xiàn)代性與自我認(rèn)同:晚期現(xiàn)代中的自我與社會(huì)[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6.
[4][5]秦朝森.脫域與嵌入:三重空間中的小鎮(zhèn)青年與短視頻互動(dòng)論[J].現(xiàn)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41(08):105-110.
[6]曹天露.網(wǎng)絡(luò)短視頻平臺(tái)中小鎮(zhèn)青年的身份認(rèn)同異化研究——基于快手APP的考察[D].華南理工大學(xué),2021.
(作者單位:西華師范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
責(zé)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