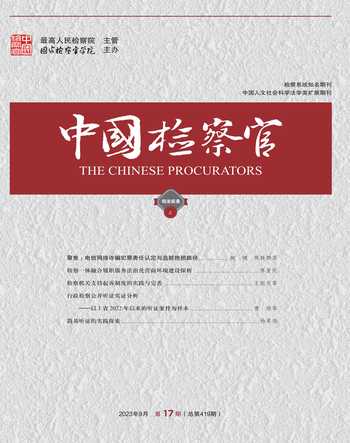輕罪治理的檢察路徑思考
趙星海 符鑫
摘 要: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當今刑事犯罪態勢發生巨大變化,呈現以輕罪為主的趨勢。輕罪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檢察機關作為黨絕對領導下的政治機關、法律監督機關和司法機關,在輕罪治理中應順應時代發展與實踐需求,體現擔當作為。通過“四大檢察”“十大業務”綜合發力,抓前端預防、抓中端履職、抓末端治理,以檢察能動履職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發展。
關鍵詞:輕罪治理 法律監督 檢察路徑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黨在新時代新征程上的目標任務。最高檢黨組書記、檢察長應勇在2023年7月19日大檢察官研討班上指出,要重視和加強輕罪治理體系的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探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檢察機關在新時代應當加強輕罪治理體系的研究,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檢察力量。
一、輕罪治理問題的提出
(一)輕罪治理的時代背景
習近平總書記在《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中指出:“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只有全面依法治國才能有效保障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規范性、協調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會共識。”[2]上述重要論斷深刻闡述了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突出作用。只有發揮法治在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效能,才能使中國式現代化得到保障。當下刑事犯罪態勢發生著巨大變化,開始呈現以輕罪為主的趨勢。針對輕罪為主的犯罪結構轉變,黨和國家陸續進行了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以及立法修訂。以往重罪治理的經驗越來越無法適應當今時代,對輕罪治理進行研究,是目前刑事立法、司法、行政執法的重要任務。
(二)輕罪治理的實踐依據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增設危險駕駛罪后,我國刑事立法逐漸體現出輕刑化立法的積極刑法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了危險作業罪、妨害安全駕駛罪等罪名,更加體現了刑事立法的動態轉向。立法機關根據社會發展及時代需求,展現出了輕刑化的立法理念,這與我國刑事犯罪的發展情況相適應,也為刑事司法提供了有力指引,更為我國輕罪治理奠定了基礎。
2019年10月,最高法《關于加強刑事審判工作情況的報告》中指出:“2014年以來,全國審判機關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占全部案件的81.6%。”[3]2020年10月,最高檢《關于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的報告》中指出:“刑事犯罪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輕罪案件占比從54.4%上升至83.2%。”[4]由此可見,輕罪案件已經成為我國刑事案件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犯罪形勢轉變中也體現出了司法機關司法理念的轉變,如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等刑事政策,通過能動司法融入社會治理的大局中。
無論從黨的理論重大論斷,立法機關的立法轉向還是司法機關的實踐轉變,無不在提醒我們輕罪治理已成為當下國家治理亟需面對的問題。輕罪治理已經成為關乎國家長治久安、關乎法治建設和國家治理大局的時代命題。輕罪治理問題是新時代刑事司法的重要內容,事關黨的執政根基,事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如何治理輕罪,如何打造現代化的輕罪治理體系,是對國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檢察機關在輕罪治理中應發揮檢察優勢,主動擔當作為,通過“四大檢察”“十大業務”綜合發力,為輕罪治理提供檢察之智。
二、輕罪治理中的檢察之職
(一)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定位
根據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法律監督職責是人民檢察院通過行使檢察職能,保障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法律監督是國家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職能定位,暗含著深層次的監督邏輯。輕罪治理涉及國家及社會治理的多個方面,檢察機關履職時面對輕罪治理可能存在的監督真空,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嚴格在職責范圍內進行監督,從而推進輕罪治理穩步規范發展。
(二)新時代檢察履職新要求
2021年6月,黨中央印發《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提出新要求。《意見》要求檢察機關根據犯罪情況和治安形勢變化,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嚴格依法適用逮捕羈押措施,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意見》的要求與輕罪治理理念不謀而合。《意見》要求根據犯罪情況變化適時調整司法實踐,慎重適用羈押措施,維護社會穩定發展。輕罪治理的目的同樣在于減少社會對立面,對于輕罪與重罪區分處理。對于輕罪側重消解社會犯罪面的對立及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和諧;對重罪側重嚴厲打擊,避免出現不穩定因素。《意見》的出臺對檢察履職提出了更為實質化的要求,這也與當下犯罪呈現輕刑化的形勢密不可分。輕罪治理事關國家長治久安,檢察機關應當深化履職能力,積極主動參與輕罪治理,確保輕罪治理在法治軌道上運行,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新的貢獻。
(三)輕罪治理中的檢察履職優勢
隨著中國社會發展日新月異,刑法修正案中關于輕罪的規定逐漸增加。司法機關根據立法的變化,不斷調試司法理念,從而適應輕罪立法與當下時代的發展。積極的刑法觀雖然密織了法網,一定程度上對社會治理起到積極作用,但不可忽視的是,刑罰發動的后果與社會治理之間出現了不相匹配的連鎖反應,給社會和諧及國家治理帶來了一定影響。在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居于公安機關與審判機關之間,在刑事犯罪治理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在輕罪治理中,檢察機關具有天然的“區位”優勢。其一,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居于中間位置,與公安機關較為側重打擊犯罪不同,檢察機關具有分流輕微刑事案件的職能。其二,相較審判機關居中裁判,恪守不告不理,檢察機關的職責要求其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檢察機關可以通過檢察履職,在輕罪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其三,檢察機關對刑事訴訟進行全過程的監督,在輕罪治理中具有其他國家機關不可比擬的便利性。
(四)順應時代發展的檢察履職探索
隨著刑事犯罪態勢的變化,如何適應社會變化治理輕罪,開始成為檢察機關不斷探索的目標。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寫入刑事訴訟法開始,檢察機關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通過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刑事和解、不起訴制度,多方面全方位參與輕罪治理,積蓄了輕罪治理的檢察經驗。通過上述有益探索,檢察機關目前已經形成了以“四大檢察”“十大業務”為抓手的社會治理組合拳,通過數字檢察建立了“個案辦理—類案監督—訴源治理”的法律監督新路徑,豐富了參與社會治理的手段。這些經驗的積累,為檢察機關參與輕罪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鑒。
三、檢察機關參與輕罪治理的路徑選擇
(一)抓前端預防強化訴源治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建設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5]這為推進國家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指明了發展方向。檢察機關做好前端預防可從兩方面入手:
1.法治宣傳工作的創新。檢察機關在輕罪治理中抓前端,重在犯罪預防。結合我國犯罪治理的經驗來看,傳統的自然犯已不再成為犯罪預防的主要對象,反而是互聯網的發展給犯罪預防帶來了新的挑戰。檢察機關的宣傳工作一直長抓不懈且成果突出,但工作方式方法仍集中于線下宣傳。面對互聯網浪潮下刑事犯罪出現的多樣性、復雜性,部分檢察機關并未將互聯網傳播思維與檢察宣傳相融合或融合的深度、廣度還遠遠不夠。概言之,檢察機關應深入學習宣傳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法治宣傳教育與刑罰處罰相結合,加大對群眾的普法力度。重點面向青少年進行普法宣講,以法治副校長制度為抓手,認真落實“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制,將法治宣傳與新形勢下網絡傳播理念相結合,創新法治宣傳工作思路,改變傳統宣傳方式。融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數字宣傳,使檢察工作更接地氣,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法治思想,更新群眾法治觀念,防微杜漸,從而做到“治未病”。
2.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檢察機關在新形勢下貫徹黨中央指示要求,可以踐行“楓橋經驗”為契機,通過暢通信訪申訴情況反映渠道,打開群眾心結,解答群眾疑惑,并適當參與重大矛盾糾紛調解,就地化解矛盾,推動涉法涉訴信訪在法治軌道上解決。創新信訪矛盾源頭化解機制,整合基層矛盾糾紛化解資源和力量,不斷參與并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提高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努力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
(二)抓中端履職深化能動檢察實踐
2023年最高檢工作報告中提出了“能動檢察”這個關鍵詞,這是報告的一個主題詞,也是新時代檢察工作的鮮明特色。能動檢察就是檢察機關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把法理情融為一體,積極主動深化履行檢察職能,不就案辦案,跳出檢察看檢察,胸懷“國之大者”,自覺、主動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之中。檢察機關做好中端履職可從以下三方面展開:
1.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就是要堅決嚴懲嚴重犯罪,讓社會感受到“嚴”的震懾力度,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規范“寬”的一面,對輕微犯罪等嚴格依法落實“寬”的政策,通過輕緩刑、不起訴制度等最大限度分化犯罪、促進罪犯改造,從而實現治理與治罪并重。
2.善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創新。與西方的訴辯交易不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既與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一脈相承,又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情,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刑事司法中的最新成果,豐富了刑事司法與犯罪治理的“中國方案”。用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使案件辦理“繁簡分流、輕重分離”,輕罪快辦,程序從簡,處罰從輕,減少社會對立面;重罪案件重點辦,實體與程序并重,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
3.做好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探索。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是檢察機關治理涉企犯罪領域的重要創新成果,是當下輕罪治理中的積極探索,對于服務“六穩”“六保”具有重要意義,是檢察機關能動履職的生動體現。探索涉案企業合規整改,消解涉及企業經營和管理結構中的違法犯罪行為,從而實現企業自我改正、自我監管、自我預防,既為檢察機關對其從寬處理提供正當依據,也為涉案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注入內生動力。
(三)抓末端治理多維度同頻共振
輕罪治理的目的,不僅在于懲罰犯罪,更在于化解矛盾糾紛,使誤入歧途的行為人能夠改過自新,盡快回歸社會,繼續投身于國家建設和發展中。解決該問題,檢察機關應從末端治理抓起,多維度同頻共振,一體同步推進輕罪治理。
1.檢察機關要做好不起訴后半篇文章。不起訴并非不訴了之,而應在不起訴后做好與行政機關的銜接工作,建議行政機關采取訓誡、行政處罰、社會公益服務等措施,既避免檢察機關不起訴后陷入既無刑責又無行責的無責境地,又為社會公益服務提供了源泉活水,更讓行為人深刻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從而做到“三個效果”有機統一。
2.輕罪治理中無法回避的問題即是輕緩刑的適用所導致的社區矯正監管問題。司法行政機關的社區矯正目前尚未能利用好數字技術的紅利,輕罪治理所帶來的輕緩刑的適用,勢必會導致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案件量直線上升,人案矛盾將更為突出。對此,檢察機關應當以數字檢察為契機,加強對司法行政機關的法律監督工作,協助司法行政機關提升社區矯正數字化監管水平,做好輕罪治理的后方保障,以雙贏多贏共贏理念,完善好輕罪治理體系。
3.輕罪治理最核心的問題即是嚴苛的前科后果與罪行之間的不匹配。也正是由于前科制度的存在,導致輕罪后果不輕,輕罪人員回歸社會存在困難,進而影響自身家庭成員社會生活,加劇了社會不穩定因素。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站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上,需直面該問題,貢獻檢察智慧。對此,檢察機關可就前科消滅與封存問題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適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申請進行試點工作,探索建立前科消滅與附條件封存制度,并在實踐探索及完善的基礎上,推動相關制度適時立法,真正補上輕罪治理體系最后一塊短板。
*河南省淮濱縣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四級高級檢察官[464400]
**河南省淮濱縣人民檢察院第一檢察部五級檢察官助理[464400]
[1] 參見《一睹為快!大檢察官研討班釋放這些重要信號》,最高人民檢察院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h7adPurGMQJpJkgOJqwZBA,最后訪問日期:2023年7月21日。
[2] 習近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2021年第5期。
[3]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強刑事審判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10/9530cb30be344843a2c9792e3215b515.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3年6月2日。
[4]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的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網https://www.spp.gov.cn/zdgz/202010/t20201017_482200.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23年6月2日。
[5] 同前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