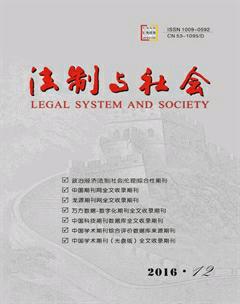淺議術前協議公證
嚴佩文+郝靜濤
摘 要 近年來,術前協議公證作為一種全新事物在我國已逐漸開展,從全國第一例術前協議公證的辦理開始,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對于它的社會意義和存在價值,更是褒貶各異。筆者作為一名執業公證人員,通過自身的執業經歷以及法律賦予公證的職能作用,對術前協議公證的實質及價值進行了剖析,提出只有加強醫療行為的法律監督和相關立法工作,才是預防與解決醫療糾紛的根本。
關鍵詞 術前協議 證據效力 醫療糾紛 法律監督
作者簡介:嚴佩文,山西省侯馬市公證處,四級公證員;郝靜濤,山西省侯馬市公證處。
中圖分類號:D926.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061
近年來,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不時成為暴力傷害的對象,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報告》顯示,2002年到2012年,全國醫療糾紛案件在10年間增長了10倍,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醫院管理及醫務人員方面的原因,也有患者的原因,甚至存在醫療體制方面的因素。不斷增長的醫療糾紛給醫院管理者的日常工作和醫務人員的執業帶來極大的困繞。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下稱《若干規定》)的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為規避風險,分清責任是非,1999年3月4日我國武鋼二院成功地為87歲高齡的患者周梅根實施了人工股骨頭置換術,這是我國首例經過公證的手術。之后,全國各大醫院也紛紛仿效。即醫院與醫療患者及家屬在術前訂立協議,要求公證處派員進行術前協議公證,數量雖然不多,但涉及面很廣,既有骨科、血液科、婦產科,也有神經科以及泌尿科等方面的醫療手術,這些手術的特點都是:手術患者年齡偏大或偏小,病情疑難復雜,手術風險較大。面對危重病癥,筆者認為這項新舉措或許更有助于醫患雙方互相理解,共擔風險。
一、術前協議公證的法律效力
(一)術前協議公證的合法性及可行性
所謂術前協議公證指公證機關根據醫患雙方的申請,為劃清醫療風險與責任,避免不必要的醫患糾紛,依照法定程序,對其法律行為、事件或有法律意義的文書,證明其真實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的一種非訴訟活動。“術前協議”即通常所指的“手術知情同意書”,從法學角度講只要醫患雙方的表達是真實、自愿的,同時強調醫方履行告知義務和患方知情同意等內容,并且按照《公證法》及《公證秩序規則》的規定實施公證行為就具有其合法性。術前協議公證是賦予《知情同意書》法律效力、證據效力的一種措施,在醫療糾紛訴訟過程中,具有能夠直接證明公證所確認的《知情同意書》真實性的效力,可以直接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知情同意書》公證時應要求醫院加蓋公章,使之更加完備,具有可行性。
(二)術前協議公證起到加強證據效力的作用
術前協議公證書一方面體現了醫方的告知義務的履行及相關內容;另一方面也明確了患方在“知情”情況下的“同意權”的自愿行使。在實踐中,由于公證機構對醫療技術內容等專業知識并不太了解,仍然要由醫療衛生行政主管部門以及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根據法律規定來解決。因此,公證機構僅審查并證明協議上雙方簽名及印鑒的自愿性、真實性,并不對協議內容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和確認。就此而言,辦理公證的“術前協議”與日常的“手術知情同意書”并無實質區別,但是《若干規定》中關于“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迫使醫方為避免因手術的失敗或意外而可能發生的糾紛,必須對“術前協議”這一關鍵證據認真做好固定與保全等工作,這就需要賦有法定證明職能的公證機構的介入,由公證機構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對與申請人權益有關的,有法律意義的文書證據即“術前協議” 的形成過程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的真實性予以證明,從而避免了日后因舉證不能帶來的賠償與責任。
(三)術前協議公證并沒有也不能免除醫療行為的法定責任
術前協議公證主要是對醫患雙方各自履行權利義務即“醫務人員履行告知義務”和患者“知情同意權”所做的證據保全,以保護當事人的正當權利和合法權益,使之不受侵犯和破壞。它通過證明活動,證明公證對象客觀存在的事實和合乎法律、政策,目的是為日后可能發生的醫療訴訟固定證據使用。如果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在醫療活動中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及行業規定,存在過失,并給患者的人身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后果,即使辦理了術前協議公證,并不免除醫方法定的侵權賠償等相關責任,患者及家屬依然可以通過法律手段予以追究。
二、術前協議公證的現實意義
(一)有利于醫患雙方加強溝通
通過我國目前醫療糾紛的調查統計數據來看,其實只有20%的案例與醫療技術有關,80%的醫患糾紛與醫患雙方溝通不到位有關。針對手術病例,按照傳統做法,院方交待手術事宜時往往簡單、生硬,既使主動與病人和家屬簽訂《手術同意書》,可病人發生意外后,往往仍然找醫療機構索賠,各執一詞,難辨是非。因此,加強醫患雙方的溝通是將醫患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減少醫患糾紛的關鍵。
所謂醫患溝通,是指在醫療服務過程中,為使醫患雙方充分了解雙方的權利義務,有利于了解患者病情、明確診斷,使患者及家屬對診療行為合理性、必要性有清晰認識而開展的醫學互動行為。包括“醫務人員履行告知義務”即:詳細向病人及家屬告知所患疾病的診斷情況,主要治療手段、重要檢查目的及結果、某些治療可能引起的嚴重后果、手術方式、手術的并發癥等內容和聽取病人及其家屬的意見和建議,讓病人“明明白白看病”,即“知情”以及當患者獲得告知并了解情況后,所享有的同意或拒絕治療的權利,即“知情同意權”。而術前協議公證實際上正是對醫務人員履行告知義務和患者的知情與同意的法律證明。主要是對醫患雙方的約束,一方面避免患者手術后后悔不認帳,另一方面,防止醫者由于瀆職而導致醫療事故而事后篡改手術同意書,為日后發生的訴訟固定證據。
(二)有利于醫務人員卸下思想包袱,輕松上陣,使執業技能與內在潛力得到充分發揮
醫療訴訟“舉證責任倒置”的推出以及新《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中關于將發生醫療事故的賠償問題納入“民事責任”范疇的規定,針對病情疑難復雜的高風險手術,因為醫患之間互不信任,當病情發生變化時,患者及家屬往往第一反應是,手術是不是做錯了,甚至用設備監視醫生的行為,比如攝像機、照相機、錄音筆等為了告狀準備證據。這種壓力導致醫生在處理問題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術前協議公證是根據法定的公證程序,為明確醫患雙方各自的權利義務范圍,醫方將手術風險及術后并發癥甚至包括由于醫療事故導致手術發生意外時醫院應該負擔的責任,如何進行賠償等內容以書面形式告知患者及家屬,在患方充分知情且雙方自愿的前提下所簽訂的協議。這個過程既充分保障了患者的“知情權”,也使醫患雙方的責任范圍置于法律的監督之下,一旦意外發生,患者和家屬一方面能調整心理狀態,理性面對,同時,公證書具有法律效力,將直接被人民法院采納,患者及家屬完全可以憑此獲得相應的賠償。另一方面也減輕了醫務人員的工作壓力,不再畏手畏腳,從而全身心投入醫務工作的分析與鉆研,使執業技能與內在潛力得到充分發揮,從整體上有力推動了醫療事業的進步和醫學界技術水平的提高。
(三)有利于醫療糾紛的及時解決
即使醫患雙方都在手術之前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有時也難以避免意外的發生,一旦醫療糾紛發生后,醫務人員是否履行了告知義務往往成為醫患雙方爭執的焦點,然而,任何糾紛的最終解決都要靠證據,單方面提供的證據材料,其證明效力往往受到質疑。公證機構作為代表國家行使證明權利的第三方,術前協議經其公證后,具有法律認可的證據效力,可以直接作為證據被人民法院采納,明確醫患權利義務,分清責任承擔,促使醫療糾紛得以及時、公平、公正的解決。
三、術前協議公證所引起的法律思考
(一)術前協議公證自身的規范與發展
術前協議公證既是醫患關系緊張的無柰之舉,也是公民自身法律意識不斷增強的體現。作為一種新生事物,要想有生命力,關鍵問題在于能否實現利益雙贏。能否同時贏得醫患雙方的認可。這就要求術前協議公證必須具有統一性和規范性。具體諸如:“哪些疾病,哪些手術需要公證?以防公證被濫用。”、“如何保障患者的知情權?”、“如何保證術前協議公證內容的公平、合理?”、“如何借道第三方力量來規范和管理醫生的治療行為?”、“術前協議公證的費用如何承擔?”等等……要想讓術前協議公證得到進一步的推廣,就必須將其上升到真正的管理制度層面,由衛生部門主導與牽頭,給術前協議公證制訂出統一的規范,同時借助第三方,有效保護醫患雙方各自的合法權利,使術前協議公證產生真正的生命力與公信力。
(二)減少醫患糾紛根本上應從醫務界自身入手
1.醫者要規范自身的行為,尊重病人的權益,加強與患者的溝通交流,充分履行告知義務,針對不同患者,根據其所處的實際情況和自身的特點,如文化水平、意識狀態、生活環境等因素,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努力做到耐心、細致、全面、充分。
2.我國現有的醫療方面的立法無法面面俱到,更多的裁量權操縱在醫方手中,醫療服務行為是否適當,缺少有效的監督,因此加強醫療服務質量監控體制的建設,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良好的醫療環境,充分保障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才是減少糾紛,緩解矛盾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