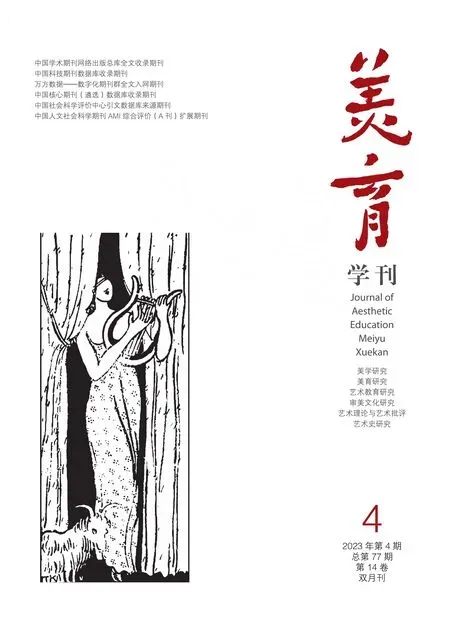詩藝、詩人與詩教
——重回賀拉斯“寓教于樂”的語境
吳明波
(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詩人賀拉斯生活在古羅馬共和國末期和帝國早期,親歷了共和國末期的內戰和帝國初期的強盛。《詩藝》寫于公元前20—公元前10年前后,羅馬結束了數十年的內戰迎來和平。維吉爾大約在同時期完成了史詩《埃涅阿斯紀》,講述羅馬城邦從童年到羅馬的輝煌故事,用神話為新的羅馬帝國奠定基礎。賀拉斯的《頌歌》同樣致力于塑造羅馬的民族性,他也是古羅馬的“民族詩人”。除了創作詩歌,賀拉斯還寫作了《詩藝》,討論“詩人”和“詩藝”,思考詩人在新的國家形態下的身份和作用。賀拉斯面對奧古斯都時期形成的文學秩序,在國家、恩主、朋友、公眾等各種權力關系之中,形成了自己的詩歌風格。[1]
賀拉斯作品主要分為三類,詩歌(包括《頌歌》與《長短句集》等)、閑談(sermon)與書信,其中《詩藝》通常被歸入書信作品。學者主要關注《詩藝》中提出的“合式”(decorum)、詩畫關系以及“寓教于樂”的教育思想,因為它與17世紀古典主義時期的藝術批評有密切關系,主要被看作文藝批評作品。[2]然而,這種理解方式容易忽略它作為書信的形式以及文本特征,且脫離當時的政治背景、古羅馬的修辭實踐和賀拉斯自身的關切。《詩藝》是賀拉斯應皮索之請而寫作的回信,有具體的教學意圖。本文嘗試結合《詩藝》的形式對文本做些梳理,重新回到賀拉斯《詩藝》作品本身、古羅馬的政治語境和文學秩序、古典修辭學語境下來理解“寓教于樂”這一說法,并將其置于西方的詩教傳統當中加以審視。《詩藝》曾經引起很多的論爭,尤其是《詩藝》的形式結構以及主旨聚訟紛紜。[3]15-40大體可以確定的是,賀拉斯討論了“詩人”和“詩藝”的問題,在他看來,“詩人”問題是討論“詩藝”的前提和基礎。當詩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承認,討論“詩藝”才可能而且必要。
一、“詩人”與《詩藝》
《詩藝》又名《致皮索父子的信》,以詩體寫作,全文共476行。在賀拉斯之后大約一百年的昆體良在他的《修辭術原理》(8.3.60)中以“論詩藝之書”(liber de arte poetica)來稱呼這封信,這個名稱延續至今。從昆體良開始,它就從論詩的書信變成了文藝批評作品。到了中世紀,又有學者將它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放在一起,認為這部作品承繼了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思想,由此形成“亞里士多德—賀拉斯”的解釋系列,這一理解方式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4]
因為它曾被看作是嚴格的批評作品,以及與亞里士多德《詩學》的親緣關系,所以多數學者以理解《詩學》的方式來理解《詩藝》。他們認為《詩藝》應該有嚴謹的結構。但是,《詩藝》表面結構的松散、隨意和跳躍,與嚴謹的文藝批評作品嚴重不符。《詩藝》的結構引起相當多學者的爭論,學者們想盡各種辦法對它進行劃分,但是仍然沒有公認的劃分方式。[5]170-174因為對《詩藝》結構的分歧較大,我們也僅能作大體的劃分。《詩藝》大體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討論詩藝(ars),一部分討論詩人(artifex)。對于“詩藝”部分的具體劃分,歷來分歧很大,但“詩人”部分則比較統一,基本認可從第295-476行為專門討論“詩人”的部分。[5]154-157(1)有人將“詩藝”再分,變成三部分,也即“詩藝”(1-152)、“悲喜劇”(153-294)、“詩人”(295-476)。王煥生也持兩分法,即分為“詩藝”和“詩人”。還有一種劃分方式,將之分成“詩的樣式”“詩的內容”“詩人”。
如果我們不把《詩藝》當作《詩學》這類嚴謹的哲學作品看待,而將它還原為與友人論詩的文學書信,或許更容易接受它結構的松散和隨意,以及多處的跳躍。[3]244-272《詩藝》是賀拉斯寫給皮索父子三人的回信。大概是皮索的兒子想從事詩歌創作,特別是戲劇創作,就向他請教,賀拉斯作了回信。有關皮索父子的身份,歷來爭議較多,沒有固定的結論,但我們知道他們是羅馬貴族,愛好詩歌。賀拉斯是奧古斯都時期的“桂冠詩人”,處于古羅馬由贊助體制和流通機制支配的文學秩序當中。[1]《詩藝》這封回信也表明,當時古羅馬的貴族圈子中,詩歌作為一種貴族間的交際手段,深嵌在古羅馬的政治生活當中。作為一封書信,它有明確的針對性,有具體的對象和內容。但是,它又有公開性,它的讀者不僅僅是收信人,還包括其他讀者。賀拉斯的直接讀者是皮索父子三人,潛在的讀者則更加廣泛。皮索父子三人的身份,恰好符合這部作品的理想讀者。賀拉斯可能借這封回信,向這類讀者——對詩歌和詩藝有了解和愛好的人,來全面談論他對詩藝和詩人的看法。因此,《詩藝》文本具有明顯的“對話式”特征。[3]3-14
《詩藝》雖然結構相對松散,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基本的思路和線索。《詩藝》始于討論“詩藝”,賀拉斯卻在后面用很多筆墨來討論“詩人”。將《詩藝》回歸其教育的意圖才能理解兩者關系:“詩人”問題是討論詩藝的前提。當詩人和詩歌的地位得到確定之后,談論具體的詩藝才有價值。在《詩藝》中,“詩藝”部分附著于“詩人”,從屬于該文的教育目的。在“詩藝”與“詩人”銜接部分,賀拉斯明言,自己雖然不再從事寫作,但想到“磨刀石”的作用,要告訴他們,“詩人的職責和義務,從何處汲取材料,如何培養和塑造詩人,什么適合,什么不適合,如何走向美德,避免錯誤”(306—308)。(2)本文《詩藝》的翻譯主要參考楊周翰中譯本,并據Niall Rudd的拉丁文本對部分詞語作了修改。[6]153,[7]這既是賀拉斯《詩藝》文本從“詩藝”向“詩人”的轉折,也是寫作《詩藝》的意圖之一,他由此開始討論有關“詩人”的問題。賀拉斯以談論詩人的“職責和義務”(munus et officium)開始討論“詩人”。“義務”(officium)是典型的古羅馬用詞,突出個人對共同體的道德責任。西塞羅曾經寫作了論“義務”的長信《論義務》(De officiis),告誡自己的兒子如何認識高尚(honestum)與益處(utilitas)的關系。[8]賀拉斯提到的美德與錯誤,同樣指涉道德哲學。以此來看,《詩藝》處理的問題,除了詩藝,也與道德教育密切相關。賀拉斯討論“詩人”,以期塑造他心目中的“理想詩人”。
二、“理想詩人”與公共教育
賀拉斯提到他教導詩人的“職責和義務”,但他沒有直接談論“職責和義務”,而是從批評兩位希臘詩人開始,在論“詩人”的中間位置討論了“古代詩人”。不管是被批評還是被贊揚的詩人,賀拉斯所舉的例子主要是希臘的古代詩人,在希臘的兩種詩歌傳統中有抉擇,在繼承和揚棄希臘傳統之時塑造古羅馬的“理想詩人”形象。“詩人”部分內容豐富,結構錯綜復雜,結合賀拉斯有關“職責和義務”的論述以及教育的意圖,主要處理三個問題,一是從何處學習作詩,二是塑造和培養詩人,三是詩人的作用。在具體文本中的主要線索則是首先處理天資與技藝的關系,其次是強調“睿智”作為寫作的開端和源泉,最后處理詩歌的娛樂和教育功能。[9]325-328
首先是討論天資與技藝的關系,擯棄只認天資以及“迷狂”的詩人。賀拉斯論“詩人”部分從批評德謨克利特開始,以批評另一位詩人恩培多克勒結束。賀拉斯論“理想詩人”部分恰好處于批評兩位詩人的中間。德謨克利特主張天資重要,排斥頭腦健全的詩人,并遠離人群(295—304)。恩培多克勒希望人們把他看作天神而跳入火山口(465—476)。賀拉斯將他對“理想詩人”的論述置于這兩位詩人中間,基于天資與技藝這兩者的關系批評這兩位詩人,為他的“理想詩人”設定了邊界。這里的說法也指向了該書的主題——技藝(ars)。[9]330賀拉斯教人如何寫詩,自然要給技藝留下足夠的空間。如果立足于詩人與共同體的關系,賀拉斯此處的論述就會更清楚。賀拉斯的“理想詩人”關注“職責和義務”,必然排斥“迷狂”的詩人。此外,這兩位詩人是前蘇格拉底的自然哲人,不關注道德哲學。按西塞羅的說法,蘇格拉底與前蘇格拉底哲人最大的差別在于,“蘇格拉底第一個把哲學從天上喚下,并將其安置于城邦之中,甚至還把它導向家舍,又迫使它追問生活、各種習俗以及諸多善和惡的事情。”[10]《詩藝》教人作詩,詩人又與共同體密切相關,尤其推崇道德哲學,必然肯定和重視技藝、貶斥“迷狂”,并且批評前蘇格拉底的自然哲人。這部作品又是應皮索父子需求而作,直接的教育目的更勝于其詩學意圖。賀拉斯對天資與技藝的處理,既是回應古希臘以來的詩學問題,更是出于古羅馬的現實語境及其作品的教育意圖。
其次是確立“睿智”作為詩歌寫作的開端和源泉。賀拉斯批評了前面這兩類詩人,擺正了詩人的位置后,他才開始強調“睿智”的重要性,認為“睿智”是寫作的開端和源泉。這里的“睿智”(sapere),應該從賀拉斯的意義上來認識它。(3)在賀拉斯的意義上,“sapere”這個詞有非常強的倫理意味,也有實踐的意味。英譯一般譯為“wisdom”,楊周翰翻譯成“判斷力”,李永毅翻譯成“智慧”,本文將其翻譯成“睿智”。它有很強的倫理意味,偏重道德哲學。賀拉斯說這種“睿智”可以從“蘇格拉底的文章”那里獲得。“蘇格拉底的文章”,指的是柏拉圖、色諾芬以及亞里士多德等人對蘇格拉底生活和言論的記述。賀拉斯的“睿智”呼應了前面提到的“職責和義務”,從對國家和朋友的職責開始,涉及方方面面的社會關系,包括愛父兄、愛賓客、元老和法官的職務、將領的作用,等等(312—315)。這也再次將《詩藝》與蘇格拉底的道德哲學聯系起來。詩歌不僅僅是藝術作品,也應在具體的政治生活當中承擔政治教育功能。在另外一封《致弗洛魯》的書信中,賀拉斯還認為,荷馬和維吉爾等詩人,比起道德哲學家來說更懂得“高貴和低賤,有用和無用”(《書信》1.2.3-4)。[11]589由此來看,詩人應該是“高貴和低賤,有用和無用”方面的專家。由此,賀拉斯才將具有倫理意味的“睿智”置于詩中最重要的位置,將其當成詩歌寫作的開端和源泉。賀拉斯批評兩位希臘詩人,強調“睿智”的首要性,突出“理想詩人”與公共教育之間的關系。
最后是突出快樂與教育之間的關系。在賀拉斯那里,詩人通過“詩教”與政治共同體相關聯,他在第333-334行提到:“詩人想要的是,要么有益人,要么取悅人,要么他所寫的同時帶來快樂和有益于生活。”[6]155賀拉斯隨后進一步解釋了前面提到的概念:這種人能夠結合快樂與益處(miscere utile dulci),既取悅,又規勸(343-344),贏得所有人的贊揚[6]155。“結合快樂與益處”也即我們所說的“寓教于樂”。賀拉斯在這里列舉的三種方式是并列關系。這里指的可能是三種類型的詩人,或者是三種類型的詩歌。一種教育人,一種取悅人,而另一種既讓人愉悅,又有益生活,也可以說是結合了前面兩種。這句話表明,在當時的普通詩人那里,教育人和取悅人是分離的。或者理解為,針對不同對象,詩人創作不同類型的詩歌。賀拉斯特別看重的是第三種,他的“理想詩人”既能取悅人又能教育人。賀拉斯提到要結合這兩種功能不僅僅是教育方法,也有政治上的功能,涉及政治階層的融合。因為長老的“百人連”喜歡帶有益處的戲劇,他們看重詩歌的教育意義;青年騎士團更喜歡有趣味的戲劇,排斥無趣的戲劇(342-344)。[6]155那么,賀拉斯提出結合快樂與益處的說法,也有彌合政治階層和年齡分歧的考慮。首先,這是古羅馬政治語境和文學秩序中的問題。賀拉斯在古羅馬戲劇演出的語境下談論這個原則:詩人身處城邦,承擔城邦教育的職責,教育觀眾和邦民,彌合政治分歧,獲得觀眾的喜愛。其次,結合快樂與益處,是古希臘羅馬詩學與修辭學的主題。賀拉斯在這里的用詞,有益(prodesse)、取悅(delectare)、規勸(monendo)等,都深深浸淫于古希臘羅馬的修辭學實踐中。它既指向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的相關說法,又與古羅馬的修辭術直接相關。[9]353-354,[12-13]除此之外,這里有關快樂與益處、取悅與規勸的說法,必然關涉人的靈魂類型與性情,又與古典詩教關聯。我們借助柏拉圖《理想國》中對詩歌的兩次批評來理解詩與城邦的關系。在《理想國》第二卷和第三卷,詩只是承擔著城邦教育的功能,以城邦之是為是,以城邦之非為非,不符合城邦標準的詩人就要被驅逐。[14]69-94但是在第十卷,詩被賦予更高的地位,它與認識人的靈魂和性情相關,詩超越了具體的城邦。[14]356-395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詩關注人的性情,旨在教化,歸屬于政治學。[15]賀拉斯的《詩藝》結合快樂與益處,同樣有這方面的考慮。賀拉斯與古典詩教的關系,在他有關“古之詩人”的說法中更明顯地體現出來。
結合賀拉斯前面的論述來看,其“理想詩人”既要學又要教。他從“蘇格拉底的文章”中學習個人對于共同體的職責,也即“睿智”,而他教的內容能帶來快樂且有益于生活,結合了快樂與益處。這種結合也能夠用另一種方式理解。賀拉斯的“結合快樂與益處”既是對詩人創作而言的,也就是針對讀者的接受而言的。對詩人來說,寫作的時候要兼顧兩者,也就是兼顧兩種讀者(觀眾)的需求。對讀者而言,在閱讀和欣賞的時候,能夠發現詩人教的內容。這必然涉及兩個層次的讀者:一種是普通讀者,他們在閱讀或者欣賞詩作時,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另一種讀者則從詩歌認識到詩人背后的“教”,獲得對靈魂的某種認識。接著,賀拉斯揭示了俄耳甫斯、安菲昂與共同體的關系,進一步推進這一問題。我們必須意識到,賀拉斯的這些內容都是針對皮索父子以及類似的讀者來談論“理想詩人”的。
三、“古之詩人”與詩教傳統
賀拉斯的“理想詩人”的核心部分插入了一段追溯古代詩人的內容,這是“詩人”部分的重點。詩人之所以承擔教育的角色,不只在于他在政治共同體中的角色,而是超出政治共同體。賀拉斯確立詩人的地位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從批評兩位希臘詩人開始,另外一條從延續古代詩人的地位來討論詩的起源。
賀拉斯談論古代詩人,進一步解釋了他的詩學觀念以及他的“理想詩人”:
當人類尚在草昧之時,神的通譯——圣明的俄耳甫斯——就阻止人類不再屠殺,放棄野蠻的生活,因此傳說他能馴服老虎和獅子。同樣,忒拜城的建造者安菲昂,據傳說,演奏豎琴,琴聲甜美,如在懇求,感動了頑石,聽憑他擺布。(391—396)[6]157-158
在賀拉斯筆下,最早的詩人既是啟蒙者,也是立法者。詩人和詩歌都被看作是神圣的,享受榮譽和美名。賀拉斯在這里提及的古代詩人,都屬于傳說中的人物,他們的功績也限于傳說。最早提到的俄耳甫斯是神的通譯,溝通神和人,傳達神的旨意。他阻止了人類的屠殺,使人類放棄了野蠻的生活。傳說中詩人馴服了老虎和獅子,應該以另外一種方式來理解,實際上是他用音樂改變了人類兇殘的習性。被馴服的老虎和獅子只是人類野性的代表。賀拉斯扮演了通譯者的角色,溝通古代和現代、傳說與現實。其次提到忒拜城的建造者安菲昂,他的詩藝能夠感動頑石。這里又涉及一個傳說,安菲昂和他的兄弟一起建造城墻,他兄弟以手來搬石頭,而他通過奏樂,讓石頭自己動起來。賀拉斯提到安菲昂的音樂感動頑石,也暗示出詩歌對城邦和民眾的教化意義,以及詩人與安邦定國的關系。此處出現的人物,要么是神的通譯,要么是城邦的建造者,都停留在傳說當中。賀拉斯總結出古代詩人的智慧:“劃分公私和敬瀆,禁止淫亂,制定婚姻禮法,建立邦國,銘法于木。”(397—399)[6]158
古代詩人為人類生活劃分公共和私人的領域,劃定神圣和世俗的領域,同時引導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建立城邦,制定法律。他們主要扮演了建城者和立法者的角色。除了與政治生活直接相關,此處還暗示了詩人與引導和訓誡人的靈魂相關,與教化相關。古代詩人與公共生活的關聯主要通過教化達成,從而形成“詩人—詩歌—靈魂—城邦”的模式。在此之后,賀拉斯提到了希臘的荷馬和提爾泰奧斯。荷馬留下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被稱為所有希臘人的導師,而提爾泰奧斯以寫哀歌著稱。他們的詩句曾經激起戰士的士氣,最終取得戰爭勝利。賀拉斯此處沒有提到傳說,只提到詩人的功績是刺激將士追求榮譽。從神的通譯和建城者,到士氣的激勵者,在賀拉斯的歷史敘述中,從傳說轉變到現實,詩人的地位在下降,但詩人與政治生活之間的關聯并沒有變化,詩人通過詩歌影響個人的靈魂,進而影響到共同體。這里也看出詩教的不同層次。賀拉斯這個時候再次總結詩人的地位和作用:“傳達神的旨意,指示生活道路,求得帝王恩寵,在勞作之后給人帶來歡樂。”(403—407)。[6]158
賀拉斯在此追溯古代詩人,確立詩人與政治共同體的本然關聯,詩人不僅能表達城邦或者國家的意見,也可以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超越古羅馬的政治語境和文學秩序。如果在這個意義上談快樂與益處,則不僅是功利的教育目的,而且涉及詩人對靈魂的認識與思考。詩人只有深刻認識不同的靈魂類型,才可能結合快樂與益處。賀拉斯談論古代詩人,解釋他的詩學原則,突出詩人通過創作詩歌影響人的靈魂,與公共生活建立聯系,在城邦教育而非文藝理論這個維度繼承了《詩學》。賀拉斯主要討論的詩歌形式是悲喜劇(153—294),這是當時非常重要的公共教育手段。[11]671-693(4)賀拉斯在《致屋大維》的書信中也主要討論戲劇,可作為《詩藝》的補充。賀拉斯寫作的《詩藝》針對作為公共教育者的“理想詩人”,討論如何寫作以及通過寫作進行教育,而非泛論詩藝。
我們將賀拉斯的詩學觀點置于其產生的語境,可以清楚地看到《詩藝》作為公共教育的文本性質。它以書信的體裁提供一種對話的開放性。它不僅討論了具體的詩歌技藝問題,更是通過討論詩人聯結了詩歌、詩人與城邦。詩人也通過創作詩歌進入奧古斯都時期的文學秩序當中,通過創作詩歌影響讀者,教育公民。我們至少有三條線索來理解賀拉斯的“寓教于樂”和《詩藝》。第一條也是最常見的,即《詩藝》是“詩藝之書”,從詩藝以及西方文藝批評史來認識《詩藝》,我們在此基礎上補充古希臘羅馬的修辭學傳統。第二條線索是“羅馬之書”,它深嵌在古羅馬的政治語境當中以及由古羅馬的國家、恩主、朋友、公眾組成的文學秩序中,不管是它的具體語境還是它的用詞,都具有典型的羅馬特色。第三條線索,《詩藝》是“教育之書”,它是古典詩教的一部分,突出詩歌在城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詩不僅表達城邦意見,不只是傳聲筒,詩人還類似立法者,是靈魂的導師。賀拉斯追溯“古之詩人”也抬高了詩人在教育中的地位。在這條線索上,賀拉斯的《詩藝》既與古希臘羅馬的修辭學教育相關聯,又與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柏拉圖的《理想國》、赫西俄德的《神譜》以及《荷馬史詩》這條詩教傳統聯系起來。《詩藝》既是文藝批評作品,也是現實政治教育之作,更是超出具體時代和城邦的詩教之作。從這三條線索認識《詩藝》,賀拉斯的“結合快樂與益處”(也即“寓教于樂”)能在更高的層面得以理解。此外,西方的古典詩教又可以跟中國的古典詩學批評以及禮樂制度聯系起來。中國的古典詩學同樣有“興、觀、群、怨”的傳統,中西詩學可以在詩教層面互相發明。
《詩藝》被當成文藝批評作品,讀者對“寓教于樂”的理解就脫離了其具體的語境,往往強調其詩學原則和文藝思想,注意其形式和技藝因素,而淡化了它在古羅馬語境中的作用尤其是公共教育的意圖以及價值,更是忽略了賀拉斯對詩人的期望。這是大多數古典作品后來的命運,其詩教的意義被弱化,而突出其審美和藝術的因素。重新審視其最初的語境,恢復詩藝、詩人與詩教的視野,仍然有現實意義。
四、結語
賀拉斯的《詩藝》是一部復雜的文本,有多個面向。把“寓教于樂”之說放置到具體的歷史語境,可以看到《詩藝》與詩教密切關聯,《詩藝》的核心是詩教。古典的教育主要以詩教的形式進行,蓋因詩歌有打動人心的能力,能幫助認識人的靈魂。賀拉斯在《詩藝》中塑造了“理想詩人”的形象,在此基礎上討論具體的詩藝。“詩人”部分是整部《詩藝》的前提和基礎。賀拉斯追慕古代詩人,把詩人提升到“立法者”“通譯者”的地位,突出了詩歌與靈魂的關系。“理想詩人”處在古羅馬具體的政治語境和文學秩序當中,也深嵌在古希臘羅馬的修辭傳統當中。此外,賀拉斯又超出了具體的政治語境,“寓教于樂”必須立足于對人的靈魂的洞察和對人的性情的把握。
賀拉斯的詩學觀念在古典主義時期受到推崇,并與戲劇實踐相結合,成為文藝批評的經典文本。在賀拉斯的作品、古羅馬的現實處境以及古希臘羅馬修辭學的語境下,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賀拉斯的詩教觀,進而認識古典詩學的政治維度。就此而言,回到語境中重新認識賀拉斯的詩學觀念,思考古典的詩教傳統,也對我們當今的美育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