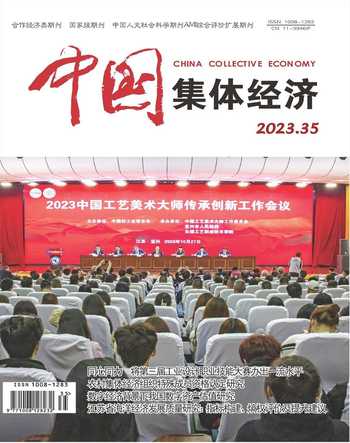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影響就業的路徑分析
潘丹丹
摘要:文章系統梳理了人工智能技術影響就業相關文獻,并從就業補償、就業替代、就業結構、商品的可貿易性、勞動力市場運行效率、就業形式、所有權與就業收入七個方面詳細分析了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對于就業產生的影響路徑,最后提出了相關的應對措施。
關鍵詞:人工智能 就業 路徑
一、前言
2023年開年以來,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引發的就業焦慮成為社會關注的新焦點。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近年來伴隨著大數據、云計算、機器學習、智能語音、圖像識別、智能機器人等人工智能相關技術的發展、突破和應用,人工智能技術正在日益對于社會生產關系產生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對就業的沖擊。理解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對于就業影響的原理、路徑與后果,對于更好的調整社會生產關系,進一步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至關重要。
人工智能技術影響就業的方面眾多,涉及就業總量、就業結構、就業工資水平、就業收入以及衍生出的技能溢價、收入分配、機器稅、人力資本投資等問題;同時人工智能技術影響就業的路徑眾多,涉及就業的補償與替代、生產效率、要素相對價格、空間布局與人口流動等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的后果如何去辯證看待,技術沖擊的短期影響與長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辯證邏輯關系如何去梳理等等問題也需要去研究。
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就業的影響問題,根植于技術的發展所導致的創造性破壞問題。對于人工智能技術的擔心實際上是對于工作計算機化、自動化的擔心的延續,不同之處出在擔心人工智能技術不僅僅會替代簡單勞動,還能夠替代部分腦力勞動。實際上,學者們早已對于科技的發展引起的就業問題進行了較多的研究,這是人工智能技術就業影響研究的基礎。
人工智能技術與就業理論研究分成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Acemoglu and Restrepo(2016)為代表的基于任務的模型,另一方面是以Prettne(2019)為代表的將人工智能技術納入生產函數的模型。基于任務的模型方面,Autor et al.(2003)提出、Frey and Osborne(2017)等拓展的ALM模型,將勞動力市場分為可被替代的常規工作和起到互補作用的非常規工作兩大類,研究了計算機技術的應用對于勞動力市場的沖擊機制;Benzell et al.(2017)通過構造跨期迭代模型,認為在一定條件下,機器人可以完全替代低技能工作,并替代一部分高技能工作。將智能技術納入宏觀經濟增長模型以Steigum(2011)、Prettner(2019)為代表。Steigum(2011)通過設定CES生產函數,將資本分為傳統資本和智能化資本兩大類,智能化資本與拉動之間存在替代關系,分析了經濟的穩態以及內生增長機制。Prettner(2019)則直接將智能化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設為1,即完全替代關系,基于索羅模型分析了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情況下,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綜上,現有研究對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就業影響從多個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為我們理解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就業的作用機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長期來看,只要經濟不斷增長、勞動者素質不斷提升,補償效應總會覆蓋替代效應,但是短期不同,在經濟增長、技術進步沒有發生大的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短期內替代效應所導致的失業問題是引起人們對人工智能技術“恐慌”的最根本原因。下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全面梳理和分析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就業的影響機制,以期推動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二、人工影響就業的路徑分析
(一)人工智能技術的就業補償
人工智能技術的補償效應有兩條:直接補償效應與間接補償效應。這兩種補償效應在不同的產業部門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導致產業間的就業結構、產業內的就業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
人工智能技術的直接補償效應是指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對于就業的直接拉動作用。也有兩個方面的表現。一方面表現為人工智能技術相關產業規模的擴張所導致的就業數量的擴張。對于人工智能技術相關產業而言,人工智能技術的開發會直接導致相關產業高端技術人員的就業水平提升,同時帶動人工智能技術企業的其他諸如營銷、財務、后勤等相關部門的勞動就業,從而導致人工智能技術相關產業就業比重在全社會就業比重的上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在企業的應用,也會直接拉動企業內部高端技術人員的需求,企業需要專門人員對于相關設備和軟件進行操作,對相關的應用、業務等進行開發和運營,表現為企業內部人工智能技術相關工作人員的比重不斷上升。
人工智能技術的間接補償效應表現為通過提升企業管理效率、競爭水平,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等途徑,提升了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生存能力和盈利水平,使得企業愿意進一步擴張生產規模。在企業規模擴張過程中,對于生產要素的需求增加,從而拉動人工智能技術等相關的就業。
人工智能技術的直接補償效應會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開發和應用而強化,對于就業的拉動作用將會是持續性的。但是人工智能技術的間接補償效應會受到企業規模擴張的影響。如果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企業的應用,企業規模不能得到有效的擴張,那么間接補償效應就會受到抑制。
(二)人工智能技術的就業替代
人工智能技術的替代效應發生在企業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的過程中。在企業生產規模保持不變的前提下,由于人工智能技術不斷代替簡單重復勞動和部分腦力勞動,使得企業內部單位產出需要的勞動力數量減少。但是由于就業剛性和勞動力市場中的工會以及其他勞動者保護組織的存在,企業不會在短時間內裁員。更多的形式是通過規模擴張,在企業規模擴張的時候,增加人工智能等資本的投入,而不增加或少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因而在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應用過程中,替代效應的產生有一定的滯后性。短期內,如果企業規模無法實現擴張,在技術投入不斷增加而勞動力投入不能減少的情況下,企業利潤會受到擠壓,替代效應占據主導。
上述替代效應與補償效應的方向應當是相反的。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就業的總影響的方向取決于兩種力量的相對強弱,如果企業的規模可以無限擴張,那么我們無須擔心機器對于人工的替代,但是在短期內,在企業規模擴張受到經濟增長、對外貿易、技術水平等條件限制的情況下,有必要通過實證計算,分析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就業影響的大小、方向和特征。
(三)人工智能技術與就業結構
結構效應著重在于分析智能化、自動化技術對于不同勞動力的影響差異性。一般認為相對于低水平重復勞動而言,智能化和自動化技術可以實現對于這部分就業崗位的完全替代,而對于非重復性的復雜勞動,自動化技術是無法實現對于勞動的完全替代的,但是人工智能技術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于這部分勞動的替代。特別是伴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進一步深入發展和應用,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復雜勞動的智能化機器人、智能化決策系統、智能化生產線等的部署、使用和技術演進,人工智能技術替代復雜勞動的能力將逐步增強。即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勞動力的替代會從低端簡單重復勞動開始,逐步向高端復雜非重復性勞動擴散,在未來的某一個時期,將可能實現對于大部分勞動的替代。
(四)人工智能、貿易結構與就業
人工智能技術正在改變著貿易結構,進而對于就業產生結構性影響。通常貿易構成可以分為產品貿易與服務貿易。產品貿易來自生產分工,各個國家或者地區基于比較優勢,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而在貿易成本約束下,與鄰近地區或者國家產生產品貿易行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典型比較優勢就是勞動力優勢,通過吸引外資,充分利用國內廉價的勞動力帶來的人口紅利,采取“兩來一補”式生產方式,中國制造的產品獲得全球比較優勢,使得中國的進出口規模大幅度增加。勞動力的低成本比較優勢是中國產品出口的國際優勢的重要來源,支撐了改革開放后中國至少2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以中美為例,正是由于中國勞動力比美國便宜,中國才得以從美國吸引大量的國際投資。但是,如果勞動力可以大量被廉價智能化機器勞動力所替代,那么中國的這種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相對美國而言,將會消失,大量的資本將回流美國,尋求更大的制度優勢,全球貿易結構也將發生重大變化。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伴隨著人工智能的應用,智能化機器勞動力將會通過產品貿易結構的變化,影響到就業結構。
除了產品貿易,實際上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也在改變著服務貿易的結構,使得大量原先依賴于接觸式服務的服務產品,被非接觸式服務所替代,同時,大量的不可貿易的服務產品開始變成可貿易性服務產品,服務業的就業形式和就業內容也可能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發生變革,部分可以被人工智能的替代的服務形式消失,部分可以貿易化的服務產品可以獲得與產品生產類似的規模經濟,從而生產成本進一步降低,規模進一步擴張,就業持續增加。
(五)人工智能技術與勞動市場運行效率
信息技術的進步,使得信息的發布、搜尋、處理、使用等的成本和效率大幅度降低,改善了勞動力市場的信息傳遞機制和價格發現機制,能夠降低勞動力市場的非對稱信息現象。而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特別是智能化的招聘、管理以及崗位推薦算法的應用,更是進一步提升了勞動力市場中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方的信息匹配程度,使得需求方更容易通過相關平臺獲得精準的勞動力供給信息,能夠更容易發現潛在供給,并能夠更為準確地評估潛在勞動者的崗位適應能力,降低招聘過程中人崗不匹配程度;對于求職者而言,也更容易和更精準地獲得推薦崗位,同時,勞動者信息化素養的不斷提升,也進一步增強了勞動者的綜合技能,拓展勞動者的潛在就業機會。上述兩個方面來看,不論是供給還是需求側,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從本質上進一步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交易成本,提升了勞動市場的運行效率。
(六)人工智能技術與就業形式
人工智能技術進一步拓展了個體勞動者就業形式。尤其是伴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產生的新興崗位和新興就業方式,使得大量的靈活就業人員得以在經濟波動的沖擊下能夠盡快匹配到合適的靈活就業崗位,例如以外賣快遞員、跑腿、網約出租車司機等為代表的靈活就業形式,智能化技術的應用極大降低了此類靈活就業人員的招聘成本和管理成本。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改變了部分就業的工作模式和工作內容,引發就業形式的變革,特別是部分難以被傳統技術替代的崗位,開始出現就業形式的變革。例如智能化語音識別技術的應用,導致速記、翻譯等工作崗位的就業形式開始被技術深度替代,另外人工智能技術與傳統的藝術創作的深入融合,導致基于AI的繪畫程序可以在短時間內畫出精美的個性化圖像,對于美工、插畫、繪畫等高度個性化的難以被傳統工業化技術替代的崗位產生了重大的沖擊,改變了這些崗位的學習、創作、工作方式與形式。此外,基于AI驅動的數字人開始在營銷、教育、表演等領域的大量應用,替代了這些領域的原有勞動力,同時增加了對于后開發、維護人員的崗位需求。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特別是強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從低端到高端對于就業產生沖擊,產生了大量新興的就業崗位,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著從低端到高端的就業形式。
(七)人工智能技術、所有權與就業收入
經濟模型在進行問題分析時,往往假定資本由人所有,智能化資本與傳統資本一樣,同歸屬于資本的類別,因而也由人所擁有,因而憑借資本所有權,人的收入實際上可以分為勞動性收入和資本性收入兩大部分,但是模型往往會忽略所有權結構問題,即誰擁有資本。在非智能化時代,資本家擁有資本,勞動者擁有天生的勞動力,二者結合才有了現代化大生產體系。但是在智能化時代,由于智能化資本能夠近乎完全替代勞動力,那么必將導致部分勞動者由于失業而喪失工資性收入,且由于智能化資本對于勞動力的替代是從低端勞動開始逐步向高端勞動全面滲透,失業導致的工資性收入降低甚至消失成為社會所必然面臨的問題。增加資本性收入,特別是智能化資本的收入成為解決問題的鑰匙,當勞動者由于被智能化機器替代,而喪失工資性收入的時候,可以憑借資本性收入獲得生活保障。因而在今后的智能化時代,資本的所有制結構問題不可忽視。
一個美好的前景規劃是:智能化資本由勞動者擁有,勞動者的富裕程度不取決于其擁有多少勞動力資源稟賦,而是取決于其擁有多少智能化資本。勞動者不需要像現在的生產一樣,投入自己的時間、體力、腦力去滿足現代生產流水線、服務過程等的一個環節,不需要再做一顆現代化生產大機器的螺絲釘,而是做智能化資本的擁有者,由智能化機器完成現在人工所完成的幾乎所有工作,勞動者的勞動形式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由親自參與勞動轉化為讓智能化資本替代人進行勞動,勞動者的勞動形式轉換為管理智能化資本的勞動。因而誰擁有智能化資本至關重要。
由于機器可以替代勞動,而智能化機器的眾多優點使得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與智能化機器競爭時將不占據優勢,進而導致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談判地位很低,處于劣勢。如果智能化資本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擁有智能化資本的少數人將支付保留工資給沒有擁有智能化資本的勞動者,這一保留工資將僅僅能夠維持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伴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張,社會收入的不平等現象將會日益加劇,最終引發社會動蕩。一個符合前文美好前景規劃的所有制結構必須能夠應對上述問題,智能機器稅成為必然。通過征收智能機器稅,通過收入的二次分配,支持勞動者能夠獲得智能化資本的所有權,將有助于改善社會的收入分配結構。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系統梳理了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就業影響的相關研究,并從就業補償、就業替代、就業結構、勞動力市場運行效率、就業形式、所有權與就業收入六個方面詳細分析了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對于就業產生的影響路徑。就業補償與就業替代的深入,必然表現為就業結構問題,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提升了市場運行效率,促進了新型就業形式的出現。伴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更深入應用,長期來看,對于智能化技術、智能化設備、智能化生產要素等的占有,即所有制問題將會成為未來人工智能技術改變收入分配關系的重要影響因素,一旦今后勞動力能夠輕易被高度智能化的廉價機器勞動力所替代,對于大多數靠提供勞動力獲得必要的生活收入的居民而言,將會產生非常嚴重的收入沖擊,社會由于智能機器勞動力的大量使用而實現高速增長,但是居民個人由于勞動力被完全替代而面臨生活困境,社會的繁榮成果不為大多數人所占有,因此未來智能化資本的所有制問題以及社會收入的再分配機制至關重要。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應當采取積極的就業應對措施,推動政策前置,幫助低技能勞動者的靈活就業,為高技能勞動者的再就業、為創業提供更多的支持性政策,同時要強化收入分配制度的進一步改革,特別是要強化智能化要素,尤其是能夠代替勞動者進行工作的諸如人工智能機器人、虛擬數字人等要素的所有權改革,要能夠使得勞動者占有最基本數量的智能化生產要素,讓居民能夠通過占有智能化生產要素而獲得要素性收入,以達到能夠彌補勞動力被替代所造成的收入損失的程度,使得勞動者能夠進一步減少勞動時間,享受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社會福利,勞動者有更多的收入和閑暇時間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
參考文獻:
[1]Acemoglu D.& Restrepo P.,“The race between machine and man:Implications to technology for growth,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6).
[2]Prettner K.,“A note on the implications of automation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labor share,”Macroeconomic Dynamics,Vol.23,No.3(2019):pp.1294-1301.
[3]Autor D.H.& Dorn D.,“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3,No.5(2013):pp.1553-1597.
[4]Frey C.B.& Osborne M.A.,“The future of employment: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Vol.114(2017): pp.254-280.
[5]Benzell S.G.,Kotlikoff L.J.& Lagarda G.et al.,“Robots are us:Some economics of human replacement,”Idb Publications(2017).
[6]Steigum E.,“Robotics and Growth,”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ontiers of Economics and Globalization,Volume 11).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Vol.11(2011):pp.543-555.
[7]于曉龍.我國信息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研究[M].中共中央黨校,2015.
*基金項目:江蘇省教育廳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21SJA2435);南京郵電大學通達學院院級科研項目(XK205XS19015)。
(作者單位:南京郵電大學通達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