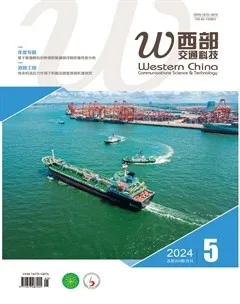基于數字孿生模型的公路橋梁設計施工一體化系統






摘要:針對公路特大橋梁設計與施工之間無法有效建立精細化管理等問題,文章基于傳統數字孿生模型深化橋梁設計施工一體化管理系統。該系統通過制定一體化編碼結構,將自動化數字編碼與大數據融合算法模型相掛接,并與項目管理業務過程融合,提高了橋梁施工的數字化管理水平,為后續實現橋梁數字化資產管理和養護奠定了基礎,對于可視化設計成果快速交底以及施工進度管理等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數字孿生;公路橋梁;BIM;設計施工一體化
U495A290923
0 引言
隨著“十四五”發展戰略的持續推進以及“一帶一路”發展規劃的實施推進,大批新建高速公路相繼開工建設。跨越江河湖和海峽的大型橋梁作為高速公路的關鍵性控制工程,是保證公路全線通車和正常使用的關鍵[1]。BIM技術[2]作為工程領域智能化的發展趨勢,能夠針對不同橋梁設計進行精細化管理,建立特征化數字仿真模型,實現項目前期工程預排以及施工進度跟蹤與監測。然而現階段BIM發展的底層算法技術尚缺乏體系,基于不同橋梁設計規范的系統研發之滯后,未能根據材料屬性和安全耐久性要求滲透實際施工過程中[3]。特別是對于公路特大橋梁設計與施工之間的數據流通工作缺乏效率,二維圖紙向三維信息多維建模存在困難[4]:(1)公路特大橋梁從傳統線條繪制的二維設計方式向構件布置的三維設計轉變受阻;(2)BIM信息系統獲取的海量監測數據混亂,未能根據相關多元數據分析施工過程存在的不確定性問題。
因此,提高公路建設項目特大橋梁設計質量和實現工程數字化管理,采用三維數字化集成幾何表達與信息模型協同設計,成為公路特大橋梁數字化施工領域的又一關鍵性問題。
近年來,隨著計算機算力的發展進步,數字孿生技術在橋梁設計與施工中的應用受到各個組織的廣泛關注[5]。通過與工程數字化技術的融合,實現橋梁設計流程的再造和施工管理過程的優化,實現橋梁全生命周期建設的數字化、自動化、信息化[6]。因此,研究基于數字孿生的公路橋梁設計施工一體化管理應用,具有重要的工程意義。
1 基于數字孿生模型的設計施工系統
在設計施工一體化管理平臺的應用中,數字孿生技術以橋梁物聯網為基礎,通過海量分布在類似橋梁施工現場中的傳感器獲取各類數據,例如施工流程、現場監控、進度情況等數據,將數據集成于高還原度的虛擬橋梁模型中,分析、優化相應設計以及施工管理,根據反饋數據可以形成智能決策;此外,結合智能決策結果以及人工經驗,通過操作數字孿生模型下達指令來更新設計圖紙和施工流程,達到以虛控實的效果。系統自上而下的整體架構為信息感知編碼層、多源數據傳輸融合層、數據虛實交互層、智能決策層。
1.1 模型一體化編碼結構
由于特大橋梁設計與施工之間的信息數據缺乏有效連接,而且現有三維模型的拆分工作以及系統底層算法編碼工作量大,代碼出錯無法及時維護。為此,基于數字孿生系統的原有框架,考慮特大橋梁設計周期內的建設管理、成本計算工作以及施工過程中的大數據監測反饋、各工程段檔案管理等要素,通過架構短短為公路信息模型分類編碼,結合三維數字化軟件實現公路橋梁的設計施工一體化管理系統建立。
模型表示編碼的整體思路為:首先將各橋梁工程項目的建設與運營數據匯總收集至大數據平臺,然后通過關聯表示編碼進行公路工程信息分解,最后根據空間部位、專業要素、結構構件以及檔案版本實現相應目標。其中項目編號采用企業級項目碼,由項目建設單位在規范基礎上自行擬定;工點編號參照專業+單位工程號劃分;構件分類按國家標準針對建筑信息模型面分類法中建設成果內容進行分類;位置關系則通過某類構件的左右幅以及三向維度進行編碼;版本序號考慮版本變更后添加的版本序號信息重新組成。如圖1所示。
1.2 多源數據傳輸融合層
由于特大橋梁施工過程中不確定性顯著:地質條件復雜、橋梁設計方案多樣、現場施工材料機械多、施工管理不完備等。不論是設計階段還是施工周期內,相關要素信息無法有效流通,針對多樣化工點與構件之間的設計與施工,提出基于多源數據與協同管理的數字孿生設計施工一體化系統,建立不同業務渠道的連接。
數據融合功能模塊的構建(見圖2),主要通過RFID以及PLC等獲取設計與施工的時序數據,對時間傳播鏈條上的信息實時多元感知;基于傳感器或衛星遙感等工具對目標的點跡與坐標變換進行軌跡獲取;最后通過現場施工的協同管理器對大數據信息進行誤差校正。在多元數據關聯的過程中,天地系統可以精確化處理點軌跡,在進行軌跡關聯時借助各方工具實現參數的屬性、狀態融合。基于數據關聯之后可判斷設計與施工態勢,對實時狀態進行評估,繪制軌跡濾波曲線,根據局部態勢圖反饋指導設計施工[7]。
1.3 數據虛實交互層
考慮到多元信息獲取的隨機性與多變性,針對不同方式得到的海量數據需進行差異化篩選分析,針對重復要素以及無效數據去除清空,對缺項重要數據進行自動化填補。而且新構建的數據集與原始數據可相互兼容轉換,以便后續不同階段的調用與共享。首先依據各類屬性進行數據的向量化處理;其次針對干擾數據采用三倍標準差剔除標準進行誤差排除;然后歸類每種屬性目錄下的各類向量,基于時空對齊操作獲取結構化完整的大數據集[8]。
借助兩個低維的尺度函數進行二維的分離式函數構建,其中小波函數以及相應的尺度函數[9]可根據ψ(x)與φ(y)公式表達,進而方向敏感波為:
ψH(x,y)=ψ(x)φ(y)
ψV(x,y)=ψ(y)φ(x)
ψD(x,y)=ψ(x)ψ(y)(1)
式中:ψH——度量沿列方向的變化;
ψV——度量沿行方向的變化;
ψD——度量對角線方向的變化。
1.4 智能分析決策層
交互后獲得的感知多源數據能夠進行原有態勢的評估操作,并將結果進一步驗證反饋,針對原有態勢的分析結果修正以此提高可靠度。基于融合協作的數據可重新進行監測評估,更新重組信息庫內的各類屬性資源。如果數據庫內的資源符合算法預先規劃的各種約束,可依據可靠性進行更新操作[10-11]。若融合后的數據可信力高于原數據集則更新舊數據,否則保持原系統內資源不動。基于此種小波融合算法的表達方式能夠進行新舊數據之間的信息互補,在設定的評估范圍內動態調整,對設計施工全周期提供了可靠的鑒別庫。其中態勢評估可靠性主要依據規則信度來進行操作,假設存在相容的n個集合Ω1、Ω2、…、Ωn,這些辨識框架內部存在多重異構的命題集合,若存在命題集Ai∈Ωi,那么對應映射法則F:A→B且A∈Ωi,B∈Ωj,則Ω1、Ω2、…、Ωn中所規定的命題可以由規則F進行表述。而組合命題的可信度可表示為:
m*R(c)=
mR(A)×mRi(c)
m(c)×1-m*(A,B)1-m(A,B)(2)
式中:m——根據映射法則的原始可信度分配值;
m*——根據映射法則調整后的可信度值。
2 工程應用
以相思洲大橋主橋為例,該橋是一座雙塔雙索面半漂浮體系斜拉橋,跨度分別為40 m+170 m+450 m+170 m+40 m。其中,主跨450 m橫跨南汊通航孔,170 m邊跨橫跨相思洲北汊。大橋的主塔承臺基礎為長54 m,寬17 m的圓端形承臺,厚6 m,下有23根直徑2.5 m的鉆孔樁。大橋南北主塔的高度均為147.3 m。主梁采用分離式雙箱組合梁,組合梁中心高度3.5 m,梁的全寬為33.5 m。北岸引橋由預應力混凝土小箱梁橋和預應力混凝土T梁橋組成,而南岸引橋則是鋼混組合連續梁橋。
從項目設計源頭開始進行BIM總體應用策劃,通過制定項目BIM建模標準、BIM軟件平臺應用方案、協同方式以及二次開發等手段,實現基于“一個數據源、一個模型”的大跨徑組合梁斜拉橋設計施工一體化的BIM融合應用。
2.1 實施方案與建模標準
建模過程中結合本項目的特點制定項目不同階段BIM模型精度等級應用方案滿足以各階段的實際需求,避免陷入“過度建模”的誤區。(1)在方案設計階段采用Bentley的OpenRoadsConceptStation作為核心軟件,通過利用無人機傾斜攝影技術生成三維實景模型重構項目工程環境;同時結合PowerCivil、SketchUp等軟件建立起的模型精度為LOD100的道路、橋梁BIM模型,形成項目的真實三維場景展示,實現項目前期階段的快速概念設計。(2)在勘察設計階段在項目方案設計的基礎上采用LOD200~LOD300的模型精度分別進行詳細的BIM設計。主要采用Bentley的MicroStation作為核心軟件,并結合OpenRoadsDesigner、ProStructures等專業軟件進行詳細設計,實現對關鍵構造的精細化設計、工程量統計、二維出圖等。(3)設計完成后根據需要采用LOD300~LOD400的模型精度對橋梁復雜結構進行施工階段的深化設計,并根據施工分部分項進行EBS編碼分解,應用到施工管理階段。
2.2 協同原則
鑒于目前計算機軟硬件的性能,整個項目使用單一模型文件進行工作是不現實的,需根據結構的拆分分別進行模型的創建。不同的建模軟件對模型的處理方式有所不同,且分別有各自的協同工作解決方案。需根據實際的項目需求靈活處理,主要的協同原則為:(1)采用同一坐標系;(2)劃分成員工作范圍,減少工作交叉;(3)設置成員的工作權限,建立暢通的反饋機制;(4)不同的人員建立不同的模型時建模習慣要基本一致,圖層、構件命名規則要一致,線條寬度、樣式、顏色要保持一致;(5)對模型進行的更改要做好記錄,記錄項目各階段模型的修改和版本變化,方便復核管理。
2.3 二次開發
基于Bentley的MicroStation CONNECT Edition定制開發本項目的電子沙盤,根據項目的分部分項對大橋BIM模型進行拆分并賦予編碼及相關工程屬性,進行3D的項目過程管理。同時利用輕量化工具將項目BIM模型轉換格式后上傳到基于Cesium開發Web GIS端,實現輕量化的BIM模型信息瀏覽、管理和共享。項目基于同一個云數據庫和先進成熟的數據架構方式,實現電子沙盤端、Web GIS端及手機App多個不同終端平臺直接對BIM模型所關聯的屬性進行管理、檢索和修改。通過BIM與GIS的集成應用,最終形成以BIM模型為載體,集資源、工序、進度、安全、質量管理等于一體的施工管理系統(見圖3~4)。
3 結語
本文針對公路特大橋梁設計與施工之間二維圖紙向三維信息多維建模存在的困難,研究了設計施工“數字孿生模型”銜接融合技術,制定了設計施工“數字孿生模型”轉換規則。研發轉換工具完成設計施工“數字孿生模型”無縫銜接,解決設計施工信息流轉與共享的障礙,滿足工程三維數字化技術在不同工程生命階段應用的需求。
參考文獻:
[1]邵旭東.橋梁工程[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
[2]龍 波,彭 欣.基于Bentley的公路BIM協同設計與施工管理應用研究[J].西部交通科技,2019(5):160-163.
[3]朱覺文.申威特大鋼管拱橋設計施工一體化BIM技術應用分析[J].西部交通科技,2022(3):127-130.
[4]沈新福,梁慶慶,蔣國富.基于BIM技術的土木工程數字化實訓平臺系統架構及關鍵技術研究[J].西部交通科技,2021,173(12):198-200.
[5]S.P.Sreenivas,Padala.A.Roadmap For Integration Of Design-Construction Decision Mak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2016,5(32):236-241.
[6]Gregory P Luth.Alyssa Schorer.Yelda Turkan.Lessons from Using BIM to Increase Design-Construction Integration[J].Practice Periodical on Structur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2014,19(1):103-110.
[7]朱 肖,劉彥明,李宗建,等.基于BIM技術的鐵路橋梁構件編碼應用研究[J].鐵道標準設計,2023(12):115-120.
[8]李蘇生,朱學軍,王媛青,等.BIM建模與健康監測預警相融合的橋梁運營管養一體化研究[J].交通與運輸,2022,38(4):52-57.
[9]Li Xiaofei,Xiao Yuyu,Guo Hainan,et al.A BIM Based Approach for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of Bridges[J].KSCE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2021(1):155-165.
[10]張繼偉,楊貴華,陳星宇,等.BIM技術在道路橋梁工程運用的研究現狀[J].中國水運,2022(8):142-145.
[11]王 勇,路盛敏.基于BIM技術的公路工程管理系統應用[J].西部交通科技,2022,178(5):156-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