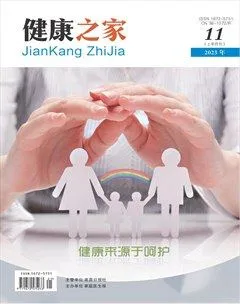蛋白質乙酰化在消化系統腫瘤中的作用及機制研究進展
孟祥云 蘇麗婭
摘要:蛋白質乙酰化是許多細胞生理和病理過程中廣泛存在的關鍵角色,是蛋白質翻譯后修飾(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PTM)中最重要的修飾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發現蛋白質乙酰化參與人體各個系統的調控作用,它不僅可以參與調節蛋白質的穩態、轉錄活性、調節代謝,還在基因轉錄、自噬等方面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對蛋白質乙酰化、蛋白質乙酰化的生物學意義進行概述、回顧和探討,并闡述其在消化道腫瘤中的作用及機制,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可行的指導。
關鍵詞:消化道腫瘤;翻譯后修飾;乙酰化;代謝;自噬
蛋白質的翻譯后修飾(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 tion,PTM)是所有生命活動的主要調控機制。PTMs賦予修飾后的蛋白質新的性質,包括酶活性的變化、亞細胞定位、蛋白質穩定性及DNA結合等。蛋白質的PTMs方式極其多樣,目前已確定的翻譯后修飾方式超過400種,以磷酸化、泛素化、甲基化、乙酰化等較為常見,大多與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心血管系統、免疫系統以及腫瘤的發生發展等諸多系統疾病密切相關。作為一種重要的翻譯后修飾,蛋白質乙酰化參與著幾乎所有的生物學過程,如轉錄、應激反應、新陳代謝以及蛋白合成與降解等。本文將闡述蛋白質乙酰化的背景、分類、功能以及與消化道腫瘤之間的關系,以期為研究消化道腫瘤的靶向治療提供可行的思路。
1蛋白質乙酰化及相關概念
蛋白質功能的精確調控,對于調節機體多樣化的生命活動至關重要。蛋白質乙酰化是指乙酰轉移酶(Lysine Acetyltransferase,KAT)將乙酰基轉運到蛋白質氨基酸殘基上的過程。根據乙酰化位點的不同,存在3種主要形式:N-端乙酰化(Nα-乙酰化或N-ter乙酰化)、賴氨酸乙酰化(Nε-乙酰化或K-乙酰化<KAc>)和O-乙酰化。
N-端乙酰化是由Kozo Narita在1958年發現的一種不可逆的修飾,發生在蛋白質骨架的α-氨基或蛋氨酸裂解后的第二個氨基酸。N-端乙酰化的生物學功能尚不完全清楚,但其參與調節蛋白質降解、穩定性、蛋白-膜/蛋白-蛋白相互作用以及抑制內質網易位等。此外,N-端乙酰化還與多種病理過程有關,包括腫瘤發展和神經退行性疾病等。
賴氨酸乙酰化在底物賴氨酸殘基的側鏈上加入了乙酰基,這一過程是可逆的。賴氨酸乙酰轉移酶(KATs)和賴氨酸去乙酰化酶(KDAC)調節KAc修飾水平。KATs將乙酰基從乙酰輔酶a轉移到蛋白質中特定賴氨酸殘基的ε -氨基上,同時乙酰化也可以被KDACs逆轉。乙酰基的加入可以中和賴氨酸殘基的正電荷,從而改變修飾后氨基酸的大小及蛋白質的局部疏水性。這一機制使得KAc成為細胞信號轉導和代謝中最重要的PTM。
O -乙酰化是一種可逆的修飾,在絲氨酸或蘇氨酸的羥基側鏈上加入乙酰基,只在少數真核生物中被檢測到。初步報道的O-乙酰化表明,這種類型的PTM在感染鼠疫耶爾森菌后調節生物信號通路(如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s>)中發揮重要作用。組蛋白H3的絲氨酸和蘇氨酸的O-乙酰化已被證實從酵母到人類高度保守。然而,發生O-乙酰化是相對罕見的。
2組蛋白與非組蛋白乙酰化修飾研究進展
1964年,Vincent Allfrey等報道了組蛋白乙酰化的鑒定,并深入地提出了組蛋白乙酰化修飾在轉錄調控中的調控作用。隨后,組蛋白乙酰化轉移酶(HATs)、a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和乙酰- lys結合蛋白被鑒定為轉錄調控蛋白。近年發現的HATs主要有300/CBP、GNAT、MYST、P160、PCAF、TAFII230家族。在高等真核生物中,HDACs根據其與酵母原酶序列的同源性,可分為4類:I類HDACs,包括HDAC1、2、3、8;II類HDACs由HDAC4、5、6、7、9、10組成;III類HDACs,也稱為Sirtuins,由SIRT1-7組成;IV類HDACs,包括HDAC11[1]。一般來說,組蛋白乙酰化與轉錄升高相關,而組蛋白去乙酰化往往與基因抑制相關。以往的報道表明,組蛋白乙酰化與腫瘤發生密切相關,并能影響腫瘤細胞的某些生物學過程,包括增殖、凋亡、轉移和干細胞。
除了組蛋白,在進化上不同的生物中,數以萬計的非組蛋白也發生了乙酰化。1997年,Gu團隊在人腫瘤抑制因子p53上首次發現了乙酰化修飾參與非組蛋白的轉錄調控。隨后,基于乙酰化肽段的免疫親和純化和液相色譜-串聯質譜的乙酰化蛋白質組技術不斷發展,大量非組蛋白賴氨酸乙酰化修飾被發現,它們參與了轉錄因子、核相關蛋白、激素受體、細胞代謝相關蛋白、癌癥相關蛋白等相關的乙酰化修飾。
3蛋白質乙酰化的功能
蛋白質乙酰化是基因轉錄的主要調節因子[2]。大多數規范的KATs定位于細胞核,并作為轉錄協同激活因子發揮作用。研究表明,大多數組蛋白乙酰化都依賴于轉錄,這種依賴性的部分原因是RNA聚合酶II(RNAPII)對H4組蛋白乙酰化轉移酶(HATs)與基因相互作用的要求。乙酰化調節轉錄后,參與RNA加工的各個步驟,包括mRNA前剪接和聚腺苷化,以及聚腺苷化mRNA降解等。有研究學者發現,U2 snRNPs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PHF5A,它可以在K29位點發生乙酰化,以應對多種細胞應激,這主要依賴于p300。PHF5A乙酰化增強U2 snRNPs之間的相互作用,影響Pro-mRNA的整體剪接模式和廣泛的基因表達[3]。PHF5A高乙酰化誘導的選擇性剪接可穩定KDM3A mRNA,并促進其蛋白表達,通過PHF5A的乙酰化促進癌細胞抵抗應激的能力,從而有助于腫瘤的發生。活性氧(ROS)在細胞中不斷產生,過多的活性氧會導致氧化應激。ROS與Hippo通路的調節有關。數據報道,氧化應激- CBP調節軸控制MOB1-K11(MOB1是Hippo通路中的共激活因子,屬于MOB家族)。乙酰化并激活LATS1,從而激活Hippo通路,抑制YAP/TAZ核易位和腫瘤進展[4]。PTMs被認為是氧化應激-炎癥-老化三位一體之間的聯系。組蛋白乙酰化可以調節生物氧化應激反應,從而影響機體老化。
4乙酰化修飾與消化道腫瘤
4.1 胃癌
表觀遺傳過程的研究強調組蛋白乙酰化在癌癥發展中的意義,主要受HATs和HDACs的調控。在各種癌癥中,HDAC的改變導致HDAC抑制劑(HDACis)的產生。在GC小鼠模型中發現,HDACis具有抑制細胞增殖、誘導細胞凋亡和抑制腫瘤生長的作用。不同的研究表明,其中一些還與細胞周期阻滯、遷移抑制、轉移形成和腫瘤抑制基因表達有關[5]。
為了確定在GC中可能存在受組蛋白乙酰化調節的新基因,研究者通過微陣列分析比較未處理和曲古霉素A(TSA)處理的GC細胞株,發現在鑒定的上調基因中,BMP8B mRNA和組蛋白乙酰化在配對的GC和非腫瘤樣本中被定量[6]。胃癌組織中,BMP8B mRNA的表達較癌旁非腫瘤標本減少。BMP8B mRNA的減少和乙酰化H4K16水平在低分化的GC中呈正相關。由此證明,BMP8B在GC中可能是一個受H4K16乙酰化調控的腫瘤抑制基因,特別是在低分化腫瘤中。
4.2 食管癌
HMGA2乙酰化可增強與靶基因的結合,抑制其泛素化和蛋白酶體降解,導致HMGA2積累,也可以促進食管鱗狀細胞癌的生長[7]。Survivin基因是一種存在于多種惡性腫瘤中的獨立標記物,且在惡性腫瘤中呈現過表達狀態,可抑制腫瘤細胞的凋亡、促進細胞增殖和腫瘤血管生成。NU9056(乙酰基轉移酶抑制劑)可能通過抑制乙酰基轉移酶KAT5的表達,下調食管癌EC109細胞中Survivin的乙酰化水平,進一步抑制腫瘤增殖通路中的相關蛋白表達,從而抑制食管癌細胞增殖、侵襲和遷移能力。
此外,國內學者通過一系列實驗發現,在食管鱗癌(ESCC)細胞質中,Fascin(肌動蛋白結合蛋白)與PCAF(乙酰轉移酶P300/ cbp相關因子)直接相互作用,并被PCAF定位在賴氨酸471(K471)位點發生乙酰化,通過破壞肌動蛋白的捆綁活性,減少絲狀基的形成[8]。在功能上,Fascin-K471乙酰化可顯著抑制體外ESCC細胞遷移和體內腫瘤轉移,而Fascin-K471去乙酰化則顯示出強大的致癌功能。此外,Fascin-K471乙酰化降低了ESCC細胞絲狀足的長度和密度,縮短細胞的壽命,而去乙酰化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臨床上,食管鱗癌組織中高水平的AcK471-Fascin與延長食管鱗癌患者的總生存期和無病生存期密切相關。
4.3 胰腺癌
乙酰輔酶a(Acetyl-Coa)是一種中樞代謝產物,作為賴氨酸乙酰化的乙酰基供體,在生物合成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具有脂肪酸、膽固醇的生物合成以及信號轉導功能。國外研究發現,KRAS突變的腺泡細胞中乙酰輔酶a的豐度升高,并且乙酰輔酶a在甲瓦酸途徑中的使用支持腺泡-導管化生(ADM)。胰腺特異性缺失產生乙酰輔酶a的ATP -檸檬酸裂解酶(ACLY),會相應地抑制ADM和腫瘤的形成。在胰腺腫瘤細胞中,生長因子促進AKT-ACLY信號轉導和組蛋白乙酰化,同時抑制BET和他汀類藥物治療,從而抑制細胞增殖和腫瘤生長。因此,KRAS驅動的代謝改變可促進腺泡細胞的可塑性和腫瘤的發展,并針對乙酰輔酶a依賴過程發揮抗癌作用。支鏈氨基酸轉氨酶2(Branched-Chain Amino Acid Transaminase 2,BCAT2)是BCAA分解代謝中的一種重要酶。BCAT2在賴氨酸44(K44)位點上發生了乙酰化,BCAT2的K44乙酰化通過泛素-蛋白酶體途徑促進其降解,導致BCAA分解代謝降低。CBP和SIRT4分別是BCAT2的乙酰轉移酶和去乙酰化酶。CBP和SIRT4結合BCAT2,根據BCAA的有效性,可實現對K44乙酰化水平的控制。K44R突變體不僅能夠促進BCAA分解代謝、細胞增殖,還能影響胰腺腫瘤的生長。
5結束語
隨著新技術的不斷發展,人類對蛋白質翻譯后修飾的不斷研究及鑒定,為醫學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便利與幫助。蛋白質乙酰化的快速發展正在為表觀遺傳學的探索尋找新的目標,同時為腫瘤的靶向治療帶來新的發展方向,并為醫學研究領域邁進新的一步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莊薇,鐘寧.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對肝癌誘導自噬的作用[J].廣州醫藥,2022,53(2):39-43.
[2]呂斌娜,梁文星.蛋白質乙酰化修飾研究進展[J].生物技術通報,2015,31(4):166-174.
[3]耿樓,顧文莉.蛋白質的翻譯后修飾與腫瘤代謝[J].生命的化學,2020,40(4):600-606.
[4]鄭璐,沈仁芳,蘭平.植物非組蛋白賴氨酸乙酰化修飾的蛋白質組學研究進展[J].生物技術通報,2021,37(1):77-89.
[5]賁涵芝,邱丙全,楊洋.SIRT1調控其下游非組蛋白分子乙酰化修飾影響細胞凋亡的分子機制[J].中國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報,2021,37(10):1281-1290.
[6]安心麗.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3對胃癌增殖和脂代謝的影響及分子機制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20.
[7]單怡茹,田福華.組蛋白乙酰化在消化系統腫瘤中的研究進展[J].中國醫藥科學,2020,10(24):65-67.
[8]梁宗英,楊陽,鄭競雄,等.乙酰基轉移酶抑制劑對食管癌細胞KAT5、Survivin乙酰化水平及細胞增殖和遷移的影響[J].重慶醫學,2023,52(2):167-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