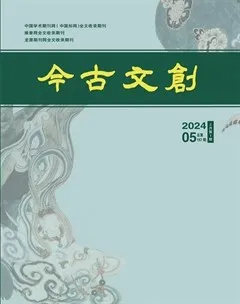作為復調時空體的草原
【摘要】《一日長于百年》是吉爾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瑪托夫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其描述的時空體系聚焦于草原,以長時段和空間的多層次為特點,書寫了對于自然和現(xiàn)代,傳統(tǒng)與文明的看法,也蘊含著對于現(xiàn)實世界秩序的回應。本文擬以巴赫金時空體理論與復調理論相結合分析艾特瑪托夫對這一以草原和草原上的人為主體的對立秩序空間的解構,和其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身份認同困境中對于未來暢想的重構。
【關鍵詞】時空體;復調理論;自我與他者;身份認同
【中圖分類號】I512?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05-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5.008
基金項目:本文系西安外國語大學研究生科研基金項目“區(qū)域國別研究視域下的環(huán)里海研究——以巴托爾德著作‘里海史’及其解讀為例”(項目編號:2023SS120)的階段性成果。
艾特瑪托夫(Ч.Т.Айтматов)出生在吉爾吉斯斯坦塔拉斯山區(qū)舍克爾村一個吉爾吉斯族農牧民家庭。《一日長于百年》是艾特瑪托夫的代表作之一。該作品被稱為20世紀現(xiàn)實主義文學發(fā)展的路標,在簡短的一日敘述中卻利用倒敘的手法將回憶穿插于其間,將時間的跨度拉長到近百余年,將空間的維度從草原上升到太空,歷時與共時的交織搭建了現(xiàn)實、神話傳說與科學幻想這三個時空。三個時空所穿插而成的敘述網絡將人物的經歷與故事串聯(lián)起來,映射出當時社會的縮影。學界對于該文學著作的研究十分關注其生態(tài)思想,認為其對于民族身份的構建體現(xiàn)在對于地方性的描述上,特別是其中的“地方依戀”以及“地方認同”。而這種特殊的地方認同借助于自然的認同和自然的依戀,體現(xiàn)了其生態(tài)思想,并將這種自然生態(tài)的認同轉化為人類范疇的認同。而這種扎根于自然的世界主義認同也體現(xiàn)了作者自己的世界性眼光。①但是對于該著作的時空體的敘述鮮少,著重于會讓小站的時空功能的分析。②
鑒于《一日長于百年》中以草原作為連接歷史、現(xiàn)實與未來三個時空的場域,并以草原上生活的人為故事發(fā)展的重要線索鏈,本文將草原這個承載著更加多維歷史和現(xiàn)實的場域作為分析對象,采用巴赫金(М.M.Бахтин)時空體理論和復調理論從微觀文本分析拓寬到宏觀歷史語境,深度理解歷時與共時空間下草原上人的認同困境與社會矛盾。
一、草原上的復調時空體
時空本屬于哲學概念,受牛頓、愛因斯坦等時空觀的影響,巴赫金在批判和部分吸收康德的時空觀的條件下,以《長篇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歷史詩學概述》為標志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時空體理論。巴赫金對于時空體的定義為:“文學中已經藝術地把握了的時間關系和空間關系相互間的重要聯(lián)系。”“重要的是這個術語表示著空間和時間的不可分割(時間是空間的第四維)。” ③巴赫金對于時空體的界定跨越微觀文本分析和宏觀歷史語境分析兩個層面。在微觀文本分析層面,時間和空間被認為是分析和闡釋小說中人的形象的重要維度。巴赫金將主人公人生歷程的重要時間節(jié)點和空間位置的變換作為研究的切入點。④
在《一日長于百年中》中,現(xiàn)實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一日,可是生活在薩雷-奧捷卡大草原的人以面向過去的傳說和面向未來的科幻兩條復線共同構成了一個長達百年間的時空。以草原鐵路站鮑蘭雷-布蘭內為現(xiàn)實的空間,“在這個地方,列車不斷地從東向西和從西向東地行駛……在這個地方,鐵路兩側是遼調無垠的荒原——薩雷-奧捷卡,黃土草原的腹地。在這個地方,任何距離都以鐵路為基準來計算,就計算經度以格林威始子午線為起點一樣……列車駛過這里,從東向西,或從西向東……” ⑤而鮑蘭雷和布蘭內是這個空間的符號,這一符號承載著兩種不同的人的價值情緒,其一是哈薩克名字,其二是俄羅斯名字。原始的草原和其上轟鳴不斷的汽笛構成了這一空間的雙重屬性——聯(lián)通過去與未來。
在這樣一片草原中,以卡贊加普的送葬之行開啟了對歷史的游歷之行,送葬的早上,天氣炎熱,草原是干旱的,因此植物很難生長,但地質學家葉利查羅夫說過,這里早先是青草茂盛的地方,氣候跟現(xiàn)在完全不同,雨水比現(xiàn)在多兩倍,草原上到處都是牲口,駿馬飛奔,牛羊成群。在這片沒有邊界的草原中,地理條件決定了其土地上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中說道:“游牧,僅指畜牧生活的一種形態(tài)。隨著氣候和季節(jié)的變化,牲畜需要不停地更換草場,追隨著水草的生長地帶進行轉移。而這種逐水草而居的移動性家庭便是游牧生活的方式,也是他們的特點。由于都市和聚落是經濟活動的必要聯(lián)系,游牧必須與綠洲共存共榮。而游牧及游牧社會造就了機動遷徙、群居和善于射御之術的特點。” ⑥這種機動性便造成了草原上大大小小的戰(zhàn)爭,這是自然的抉擇也是人類的原始本性。
因為草原的優(yōu)渥條件,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本性使得乃蠻與柔然族人的傳說也就留在了這片土地上。頭戴希利的乃蠻兒子在柔然的侵占中忘記了自己的過去成了曼庫特,乃蠻母親阿納為了幫助兒子找回記憶而死去,她的墓地便是阿納貝特——母親的安息之地。小說中提道:“他們找到了剝奪活奴隸的記憶的方法,從而對人類犯下了所有可以想象與不可想象的罪行中最為嚴重的罪行。” ⑦記憶被視為一個人最重要的東西,對于一個民族來說,承載著傳說與歷史的民族記憶所具有的厚重感是一個人內心充實的基礎,阿納貝特并非是簡單的一個地點,它是草原民族的記憶,這是一種對于自然的依戀和歸屬。記憶和傳說構成了一個特殊的時空,即草原民族的安息之地,也是小說中的主人公葉吉蓋認為卡贊加普應該被埋葬的地方。
當送葬的小隊來到了這個溝通古今的安息之地,卻發(fā)現(xiàn)這片擁有共同歷史和民族記憶的空間,已經被重塑和轉換為了聯(lián)系未來的航天站。“葉吉蓋首先停了下來——真新鮮!他在駱駝背上微微欠起身,左右看了看,只見草原上彎彎曲曲、時高時低地圍著一層支楞著尖刺、根本無法通過的鐵絲網,一道道的掛在四四方方的水泥柱上,這些水泥柱深深的埋在地里。從這里是休想通過了。”當初的阿納貝特墓地已經被層層圍起來由當時的軍官把手,保護著航空發(fā)射基地。這一與宇宙空間的聯(lián)系構成了時間意義上的三個維度,即歷史上的草原、現(xiàn)實的草原與未來的草原。
在使用時空體理論分析復調小說時,巴赫金特別強調了時空的有機融合,即歷時的一切事物共存在同一空間中,從而闡明了復調理論中時間與空間的結合問題。⑧三個時間維度下草原空間的變化并非是僵化和單線的線性時間的變化,其空間也經歷了由草原上的安息之墓、草原上的鐵路線到連接科幻太空世界的航天發(fā)射基地的變化。三維的空間與時間共同構成了巴赫金時空體中的“四維”空間,即復調的時空體,一個動態(tài)的、充盈的、鮮活的世界,一個與小說中人物能夠產生互動的時空。
二、“屬人的”復調時空體
時空體是“屬人的”,“人”是時空體理論的價值中心。⑨巴赫金指出,“生活中存在原則上不同卻又相互聯(lián)系的兩個價值中心,即自我的中心和他人的中心;一切具體的生活要素都圍繞這兩個中心配置和分布。” ⑩即巴赫金認為小說中存在著同一時間下的空間的分層,這種層級受到小說中以人為中心的時空的影響,這種時空是一種包含著復雜情感和復雜成長經歷的獨特的時空體,它受到關于這個人所經歷的一切影響,是具有特殊性的。因而形成了一種二元的即自我——他者的對抗。這種二元論與《東方學》中薩義德所說的知識—權力—話語三角所構成的東西二元對立不同,而是更傾向于布迪厄的慣習、場域與資本理論。所謂場域便是一個人的生活空間,而這個場域中的人擁有著相似的行為習慣即慣習,資本的積累能夠使得人在這個活動空間中將其轉化為權力。擁有類似慣習的人更有可能進入同一個場域中并共享精神價值和物質資本。而不同場域的人會在各個空間的層級下以自我——他者的方式進行對抗。
在這個荒涼的草原鐵道站上居住著幾戶工人。原本是阿拉爾斯克附近的哈薩克人卡贊加普因家庭原因被錯誤流放,只好申請到邊遠的地方去,他和妻子布凱便當上了鮑蘭雷—布蘭內會讓站的區(qū)間養(yǎng)路工,他們有一個兒子薩比特讓,還有一個女兒。出生于咸海草原的葉吉蓋和妻子烏庫芭拉,因戰(zhàn)后受傷,只能退伍回家,家鄉(xiāng)的貧困逼迫他們離開家鄉(xiāng)去尋找生路,輾轉到達了這個草原上的會讓站,葉吉蓋還飼養(yǎng)著一只黑毛公駱駝。循著歷史的流動,這一小小草原之上,生活著至少兩代人,即以出生于游牧草原的父輩和生長在現(xiàn)代化新時代的子輩。
以此為典型的便是卡贊加普的兒子薩比特讓,作為接受新式教育的他與擁有咸海和草原記憶的葉吉蓋和卡贊加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對一切新興事物感到好奇,對于鐵路的便利和航空基地的修建都采取著積極的態(tài)度,對附近傳出的類似于發(fā)射火箭的爆炸聲感到興奮。同時,他對于父輩對自然和歷史的眷念感到不耐煩和不理解,當自己的父親去世,面對葉吉蓋要帶著父親去往傳說中的安息之地時,他發(fā)出諷刺的回應,即便是在路上也不斷地抱怨和懊悔。而生長于草原的卡贊加普和葉吉蓋卻對自然懷抱著濃濃的眷戀之意。正是草原給他們帶來了家鄉(xiāng)的感覺,是回憶與記憶的連接。而這樣的對抗并非只是個例,而是具有延伸性的,當送葬的隊伍到達了傳說之地,站崗的年輕哨兵和后來的中年軍官都不能共享與葉吉蓋和卡贊加普共通的精神價值,即便他們也來自草原。航天基地的守衛(wèi)者他們所堅守的是上級傳達的指令,是服從的精神。
正是因為不同的成長環(huán)境造就了以人為中心的時空的分層,草原記憶、新時代情緒與職業(yè)精神,每一個主人公都具有個人的時空體,這些復調的時空體在多個層級相互碰撞,以各自的精神價值作為資本進行協(xié)調和對抗,這樣的過程便涉及宏觀的社會歷史層面,多重的時空體構成了小說的多重基調,在宏觀的社會歷史層面將小說的空間敘述多層次化。
三、時空錯位與認同困境
在宏觀的社會歷史層面,巴赫金通過對于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來研究作品與其所處歷史時空的關系。從這個角度看,時空體有助于探索文學文本與作家所處時代之間復雜而間接的勾連。?空間上的時間復調與時間上的空間復調,雙重的復調構成了歷時與共時的交織,而這樣復雜的復調時空體造成了時空的錯位和身份認同的困境。在同一個空間內,因為多種的因素所形成了不同的身份認同,這并不是因為年齡的代溝而成的,而是人為給予的身份與自然認同的區(qū)別,隨著人與時空之間的互動,人的身份并非是固定的,認同會隨著時空觀的轉變而轉變。但是同一個空間中的人卻存在不同的身份認同,擁有草原記憶的人在不同于草原環(huán)境的工業(yè)化社會產生了自我身份識別的困惑。由于精神空虛而被迫進行社會身份建構的人便失去了草原的記憶,反而進入了另一個與自然認同相對立的層級并與之產生二元的對抗。在這個時空體中作者描述的是一個充滿現(xiàn)實的卻又映射歷史的時空體。
然而,存在于未來與科幻的時空體,即遙遠的林海星卻是一個單獨的時空體。它是獨立于小說中其他時空體的一個擁有完美意志的時空體。“在地球上很難或者幾乎不可能擺脫斗爭。但待在遙遠的宇宙空間,情況就不同了,從我們這里看地球,它頂多就像個汽車輪子而已。” ?宇宙中的均等號-公約號計劃以對立雙方的合作為開端,開啟了宇宙的探索計劃,但是這一合作被嚴格的限定,所有的計劃和過程都是嚴格的對半參與,這樣的合作更像是形式上的,而并非是在精神的共通和情感上的接受。所以,在宇宙空間中,出現(xiàn)了一個完美的共和世界“林海星球”,那里有著絕美的自然環(huán)境,頗具匠心的建筑。那里科技發(fā)達但是卻沒有武器和戰(zhàn)爭,那里充滿了異質性的人群卻滿懷善意。從人類學角度來看林海星人是類人生物,與地球上的人類類似,可是他們黝黑的皮膚、天藍色的頭發(fā)、雪青色和綠色的頭發(fā)以及白絨絨的睫毛都難以符合地球上人類學范式下的人種劃分標準,正是這種與人類絕對科學化、二分化截然不同的外星系文明彰顯了世界的多元與融合。更重要的是林海星人已經能夠開采太陽能,甚至掌握了控制氣候的技術。這樣夢幻般的生存環(huán)境簡直就是人類的夢想之地,是一個存在于人類幻想中的時空。
每一種時空體都是作者想要表達的情緒或者是聲音,前者的對立矛盾與后者的和平融合結合在一起,又構成了一個現(xiàn)實與幻想之間對立的超大時空體,構成了整個小說的主題,即對立與融合。
四、結語
《一日長于百年》不止從時間跨度上以一日現(xiàn)實時間折射百年時空變化,還從地理上以草原空間延展到宇宙空間,其時間和空間跨度十分宏大。且時空層次十分分明,以歷時與共時的交織譜寫了復雜和多樣的人類社會,最后以兩個超大時空體的對立,表現(xiàn)現(xiàn)實的掙扎與未來的希冀。艾特瑪托夫認為微觀的個人時空體也是全人類精神財富的組成部分,因此,林海星上的多元融合是對未來生活和社會的美好暢想,復調時空體敘述中的矛盾與對立也是對現(xiàn)實生活和社會的警示。畢竟,人類未來的唯一出路不是“置換歷史”而是“歷史倒置” ?。
注釋:
①向潔茹:《作為方法的地方書寫——艾特瑪托夫后期小說中的地方書寫與民族身份認同》,《鄱陽湖學刊》2018年第3期,第102-107+128頁。
②?劉玉婷:《淺析〈一日長于百年〉中小站的時空功能》,《新紀實》2021年第6期,第44-46頁。
③(俄)巴赫金著,白春仁譯:《長篇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歷史詩學概述》,見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
269頁。
④?宋旸:《社會語言學視域中的時空體研究綜述》,《外語學刊》2019年第4期,第20-25頁。
⑤(蘇)欽基茲·艾特瑪托夫著,張會森、宗玉才、王育森譯:《一日長于百年》,新華出版社1982年版,第4頁。
⑥(日)杉山正明著,黃美蓉譯:《游牧民的世界史》,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9年版,第36頁。
⑦(蘇)欽基茲·艾特瑪托夫著,張會森、宗玉才、王育森譯:《一日長于百年》,新華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頁。
⑧鄭季文:《近三十年我國時空體理論研究概述》,《語言與符號》2021年第1期,第70-77頁。
⑨謝龍新:《巴赫金之后:“時空體”理論的時空之旅和場域拓展》,《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8期,第172-179頁。
⑩(俄)巴赫金著,白春仁譯:《長篇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歷史詩學概述》,見錢中文主編:《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頁。
?(蘇)欽基茲·艾特瑪托夫著,張會森、宗玉才、王育森譯:《一日長于百年》,新華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頁。
作者簡介:
任佳聞,女,漢族,四川南充人,西安外國語大學,俄語語言文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區(qū)域與國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