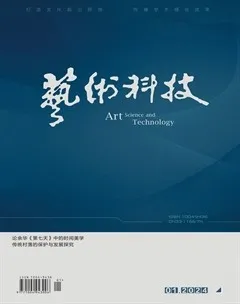“非遺”視角下浚縣泥咕咕的現代保護及發展路徑研究
摘要:目的:通過研究浚縣泥咕咕的現代保護及傳承,發現其生存困境及發展趨勢,為泥咕咕的現代發展提供路徑,拓展其市場空間,提供借鑒性意義,使泥咕咕等民間美術在保留自身傳統文化特征的同時更好地適應現代化發展。方法:從“非遺”的視角出發,結合文獻研究法及田野調查法探究泥咕咕的文化內涵及傳承現狀,最終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傳承策略。結果:增加教育體系的政策納入,挖掘深層次文化內涵,拓展“非遺”傳播渠道,摒棄同質化、泛眾化,同時針對形態結構及需求進行創新體量轉化。結論:現代社會中應充分發揮各方效應,響應國家號召,多渠道、全方位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泥咕咕等文化遺產,采取適當的措施推動泥咕咕在保留傳統文化特點的同時更好地適應現代化發展。
關鍵詞:泥咕咕;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J31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1-00-03
0 引言
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最初于2001年開始頻繁進入人們的視野,同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強調世界各國各民族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內的全部文化遺產對維護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意義。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總則第二條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1]。
1 泥咕咕的文化內涵
正如張道一先生所說,“民間的藝術是一種本質文化”[2]。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只有充分發揮自身文化的優良特質,才能在全球化背景下抵抗外來文化入侵,發揮自身的民族個性。泥咕咕源于群眾又與群眾緊密相連,為浚縣楊玘屯村世代相傳并于村落集中生產的傳統民俗工藝品,最早為戰爭傳遞信號所用。相傳,隋朝末年農民起義軍首領李密曾帶領將士在黎陽(今鶴壁市浚縣)與隋軍會戰并駐軍在大伾山東麓一帶,雙方戰斗持久,傷亡慘重,軍中有擅泥塑技藝的將士閑暇時間便利用當地特產的黃膠泥捏制出許多騎馬人造型,以悼念那些戰爭中的已故軍士。由于身上的孔洞吹之能發出響亮的音樂,便于戰時傳遞信號,因此很快在當地流傳開來,并一直延續至今。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3]人們認為秦的先祖為女修吞食玄鳥的卵而誕生。這與商人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說法一致,都描述是吞食鳥卵而生出先祖。可見,中華民族自古就有鳥崇拜現象,并將其與生殖繁衍相掛鉤。泥咕咕的鳥形象以麻雀為創作原型,這是因為我國南方民俗中曾將其視為“送子神鳥”。在鳥類中,麻雀產卵較多,生命力頑強,給人們留下多產的印象[4]。古時,人們觀察鳥飛過的地方往往會有種子落下,有的生長成為谷物,為人們帶來生存繁衍的糧食資源。因此,人們將鳥兒視為神明的化身、生育的象征、生命延續的希望。鳥在古代與男性生殖器官“屌”發音相似,民間文化中也多將鳥視為男娃的化身,即男性的口頭隱喻象征。在浚縣當地的大伾山廟會中,鳥形象的泥咕咕多受到婦女孩童的追捧,婦女逛廟都會用紅繩將咕咕鳥拴在腰間帶回家,認為是拴住了男娃娃,孩童們向大人討要咕咕鳥也會大聲唱道:“給俺個咕咕雞,讓你生子又生孫兒。”[5]來往的婦女們都會毫不吝嗇地抓起泥咕咕分給孩童,歡快熱鬧,討個吉祥寓意,正是這些吉祥文化內涵使泥咕咕能夠流傳千年而不斷發展。
2 浚縣泥咕咕的現狀
2.1 “非遺”語境下的層級化現象
“非遺”話語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民俗藝術的文化生態環境,等級制度的劃分潛移默化地對泥咕咕進行文化價值的重新定義,進而影響其藝術形態的發展趨勢。浚縣泥咕咕于2006年5月20日經國務院批準被列入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根據傳承人三級認定制度劃分出國家級、省級、市級等官方認定傳承人,便于細化分級管理與技藝保護傳承,分級制度的認定使泥咕咕的管理保護變得更加科學全面,層級化的標簽頭銜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構了泥咕咕的文化內涵及藝術價值,影響其藝術風格的分化。
售賣泥咕咕時,有明顯標簽注明國家級大師捏制的產品會被單獨陳列擺放,比沒有“非遺”名號的泥咕咕價格高幾倍,而沒有“非遺”傳承人名號加持的泥咕咕根據體量工藝的不同則是售價幾十之間,價格差異較大,這使得浚縣大多數從事泥咕咕制作的手藝人失去話語權,其藝術作品的價值不被認可,禁錮了創新精神的發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泥咕咕的審美傾向,“非遺”官方話語的介入在實行方面產生了話語誤讀,導致浚縣當地泥咕咕的藝術創作風格形成了以國家級傳承人為代表的幾大個人風格流派,對購買者來說,會影響其對泥咕咕文化價值的判斷。
2.2 市場經濟下的文化重構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民俗文化是在活態流變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在適應外部環境的同時不斷創新,在現代將其中有用的內容有機置入固有文化中,即所謂的文化重構[6]。泥咕咕在現代“非遺”語境下的文化內涵被延伸與重構,在民俗內涵的基礎上更加看重其背后的區域文化符號化表征,這也是地方品牌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文化遺產,早期核心價值是對自然的希冀和樸素的生命觀念,具有鮮明的精神功利性,是原始的圖騰崇拜與祭祀的媒介工具,蘊含吉祥文化寓意。隨著其生存環境的變化,在現代社會,泥咕咕已失去其原始的精神功利性,成為一種美學載體與文化符號。在市場經濟引導下,泥咕咕的民俗文化內涵逐漸向商品性轉換,經濟效益作為外在主要推動力,使得泥咕咕在創作內容和價值觀上以現代大眾欣賞功能為主,藝術創作在造型、紋飾、題材上呈現出同質化、泛眾化現象,缺乏地域民俗文化特點,趨向于工業化產品。手工藝者竭盡全力挖掘泥咕咕的市場價值,逐漸將其發展推向商品化的一端。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質是由特定地理、歷史民俗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形態,與大眾文化審美存在較大不同。因此,泥咕咕的商業化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非遺”保護的初衷。
2.3 手工藝者身份、生產方式的轉變
隨著國家政策的出臺,“非遺”類文化產品開始受到當地政府的保護,泥咕咕的主要生產地楊玘屯村的村落面貌較以往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如今大多數村民投入泥咕咕的生產制作當中,形成了良好的民俗藝術生態空間。浚縣當地以泥咕咕為主題的陳列館、博物館、民俗商業街紛紛投入建設,藝人的創作實踐從家庭生活空間中劃分出來,制作工坊相繼成立,傳承人則成立了個人工作室。浚縣政府領頭建設規范化的培訓基地,為泥咕咕的傳承提供中介平臺輸送人才,促使傳承人文化素養得到提高,手工藝者也被授予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頭銜,完成了身份的轉換認定。
在生產方式層面,現在的泥咕咕制作與傳統制作方式相比也有較大的變化。根據當地手藝人敘述,早期泥咕咕為藝人們純手工捏制,一件作品所需的黏土用量根據藝人們的感覺稱量,沒有太多講究,因此早期的泥咕咕相同的題材造型,形狀大小不盡相同,具有較強的藝人個性色彩。相較于現代精美的質感,早期泥咕咕沒有入窯燒制這一步驟,受浚縣當地氣候影響潮濕變色,不利于長期保存。隨著泥咕咕制作技術的完善發展,現代增加了窯燒這一步驟,使其外形更加精致細密,利于保存。生產工具也由過去的手工和泥轉變成機器和泥,更加方便快捷;制作顏料也由早期的蛋清調和壓料換成了丙烯等專業的繪畫顏料,色彩更加豐富艷麗,富有活力;繪制工具也變得更加多樣化。此外,豐富的社會信息拓展了泥咕咕的創作題材,現代審美喜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泥咕咕的藝術形態,變得更加符合現代人的審美需求,這也是“非遺”活態發展的特點。
3 浚縣泥咕咕現代發展路徑
3.1 深挖文化內涵,傳播“非遺”價值,摒棄同質泛眾化
在物質生產資料異常豐富的今天,快餐式的娛樂產品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究其根本原因,是標新立異的現代化產品內在價值及文化內涵的缺失,使得產品工業化嚴重。因此,要充分利用“非遺”話語的影響力,結合現代信息化科技與平臺,推動泥咕咕的文化傳播,普及泥咕咕的文化內涵與價值,緊抓泥咕咕吉祥文化主題內涵宣傳造勢,迎合現代人們追求美好生活寓意的祈盼。如今,“90后”等新一代青年群體逐漸成為文化傳承的主力軍,浚縣泥咕咕的宣傳要迎合市場特點,明確青年群體的消費及審美訴求,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以“非遺”“傳統文化”“吉祥”等熱點詞抓住用戶眼球,通過微信公眾號、抖音、小紅書等年輕人熱衷的媒體平臺進行“種草推薦”,制造“網紅效應”,增加其被看見、被了解的機會。
浚縣泥咕咕等民俗工藝品,應加強與工業化產品的區分,警惕過度“商品化”,充分發揮其民俗工藝品特性,摒棄藝術審美同質化、泛眾化,注重原生態生存環境的打造與維護,在創新的同時保留其本質藝術特征。同時,以“非遺”浚縣泥咕咕為中心,開展一系列宣傳。縱觀全國泥玩類工藝品,其在造型上有許多相似之處,與同類型的鳳翔泥塑、惠山泥人、天津泥人張等相比,泥咕咕的知名度較低,市場份額占比少。例如,許多人無法區分浚縣泥咕咕與其相鄰城市淮陽的泥泥狗。由此,只有深入挖掘這類工藝品背后的歷史和文化內涵,才能更好地區分彼此,從而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
3.2 發揮政府職能效應,增加教育體系納入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核心主體是人,人是傳播的載體,在不同年齡群體中,青少年是至關重要的一環。2003年10月1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明確提出,“為了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社會中得到確認、尊重和弘揚,各締約國應制訂向公眾,尤其是向青少年進行宣傳和傳播信息的教育計劃”[7]。這充分表明了青少年群體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中的重要性。在制度保障上,國外相關措施可供借鑒,如韓國教育部為了保證國家文化傳承后繼有人,在學生獎學金制度上特地設立“傳授獎學生”。《文化財保護法實施規則》要求,“傳授獎學生”必須是“從重要無形文化財的持有者或持有團體那里接受了6個月以上的傳授教育,且在該重要無形文化財的技能、技藝方面具有相當素質的人員”[8]。因此,浚縣應發揮政府職能效應,將泥咕咕工藝納入美術教育體系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學習納入評獎評優考核標準中,與青少年教育相掛鉤,培養青年群體的文化傳承使命感。在美術教學中融入“非遺”元素,或是在學校課余實踐舉辦泥咕咕主題元素設計比賽、浚縣泥咕咕知識競賽等,能夠有效激發學生的“非遺”學習興趣,普及“非遺”知識,喚起青少年的文化自信,為泥咕咕等“非遺”工藝品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拓寬傳播渠道。
3.3 創新體量改制與功能轉化,拓寬應用渠道
泥咕咕最初的功能以兒童叫吹益智為主,尺寸較小,通常為4至5厘米,最大的也不超過20厘米。早期手工藝人都是成筐地做,價格也較為低廉,目標受眾以兒童婦女為主,功能僅限于吹奏,流通平臺局限于一年一度的浚縣廟會,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范圍較為有限。
因此,在推廣手段上應更為多元化,突破“非遺”自身發展的局限性,從設計的角度入手,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取泥咕咕的造型、圖案、色彩等進行視覺推廣與包裝設計,將傳統手工造物技術融入市場經濟中,針對不同群體進行適當的體量改制,如民俗學者、藝術家等以收藏需要為主的20厘米以上的大體量泥咕咕設計,商業送禮則加大對包裝設計的研發力度,推出禮品裝等附加產品。
此外,應進行功能轉化,拓展市場應用范圍,突破單一民俗紀念品功能,促進泥咕咕文創產品的創新研發設計,推動車輛擺件、玩偶抱枕等的文創研發。拓寬私人定制、外購渠道、文藝商演活動、網絡平臺等銷售渠道,促進浚縣泥咕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代傳承及對外傳播。創新營銷方式,發揮民俗工藝品優勢,增強游客對泥咕咕的體驗互動感,以“非遺”工坊為單位提供泥咕咕半成品,挑選特定繪制環節將其提供給購買者,手工藝者提供一定的專業指導,在增強趣味感的同時促進泥咕咕的文化傳播,使游客更容易接受。
4 結語
進入新時期,市場經濟主導下民間藝人及泥咕咕的生存環境受到挑戰,因此,須創新傳承泥咕咕等文化遺存,發揮各方效應,多渠道、全方位地進行創造性轉化,采取適當措施推動泥咕咕在保留傳統文化特點的同時更好地適應現代化發展,使其發揮文化價值,找到更好的發展路徑。
參考文獻:
[1] 趙玉婷,劉瑩.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動畫表現實踐與研究:以國家級保護項目“蔣塘馬燈”(下轉第頁)
(上接第頁)為例[J].視聽,2018(1):40-41.
[2] 王威.民間美術的價值和作用[J].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8,2(28):49-50.
[3] 欒國榮.河南省浚縣泥咕咕的起源、發展與文化內蘊[J].文學藝術周刊,2022(6):93-96.
[4] 倪寶誠,倪銘.浚縣“泥咕咕”與鳥信仰[J].尋根,2008(2):74-80.
[5] 張道一.女紅文化(續)[J].浙江工藝美術,2009,35
(3):1-4.
[6] 陳勝容.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再生視角的唐山皮影戲傳承與創新[J].產業與科技論壇,2014,13(19):72-74.
[7] 王箐.網絡非遺小說初論[J].名作欣賞,2022(11):177-181.
[8] 張世均.韓國民族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0(2):22-25.
作者簡介:胡鑫(1997—),女,河南洛陽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美術史論、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