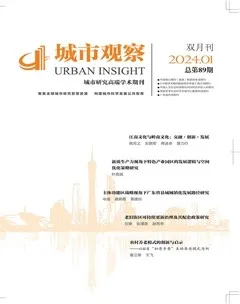農村養老模式的創新與啟示
謝立黎 王飛



摘要:隨著農村老齡化程度加劇,探索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能滿足我國農村老年人養老需求的創新性養老模式,成為發展農村養老服務的重要任務。H省創新的“婦老鄉親”互助養老模式,利用外部專業力量為本土組織和人員提供管理和服務培訓,同時吸引本土和外部的多方力量加入,為農村養老可持續發展培育“造血”能力和組織能力,實現服務對象的生活質量改善和服務主體的共同成長。這一特色養老服務模式對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發展我國農村養老具有啟示意義:協同發展農村養老服務,需要從資金的可持續性,本土人力資源的開發,基層自治組織的培育,社會力量的介入和服務的精準化、差異化及規范化等多方面共同發力。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互助養老;農村養老;養老模式;鄉村振興
【中圖分類號】 F323.89? ?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4.01.012
導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推動實現全體老年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農村65歲及以上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17.72%,比城鎮高出6.61個百分點。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流出,農村老齡化程度不斷加劇、農村家庭日趨小型化和空巢化、農村老年人的養老與照料資源缺口不斷擴大。而農村老年人在生活照料、醫療健康、精神慰藉與權益保障等方面的需求正在不斷增長,僅依靠傳統的家庭養老已無法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這無疑對我國農村養老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如何尋求和發展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能滿足我國農村老年人養老需求的創新性養老模式,成為發展農村養老服務的重要任務。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國內各地對創新農村養老模式進行了積極探索,其中農村互助養老是近年來我國在積極探索解決農村養老問題過程中提出的一種新模式,也是我國鄉村治理轉型過程中的一項重要成果[1]。本研究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通過典型案例分析,介紹以H省“婦老鄉親”模式為例的互助養老方式,剖析其特有優勢和模式特點,以期為我國農村養老服務發展提供參考。
一、農村互助養老文獻綜述
(一)互助養老的內涵與理論基礎
互助養老是基于交換和互惠、自助和互助的理念,以自我管理和互助服務為核心,把老年人力資源有序組織動員起來作為主要服務力量,為老年人提供互助型的社會養老服務[2-3]。它是介于純社會化養老和居家養老之間的一種新型養老形式,既有社會化養老的特征,又符合傳統的家庭養老習俗[4-5]。
從互助養老的內涵可以看出,基于互助的交換以及自助的賦能是其理論基礎。從社會交換理論的角度來看,人類的一切行為都受到某種能夠帶來獎勵和報酬的交換活動的支配。交換的形式多樣,并不一定是金錢和物質,也可以是勞務、時間,以及奉獻與尊重的精神[6]。互助養老即是在互惠互利和社會交換基礎上產生的同代或代際之間的養老資源、服務的交換[7]。從賦能理論的角度來看,賦權增能是指增強個人、家庭、社區、組織在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權利和能力,從而達到改善目前狀況的目的。互助養老作為老年人基于內在的情感、交往等需求而生成的基層組織方式,是老年人實現自我增能與發展的重要途徑[8]。互助養老能夠有效整合各類養老資源,使老年人群的智力資源、體力資源及社會資源得到充分利用,使其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得到充分實現,有利于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二)農村互助養老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1.中國自古以來悠久的互助文化傳統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互助的文化傳統。在傳統社會,受傳統儒家孝道倫理規范的影響,宗族互助一直占主導地位。國家依靠宗法倫理和國家支持下的由小及大的基層宗鄉互助組織進行基層治理[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非血緣個體之間的聯合在中國農村也廣泛存在[10],以“五保”制度為代表的集體互助養老,就是以農村集體組織為主體,以集體單位自上而下的統一安排為主要手段,成為集體成員之間進行的一種合作型互助。因此,農村互助養老發端于我國的儒家文化,在人倫關系層面按照“差序格局”的方式由內而外、由近及遠擴展。農村互助養老也大致經歷了從宗族和個體結社到集體互助、從民間自發到組織化制度化發展的過程[11]。
2.農村養老發展的現實困境與需求
互助型養老的集體化、低成本屬性符合中國家庭規模小型化、老年人需要養老保障的現實國情[12]。當前農村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不健全、老人對機構養老的接受度也較低[13],特別是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在人力、資源、資金、環境等方面存在短板,導致專業化、市場化的社會養老服務發展缺乏內生動力[14]。因此,低水平、保基本、有重點的農村互助養老成為農村發展社會養老的重要方式。
3.農村互助養老的戰略定位與未來發展
在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互助養老成為新時期農村養老的重要選擇和創新途徑[15]。從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視角來看,作為一種與中國農村傳統鄉土本色和現代轉型相協調、與中國現實國情相適應且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養老方式,互助養老可以整合社區內外的各種養老資源和設施,有利于推動農村養老人享有基本養老服務[16]。從鄉村振興戰略視角來看,互助養老代表著新時期老齡社會治理的實踐探索和可行模式,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廣“千萬工程”經驗①、提高鄉村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同時,互助養老所帶動形成的互助文化和互助社會,可以驅動文化發展、促進互助經濟和產業發展,構建鄉村和諧共同體。
(三)農村互助養老的發展現狀
當前我國在不同地區已經形成多種互助養老模式,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集中供養式的互助養老。其中,典型代表有河北肥鄉的“互助幸福院”模式,具有“政府主導、集體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務”的特征。該模式對政府的依賴性較強,自我管理水平和能力有限。有研究通過對山東省的“農村幸福院”的調查發現,許多“農村幸福院”的生活設施普遍閑置,村委會和社區作為責任主體無法提供專業化的養老服務[17]。典型代表還有蘇北地區的“老年人關愛之家”模式,最初由村老年人協會和社區精英發起,依靠縣、鎮兩級老齡辦予以支持和幫扶,利用村內閑置房屋、校舍建設“老年人關愛之家”,同樣具有“集體建院、集中居住、互助服務”的特征。該模式的主要目的是解決空巢老人的養老問題[18],但互助主體主要是低齡老人與健康老人,缺乏多元主體的參與;互助內容也是較為簡單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缺乏專業化的培訓。此外,吉林省的“農村居家養老服務大院”模式也是這一類的典型代表。該模式通過整合農村閑置房屋,為老人提供日間照料室和活動室等活動設施,主要依靠村里的黨員干部、老年協會和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務,并采取以下兩種服務方式:一是“服務送上門”方式,主要針對高齡、失能或半失能老人;二是“老人走出門”方式,鼓勵身體健康的老人在養老服務大院里接受日間照料、餐飲、健康保健等服務[19]。另一類是社區居家式的互助養老。典型代表有浙江安吉縣依托農村老年協會建立的“銀齡互助服務社”模式,主要通過政府、村集體、農業合作社和社會組織等出資,建立并運營養老服務中心,為老年人提供日間照料和上門照料等服務[20],但其不足是缺乏專業的管理和服務人員,互助內容以簡單的文化娛樂、老年餐桌活動為主。同時,這一模式更適合在經濟較為發達、集體經濟實力較強的地區開展,而在欠發達的農村地區開展較為困難。此外,陜西榆林地區的“農村鄰里互助養老服務小組”也屬于這一類創新模式,由村“兩委”領導,村級老年協會組織實施,主要由就近、熟悉的鄰里組成志愿者,經過崗前培訓并簽訂聘用合同后為受助者提供服務。該模式屬于居家互助養老,由志愿者定期上門為受助者提供生活照料和看護照料等[21],其資金來源主要還是依靠政府補助,存在資金困難、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而且志愿者的來源較為單一,服務內容較為有限,服務質量也難以保證、缺乏專業的第三方評估機制。然而,養老服務采用“一刀切”式地交給外來社會組織也沒有取得好的效果[22],因此,只有將內生和外在力量有機地結合才能優化農村互助養老服務。
通過梳理前述理論和文獻發現,互助型社會養老的核心不只是簡單的硬件設施建設或者老年人之間的相互幫助,還是農村非正式社會資源的持續生效和重新配置。總體而言,目前已有的農村互助養老模式主要存在以下問題:第一,資金運營方面多數依靠政府撥款,資金來源不穩定,后續投入乏力,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不足。第二,缺乏專業的護理人員和管理人員,服務水平較低。第三,沒有充分吸引本土力量參與到互助隊伍中。農村大量的留守低齡老人、婦女等,有條件成為互助養老服務的主要力量,但農村養老服務卻沒有對他們進行人力資源開發和專業技能培訓。第四,忽視了社會組織的力量,本地的村“兩委”或老年協會與外部的社會組織沒有有效結合。所以,農村互助養老發展需要內生和外在力量的共同推動,一方面,調動農村本土組織和老年人等內生資源和力量,將農村老年人間零散的互助行為有效組織起來;另一方面,通過政府推動、企業經營、專業社會組織賦能、樞紐型社會組織管理等方式協助內生組織正式化、規范化發展。H省“婦老鄉親”互助養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上述特征,因此本文對該模式的運作方式和特點進行分析,以期為發展農村互助養老提供經驗借鑒。
二、H省“婦老鄉親”
互助養老模式的運作與特點
H省“婦老鄉親”互助養老模式是在當地相關政府部門和村“兩委”的支持下,由公益基金會提供資金支持與專業指導,專業社工機構負責項目運行,通過孵化培育農村婦女組織、老人組織,解決農村老年人養老難的問題(圖1)。其中,農村婦女組織以農村留守婦女為主體,農村老人組織主要以老黨員、退休干部、教師等農村精英為主體。兩類組織是由公益基金會資助、社會工作組織具體孵化管理的民間社團。孵化執行機構根據試點村實際情況,制定具體實施計劃,然后指導農村婦女組織、農村老人組織開展具體事務。公益基金會將派駐或指定督導員,對項目執行情況進行日常監督和管理,通過與地方老齡、衛生、農業等部門協作,調動農村各方面參與的積極性,配合村“兩委”開展老齡工作,以共同改善農村老年人物質和精神生活面貌。
(一)運作方式
1.資金來源
“婦老鄉親”模式主要由公益基金會資助,招募專業的項目團隊入駐農村,結合村莊自身條件,利用當地資源開展經營活動進行創收。例如,有項目試點通過愛心人士和單位的捐贈種植板栗、對當地特色的酸棗進行深加工、因地制宜栽培蓮藕實現創收,建立手工制作社區工場、制作手工藝品進行義賣,推動果園規模化經營、發展農家樂,為留守老人提供參與經濟勞動的機會,等等。此外,社會捐助也是該模式的資金來源之一,即通過向社會募集資金,拓寬項目的資金渠道。
2.運營管理
項目的發起首先是由公益基金會聯合各級相關政府部門篩選合適的試點村,在確定試點村后,由專業機構走訪利益相關方,聯系當地政府有關部門、村“兩委”、村民和本村的潛在人脈資源,盡可能獲得政策、資金和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同時,項目通過實地調研摸底等方式,科學化評估各試點老年群體的養老服務需求與現實養老問題,以精準對接需求,為不同項目點定制切合村莊實際的老年服務方案。
項目進入執行環節后,將依托專業的孵化機構籌建農村老人組織、婦女組織,進而開展活動。組織架構主要由農村有威信、有組織能力、正直負責、熱心村務的老年人、婦女等成員組成,并由組織成員和村民共同制定相關章程和管理制度等。農村老人組織、婦女組織在開展活動時需要依靠志愿者提供具體服務,志愿者的招募對象主要包括村志愿者(農村青年、婦女、有服務能力的低齡老人等)和離巢青年志愿者(在外求學、工作或創業的本村籍年輕人)。在服務團隊確立后,專業機構將對農村老人組織、婦女組織核心成員進行組織管理技能培訓,對志愿者進行健康護理、家庭照護知識等服務技能培訓。
3.服務內容
在公益基金會的資金支持及社工機構的組織孵化之下,各試點的農村社會組織探索開展了內容豐富的養老服務。一是生活照料服務,由組織成員根據“一對一”或“一對多”的方式定期上門為老年人提供服務。如有的項目點采取“農村養老服務小組”,定期上門給老人開展打掃衛生、被褥洗換等家政服務和陪聊、心理疏導等精神慰藉服務。二是文娛活動服務,主要是結合當地村莊的傳統習俗開展社區老年趣味運動會、老年人活動等。個別項目點還舉辦餃子宴、春節聯歡晚會、乒乓球比賽、廣場舞大賽等活動。三是健康護理服務,主要包括組織志愿者提供健康服務、鏈接外部醫療資源以及村醫加入老年組織或婦女組織三種形式。
4.評估與監督
項目孵化執行機構和農村老人組織、婦女組織每月定期召開例會,討論項目執行中遇到的問題,探索應對策略,總結項目經驗和教訓。孵化機構也會派駐或指定督導員,對項目執行情況進行日常監督和管理,同時在項目點設立評議反饋平臺,及時收集村莊目標老年人群對于養老服務的評價和改進意見。每個項目點會有兩次評估,在項目開展18個月時,公益基金會對項目實施情況開展中期評估,了解項目進展情況和初步效果,及時發現問題并完善工作,或根據實際情況改進工作計劃;在項目開展36個月時進行終期評估,重點評估項目點的農村老人組織、婦女組織是否具備獨立生存能力,是否達到獨立運轉的標準,是否需要停止資助關系或延長項目期限,盡可能保證項目的持續運轉。
(二)模式特點
1.本土性:發展本土特色的養老模式
首先,該模式立足地區的差異性,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產業模式。例如,有項目試點組織愛心人士和單位捐贈并栽種16000多棵板栗樹苗,動員村中健康的低齡老人進行日常管理和養護,作物收獲后由基金會聯系板栗生產加工公司全部包銷,以解決作物出售的問題,為本地的互助養老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其次,該模式注重提供差異化的養老服務,精準對接服務需求。每個項目點在開展服務前,會通過實地走訪全方位了解當地老年人的養老需求,特別是重點關注特殊老年群體。以醫療服務為例,“婦老鄉親”項目定期開展村醫拜訪和義診服務,村醫會加入老人組織或婦女組織,定期帶領志愿者拜訪臥床、身體不便的老年人,為其進行常規醫療檢查和服務,及時發現問題和提供幫助。最后,該模式注重結合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發展不同類型的組織和成員。“婦老鄉親”項目可分為以老年組織為主和以婦女組織為主的兩種組織方式,利用不同地區的人脈資源、志愿者資源,形成“婦老鄉親+外出青年反哺農村養老”“婦老鄉親+村醫” “婦老鄉親+‘時間銀行”等模式。
2.賦能性:為本土村民和組織賦能
“婦老鄉親”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發揮本地村民的能動性,為農村留守婦女和老人賦能。項目依靠公益基金會進行模式輸出和資金支持,借助社工機構的專業能力,培育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凝聚農村老人和婦女的內生力量,建設一批本土的養老服務隊伍。專業社工機構主要起到賦權增能的作用,老人和婦女組織借助專業機構的“外力”推動激活主體動能。留守婦女和老人作為參與主體,在接受專業社工機構的組織管理技能和專業服務技能培訓后,成為養老服務的參與者和助人者,在提供養老服務的同時實現自我價值。在這一模式運作中,專業社工機構指導幫助項目點搭建完善本土的自治組織框架,制定相關的組織管理制度,培育其組織建設和自我管理能力,也提高了農村基層社區的治理能力。
3.可持續性:注重模式的可持續發展
該模式結合項目點的資源現狀和特點,不僅僅依靠外來資源“輸血”,而且依靠本土的產業資源、人力資源和風俗習慣,發展特色的產業養老和多元化的志愿團隊,打造本土化的養老服務項目,因地制宜開展本土的生產經營活動,形成“造血”能力,實現項目模式的可持續發展。
4.多元性:吸引多元力量參與其中
“婦老鄉親”模式整合了多方主體力量,包括當地政府部門、村“兩委”、公益基金會、專業社工機構、老人組織、婦女組織、志愿者等,鏈接多方資源參與其中,形成了“以老人組織和婦女組織為主、各方參與主體協同發展”的模式。在這一模式下,不同主體發揮優勢和作用,政府部門和村“兩委”起到支持、指導和監督作用;公益基金會起到模式輸出和資金支持的作用;專業社工機構起到組織孵化、人員培訓、項目督導和評估的作用;老人組織和婦女組織起到主導作用,以老年人的需求為導向,整合各方資源,提供養老服務;志愿者是養老服務的直接提供者,其團隊群體構成多元化,既有本村留守婦女、低齡老人、青年,也有在外求學和工作的年輕人,還有鄉村醫生、退休教師等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員。這一模式不是局限于某一個群體的參與,如僅強調低齡健康老年人之間互助養老,而是挖掘各種潛在的人力資源,最大可能地帶動本土有能力的人都參與到當地的養老服務中,最終形成多元供給、互助協作的運行機制。
5.共贏性:實現服務對象和服務主體的共同成長
本研究對試點村和非試點村進行了實地問卷調查和訪談,共收集907份調查數據,通過對服務對象和服務主體的評估發現,“婦老鄉親”模式實現了服務對象和服務主體的共同成長。
一方面,“婦老鄉親”模式以村民養老需求為導向,結合當地特色與實際情況開展服務活動,改善了服務對象在生活起居照料、家務勞動、就餐等方面的生活質量。這一模式為服務對象提供了切實所需的養老服務,包括探望、送餐、家務勞動和生活照料,以及文娛活動、健康講座、義診和免費體檢等。此外,許多經濟狀況較差的老年人通過參與當地的特色創收項目,拓寬了農村老年人群的收入渠道,增加了農村貧困老年人的經濟收入。通過對服務對象的生活質量改善狀況調查發現,在孤獨感方面,有22.71%的服務對象因為接受探訪等明顯改善了孤獨感,還有66.44%的服務對象認為孤獨感稍有改善;在生活照料問題和家務勞動問題方面,約17%的服務對象的生活照料和家務勞動問題因為受到幫助而明顯改善;在就餐質量方面,63.95%的服務對象表示當前就餐質量有所改善(圖2)。
另一方面,服務主體在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過程中也實現了個人成長。從服務內容來看,組織成員提供的服務非常豐富,有72.08%的成員參與過組織文娛活動,67.53%幫助做家務(打掃衛生、洗衣、做飯、幫忙購買日用品等),63.64%為服務對象送過餐。此外,服務內容還有提供探望、聊天(62.99%),開展健康講座(44.16%),進行義診、免費體檢(29.22%)和參與發展村經濟的活動(15.58%)等(圖3)。組織成員通過專業社工機構的幫助,接受了大量的技能培訓,學習到許多實用的知識和技能。組織成員接受的培訓排在前五位的分別為:骨干互訪交流(84.25%)、文娛等活動培訓(72.6%)、尊老孝老等環境改善培訓(64.38%)、鄰里互助等志愿者活動培訓(63.01%)、家庭照護技能培訓(52.05%)(圖4)。
該模式還進一步提高了鄉村基層治理能力,有助于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夯實鄉村振興的基層基礎。調查顯示,73.37%的組織成員認為本村(居)是否發展得好自己負有責任,90.97%的組織成員愿意參與村(居)的治理工作,96.13%的組織成員愿意幫助遇到困難的老人(圖5)。
三、H省“婦老鄉親”
互助養老模式推廣的條件
任何養老模式都有其限制和適用范圍。區域差異的存在決定了農村養老模式應有所側重,其構建與實施必須遵循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規律,權衡各種制約因素的影響[23]。“婦老鄉親”模式的推廣和復制有其制約條件,如硬件和軟件等方面的設施,對項目最終能否持續發展至關重要。這也啟示我們,任何養老模式的發展必須因地制宜,不可盲目照搬。
(一)資金的可持續性
在我國,農村社會化養老服務主要依賴政府買單,而政府對于城鎮養老服務的財政投入高于農村[24]。農村養老服務的發展僅僅依靠政府的財政支持不是長遠之計,許多農村開辦的養老機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對政府過度依賴,導致其不能長效運轉。因此,農村養老服務的發展需要拓寬資金來源。“婦老鄉親”模式的運轉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吸納多方力量,前期由公益基金會投資發起項目,后期開發本土產業,吸納社會捐贈等,為模式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培育自我“造血”能力,畢竟公益基金會的資金支持有限,充分利用農村資源開展本土經營活動,提高自身的創收能力才是模式長遠發展的根本保障。“婦老鄉親”模式的推廣需要有可持續運營的資金支持,在前期需要有較多的資金投入,后期需要依靠自身創收維持模式運轉。這也成為“婦老鄉親”模式在更大范圍內推廣的最大制約因素,特別是在許多農村地區,沒有公益基金會為其養老服務的開展提供相應的資金支持,加上集體經濟發展薄弱,無力為其提供資金保障,而且老年人收入水平較低,無力購買相應的養老服務。因此,“婦老鄉親”模式的推廣仍然需要借助政府和社會資本力量的大力支持,同時需要增強農村創收能力,如通過增加農業經營收入、促進農村土地流轉、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和開發本土特色產業等,提升老年人和村集體的收入水平,進而提高購買養老服務的能力。
(二)基礎設施的完善
由于政府的公共財政投入大部分優先偏向城市,農村地區養老服務公共財政投入明顯不足,使得農村養老服務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落后,多數養老設施目前尚不完備,客觀上也進一步拉大了城鄉老年人在養老服務獲得上的差距[25]。“婦老鄉親”模式作為一種依托農村內生力量的養老方式,必須具備開展活動所需的場地和基礎設施,包括公共活動場所、辦公場所、村宣傳欄等基本設施,進一步發展還需要包括培訓室、日間照料中心、老年餐廳等專門的設施和場地。因此,政府需要繼續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地區養老服務資源的投入,特別是要加強偏遠和落后農村地區的硬件設施建設和適老化改造,完善配套設施,為更多元化的養老模式和服務提供基本的環境條件。
(三)專業力量的指導
專業力量是“婦老鄉親”模式的有力支撐,對推動農村養老服務更加規范化和專業化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國許多農村地區開展的養老服務缺乏專業人才、質量偏低,特別是許多農村內部的養老服務,因其志愿性、自發性和互助性等特點,服務內容比較單一且質量難以保障[26]。而農村養老服務想要擴大化和精細化,實現可持續、有效率的運營,引入專業社工組織極為重要。他們具有社區營造、組織動員、開展互助等方面的專業優勢,也有擴大規模、增加營利的動力[27]。“婦老鄉親”模式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借助社工機構的專業能力,將社工機構作為孵化機構,根據各村具體情況籌建老人或婦女組織,并協助農村自治組織招募志愿者團隊、開展日常服務和管理工作。“婦老鄉親”模式中專業社工機構并非服務的直接提供者,而且是扮演著指導者的角色,通過自身力量或鏈接外部資源,對自治組織和志愿者進行指導和培訓,從而提升本土組織成員和志愿者的專業能力,進一步提升養老服務質量。
(四)文化和社會資本的投入
“婦老鄉親”模式的本質是在農村社會組織的協調下,凝聚本土內生力量,發揮鄉鄰之間的互助作用。農村社會組織的核心成員由本村的精英組成。這些人積極性高、能力強、能從外界獲得資金或物質援助,能夠很好地領導農村社會組織開展相關活動。農村社會組織還需要鏈接本村潛在的人脈資源,如在外從醫、從政、從商的精英能人,為開展服務提供資源或者指導,這些都離不開本土的互助傳統。費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來概括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關系,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更多的是一種“熟人社會”。在中國傳統社會,依靠家庭是老年人主要的養老方式,而當作為社會生活基本單位的家庭內部不能妥善解決養老問題時,由家庭外延的親屬關系構成的家族,或是由地緣構成的鄰里關系就承擔起一定的義務[28]。因此,鄉鄰之間的互助是鄉土社會的重要傳統,農村中的人脈關系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外遷,農村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受到巨大的沖擊。在社會化養老保障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鄉鄰之間的互助作用逐漸凸顯,本土的互助文化傳統越濃厚,農村互助養老模式越容易開展。鄉賢等農村精英在互助養老中起到重要作用,有的人即使離開故土,但依然無法割斷與故土的聯系,游離往返于城鄉之間[29],成為農村重要的人脈資源。因此,“婦老鄉親”模式的推廣既需要有濃厚的互助文化資源支撐,也需要各界社會資本予以支持。
四、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婦老鄉親”
互助養老模式對我國農村養老的啟示
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等戰略背景下,我國農村養老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如何實現農村養老服務體系的健康持續發展?本研究中的“婦老鄉親”模式在人力、組織、服務和管理等方面的獨特優勢,對我國未來農村養老服務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培育內生力量
鄉村治理是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提出,要健全現代鄉村治理體系,其中包括深化村民自治實踐,加強農村群眾性自治組織建設;健全農村基層服務體系,大力培育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農村社會組織,積極發展農村社會工作和志愿服務等。可見,我國農村養老的發展不能僅依靠外生力量,需要大力培育本土自治組織和人員,強化基層自治和服務能力。
農村互助養老,其創新點就在于自治,通過村民及老人自身的力量搭建互助養老平臺,解決自身養老問題[30]。但是,隨著我國農村人口的大量外流特別是年輕、有文化的中青年的外遷,發展養老服務僅靠農村留守人口自身的力量必定是遠遠不夠的,培育農村養老的自治力量面臨著“由誰來帶頭、誰來組織、誰來賦能”等困難。因此,養老服務的持續化和規范化發展,一方面需要政府和專業組織提供指導、支持,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吸引有威望、有能力的本土人士重返農村,參與到農村養老的組織和領導當中,充分利用本土人力資源,調動村民的積極性,而不是被動地等待政府“補缺”服務。
(二)推動政府與社會力量協同治理
專業社會組織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是政府和市場在農村養老保障和服務供給中的重要補充。“婦老鄉親”模式依靠公益基金會進行模式輸出和資金支持,借助社工機構的專業能力,彌補了政府在養老服務提供中形式僵化、內容單一等短板,對我國今后農村養老的發展有著較強的借鑒意義。未來我國農村養老需要更加重視專業社會組織的作用,發揮其優勢,鼓勵更多的社會力量介入養老服務,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促進模式創新、組織孵化和人才培育。但是從客觀來看,我國社會組織力量薄弱,參與農村互助養老的持續動力仍不強。嚴格的社會組織準入和管理體制,加之多數社會組織在資金和管理上高度依附于政府,導致我國專業社會組織發展不足,參與養老服務的動力不足。這亟須推動政府與社會力量協同治理。首先,要厘清責任關系。政府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做好農村社會化養老服務的政策制定、籌資和監管;社會力量加強服務的創新和優化,做好服務的“提供者”,為農村養老提供更多優質的人才和服務。其次,要大力培育社會組織。政府要在立法、資金、政策等方面支持和鼓勵社會組織的發展。最后,要打通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合作網絡,讓政府與社會組織建立起平等合作與利益互補的新型關系[31]。
(三)提供精準化與差異化服務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
興,加快鄉鎮區域養老服務中心建設,推廣日間照料、互助養老、探訪關愛、老年食堂等養老服務,為我國農村養老服務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目前,我國農村養老服務仍存在著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矛盾。老年人的生活狀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養老需求日趨多元化,但養老服務的供給內容卻比較單一,服務層次比較低,缺乏對不同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因此,養老服務要結合農村分化和區域差異,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資源配置,推動養老服務供給對象、方式和內容的精準化,讓養老資源投入能夠精準發力[32],進一步提高養老服務質量。“婦老鄉親”模式的一大亮點就是對不同試點村的老人進行需求調研,科學化評估各試點老年群體養老服務需求與現實養老問題,并針對不同項目點目標老年人群的真實需求,量身定做切合村莊實際的老年服務方案,為我國未來農村養老服務的優化發展提供了新思路。總結而言,養老服務不能“一刀切”,應該以老年人的實際需求為導向,細分不同的老年群體,提供更加多元化、差異化和精準化的養老服務。而且需要特別明確的是,互助養老作為家庭養老和社會化養老的重要補充,并不能完全代替政府和市場的作用;養老服務的精準化和差異化仍然需要在政府保障基本養老服務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和產業的力量。
(四)強調管理與監督規范化
良好的監督機制是保證“婦老鄉親”模式持續有效運作的基礎。有效的評議監督機制不僅能夠促進養老服務項目的規范化運作,而且有利于及時改進養老服務實施過程中的不足,促進養老服務項目更貼合老年人的養老需求。目前,我國農村養老服務存在行業標準缺乏、外部監督體制不完善、管理分散和評估標準缺失等問題[33]。“婦老鄉親”模式的這一特點對我國發展農村養老的啟示是:農村養老服務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需要加強對養老服務供給的規范化管理。首先,要對提供服務的組織和人員進行監督,確保組織的運行公正、高效和透明,并對組織的運行目標、運行內容、資金明細和發展成效進行定期監督。其次,要加強對服務的監管,對所提供的養老服務進行定期評估。一方面,由專業機構或人員對服務質量開展第三方專業評估;另一方面,建設需求和意見反饋平臺,收集目標老年人群對于養老服務的評價以及對養老服務項目的改進意見,及時改進服務、提升質量。
參考文獻:
[1] 杜鵬、安瑞霞:《政府治理與村民自治下的中國農村互助養老》[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50-57頁。
[2] 劉妮娜:《互助與合作:中國農村互助型社會養老模式研究》[J],《人口研究》2017年第4期,第72-81頁。
[3] 陳友華、苗國:《制度主義視域下互助養老問題與反思》[J],《社會建設》2021年第5期,第73-82頁。
[4] 金華寶:《農村社區互助養老的發展瓶頸與完善路徑》[J],《探索》2014年第6期,第155-161頁。
[5] 金華寶:《社區互助養老:解決我國城鄉養老問題的理性選擇》[J],《東岳論叢》2014年第11期,第123-127頁。
[6] 甘滿堂、婁曉曉、劉早秀:《互助養老理念的實踐模式與推進機制》[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第78-85頁。
[7] 李俏、劉亞琪:《農村互助養老的歷史演進、實踐模式與發展走向》[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第72-78頁。
[8] 陳靜、江海霞:《“互助”與“自助”:老年社會工作視角下“互助養老”模式探析》[J],《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第36-43頁。
[9] 林尚立:《論以人民為本位的民主及其在中國的實踐》[J],《政治學研究》2016年第3期,第2-12、125頁。
[10] 同[7]。
[11] 張云英、張紫薇:《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歷史嬗變與現實審思》[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第34-38頁。
[12] 劉妮娜、杜鵬:《中國互助型社會養老的定位及發展方向》[J],《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第140-153頁。
[13] 賀雪峰:《互助養老:中國農村養老的出路》[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第1-8頁。
[14] 劉妮娜:《中國農村老年人互助養老服務參與狀況及影響因素研究》[J],《老齡科學研究》2018年第12期,第63-74頁。
[15] 同[12]。
[16] 同[4]。
[17] 高靈芝:《農村社區養老服務設施定位和運營問題及對策》[J],《東岳論叢》2015年第12期,第159-163頁。
[18] 陳際華、黃健元:《農村空巢老人互助養老:社會資本的缺失與補償——基于蘇北S縣“老年關愛之家”的經驗分析》[J],《學海》2018年第6期,第147-152頁。
[19] 周娟、張玲玲:《幸福院是中國農村養老模式好的選擇嗎?——基于陜西省榆林市R區實地調查的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16年第5期,第51-64、95-96頁。
[20] 同[2]。
[21] 王德澤:《探索農村養老服務的新途徑——關于榆林市開展鄰里互助養老服務工作的調查報告》[A],載陜西省老年學學會秘書處主編《陜西老年學通訊》2014年第1期。
[22] 劉妮娜:《中國農村互助型社會養老的類型與運行機制探析》[J],《人口研究》2019年第2期,第100-112頁。
[23] 郝金磊:《區域差異背景下農村養老模式的構建》[J],《廣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12期,第100-104頁。
[24] 張艷霞、劉遠冬、吳佳寶、王佳嬡:《中國農村養老保障資金供給現狀及多元化探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第78-90頁。
[25] 陸杰華、沙迪:《新時代農村養老服務體系面臨的突出問題、主要矛盾與戰略路徑》[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第78-87、2頁。
[26] 黃俊輝:《農村養老服務供給變遷:70年回顧與展望》[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第100-110頁。
[27] 劉妮娜:《農村互助型社會養老:中國特色與發展路徑》[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21-131頁。
[28] 趙志強、王鳳芝:《文化社會學視角下的農村互助養老模式》[J],《農業經濟》2013年第10期,第24-26頁。
[29] 趙旭東、張潔:《鄉土社會秩序的巨變——文化轉型背景下鄉村社會生活秩序的再調適》[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56-68頁。
[30] 同[1]。
[31] 朱漢平、賈海薇:《政府與社會組織協同供給農村養老服務的推進思路——基于協同治理理論視角的分析》[J],《廣東農業科學》2013年第10期,第202-204、219頁。
[32] 于書偉:《農村養老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困境及對策研究》[J],《求實》2018年第4期,第98-108、112頁。
[33] 李俏、許文:《農村養老服務供給側改革的研究理路與實現方式》[J],《西北人口》2017年第5期,第51-57頁。
注釋:
①“千萬工程”,是“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的簡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時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一項重大決策。2023年6月,中央財辦、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關于有力有序有效推廣浙江“千萬工程”經驗的指導意見》,提出推廣“千萬工程”經驗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大舉措、是加快城鄉融合發展的有效途徑、是建設美麗中國的有力行動、是扎實推進鄉村振興的必然要求。推廣“千萬工程”經驗,要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放在鄉村,加快推動鄉村基礎設施提檔升級;推動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社會事業向農村覆蓋,健全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而發展農村互助養老,讓農村老年人享有更便捷、更多元的養老服務,正是運用“千萬工程”經驗、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生動實踐。
作者簡介:謝立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老年學研究所副教授。王飛,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李? ? 鈞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以時間銀行推動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理論和應用研究”(23ZDA10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