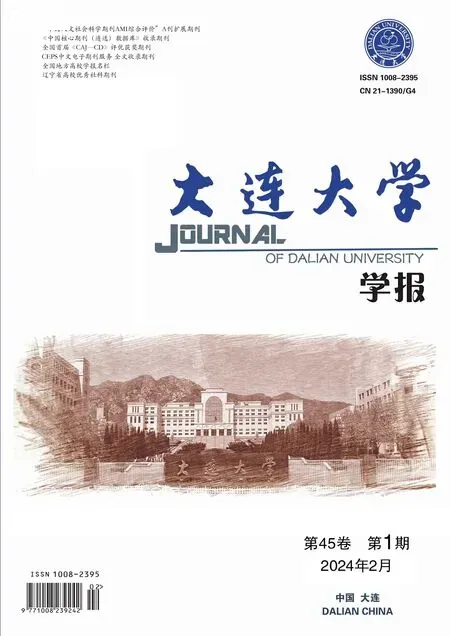語氣副詞“XX乎”的句法語義及詞匯化
李思旭,卜婷婷
(安徽大學 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1]收錄了“無怪乎、無須乎、幾幾乎、庶幾乎、于是乎、不外乎”等6個“XX乎”式“乎”尾三音詞,其中“無怪乎、無須乎、幾幾乎、庶幾乎”4個標注為副詞,“于是乎”標注為連詞,“不外乎”標注為動詞。這4個三音節語氣副詞“XX乎”中,“無須乎、幾幾乎、庶幾乎”還未見專文研究,“無怪乎”已有兩篇文獻。巴丹[2]認為“無怪乎”先從跨層短語結構(“無怪”+介詞“乎”)詞匯化為評注性副詞,再從評注性副詞語法化為關聯副詞。我們認為“無怪乎”是通過類推造詞產生的,并沒有經歷詞匯化和語法化的演變。巴丹[3]對共時層面“無怪乎”的篇章銜接功能作了詳細分析,但是在句法語義上沒怎么展開。此外,劉紅妮[4]在討論“雙音副詞+句中語氣詞”進一步詞匯化時,認為這4個詞都是從雙音副詞跟句中語氣詞“乎”再演變而來的,即副詞“無怪/無須/幾幾/庶幾”+句中語氣詞“乎”→副詞“無怪乎、無須乎、幾幾乎、庶幾乎”。對此觀點我們并不贊同,下文將證明“無怪乎、無須乎”是在雙音節構詞圖式“X乎”的類推作用下形成的,“幾幾乎”是由“幾”加“幾乎”同義疊加形成的,“庶幾乎”是由“庶幾”跟“庶乎”糅合而形成的。
本文主要討論“無怪乎、無須乎、幾幾乎、庶幾乎”等4個副詞“XX乎”在句法語義特征及其詞匯化動因與機制上的差異。具而言之,屬于同一構詞圖式構式“XX乎”的4個成員,語義上有哪些共性與差異?這4個副詞在跟語氣成分(語氣詞、語氣副詞)共現上有什么傾向性規律,規律背后的制約因素又是什么?這4個語氣副詞詞匯化過程和形成機制又是怎樣的?
一、“無怪乎”的句法語義及詞匯化
(一)“無怪乎”的句法語義特征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1]認為副詞“無怪乎”等于“無怪”,即:“副詞,表示明白了原因,對下文所說的情況就不覺得奇怪。也說無怪乎”。《漢語大詞典》[5]對“無怪乎”的解釋是“對某種現象不感到奇怪”。結合詞典釋義及相關的語料分析,我們認為副詞“無怪乎”可以釋義為:明白了之前所不知曉的原因或情況,對所產生或導致的現象有所領悟。
“無怪乎”表示明白了原因,對某種情況不覺得奇怪,是個醒悟類語氣副詞。
(1)她的樣子多美呀!無怪乎這個小伙子要為她失魂落魄呢!(高爾斯華綏《出租》)
(2)她永遠是個按照“老師的意志”行事的學生, 無怪乎葉切文給她的評語是“天資異常聰明,品行無比端莊,待人熱情誠懇。”(李靜《當代世界文學名著鑒賞詞典》)
以上兩例“無怪乎”都表達了,說話人了解了背景或原因后從而對某一現象的出現或事件的發生不再覺得奇怪,具有明顯的醒悟義。例(1)中,知道了女子長相很美,從而醒悟到為何小伙子失魂落魄。例(2)中,了解了她是個什么樣的學生后,再看葉切文給她的評語就不覺得奇怪了。
語氣詞是表達句子語氣的虛詞,常用在句尾或句中停頓處表示種種語氣。現代漢語中常見的語氣詞有“了、的、啊、呢、嘛、罷了、而已”等。語氣副詞“無怪乎”可以與“了、的、呢、吧、哩”等語氣詞共現。如:
(3)而所有這些,又與香港的花花世界那么保持著間距。無怪乎他給自己鬧個武陸莊主的別號了。(1994年《報刊精選》)
(4)船的甲板上,其中有幾個年老的人,年老的人是到處落伍。無怪乎那優勝劣敗的哲學是千對萬對的。(蕭紅《馬伯樂》)
(5)他所以與人爭訟,不過是為了獲得爭訟的快感,至于說站在問題的哪一面,則全都一樣,無怪乎他要感到這真是個費錢的玩藝兒呢。(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集》)
現代漢語中的語氣副詞,按照語氣類型的不同,大致可分為“或然、必然、斷定、指明、證實、意愿、指令、感嘆、疑問、特點、關系”等十一個小類[6]。通過對北京大學CCL現代漢語語料庫369條“無怪乎”有效語料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其中有66條語料是跟語氣副詞共現的。具體來說,“無怪乎”可以跟斷定類、特點類、或然類、必然類、意愿類、關系類等六類語氣副詞共現。如:
(6)他的輪廓實在很英俊,的確夠得上美男子之譽,無怪乎他年輕時會有那么多的風流韻事。(古龍《圓月彎刀》)
(7)斯時,斯景,他居然能嘆出氣來,無怪乎連得謝小玉也嚇了一大跳。(古龍《圓月彎刀》)
(8)無怪乎作者希望評論者要成為作者的“知音”,至少能理解作家創作的甘苦。(《讀書》)
(二)“無怪乎”的詞匯化及形成機制
最早在宋代,就出現了“無怪乎”,此時的“無怪乎”已經是副詞,修飾后面的謂詞性成分作狀語,表示“明白了原因,對所產生或導致的現象有了領悟,不再覺得奇怪”,具有表醒悟的語義特征。元代也出現了一例“無怪乎”連用的語料。
(9)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乎此錢之多。”(宋《能改齋漫錄》)
(10)官員則有賣鹽食錢、縻費錢,胥吏則有發遣交納常例錢,公私齟齬,無怪乎不可行也。(元《宋史》)
宋元時期,“無怪乎”的使用頻率很低,且北大語料庫中各只有一個用例。例(9)“無怪乎”出現在謂詞性成分之前,這樣的句法位置是副詞經常出現的位置,且例(9)可以翻譯為:“在唐朝近三百年的歷史中,都只生產開元通寶這種貨幣,怪不得這種貨幣數量如此之多。”可見“無怪乎”最早出現時就已經成詞。巴丹[2]認為例(10)“無怪乎”中的“乎”來源于介詞,但如果句中的“乎”為介詞,“無怪”就是動詞,“無怪”作動詞時,其語義為“不要責怪”,這樣整個句子的句義都不通順。以上兩例中的“無怪乎”都可以用“無怪”進行替換,替換后語義也沒有發生改變。因此,我們推論“無怪乎”是由副詞“無怪”+詞綴“乎”構成的,其詞義主要由“無怪”來承擔,“乎”作為詞綴沒有什么實在的意義,只起到舒緩語氣的作用。
古代漢語的“乎”主要有介詞、語氣詞和詞尾三種用法,其中詞尾“乎”來源于語氣詞“乎”,現代漢語“乎”主要用作詞綴。“X乎”詞匯化和語法化的過程,就是“乎”分別由介詞、語氣詞語法化為詞綴的過程[7]。通過上面的例句可知,“乎”在宋代作為一個詞綴的用法就已經出現,這也間接證明了我們的推論是具有合理性的。
明清時期,“無怪乎”的用例開始增多。以下兩例中“無怪乎”都表示“明白了原因,對下文所說的現象或結果不感到奇怪”之義,其詞匯義和“無怪”相同,都可以用“無怪”進行替換而句義不變。可見,“無怪乎”的詞義主要由“無怪”來承擔,“乎”的作用作為詞綴依附于“無怪”之后,無實義。
(11)暗室無燈,有眼皆同瞽目,無怪乎覓途不得。(明《閑情偶寄》)
(12)單太爺道:“你出門兩個月,剛剛回來,也不曾出過大門,無怪乎你不曉得。等我來告訴你。”(清《官場現形記》)
總之,“無怪乎”的用例最早出現在宋代,在明清時期開始增多,“乎”作為一個詞綴的用法在“無怪乎”成詞之前就已經出現,并且副詞“無怪”詞匯化的過程和“無怪乎”大致同步,所以三音節副詞“無怪乎”應該是在雙音節副詞“無怪”和詞綴“乎”的基礎上形成的。在“無怪乎”出現之前,雙音詞“X乎”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在雙音詞“X乎”的類推作用下,三音節“XX乎”成詞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無須乎”的句法語義及其詞匯化
(一)“無須乎”的句法語義特征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1]認為副詞“無須乎”等同于“無須”,即:副詞,表示不用,不必。《現代漢語八百詞》[8]在對“無須”釋義時提到了“無須乎”,認為“無須”是個副詞,表示不必,用不著。“無須”也常說成“無須乎”。結合詞典釋義及相關語料,表“不必、用不著”義的“無須乎”的語義特征可分析如下。
“無須乎”可以表示說話人主觀上對某一件事情的確信,因而具有確信義。例(13)徐悲鴻主觀上認為他用來題畫的詩都是杜甫的名篇,大家都知道,所以不用再標明詩的作者。例(14)作者認為跟語言相比,音樂和圖畫可以通過各自的媒介即音符和顏色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發揮審美作用,所以不用進行翻譯也無法翻譯。
(13)他作畫之后,即用杜詩原文題畫,大約偶然忘記標出杜甫的名字,也可能他認為這是人們習聞常見的名篇,無須乎再標明作者。(《讀書》)
(14)對于異國的鑒賞者,音符和顏色都無須乎翻譯也無從翻譯,而語言卻必須翻譯也是能夠翻譯的。(《讀書》)
在一定的語境下,“無須乎”還可以表示建議義。例(15)包善卿認為應該先請教山木看看他的態度,如果他主張和平,就不用帶便衣隊帶家伙,話語中帶有對方文玉的建議之義。例(16)作者指出寫文章是為了尋求真理,所以不必與古人觀點爭論不休,這句話也表示對讀者的建議之情。
(15)包善卿也掛了氣,可是還不象方文玉那么浮躁。“不過總是先問問山木好,他要用武力解決呢,咱們便問心無愧。做主張和平呢,咱們便無須乎先表示強硬。”(老舍《且說屋里》)
(16)這兩篇文字,算是一種破壞,目的在使我自己的思想獨立,所以文中多偏激之論,我們重在尋求真理,無須乎同已死的古人爭鬧不休。(李宗吾《厚黑學》)
在現代漢語中,可以跟語氣副詞“無須乎”共現的語氣詞有“的、了、嗎、呀”。其中,語氣詞“了”和“無須乎”共現的頻率最高,這是因為語氣詞“了”用于句尾的使用頻率最高。
(17)大家在一塊兒玩玩花草,也就無須乎分什么中國人與日本人了!(老舍《四世同堂》)
(18)看到那些信,我就覺得這些人還如此戀戀于生,實在是無須乎在生活上開這種大玩笑的。(沈從文《采蕨小說集》)
(19)但是他轉念一想,這件事,難道無須乎和桂英商量一下子嗎?(張恨水《歡喜冤家》)
在79條有效語料中,有14條語料是“無須乎”跟斷定類、或然類、關系類、證實類、必然類等五類語氣副詞共現的。如:
(20)夜黑天里,沒人看見他;他本來無須乎立刻這樣辦;可是他等不得。(老舍《駱駝祥子》)
(21)假若家中沒有老的和小的,她自然無須乎過節,而活著仿佛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老舍《四世同堂》)
(22)我本無須乎要他來,但他真的不來卻又更令我傷心,更證實他以前的輕薄。(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
(二)“無須乎”的詞匯化及形成機制
“無須乎”最早出現在清朝,以下兩例中“無須乎”作謂語后接名詞性成分,此時的“無須乎”應該是個動詞。劉紅妮[4]認為“無須乎”是由副詞“無須”和句中語氣詞“乎”直接結合而成的,而由下例可知,“無須乎”在近代漢語中有作動詞的用法,所以我們認為其觀點是有問題的。
(23)自來鑲埽之法,堤前必先筑土壩數十丈,然后用埽鑲,設磚壩則無須乎埽。(清 《清史稿·列傳》)
(24)光緒丁酉以后,帝年已長,擇句無須乎人。(清《異辭錄》)
面對以上語言事實,我們不禁產生疑惑:難道“無須乎”是從最開始的動詞語法化為副詞的嗎?通過檢索北京大學CCL古代漢語語料庫,我們發現“無須乎”作謂語的例子只有幾個,且穿插于副詞“無須乎”的語料中,并沒有體現出由動詞向副詞的演化過程,因此我們推測副詞“無須乎”應該不是從動詞演化而來的。結合曹德和的研究[9],我們認為這是因為“須”和“需”在古代漢語中曾有過通假用法,且二者語音相同,語義相近,所以兩者很容易混用,即把“無須乎”寫成“無需乎”。因“無需乎”是個動詞,所以語料中出現了“無須乎”誤用作動詞作謂語的例子。副詞“無須乎”最早應該出現在清代《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中,例如:
(25)以有文鈔,十要,救劫等書,固無須乎函詢也。(清《印光法師文鈔三編》)
(26)問官一提起,他就立刻承認,無須乎動刑。(清《江湖奇俠傳》)
由上例可見,“無須乎”一開始使用時就是作狀語修飾其后的謂詞性成分,表示“不用、用不著”義。我們分析了有關“無須乎”的所有歷時語料,找不到“無須乎”詞匯化的歷時過程。那么“無須乎”是怎么成詞的呢?我們認為是受到雙音節詞“X乎”類推作用的影響。
三音節詞“無須乎”應該是在“無須”和“乎”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葉雙[7]指出“乎”作為一個副詞詞綴的用法在宋代就已經出現,雙音詞“X乎”都是由副詞加詞綴“乎”構成的。因為“無須乎”出現于清朝,此時“X乎”結構已經發展得較為成熟。所以副詞“無須乎”很可能受到雙音節詞“X乎”的類推作用,由已經成詞的“無須”加上詞綴“乎”直接成詞。在“無須乎”這個副詞中,“乎”作為詞綴,無實際意義,其主要意思由“無須”承擔。清朝時期,雙音詞“X乎”已經廣泛使用,人們對其熟稔,所以對“無須乎”的直接產生也不足為奇。
三、“幾幾乎”的句法語義及詞匯化
(一)“幾幾乎”的句法語義特征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1]認為“幾幾乎”等同于副詞“幾乎②”,即“表示某種事情接近發生(多用于說話人不希望的事情),差點兒”。結合詞典釋義及相關語料,我們可以把“幾幾乎”的語義特征分析如下:
“幾幾乎”表示十分接近的差不多義。副詞“幾幾乎”在表示差不多義時,多修飾或限定表示數量或范圍的詞語。例(27)“幾幾乎”后接數量詞語“一天”,表示云姑差不多一整天都在哭。例(28)“天天”是個表周遍性數量的詞語,“幾幾乎天天”就是接近于每天的意思,表示發文章的次數非常多。
(27)云姑?云姑今天幾幾乎哭了一天,大約是同你吵嘴了罷。(蔣光慈《鴨綠江上》)
(28)當時你在《皖江新潮》幾幾乎天天發表文章,專門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思想。(蔣光慈《少年飄泊者》)
“幾幾乎”還可以表示事情接近發生的差點兒義。例(29)謂語動詞“打”后有表示其結果的補語“斷”,表示腿被打斷了,具有完全實現義。受語氣副詞“幾幾乎”修飾后,將其變為不完全實現義,表示腿差點被打斷但是沒斷。“幾幾乎”不僅能對事件表完全實現義的結果進行修飾,還能對事件本身的性質或狀態進行修飾。比如例(30)“和壁爐中添上煤塊的意義沒有什么兩樣”表示吃飯這一事件的性質,其特征具有極端性。在受“幾幾乎”限制后,其性質特征又有了不完全實現義,吃飯的意義接近于壁爐中添上煤塊的意義卻又不完全相同。
(29)去年因為天旱,收成不大好,繳不起課租,他被地主痛打了一頓,幾幾乎把腿都打斷了!(蔣光慈《少年飄泊者》)
(30)她常常覺得自己的吃飯,幾幾乎和壁爐中添上煤塊的意義沒有兩樣的。(胡也頻《到莫斯科去》)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當副詞“幾幾乎”表示差不多義,其接近的對象多為表數量或范圍的詞語;當副詞“幾幾乎”表示差點兒義時,其接近的對象多為事件的結果或性質狀態。其接近對象的共同特征就是含有極端義。當然,這里的“極端”具有較強的主觀性,是說話人所認為的極端。
在現代漢語中,可以跟語氣副詞“幾幾乎”共現的語氣詞只有“了”和“的”,如:
(31)這樣人言語吝嗇到平常一切事上,生在鼻子下的那一張口,除了為吃粗糲東西而外,幾幾乎是沒有用處了。(沈從文《游目集》)
(32)這田園之思,也妙得很,幾幾乎是終生相伴的。(《讀書》)
在67條有效語料中,有16條語料是“幾幾乎”跟語氣副詞共現,具體來說有斷定類、或然類、關系類、特點類、意愿類等五類語氣副詞,前三種共現的例句如:
(33)地方的確興隆得極快,第二年就幾幾乎完全不象第一年的北溪了。(沈從文《旅店及其他》)
(34)我似覺我的兩眼也潮濕起來,淚珠幾幾乎從眼眶內進涌出來了。(蔣光慈《鴨綠江上》)(35)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沈從文《長河》)
(二)“幾幾乎”的詞匯化及形成機制
麻愛民[10]、張慧穎[11]認為“幾乎”是由一個跨層結構“幾+乎”虛化成副詞的,但是與“幾乎”句法語義相近的“幾幾乎”卻鮮有人問津。韓陳其[12]在討論一組“幾乎”類詞語時,就“幾乎”“幾于”“幾幾”等如何演變為“幾幾乎”提出了幾種可能性的推測時,順帶提及。劉紅妮[4]認為“幾幾乎”是由副詞“幾幾”和句中語氣詞“乎”詞匯化而來的,但沒有論證詞匯化的具體過程。
副詞“幾幾乎”最早出現在明代陳治紀的《書〈張文忠公文集〉后》中,如:
(36)夫伊尹之于桐,周公之徂東,當其時,蓋亦幾幾乎不免于不臣不弟之過矣。(明《書〈張文忠公文集〉后》)
“幾幾乎”從明代出現后,其語義沒有經歷明顯的發展變化,仍然表示差不多義或差點兒義。例(37)“幾幾乎”表十分接近的差不多義,常年賭博,黃金白銀差不多要輸光了。例(38)“幾幾乎”表示某種事情接近發生的差點兒義,王六用“母老妻病”騙人,左宗棠差一點上當了。
(37)繼見累次失利,每欲出門,必默禱家中神明,然仍賭輸如故。數年間,黃白物已幾幾乎罄矣。(清《北東園筆錄三編》)
(38)少爺方才所說,不是冤枉你的吧,你倒竟敢用這母老妻病四字,前來騙人,本部堂幾幾乎上了你的當了。(民國《大清三杰》)
由上可知,“幾幾乎”從一開始出現時就已經是副詞,表示十分接近義。那么“幾幾乎”的詞匯化過程是怎樣的呢?結合韓陳其的研究[12],我們推測副詞“幾幾乎”有兩種可能的演變來源:一種是“幾幾乎=幾幾+乎”,即“2+1”韻律結構模式;另一種是“幾幾乎=幾+幾乎”,即“1+2”韻律結構模式。黃桂紅[13]認為副詞“斷斷乎”是由副詞“斷斷”+后綴“乎”演變而來的,那么同樣作為副詞的“幾幾乎”是否也經歷了類似的演變路徑呢?
“幾幾”可表示“幾乎”義的語料最早出現在清末小說中,如:
(39)骎至八國聯軍之役,神京淪陷,兩宮蒙塵,大局之敗壞,幾幾不可收拾。(清《張文襄公事略》)
(40)余年十五六,即為學詩。后以奔走四方,東西南北,馳驅少暇,幾幾束之高閣。(清《人境廬詩草自序》)
“幾幾乎”最早用例出現在明代,而“幾幾”最早的兩個用例都于清末才出現,比如例(40)成文于光緒十七年(1891年)。可見,表“幾乎”義的“幾幾”出現要晚于“幾幾乎”,所以劉紅妮提出的“幾幾乎=幾幾+乎”這一假設至少在時間上是不成立的。
相較而言,“幾幾乎=幾+幾乎”這一演變模式更符合漢語遞增的韻律特點。“幾”和“幾乎”的語義相同,“幾乎”作為副詞在宋代萌芽,成熟于元明時期。受到漢語雙音化這個主流趨勢的影響,“幾乎”逐漸取代“幾”,“幾乎”的使用頻率不斷提高,后來為了在語句中表達更為強烈的接近義,人們將表“接近義”的“幾”和“幾乎”進行同義疊加形成“1+2”的韻律結構形式,增加其表義強度。
從產生的時間來看,表“幾乎、將近”義的“幾”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如例(41);副詞“幾乎”最早出現于宋代,如例(42)。副詞“幾”和副詞“幾乎”都早于“幾幾乎”產生,故副詞“幾幾乎”很可能是由“幾”加“幾乎”疊加而形成的,“幾幾乎=幾+幾乎”。那么,劉紅妮[4]認為“幾幾乎”是由副詞“幾幾”和句中語氣詞“乎”詞匯化而來的,這一觀點就非常值得商榷。
(41)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春秋《國語》卷十)
(42)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宋《圓悟佛果禪師語錄》)
四、“庶幾乎”的句法語義及詞匯化
(一)“庶幾乎”的句法語義特征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1]認為“庶幾乎”等同于“庶幾”,副詞“庶幾”有兩個義項:①但愿,表示希望義。②或許,也許可以,表示推測義。也說庶幾乎或庶乎。《漢語大詞典》[5]對“庶幾乎”的解釋是:①或許,大概可以,如“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跡,庶幾乎不負古人者。(金《送秦中諸人引》)”;②近于,略同,如“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東漢《漢書·蘇武傳》)”結合詞典釋義和具體語料,“庶幾乎”的語義特征可分析為:
“庶幾乎”表示但愿的希望義,所希望的大都是積極向好的方面。例(43)中,魯迅先生將自己的“籍”和“系”詳細地寫出來,但愿能夠杜絕認為他是黑籍政客的流言再次傳播。例(44)中,“庶幾乎”表“希望”義,整句話的意思是“通過交互往復的方法,希望詞義、語義能夠被進行充分的解釋,從而使得詞義語義的解釋不再枯燥”。
(43)終于也明白了,現在寫它出來,庶幾乎免得又有“流言”,以為我是黑籍的政客。(魯迅《我的“籍”和“系”》)
(44)錢鐘書同志說:“交互往復,庶幾乎義解圓足而免于偏枯。”(《讀書》)
“庶幾乎”表示或許、也許的推測義。例(45)中,前一小句中的“只有”和后一小句中的“庶幾乎”語義呼應,鄉親們都覺得只有他們為丁主任效勞,也許就可以為他們之前幼稚冒失的行為贖罪。例(46)中,“我”希望通過認真做人、閱世、讀書來加深自己對于人生和社會的認識,進而“我”的評論文章或許每天都會有所進步。
(45)他們反覺得只有給他效勞,庶幾乎可以贖出自己的行動幼稚、冒昧的罪過來。(老舍《貧血集》)
(46)我希望自己認真做人,認真閱世,認真讀書,使對于人生和社會的認識日見其深起來,這樣,我的評論文字庶幾乎能日有進步。(《讀書》)
“庶幾乎”表示接近、差不多義。例(47)的句義為“某人在路上偶遇一只骨瘦如柴,差不多奄奄一息的貓,但因考慮家中鼠害嚴重,還是把它抱回家了”。
(47)某曾偶遇一貓于路途。雖見其骨瘦如柴,羸弱不堪,且庶幾乎奄奄一息,因念家中鼠害甚烈,遂抱歸之。(《讀者》)
在現代漢語中,可以跟語氣副詞“庶幾乎”共現的語氣詞有“了、的、也”。
(48)故當局者應當提倡合乎國民生活與經濟底禮俗,庶幾乎不教固有文化淪喪了。(許地山《禮俗與民生》)
(49)把人劃分為某些類別庶幾乎是可能的,而分類中最可靠的標準,莫過于那種把人們一生光陰導向這種或那種活動的深層欲望。(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能跟“庶幾乎”共現的語氣副詞僅有或然和關系這兩類,且都僅有一例。可見,“庶幾乎”跟語氣副詞共現的情況不太普遍。“庶幾乎”跟或然類語氣副詞“大致”共現的如例(50),“庶幾乎”跟關系類語氣副詞“反”共現的例(51)。
(50)現在是發現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魯迅《朝花夕拾》)
(51)他們反覺得只有給他效勞,庶幾乎可以贖出自己的行動幼稚、冒昧的罪過來。(老舍《貧血集》)
(二)“庶幾乎”的詞匯化及形成機制
“庶幾乎”作為一個線性結構最早出現在周朝的《周易》中,此時,“庶幾乎”并不是一個副詞,而是由副詞“庶幾”+語氣詞“乎”組成的線性結構。
(52)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周《周易·系辭下》)
“庶幾乎”的早期用例都是由副詞“庶幾”+語氣詞“乎”組成的線性結構,并且都位于句尾。下例中,為圃者連續說出了三句話,每句話都是以語氣詞“乎”結尾,可見句中的“庶幾乎”還只是一個線性結構。
(53)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圣,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莊子《子貢南游于楚》)
副詞“庶幾乎”最早可能出現在戰國時期。例(54)中,“庶幾乎”位于小句的句首,同時后接主謂短語“民有瘳”,此時的“庶幾乎”不再是一個線性結構,而是一個完整的詞,表“或許、大概”義。
(54)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戰國《晏子春秋》)
“庶幾乎”是如何成詞的呢?劉紅妮[4]認為“庶幾乎”是由雙音節副詞“庶幾”和句中語氣詞“乎”長期連用后,發生了進一步詞匯化而形成的。事實果真如此嗎?在翻閱相關字典辭書后發現,“庶幾乎”“庶幾”和“庶乎”三者詞性詞義相同,因此,我們認為“庶幾乎”的生成機制是糅合,即“庶幾乎”=“庶幾”+“庶乎”。
葉建軍[14]指出糅合可以分為詞法層面糅合和句法層面糅合兩種。詞法層面的詞語糅合指的是語義相同或相近的兩個詞通過刪除重疊部分合成一個新詞的過程。發生糅合的語言單位必須遵守同級原則。“庶幾”和“庶乎”都是雙音詞,所以它們符合詞語糅合的同級原則。詞語糅合要遵循詞義相近原則,即兩個源詞語的詞義必須相同或相近。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1]的釋義,“庶幾”和“庶乎”都是副詞,都可以表示:①但愿,希望義;②或許,也許可以,推測義。所以二者可以糅合生成“庶幾乎”。
詞語糅合要遵循時代先后原則,即詞義相同或相近的兩個源詞語必須先于糅合詞語或跟糅合詞語同時存在。“庶幾”出現于春秋時期,如例(55)。表或許、差不多義的副詞“庶乎”最早出現在戰國時期,如例(56);而詞語“庶幾乎”也在戰國時期開始出現,如例(54)。從時間來看,“庶幾乎”有可能是由“庶幾”和“庶乎”這兩個同義詞語糅合而成。
(55)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于魯國乎!”(春秋《墨子》)
(56)且列國有兇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戰國《左傳·莊公十一年》)
詞語糅合要遵循成分蘊含原則,即糅合而成的新詞語必須蘊含兩個源詞語的主要或全部成分。“庶幾乎”蘊含了“庶幾”和“庶乎”的全部成分,并刪除了相同的構詞語素,這樣也符合語言表達的經濟原則。漢語以雙音節為標準音步,三音節為超音步,符合這種韻律節奏的結構才會和諧穩定,所以多音節詞通常縮略為雙音節或三音節詞。“庶幾”和“庶乎”組合后刪去一個重復的語素“庶”變成“庶幾乎”,也是受到韻律規則的制約。
由上可見,“庶幾乎”=“庶幾”+“庶乎”的觀點符合詞語糅合的同級原則、語義相近原則、時代先后原則、成分蘊含原則,所以應該是合理的。由此可見,“庶幾乎”的生成機制是糅合,而不是劉紅妮[4]所認為的由雙音節副詞“庶幾”和句中語氣詞“乎”詞匯化而來。
五、語氣副詞“XX乎”的共性與差異
(一)句法語義差異
從詞性來看,“無怪乎、無須乎、幾幾乎、庶幾乎”都是副詞(《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1],更具體來說都是語氣副詞。三音節語氣副詞“XX乎”在語義上更多地表現為差異性,都有各自的語義特點:“無怪乎”主要表示醒悟義;“無須乎”主要表示否定義;“幾幾乎”既可以表示十分接近的差不多義,也可以表示事情接近發生的差點兒義;“庶幾乎”既可以表示希望義,也可以表示推測義。
詞性相同、詞形相似的“幾幾乎”“庶幾乎”,由于語義上都可以表示推測義,所以有些語境中兩者可以互換。如果把例(57)中的“幾幾乎”改為“庶幾乎”,例(58)中的“庶幾乎”改為“幾幾乎”,替換后兩句的語義基本不變。
(57)我聽了云姑幾幾乎哭了一天,我的一顆小心落到痛苦的深窟里。(蔣光慈《鴨綠江上》)
(58)某曾偶遇一貓于路途。雖見其骨瘦如柴,羸弱不堪,且庶幾乎奄奄一息,因念家中鼠害甚烈,遂抱歸之。(《讀者》)
句法位置分布上,四個語氣副詞“XX乎”都可以分布在句首,也可以分布在句中,“無怪乎”還可以單獨使用。
(59)無須乎說,他因此發大財了。(王小波《懷疑三部曲》)
(60)唉!一生懷才不遇,從今天起我庶幾乎可以小試其端了!(老舍《誰先到了重慶》)
(61)無怪乎,當有些病人痊愈告別醫護人員時竟痛哭流涕,長跪不起。(1995年《人民日報》)
從韻律結構上看,“無怪乎、無須乎”都是“2+1”韻律模式,“幾幾乎”是“1+2”韻律模式,“庶幾乎”比較特殊,是由“庶幾”和“庶乎”同義疊加并刪去相同語素“庶”形成的。從語體分布來看,“庶幾乎”是個文言詞,主要用于書面語,口語中很少使用。“無怪乎、無須乎、幾幾乎”在語體分布上沒有什么傾向性規律,書面語和口語中都可以使用,并且兩種語體的使用頻率也基本相當。
(二)跟語氣成分共現的差異及動因
語氣副詞“XX乎”在跟句末語氣詞的共現類型及其制約因素上也存在差異。四個語氣副詞“XX乎”都可以跟句末語氣詞共現,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XX乎”與句末語氣詞的共現類型
從表1可以看出:四個語氣副詞“XX乎”都可以跟句末語氣詞“了、的”共現;只有“無怪乎”能跟語氣詞“呢、吧、哩”共現;只有“無須乎”可以跟語氣詞“嗎、呀”共現。
四個語氣副詞“XX乎”跟句末語氣詞的共現差異,主要跟語氣類型、語氣關聯、語氣融合三個因素有關。
1)語氣類型。為什么四個語氣副詞“XX乎”都可以跟“了、的”共現呢?這跟語氣類型有關:不同的語氣詞都有其常用的語氣類別,“了、的”主要表示陳述語氣,而四個語氣副詞“XX乎”也主要出現在陳述句中,所以“了、的”可以跟四個語氣副詞共現。
2)語氣關聯。由于“無怪乎、無須乎、幾幾乎、庶幾乎”都是語氣副詞,所以“語氣關聯”也是它們能跟句末語氣詞共現的原因。齊滬揚[15]將語氣劃分為意志和功能兩大類:意志類語氣以語氣副詞為主,表示說話人的主觀態度和情感;功能類語氣以語氣詞為主,表示說話人使用句子想要達到的交際目的。四個“XX乎”都屬于意志類語氣,“了、的”等語氣詞屬于功能類語氣。語氣副詞“XX乎”和句末語氣詞“了、的”等都可以從不同層次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情態和語氣要求,所以可以共現。
3)語氣融合。對于語氣副詞“幾幾乎、庶幾乎”來說,語氣融合也是制約它們跟語氣詞“了、的”共現的因素之一。在例(62)中,如果只用語氣副詞“幾幾乎”,只能表示說話人的主觀推測,其推測的結果并不確定。如果只用“了”,只能表示說話人的主觀確信。語氣詞“了”和“幾幾乎”共現后,兩者可以進行語義上的協調,使得句子整體上表示不太肯定的語氣。例(63)也類似,句末使用語氣詞“的”后,加強了對自己觀點的確信程度。
(62)地方的確興隆得極快,第二年就幾幾乎完全不像第一年的北溪了。(沈從文《旅店及其他》)
(63)這種觀念飛躍縱不是天生的毛病,從整個發展看也幾幾乎近于天生的。(沈從文《綠魘》)
四個語氣副詞“XX乎”在跟語氣副詞共現及其制約因素上也存在差異。結合前文的討論,“XX乎”跟語氣副詞共現情況,詳見表2。

表2 “XX乎”與語氣副詞的共現情況
由表2可見,三音節詞“XX乎”與語氣副詞的共現情況都有各自的特點:1)四個語氣副詞“XX乎”都可以與關系和或然這兩類語氣副詞共現;2)只有“無怪乎、幾幾乎”可以跟特點類和意愿類語氣副詞共現;3)只有“無怪乎、無須乎”可以與必然類語氣副詞共現;4)只有“無怪乎、無須乎、幾幾乎”可以和斷定類語氣副詞共現;5)只有“無須乎”能夠跟證實類語氣副詞共現。
四個副詞“XX乎”能否與語氣副詞共現,語義是一大制約因素。副詞“無怪乎”能跟關系類、特點類等語氣副詞共現,不能跟證實類語氣副詞共現,就跟語義有關。關系類、特點類語氣副詞都屬于評價類語氣副詞這個大集合,表示對句子所敘述內容的價值或特點的主觀評價。“無怪乎”本身就屬于特點類語氣副詞,所以能與其共現。證實類語氣副詞表示根據上文或當前情境對命題真實性的推定,而“無怪乎”表示醒悟義,即明白了原因對某種現象不覺得奇怪,兩者語義不相容,所以不能共現。或然類和必然類語氣副詞同屬于推斷類語氣副詞這個大集合,表示對命題真實性進行推測估量:或然類語氣副詞表示揣度性推測,必然類語氣副詞表示確定性推測。“幾幾乎、庶幾乎”都表示差不多義,所以能跟或然類語氣副詞共現,不能跟必然類語氣副詞共現。
(三)歷時演變與形成機制差異
從詞匯化時間上看,“庶幾乎”最早出現于戰國,在戰國時期由線性結構變成詞,表“或許、大概”義。“無怪乎”最早出現在宋代,受到“X乎”的類推作用,出現時就已經成詞,表示“醒悟義”。“幾幾乎”最早出現在明代,一開始出現時就是副詞,表示“十分接近、差不多義”。“無須乎”最早出現在清代,表示“用不著或不用”義。按照出現時間早晚,四個語氣副詞“XX乎”可形成一個等級序列:庶幾乎>無怪乎>幾幾乎>無須乎。
從語義固化程度上看,“庶幾乎”是古代漢語文言詞語的遺留,語義固化程度最高,表示希望義和推測義,詞義跟字面義看不出任何聯系。“幾幾乎”意思等于“幾乎”,表示差不多義、差點義,詞義與字面義有關聯。“無怪乎”,表示“明白了原因,對下文所說的情況就不覺得奇怪”的醒悟義,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解讀為“不覺得奇怪”也可以。“無須乎”表示“不用,不必”義,即詞義基本上等于字面義的相加。按照語義固化程度高低,就可形成等級序列:庶幾乎>幾幾乎>無怪乎>無須乎。
從形成機制上看,“無怪乎、無須乎”的形成機制都是類推,“幾幾乎”的形成機制是同義疊加,“庶幾乎”的形成機制是糅合。結合具體的語料,我們發現“無怪乎”和“無須乎”最早出現時就是副詞,應該是在“X乎”形成的基礎上類推而成的,因為考察二者的古代漢語語料,沒有發現能證明其詞匯化過程的例句。且“無怪乎”最早出現在宋代,“無須乎”最早出現在清代,此時雙音詞“X乎”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在雙音詞“X乎”的類推作用下,三音節“無怪乎”和“無須乎”成詞也不足為奇。
“幾幾乎”的形成機制是同義疊加。“幾幾乎”是由同表“接近義”的“幾”和“幾乎”進行疊加形成“1+2”的韻律結構形式,因為“幾”和“幾乎”的詞義中都包含著一種隱性的事態傾向義,為了使這種隱性的事態傾向義更加凸顯,“幾幾乎”一詞出現并被使用。且表“接近義”的“幾”和“幾乎”都早于“幾幾乎”的產生,這為“幾”“幾乎”疊加形成“幾幾乎”提供了可能。
“庶幾乎”的形成機制是糅合。即表希望和推測義的“庶幾”和“庶乎”,通過刪去相同的部分“庶”糅合成一個新詞“庶幾乎”。“庶幾乎”=“庶幾”+“庶乎”這一論證符合詞語糅合的同級原則、語義相近原則、時代先后原則、成分蘊含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