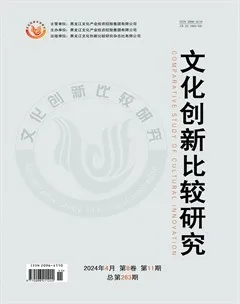多模態視角下民族非遺傳承與發展
邱心彥 許韻嘉 曾瑜
基金項目:云南藝術學院民族藝術研究院研究生特色品牌建設科研項目“多模態視角下民族非遺傳承與發展——以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為例”(項目編號:YJS2022TSPPOO4)。
作者簡介:邱心彥(1996,2-),男,山東青島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民族藝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摘要: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具有多元價值的民族財富,對民族非遺進行保護是具有深遠意義的時代課題。博物館是非遺傳承與發展的重要場域,也是博物館實現自身文化功能的重點所在。隨著科技的引用及多模態的傳播方式,非遺的傳播路徑逐漸從單一的影音圖像模式發展到多媒體、多元化、多模態等多種向外傳播非遺的方式途徑。該文通過對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這類綜合性場所向大眾傳播的方式方法展開研究,讓大眾從不同角度感受哈尼族非遺和哈尼族梯田的魅力,并且博物館借助新興的交互手段增強“科技賦能”的效果,助力觀眾以多種視角來感受哈尼族原生情境。通過分析博物館主題展覽與哈尼族內部文化語境之間的互動,增強觀眾在參觀過程中的感知與體驗。
關鍵詞:多模態;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非物質文化遺產;哈尼族;空間敘事;科技賦能
中圖分類號:G260?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文章編號:2096-4110(2024)04(b)-0088-05
National Non-Genetic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Multimodal Perspective
—Taking the Hani Terrace History Museum as an Example
QIU Xinyan, XU Yunjia, ZENG Yu
(Ethnic Art Research Institute, Yunnan Art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national treasure with diverse values and a profound issue of the tim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s are an important field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also a key focus for museums to achieve their own cultural functio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multimodal dissemination methods, the dissemination path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 single audio-visual image mode to various ways of external dissemination such as multimedia, diversification, and multimodality.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methods of comprehensive venues such as the Hani Terraces History Museum to the public, allowing the public to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Han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Hani terraced field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museum also enha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hrough emerging interactive means, helping visitors to experience the original Hani contex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By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useum themed exhibitions and the internal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Hani ethnic group, we aim to enhance the audience's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during the visit process.
Key words: Multimodal; Hani Terraces History Museu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i; Spatial narrativ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文化多樣性最直觀的表征,保護非遺就是保護多元文化的基礎,通過對非遺的保護,就會逐漸將保護視角轉移到傳承主體的族群文化及原生文化場景。透過非遺,可以看到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文化發展延續的價值所在,通過多模態的技術手段,還原原生場景,立足原生文化的發展、傳承的脈絡當中,重建中華文化的歷史價值。多模態是近三十年來不斷完善的研究課題,指從多個視角出發對事物進行觀察、描述及各種應用實踐。隨著科技及互聯網的發展,博物館作為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生活方式,單一的語言文字已經不能滿足大眾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知需求,逐漸開始從文字轉向聲音、圖像及影像等多模態方式,以感知渠道的多樣性、媒介的豐富性及符號資源的多元性和社會性來強化“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引發觀眾對非遺保護與發展的思考與興趣,增強傳播效果。坐落于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陽縣哀牢山區的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是世界文化景觀遺產——紅河哈尼梯田農耕文化的集中展示區。在以多模態為博物館設計理念的引領下,融合哈尼梯田文化的傳統智慧,充分展示世界文化遺產紅河哈尼梯田的千年農耕文化,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在地博物館的代表性展館,也是當地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典范。
1 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多模態敘事空間構造
紅河哈尼梯田以其壯觀、磅礴的梯田景觀于2013年6月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紅河哈尼梯田是以哈尼族為主的多個民族歷經1 300多年世代開墾的農耕文明杰作,其中心位置處于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陽縣哀牢山南部。因階數多,海拔落差大,儲水期倒映天空與朝霞、晚霞而馳名中外,最佳觀賞期為12月至來年3月。展館力求還原當地情景,以此來展示哈尼族生活原貌,利用互動技術讓觀眾親臨體驗,感知元陽的梯田美景,喚起觀眾對哈尼族“鄉愁”記憶中情感價值的理解與共鳴。
1.1 流線型空間敘事的多模態構造
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內部場館構造圍繞產生“梯田”的哈尼族及哈尼族文化為展示主體,梯田集中了哈尼族人文內涵,梯田景觀是哈尼族在惡劣條件下歷史遷徙的生存智慧,也是哈尼族最直觀的文化表征。元陽景區內的哈尼族以梯田耕種為主要生計手段,他們的日常勞作、飲食方式、節慶活動、音樂歌舞都離不開梯田。觀眾通過場館隨處可見的多媒體視頻去了解哈尼族民族語言、發展歷史等概況,從梯田到哈尼族日常生活,再到現代科技社會助力梯田的發展,將哈尼族獨具魅力的文化特色逐一體現,使人們在有限的空間里感受到哈尼族非遺所傳達的文化內涵。
通過流線型的場館布置,觀眾以梯田為線索,順著內部場景的走向,更直觀地了解梯田是哈尼族“萬物有靈”文化系統中最重要的關鍵節點。圍繞梯田,哈尼族文化產生了諸多國家級非遺項目,通過對非遺多個文化關鍵點的塑造,將哈尼族文化串起一條線,突出“梯田”主題,由梯田串聯起哈尼族生活狀態、勞動形態等文化要素,向觀眾呈現出元陽地區哈尼族的全貌。博物館將非遺還原于原生文化生活中,在有限的空間里“見人、見物、見生活”,并以流線型的敘事來展示哈尼族文化,不僅提升了哈尼族文化的傳播效率,破除了以往在傳統型博物館展示中形式單一、古板說教等缺陷,更向觀眾呈現出哈尼族非遺的原生生活環境,并由梯田引申到哈尼族地區的自然生態、勞作場景、民俗活動等,以此來引發觀眾的情感共鳴,其中每個展覽都是對展示環境的重新建構和塑造[1]。博物館以哈尼族梯田文化為主的敘事空間,構成哈尼族集體記憶與他者文化認同互動的獨特平臺,讓文化互動和交流成為觀眾連接自身與族群文化記憶的紐帶。觀眾通過具身來感知博物館所營造的哈尼族原生文化的原始生活村落,進而加深對哈尼族文化的理解與感知。
1.2 場景化空間的多模態營造
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內部館藏對哈尼族非遺進行詳細又全面的整理和保存,并不斷挖掘和記錄原生態歌舞文化,把哈尼族非遺的真實樣態原汁原味地保存、傳承下去。博物館在保護非遺的同時,注重展館科技與多媒體技術的應用,通過多模態的場館搭建來塑造一個哈尼族原生態氛圍的舞臺。博物館利用新科技,尤其是影像影音及互動設備的發展,動態地呈現《哈尼古歌》《四季生產調》等與哈尼族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第二部分“民族的智慧”主題單元中,特地用整個場館來構建哈尼族日常活動,通過場景的真實再現將該場館劃分成哈尼古歌、日常生活、哈尼舞蹈、節慶活動等部分。場館運用虛擬投影和播放哈尼古歌音樂兩種模態來進入哈尼族節慶的日常,跟隨音樂讓觀眾了解梯田是哈尼族的物質依托,通過吟唱來祈求一年風調雨順、稻谷豐收。
哈尼文化當中,“十月年”長街宴是一年中最隆重的民俗活動,在長街宴的展廳當中,從簡單的哈尼族長街布景的陳列拓展為哈尼族數字沉浸展,增加多種互動的音樂裝置帶給觀眾視聽上的感官體驗,整體還原哈尼族長街宴的原生環境,提升了觀眾對于哈尼族原生文化價值、歷史價值的直觀感受。通過還原哈尼族村落場景提升觀眾的參與興趣,增進觀眾與哈尼族文化之間的距離。同時,將非遺還原于哈尼族日常生活當中,讓觀眾以更直觀的視角來“參與”梯田的生產勞動,體驗哈尼族的“衣食住行”,以更加活態化的方式來了解哈尼族,感知哈尼族文化與梯田農耕文化的內在聯系。
2 多模態空間場景的內部闡釋
博物館的建成保存了逐漸流失的哈尼族文化,通過收集、展示、塑造原生場景等將哈尼族傳唱史詩、非遺、生活習俗等哈尼族民族文化進行保護和陳列,對哈尼族地區的文化傳承起到重要作用。隨著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的建成,哈尼族的非遺保護得到了有效解決,通過博物館的展覽向觀眾傳遞哈尼族非遺的內部語境,以多模態的互動方式向觀眾傳遞哈尼族信息。博物館敘事方式上注重在有限的空間里如何“由物及事”[2],即從物體的描述與表達中延伸到一個族群的文化、集體記憶及景觀的敘事內容,博物館的場景布展只是基礎載體,文化才是其核心。敘事的視角設置包含三層意義:一是選擇闡釋的角度;二是具有一定的目的;三是需要通過視角把意義和觀眾關聯起來[3]。這個敘事框架的主體借助多模態的傳媒手段來引人入境,在多模態的敘事過程中包含內化與外化兩個階段。內化階段深入探索哈尼族地區無形文化遺產的價值,側重于隱性文化內涵的挖掘;在外化表達上注重多模態手段的敘事方法,以多學科視角來展示哈尼族自然、人文、歷史等多方因素影響下產生的物質載體的動態發展歷程,通過相關物質載體的展示和輔助性的媒介技術加以補充介紹,讓觀眾更進一步了解哈尼族集體記憶,來達到感知、體驗的目的,讓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在哈尼族文化傳播中起到重要作用,促進文化的傳承。
2.1 口傳身授——集體記憶傳承建構
哈尼族是我國云南地區的跨境民族之一,境外分布于泰國、老撾、越南等國。其分布地區較廣,內部支系眾多。自稱與他稱說法不一,有哈尼、豪尼等十多個自稱[4],如沿紅河流域,其上游元江地區部分哈尼族自稱“臘咪”,下游稱為“臘比”。我國境內統稱為哈尼族,境外稱為阿卡人。眾多的自稱和他稱反映的是哈尼族在遷徙歷史時期的定居環境、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等不同情況[5]。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集中介紹了哈尼族的歷史往來及遷徙歷史,將其進行藝術化的處理,以直觀的布展將哈尼族族群從起源地“虎尼虎那山”被迫遷徙,從今四川地區沿云南曲靖、昆明、大理三條遷徙路線逐漸向哀牢山南部元江、墨江、紅河等地定居,最終向老撾、越南、泰國等地遷徙定居。通過對哈尼族族群源于遷徙歷史的展示,增強哈尼族人對自我歷史文化與族群記憶的認知,以此來保護多元文化的歷史。由于哈尼族沒有文字,相關的傳說與遷徙傳唱史詩都是口頭相傳,傳承極為不易,博物館將早先翻譯整理的《哈尼阿培聰坡坡》《十二奴局》《哈尼古歌》等傳唱文學進行集中保存,以物質載體對哈尼族族群的文化記憶進行展示,通過音樂、視頻、投影、電子互動展示屏等綜合地展示哈尼族群珍貴的傳唱文學史詩,并與在地風貌相結合,轉化為另一種文化資源。利用視聽效應營造出一種鄉村與歷史相交織的空間景觀,以此來增強哈尼族族群對自身文化與集體記憶的認同。以場景構建的形式實現口頭傳承向物質載體的轉化,讓族群的歷史記憶有了集中保存的場所,博物館運用多種模態的展示效果讓存在于記憶里的文化有了實景化的演示效果,組成了“地域+遺產+記憶+居民”的生態博物館,既超越了傳統博物館的功能,豐富了記憶與情感的承載方式,又讓博物館成為承載文化記憶當中的重要一環,保護了哈尼地區集體記憶的向下延續。
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不僅創造了一個新的公共空間,更形塑了一種新的文化傳承機制[6]。不同地區哈尼族的風俗習慣不同,所以哈尼族內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和形式也略有不同,博物館將不同支系的哈尼族非遺集中展示,有利于哈尼族各支系對自身民族的認知與認同,增強哈尼族內部文化的交流往來。
2.2 留住鄉愁——整體生態文化保護
哈尼族是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典范,其村規民俗中對水、田、山林的要求極高,對于水源,哈尼族總結出“木刻分水”這一方法以確保到達各家梯田的水都是公平的;對于有肥力的水源,各家各戶也互相遵守約定,不得擅自打開梯田的入水口。博物館將哈尼村落的村規進行集中展示,通過圖片、文字的講述喚起觀眾對習俗禮儀的思考,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展示了哈尼族非遺的原始文化生境,以更加鮮活的活態化傳承方式增進不同文化程度觀眾對非遺價值的認知與理解,也讓非遺不再是一種保護的對象,而是一種文明的集中展示,一個地區鮮活的族群文化記憶,更建構起博物館保護和傳承文化多樣性發展的職能,還原了非遺文化生態與傳統鄉村的完整性。其中,對村規民俗的保護才是讓村落“活”起來的關鍵,其是地方文化對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的總結,是鄉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法則。從物質載體的空間場景延伸至“非物質”文化的思考,將背后的文化傳統與生活習俗相關聯,通過多種物質載體的展示來構建哈尼族整體的文化風貌。
通過展示讓觀眾感知傳統的耕種方式,有利于讓游客了解哈尼族人與自然互相協作的民族文化,破除文化壁壘,完成對哈尼族身份形象的初步了解。同時,將觀眾帶入傳統哈尼族互相協作場景,以此來提升觀眾與哈尼族文化的交流互動,并保持文化的強有力發展。既提升了觀眾對傳統生活方式的了解,也保留了哈尼族文化的現實傳承需求,也是記錄、保留哈尼族村落整體風貌的最好方式。博物館完整記錄了哈尼族的集體記憶,將哈尼族文化中的人、物、環境、自然多方之間的固有生態關系進行集中保護,將哈尼族社會結構與自然風貌完整保留的同時,也將哈尼族非遺包括風俗習慣、日常生活、審美取向等完整地保留進博物館,也是哈尼族認識自我的精神載體之一。
3 多模態視角下民族非遺傳承與發展啟示
3.1 增強游客文化感知力
以多種模態的展陳方式向觀眾展示物質載體或虛擬載體等哈尼族地方性獨特文明,更以全方位的博物館敘事理念向觀眾展示哈尼族生活的全樣態。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將元陽地區哈尼族各支系相同的民俗節慶、生活習俗進行陳列展示,也將不同支系的服飾、歷史文化等進行逐一介紹,對哈尼族原生態文化及非遺的傳承與傳播起重要作用。原生態文化一般藏匿在民間,尤其在少數民族地區,是由其先民在漫長的征服自然、繁衍生存的過程中創造的,與民族的鄉土環境、人文歷史、民俗風習融為一體[7]。博物館利用多媒介展示手段向觀眾傳遞哈尼族原生態文化更有效的信息,促進觀眾與哈尼文化的交流互動,有助于觀眾對哈尼族的民族形象有基礎的認知,提升邊疆地區民族文化的傳播效率。
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利用內部場館空間,搭建起哈尼族原生態文化的空間展示構造,并通過自身的構造搭建起哈尼族文化的舞臺,向觀眾呈現哈尼族文化的實景演出。以實體性的場景演出,讓觀眾更高效地接收哈尼族文化信息。
3.2 塑造完整哈尼族形象
哈尼族文化圍繞“森林—水源—村莊—梯田”組成“四素同構”,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基于此來建成內部展館空間。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在建筑造型上取材于哈尼族地區森林中的圖騰鳥——白鷴鳥,建筑外形呈現哈尼梯田的靈活布局,與當地梯田相融合,依山而建,呈階梯狀。內部場館共有四大主題:人類的杰作、民族的智慧、莊嚴的承諾及中意友好展。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屬于地區性的綜合類博物館,內部展館具有陳列展示、保護非遺和研究民族文化的功能。博物館圍繞梯田向觀眾展示元陽梯田景區周圍生物的多樣性及多樣的自然景觀,并收集、展示元陽地區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詳細介紹哈尼族的遷徙歷史、生活習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等。通過展館向觀眾展示元陽地區哈尼族、彝族等多民族混合聚居的民族風情,根據展館內不同顏色的服飾觀眾可以了解元陽地區愛倮支系、郭和支系、白倮支系等哈尼族豐富的服飾文化,不同服飾展示了哈尼族的民族特色與風格特點。
3.3 拓寬傳播渠道
哈尼梯田的向外傳播較為薄弱,易與龍脊梯田混淆,多數游客更不知曉哈尼梯田的最佳觀賞期,許多前來的游客因冬天大霧天氣失望而歸,這是宣傳不到導致的。哈尼梯田歷史博物館建成之后,景色與導覽就有了相應的保障,利用該平臺發布天氣預警及各村落梯田的最佳觀賞信息會贏得游客的口碑,進而帶動文化與經濟的繁榮。
通過多種展示形式、多種科技手段向觀眾展示哈尼梯田波瀾壯闊的景色及世代口頭傳承的文化魅力。觀眾也擺脫了過去靠閱讀來想象、還原的單一情境,通過場景塑造來刺激多感官的互動,增加觀眾對參觀游覽過程中的感知、體驗,成為一種原生地開發模式[8]。以多模態的視角分析博物館將哈尼文化轉換為觀眾所能理解的文化的感知方式,增強哈尼族文化向外傳播的媒介手段。在地博物館集中展示哈尼族文化,其文化背后是上千年以來哈尼族先人的智慧結晶,多種科技手段集中展示、還原哈尼梯田原生環境,以多模態的敘事方式引人進入哈尼族的族群記憶,讓觀眾高效地認識哈尼族、認識哈尼梯田。博物館還利用內部場館,搭建起農產品售貨平臺,利用哈尼族元素符號來提升文化創意的設計,帶動農產品的銷售,促進鄉村經濟的發展,為文化的傳承提供強有力的現實保障。通過博物館平臺,帶動周邊文化的發展,承擔起元陽地區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使命[9-10]。
4 結束語
博物館在特定文化語境的轉化中必定要兼顧全方位的文化輸出理念,這個理念的建構過程伴隨著多模態的思維解構為符合現代觀念的認知方式,這個過程可以理解為一種創作,即接受外來技術并運用到哈尼族傳統文化當中,雖然受到文化意義及語言理解程度的影響,但總體上還原了在地文化的傳統生態環境,促使參觀者身臨其境地參與體驗,使參觀者產生記憶共鳴,進而增強所屬群體的文化認同。將過去的文化記憶融入現代生活的發展中,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也是對族群集體記憶的保護。筆者于元陽梯田地區進行實地調研,恰逢路邊一群人正在進行祭拜活動,詢問司機師傅得知,都是即將外出打工的人,因為趕不上年內的重大節日,所以對交通要道上的水、樹進行祭拜,以此來祈求一年的平安,一把香、一點米都是文化在內心的延續,一方水土的樹與物都是情感的寄托。鄉村文化在城市的快速發展中急速轉變,在這種社會的變革中不得不思考鄉愁的未來,如何讓鄉愁更多地保留住,博物館是保存這些記憶最好的方式。
參考文獻
[1] 李佳一.從展場到展覽:中國當代藝術博物館展覽空間研究[D].上海:上海大學,2018.
[2] 馬玉靜.“數字人文”視域下的博物館文化遺產數據資源開發模式研究[J].中國博物館,2022(4):102-106.
[3] 何修傳,夏敏燕.空間敘事:博物館展示主題的意義建構與話語體驗[J].藝術百家,2022,38(1):178-184.
[4] 《哈尼族簡史》編寫組.哈尼族簡史[M].修訂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5] 雷兵.哈尼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
[6] 武洪濱.博物館敘事語境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2,36(1):183-192.
[7] 黃永林.“文化生態”視野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J].文化遺產,2013(5):1-12,157.
[8] 賈鴻雁.論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性旅游開發[J].改革與戰略,2007(11):119-122.
[9] 韓曉明,喬鳳杰,楊慧.博物館的空間與記憶敘事對文化認同的建構與形塑:以中國太極拳博物館為例[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1):125-133.
[10]黃夢君,張照然,張楊.基于用戶體驗的多模態數字場景構建策略研究[J].設計藝術研究,2023,13(2):6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