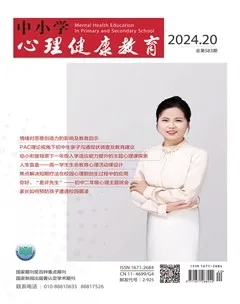經(jīng)典理論思想俱是“春風(fēng)化雨?潤物無聲”
侯瑞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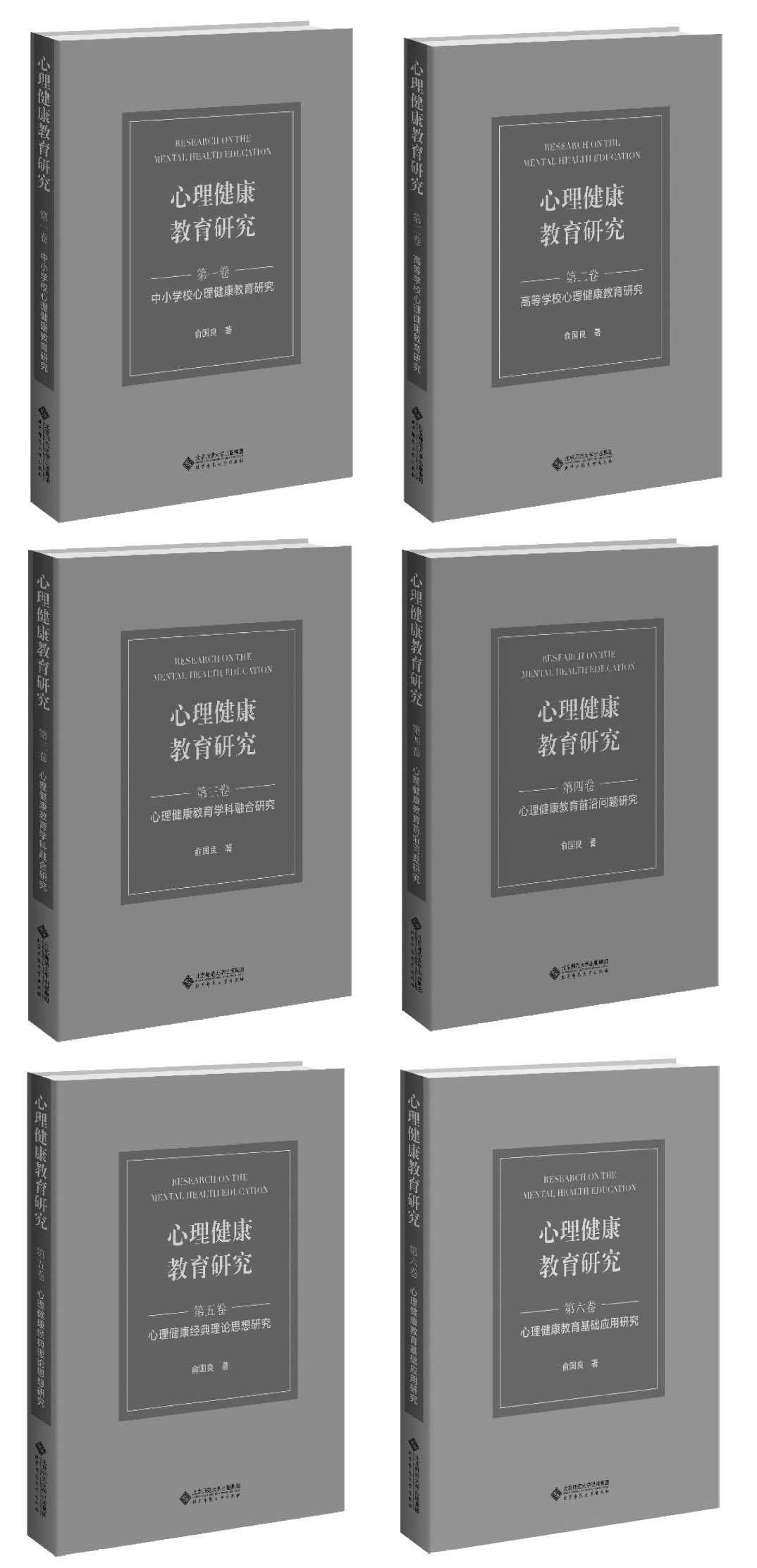
關(guān)鍵詞:心理學(xué)家;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意義
中圖分類號:G44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B文章編號:1671-2684(2024)20-0078-03
“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xué)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恩格斯),而要深入理解一個理論,一定要認(rèn)真研究提出理論的人。心理學(xué)理論如此,心理健康教育理論更是如此。
事實上,世界上每一個人,不管你是否意識到,都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樸素心理理論,不同的理論從不同的視角和層面,提供了人的內(nèi)在世界的不同畫面。心理大師只是更有意識、科學(xué)、系統(tǒng)化地總結(jié)概括了他們的心理理論。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俞國良教授新作《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第五卷“心理健康經(jīng)典理論思想研究”,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多視角理解人內(nèi)在世界的畫面。相信,不同的人可以從中品嘗到屬于自己的味道。
作為一名心理學(xué)工作者,雖然在心理健康教育領(lǐng)域辛勤耕耘已超二十載,然而,當(dāng)我拿起這部書并沉浸其中閱讀時,仍然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新鮮氣息。就像有一位老朋友坐在我的面前,如數(shù)家珍地向我介紹心理領(lǐng)域的大師,或傳奇、或有趣、或顛沛流離,或神秘、或沖突、或平順、或掙扎,但同樣是精彩的人生。我一路跟隨著大師成長的步伐,時而遺憾,時而驚嘆,那些抽象的概念也逐漸變得鮮活起來;一些略顯艱澀模糊的理論放到大師的生活經(jīng)歷中,也逐漸清晰、落地而變得親切起來。在領(lǐng)略大師思想的過程中,我時不時地掩卷沉思,感受和思考自己即將過半的人生。時不時地在某一刻,電光石火般跨越時空,我理解了自己的同時,也讀懂了大師。在人的層面上,我和大師有了更多、更深的聯(lián)結(jié)。是的,我們本來就是一樣的“物種”,感動在心中蕩漾開來。猶如鬧市中盛開的牡丹和深山里的野花,不管璀璨還是默默無聞,生命的本質(zhì)都是努力活出自己本來的模樣。
“心理健康經(jīng)典理論思想研究”選擇了18位致力于心理研究的大師,并對他們的思想進(jìn)行研究和梳理。大師名錄來自一項名為“20世紀(jì)最杰出的100名心理學(xué)家”(其實是99名)的調(diào)查,這項調(diào)查是國際心理學(xué)界久負(fù)盛名的《普通心理學(xué)評論》雜志在21世紀(jì)初公布的。作者根據(jù)心理學(xué)科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以精神分析、行為主義、人本主義與認(rèn)知主義為綱,把18位大師分到了四個經(jīng)典流派里,幫助讀者把握心理健康教育思想發(fā)展的歷史脈絡(luò),同時也使大師的理論和思想各有所屬、各有所依。特別是,從大師的生平到理論提出的背景,帶著讀者回到理論提出的第一現(xiàn)場,了解理論背后的故事,發(fā)現(xiàn)高大上的大師其實擁有我們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樂、掙扎和彷徨,理論也變得可愛和好懂了。比如,提出心理發(fā)展八階段理論的埃里克森,其自我認(rèn)同理論何嘗不是對自己身份認(rèn)同的救贖與努力。同時,大師彼此之間并非孤立,通過了解他們的故事,可以看到大師平凡如你我的另一面,他們之間有如師如友的關(guān)系,也有愛恨交織穿插其中。透過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也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理解了不同理論之間的相異和相同、傳承與發(fā)展,典型的如弗洛伊德和榮格、阿德勒之間從相見恨晚到分道揚鑣的故事。了解了人的故事,就理解了彼此之間理論的傳承與發(fā)展。更何況這些悲喜誠如你我生活的日常,只是不一樣的舞臺而已。
當(dāng)然,了解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回應(yīng)當(dāng)下和未來。作者雖然論述的是20世紀(jì)的大師,但是穿越時間的長河,歷久彌新,對當(dāng)下我們的生活仍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指導(dǎo)意義。下面僅就精神分析理論擷取一二,與大家一起分享。
埃里克森在提出人生八階段理論時,雖然強調(diào)小學(xué)階段是勤奮感的發(fā)展,他同時也強調(diào)了過度用力會導(dǎo)致出現(xiàn)心理問題。他提到,“如果孩子過分重視,把某種工作或?qū)W業(yè)作為唯一有價值的標(biāo)準(zhǔn),看不到人類生存的其他重要方面。那么就可能發(fā)展成為一個因循守舊的人,成為他自己的技術(shù)和可能利用他的技術(shù)的那些人的毫無思想的奴仆。對這樣的人來說,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而看不到生活的其他意義。”當(dāng)我們把視線從書中拉回現(xiàn)實,你會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總是比理論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當(dāng)下一些學(xué)業(yè)優(yōu)秀的青少年產(chǎn)生的心理健康問題,或許比起埃里克森所處的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看到,有一部分同學(xué)選擇了退縮,或許再也沒機會當(dāng)一個哪怕是沒有思想的工具了,但他在拒絕成為工具的同時,徹底失去了對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因此,基于埃里克森的理論,對于學(xué)業(yè)優(yōu)秀的中小學(xué)生而言,我們要強調(diào)其生活的其他方面,弱化學(xué)業(yè)本身對其生活的重要性。而對于學(xué)業(yè)一般的學(xué)生,則要通過鼓勵和信任,促進(jìn)其勤奮感的發(fā)展。
關(guān)于現(xiàn)代性問題,榮格已經(jīng)很有前瞻性地進(jìn)行了反思。榮格與弗洛伊德不同,他認(rèn)為心理治療的目的是發(fā)展健康人格,而不是消除癥狀;并且認(rèn)為神經(jīng)癥的癥狀是人們的精神嘗試自我調(diào)整的一種企圖,是病人在無意識深處想獲得更完整人格的一種外部表現(xiàn)。他雖然強調(diào)人性積極的、創(chuàng)造的一面,同時也認(rèn)為人性本身具有的黑暗性也是人的健康和平衡發(fā)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中蘊藏著創(chuàng)造力,是生命的源頭活水。當(dāng)時,榮格已經(jīng)對現(xiàn)代性進(jìn)行了反思,認(rèn)為現(xiàn)代人的意識過于發(fā)達(dá),無意識受到過分壓抑,將導(dǎo)致人的異化,被壓抑的能量很可能會以陰影等負(fù)面原型的形式進(jìn)行補償,從而反過來傷害人類自身。因此,榮格強調(diào)超越性的內(nèi)容對人的健康具有很大的價值,而現(xiàn)代人缺少的正是這種東西。顯然,現(xiàn)代人如何活得更超越一些,是提升身心健康,尋求生命意義的重要途徑。
然而,這些精神分析大師并非一開始就來到了心理學(xué)、心理健康教育的殿堂,而是經(jīng)歷了輾轉(zhuǎn)反復(fù),才找到了自己的責(zé)任與使命。
埃里克森早年壓根沒有受過正規(guī)院校教育,他學(xué)習(xí)過藝術(shù)、歷史和地理,后來又擔(dān)任過小學(xué)的美術(shù)老師,在那里結(jié)識了安娜·弗洛伊德,命運的齒輪開始轉(zhuǎn)向。直到此時,他“尋找自我”的生命底層動機終于找到了安放的地方,從此投入精神分析的懷抱。
榮格大學(xué)選擇的是醫(yī)學(xué)專業(yè),直到快要大學(xué)畢業(yè)時讀到關(guān)于精神病學(xué)的教科書,24歲的他立刻意識到,精神病學(xué)研究正是他命中注定要從事的職業(yè)。相對于醫(yī)學(xué),對于當(dāng)時的社會背景而言,他真的是丟了金碗,撿起來的甚至連個碗都不是,當(dāng)時精神病學(xué)可是沒有前途的“荒唐”職業(yè)。事實上,榮格早年就對歷史、哲學(xué)很感興趣,也有一些神秘體驗,只是為了更好地支持家用,他才選擇了醫(yī)學(xué)。然而,好飯不怕晚,當(dāng)他有一天真正與命中的“天使”相遇時,就立刻認(rèn)出了它。其實,這個聲音一直都在,只不過榮格在合適的時候傾聽并尊重了自己內(nèi)在聲音的引領(lǐng)。
鮑爾比的童年經(jīng)歷了母愛剝奪,他從事心理學(xué)工作后一生致力于母愛剝奪與依戀的研究。他開始就讀的是海軍學(xué)院,后來作為海軍學(xué)員在戰(zhàn)艦上接受訓(xùn)練。枯燥的訓(xùn)練使他想方設(shè)法退出后改學(xué)醫(yī)學(xué),在學(xué)校最后一年里,他第一次讀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埋下了踏入心理學(xué)領(lǐng)域的種子。之后,他將畢生的精力放在了研究依戀與分離的問題上。這顯然與其成長經(jīng)歷密切相關(guān)。7歲被送往寄宿學(xué)校的鮑爾比,稱寄宿為可怕的時期,他曾說:“即使是一條狗,我也不會在他7歲的時候把他送往寄宿學(xué)校。”這些經(jīng)歷使他尤其對兒童遭受的苦難非常敏感,也成就了他在心理學(xué)史上的地位。他一生都關(guān)注兒童福祉,這何嘗不是在安撫早年的自己。回頭來看,生命中經(jīng)歷的痛苦,好像早已暗暗標(biāo)了價,在合適的時候,就會出現(xiàn)在你眼前,體現(xiàn)出它的價值所在。鮑爾比的“痛”也是他一生的職業(yè)使命所在。當(dāng)然,痛苦的經(jīng)歷能否被轉(zhuǎn)化,也取決于個人的勇氣和力量。比如克萊因和鮑爾比之間對母親角色理解的分歧,使鮑爾比即使被當(dāng)時的主流精神分析所排斥,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因為那背后是對自己生命體驗的誠實。否則,就如榮格在動手寫《無意識心理學(xué)》時,即使努力壓抑,他再也無法忽視與弗洛伊德觀點的差異,因而感到痛苦不堪。最終榮格頂著巨大的壓力,同樣選擇了對自己生命體驗的誠實,而與如父般的弗洛伊德決裂。
雖然與大師身處不同時代,但是,大師走上心理健康研究生涯的道路,留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對于越來越內(nèi)卷的現(xiàn)代社會,職業(yè)本身能夠給人提供的安全感越來越小,大廠、公務(wù)員、體制內(nèi)都不再能提供真正的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來自你對所從事工作內(nèi)容的一份“篤定”。這需要我們能夠靜下心來傾聽內(nèi)在的聲音,對自己真誠,再加上勇氣和堅持,相信不管從事什么工作,必將走出屬于自己的職業(yè)道路。這些恰恰是現(xiàn)代人所欠缺的。通過與大師的交流,希望能夠幫助我們找回本來屬于自己內(nèi)在的本質(zhì)力量。
總之,“心理健康經(jīng)典理論思想研究”通過大師們真實而感人的故事,在展現(xiàn)其成長和心理健康思想的過程中,也教會我們學(xué)會坦然面對人生的痛苦與沉浮,打開心理的空間,臣服生命的各種恩賜。正如圣人所言:雷霆雨露俱是天恩,逢魔遇佛皆為度化。大師們曲折的人生之路完美地詮釋了“世上一切因緣所生,不必遇喜狂歡,遇悲消沉”。關(guān)鍵是我們以什么樣的心態(tài),如何正確面對成長路上的“雷霆”和“魔鬼”。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xué)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博士、副教授)
編輯/張國憲 終校/孫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