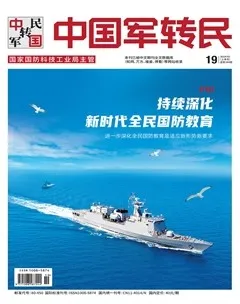中華傳統文化視角下的軍民融合思想
【摘要】在中華傳統文化中,軍民融合思想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從富國強兵思想、備具思想、重民思想和以法治軍思想,借鑒當今軍民融合理論統籌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注重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向政治層面和法治化發展,對于軍民融合理論實踐具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軍民融合|傳統文化|富國強兵|備具|重民|以法治軍
清朝晚期的劉璞在《將略要論》中曾提到“民為兵之源,兵無民不堅”“兵為民之衛,民無兵不固”,前者強調軍隊如果脫離了民眾,就會“如魚失水”;后者表明民眾如果沒有軍隊的保護,就會“如卵失殼”,因此需要“倚民養兵,倚兵護民”。軍民融合在我國歷史上經過了原始社會末期的兵民合一簡單模式,又經過了戰爭專業化之后的兵民短暫分離,后來逐漸發展到了軍民融合中的以農養戰模式。農戰結合更是發展為了遼宋至清朝前期軍民融合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元末的朱元璋和明末的李自成都是農民領袖,本身更是善于組織農民進行戰爭。通過當時的軍民融合,不僅解決了糧食補給問題,軍隊力量建設問題,在戰法上也創造出了流動作戰、以走制敵等新式戰法。因此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有益養分,對于推進當代軍民融合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借鑒古代“富國強兵”,軍民融合統籌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
我國古代軍事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備戰思想,而備戰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物質準備。《孫子兵法》曾提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1]”,強調了物質儲備、武器裝備的重要性。與孫武同一時期的齊威王,也曾召集過當時的軍事思想家討論如何強兵。彼時的儒家認為要通過“政教”強兵;墨家認為要通過“散糧”強兵;道家認為要無為而治,也就是以靜強兵。只有兵家的代表孫臏認為,以上“皆非強兵之急[2]”,“富國”才是“強兵之急”。在軍隊建設方面,軍需物質是以經濟的富庶作為基礎的。儒家主張的思想政治教育、墨家主張的提高士兵待遇、道家主張的提高治軍效率,最基礎的首先是經濟實力。甚至建立在絕對的富國基礎之上的強兵,還可以實現“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3]”。可見在我國古代備戰思想的關鍵就是富國強兵,富國是強兵的基礎。
富國的主力是人民,強兵的主體是軍隊,富國與強兵在當代最好的結合就是人民與軍隊的結合,即軍民融合。人民作為主力做好經濟建設,軍隊作為主體做好國防建設,因此軍民融合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統籌好人民和軍隊,統籌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習主席在2013年3月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曾指出,“要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進一步做好軍民融合式發展這篇大文章”,說明軍民融合的應有之義便是統籌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在2013年8月,習主席視察沈陽戰區時強調,“要拓展軍民融合的領域和范圍,積極推進國防經濟和社會經濟”的兼容發展;在2014年3月的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指出,軍民融合要“遵循國防經濟規律”,說明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軍民融合大有可為,其深度和廣度是一個動態可持續發展過程。
二、源于古代“備具”思想,軍民融合重點關注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
從春秋時期開始,我國傳統兵學就認識到了武器裝備的重要性,認為建設軍隊需“備必先具”,并作為戰爭制勝的先決條件。如《論語·衛靈公》曾提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4]”,強調器具的重要性;《管子·參患》也提到“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5]”,《管子·幼官》更提出“備具,勝之原[6]”,認為要想“制敵”,首先要“致器”。沿襲到明代的戚繼光在《練兵實紀》中也強調“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7]”。
既然武器裝備如此重要,軍用技術就尤為關鍵。據春秋時期的《考工記》記載,當時的軍事工業已經十分精細。僅當時常用的武器裝備戰車的制造就達到了70多道工序,其中木工就有7部,金工有6部,革工也有5部。
我國傳統兵學雖然重視“備具”,也重視軍用技術的發展,但是需要找到一個更好地提升武器裝備的路徑,也就是軍民融合。立足于現有的生產力水平,充分實現民用技術為軍用技術所用,縮短民用領域與軍用領域的時間差,提高民用技術轉化為軍用技術的即時轉化率,甚至從項目規劃開始便著眼于武器裝備升級的目標。
習主席在2013年8月視察沈陽戰區時曾講過,軍民融合需要“軍用技術和民用技術”兼容發展;在2014年12月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又指出,要“扎實推動國防科技和裝備領域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在2017年3月的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又強調“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是軍民融合發展的重點,也是衡量軍民融合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我們發現,軍民融合發展的思路,始終圍繞著軍用技術和國防科技展開,始終致力于通過科技促進武器裝備的提升,這是古代“備具”是“勝之原”軍事思想在當代的新發展。
三、源于古代“重民”思想,軍民融合最核心的是政治層面
早在春秋時期,民本主義思想就已萌芽。在《左傳·桓公六年》中曾記載了季梁對隋侯的說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8]”,說明當時已出現了以民為神,或者重民輕神的現象。在《詩經》中也記載了當時民眾對于不同性質的戰爭,持有不同的態度,如《無衣》中的“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9]”,體現了民眾擁護正義戰爭;而《何草不黃》中的“哀我征夫”“朝夕不暇[10]”,體現了民眾詛咒兵役徭役,反對不義戰爭的態度。民眾對于不同性質戰爭的態度,是孫武所認為的戰爭制勝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道”。孫武認為戰爭制勝因素有五個,他稱其為“五事”,即道天地將法,顯然“道”是“五事”之首。孫武主張“修道”,強調“道勝”。孔子也認為“民無信不立[11]”,這里的“民信”也是“道”,即政治與民心。可以看出,當時的兵家很“重民”,也倡導“保民”。孫武備戰思想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思想準備,即政治準備。在做法上,孫武一是提倡“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12]”,即“素教”,也就是平常的作風養成教育;二是提倡“與眾相得[13]”,也就是加強與民眾的團結,這樣才能“攜手若使一人[14]”,延伸至現在,就是軍民融合的深度發展,從“術”“器”層面向“道”的層面發展。
習主席在2014年10月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形成“軍民融合的政治工作格局”;在2015年2月看望駐西安部隊時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維護軍政軍民團結”,深入推進軍民融合。這說明源自于春秋時期的民主主義思想,孫武倡導的“道勝”“政勝”,應是軍民融合最核心的本質。
四、延伸于古代“以法治軍”思想,軍民融合上升至法治化層面
早在西周時期,《易·師》曾提到“師出以律,否臧,兇[15]”,孫武也把“法”作為了“道天地將法”戰爭制勝的五因素之一。實際上,古代治軍基本都是以“法治”作為核心的。孫武曾講過:“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16]”。曲制,是軍隊組織編制;官道,是人事制度;主用,是軍備物資的供應管理制度。也就是說,當時的“法”是包括管理軍隊的一系列制度的。且孫武認為法令素行,才能形成穩定的戰斗力。同一時期的《司馬法》是當時齊國的古老軍法,這種軍法也不只是“軍法處置”“軍法從事”中的賞罰紀律規定,而是涵蓋了管理軍隊層面的所有的“法”。
同理,軍民融合作為一項與強軍相關的政策舉措,也應有法可依、依法進行。習主席在2013年提出要“做好軍民融合式發展”,在2018年10月的十九屆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時指出,要“提高法治化水平”,“加快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經過五年探索,習主席第一次把軍民融合上升到了法治層面。至此,以法律法規明確軍民融合具體做法,從法治角度使其成為常態化工作,是我國軍民融合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顯著標志。
五、結語
總體來看,當代軍民融合理論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根源,這是其在當今社會主義中國煥發勃勃生機的重要原因。源于古代富國強兵、備具、重民與以法治軍思想,當代軍民融合統籌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注重國防科技與武器裝備、強調軍民融合政治工作與注重軍民融合法治化。中華優秀傳統中厚重的軍民融合思想,蘊含著緊密的軍地鏈接與先進做法,從中汲取養分發展當代軍民融合理論很有必要。中國軍轉民
參考文獻
[1]吳九龍.孫子校釋[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115.
[2]孫子·孫臏兵法·尉繚子.李敖,主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309.
[3]劉仲平.尉繚子今注今譯[M].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11.
[4]論語譯注.楊伯峻,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9:161.
[5]管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29.
[6]管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3.
[7][明]戚繼光.練兵實紀.邱心田,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1:236.
[8]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一)(修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6:165.
[9]程俊英.詩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8-199.
[10]程俊英.詩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05.
[11]論語譯注.楊伯峻,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9:124.
[12]吳九龍.孫子校釋[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165.
[13]吳九龍.孫子校釋[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165.
[14]吳九龍.孫子校釋[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202.
[15][商]姬昌,[春秋]孔子.易經·尚書[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13:11.
[16]吳九龍.孫子校釋[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9.
(作者簡介:蘇宏雁,空軍航空大學,碩士,助教;呂興江,空軍航空大學,碩士,教授;劉海峰,空軍航空大學,碩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