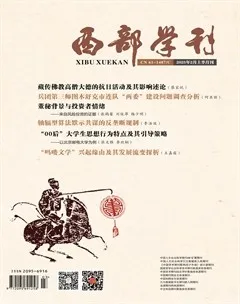網絡欺凌中旁觀者的內涵、影響因素和轉化策略
摘要:網絡欺凌旁觀者是指在網絡互動環境下人的虛擬在場,但在網絡欺凌事件中并未直接參與其中的群體,主要類型包括網絡欺凌助推者、網絡欺凌煽風點火者、網絡欺凌局外者和網絡欺凌中受害者的保護者,對受虐者情況的判斷、共情反應、社會責任感、社會自我效能感和風險評估等因素影響角色選擇。實現旁觀者的轉化要以新時代公民道德培養為依據,加強學校道德教育;以新時代家庭道德教育為遵循,引導正確道德實踐;以回歸生活的德育觀,培育社會責任感。
關鍵詞:大學生;網絡欺凌;旁觀者;影響因素;轉化
中圖分類號:G44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5)03-0113-04
The Connot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of Cyberbullying Bystanders
Li WeiQin Linzi
(Xiangnan University, Chenzhou 423000)
Abstract: Cyberbullying bystanders refer to people who are virtually present in the network interactive environment, but are not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yberbullying incidents, the main types include cyberbullying facilitators, cyberbullying instigators, cyberbullying bystanders and protectors for victims in cyberbullying, which influence the role selection, empathy,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risk assessment, factors such as judgment of the victim’s situation, empathic respon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cial self-efficacy and risk assessment influence role selection.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bystanders, we should 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s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civic morality in the new era; guided by the family mo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guide the correct moral practice; cultivate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returning to the moral education of life.
Keywords: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cyberbullying; bystanders; influencing factors; transformation
截至2023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10.92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77.5%[1]。網民在通過網絡空間獲取信息與發表個人意見,充分享受互聯網帶來的巨大紅利的過程中,網絡欺凌應運而生。網絡欺凌是傳統欺凌在網絡空間的延伸,是虛擬空間中的施暴行為,具有普遍性與隱蔽性,主要表現為通過網絡針對個人或群體組織肆意發布謾罵侮辱、造謠誹謗、侵犯隱私等信息的網絡暴力行為,對網絡秩序和網絡生態造成嚴重破壞,影響著社會公眾的信任與安全感。據調查,有10%—21.9%的大學生曾出現過網絡欺凌行為,55.3%的大學生在網絡上至少被欺凌過一次[2]。在完整的欺凌鏈條中包括欺凌者、受虐者、旁觀者,一個遭受暴力的個體,難以憑借自己之力擺脫暴力,而旁觀者是否參與其中將對欺凌的強度和后果產生影響。本文以大學生網絡欺凌為例,從大學生視角對網絡欺凌的旁觀者進行分析,梳理網絡欺凌旁觀者的內涵,探討旁觀者角色選擇的影響因素,構建“旁觀者”向“參與者”的轉化策略。
一、善與惡的距離:旁觀者的內涵
在網絡欺凌事件發生的過程中,人們的關注點主要集中于施暴者與受虐者交互過程,因其特殊身份,旁觀者角色易于被忽略。高校大學生處于個體“三觀”形成的重要時期,還不夠成熟,大學生群體既可能是施暴者和受虐者,也可能是旁觀者。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有一句臺詞:“你留在這里,你得想辦法改;你不改變,你就是幫兇,你就是推手。”網絡匿名與網絡旁觀并不等于責任的豁免,在網絡中隱匿身份不負責任地發表言論,這是一種平庸之惡。阿倫特將平庸之惡的出現歸因于社會大眾普遍陷入無思狀態而造成的集體道德崩潰與淪喪[3]。對我國5個省份2 434名學生的調查揭示,曾經旁觀過和多次旁觀過校園欺凌的學生比例分別為81.4%和34.7%[4]。旁觀者對網絡欺凌行為進行干預有助于個體欺凌強度弱化乃至阻止欺凌事件發生,有時,“善”與“惡”的距離僅有一步之遙。
(一)網絡欺凌旁觀者的概念
旁觀是指當他人或社會公共生活受到侵害時,在場的目擊者一味消極觀望或等待,沒有積極行動起來,最終導致悲劇或苦難發生的現象[5]。網絡欺凌旁觀者,是指在網絡欺凌事件中虛擬在場但未直接參與其中的群體,虛擬在場意味著旁觀者并非無視網絡欺凌過程,他們通過利益衡量后表達態度。旁觀者的積極保護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成功阻斷欺凌,使欺凌事件在很短的時間內中止[6]。由于社會文化的影響,在網絡欺凌過程中相助不具有行為的普遍性,大多數網絡欺凌旁觀者依然選擇無視。正因如此,關注網絡欺凌中的旁觀者效應,是有效解決網絡欺凌與個體道德認知提升的重要視角。
(二)網絡欺凌旁觀者的類型
依據芬蘭著名校園欺凌研究專家Salmivalli對旁觀者行為特點的分類,可以將網絡欺凌中的參與者分為網絡欺凌助推者、網絡欺凌煽風點火者、網絡欺凌局外者和網絡欺凌中受害者的保護者。
網絡欺凌助推者也稱為協助者,雖不是直接發起者,但是對欺凌行為進行協助,與欺凌實施者一起對受害者施加傷害。在目睹網絡欺凌發生時,通過幫助欺凌者加害的行為也被稱為親欺凌旁觀行為,這種行為直接增加了欺凌的發生率及強度。
網絡欺凌煽風點火者,雖不屬于侵害行為的直接實施者范疇,但以言語鼓動、挑唆欺凌者實施侵害行為,對欺凌者表達肯定的態度,以擴大雙方對立的情緒。在網絡社會中,一般性質的煽風點火難以構成犯罪,但如果在網絡欺凌中通過鼓動他人,對受害者產生較大影響則可追究責任。
網絡欺凌局外者,意指不參與欺凌事件的人,在網絡欺凌中將旁觀者的局外人身份細分為關心的局外人和不關心的局外人。關心的局外人表現為目睹了網絡欺凌事件的發生,對于欺凌行為未進行相助并感到內疚,而不關心的局外人則表現為對欺凌事件全過程持無所謂的態度。這樣看來,網絡欺凌局外者并未涉及任何言語或行動上的直接或間接侵害,而體現出旁觀者道德認知的漠視。
網絡欺凌中受害者的保護者,是旁觀者類型中積極旁觀表現,在欺凌者實施欺凌過程中表現出保護受虐者行為的人,對欺凌行為終止具有重要作用。與網絡欺凌者、協助者不同,保護者往往表現為具有更親社會的個體,具有較強的同理心以及自我效能感,對欺凌事件中的受虐者產生同情心并對消除侵害有一定的自我判斷,并做出相應干預行為。
二、袖手旁觀或挺身而出:旁觀者角色選擇的影響因素
在網絡欺凌事件中扮演著何種旁觀者角色,受到諸多因素影響。本文就旁觀者對受虐者情況的判斷、共情反應、社會責任感、社會自我效能感和風險評估等影響因素,通過問卷與訪談調查,對342名參與網絡欺凌旁觀的在校大學生進行分析,探析影響旁觀者相應行為結果的因素。
(一)基于對受虐者情況的判斷
大學生扮演網絡欺凌局外者角色時,70.83%的人認為自己不清楚事件的過程,所以做局外人。在體現諸如告誡實施者欺凌行為不合適、呼吁其他人幫助受虐者、勸誡他人來阻止實施者欺凌行為等積極干預行為方面,均超過30%的旁觀者表現出了不確定性等反應。受訪者認為欺凌事件的發生和結果與自身毫無關系,沒有義務提供任何幫助,并認為存在著較多的旁觀者,自己不出手相助也不會有任何愧疚感,當局外人是最佳選擇。對網絡欺凌事件缺乏真實情況的了解,難以對事件所處環境作出判斷并進行角色選擇,加之多人在場情況造成的責任擴散,阻礙旁觀者做出積極反應。
(二)共情反應
共情是道德情緒的主要成分,對抑制個體做出主動性攻擊行為起著重要作用[7]。在網絡欺凌事件中,受虐者表現出恐懼與無助、孤獨與沉默時,渴望旁觀者給予情緒的共鳴,從而獲得幫助。調查顯示,網絡欺凌局外者在是否為受虐者提供幫助方面表現出了強烈的不確定性,但43.48%的人更傾向于成為網絡欺凌事件中受害者(或受虐者)的保護者,其中有20.8%的人覺得“受害者很可憐”“聯想到自己有過相似的經歷”,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共情反應。共情包括認知共情和情緒共情兩個子維度[8]。認知共情通常被定義為個體識別他人情緒和感受的能力,情緒共情被定義為個體對他人的情緒和感受做出相應情緒反應的能力。有60.87%的大學生在過去半年內經歷過網絡欺凌事件,受訪者反饋受欺凌經歷使其對受虐者更容易產生情緒共情,而采取積極行動保護受虐者的旁觀者體現出更強烈的認知共情,產生情緒共情而伸出援手。
(三)社會責任感
社會責任感是個體以利他為出發點,具有愿意為社會及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而維護社會規范的態度和行為傾向[9]。大學生是社會治理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與網絡欺凌事件治理體現出個體的社會責任感。網絡欺凌行為中受害者的保護者作為積極反應的角色,在調查中,近50%的人出于社會責任感認為不幫助內心會覺得不安,表現出網絡利他行為。網絡利他行為主要是以網絡為媒介,發生在網絡環境背景下的具體行為,完全是出于行為主體的自愿行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他人或者群體,是一種對他人、群體、社會有益的行為[10]。在網絡欺凌事件中,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表現出來的利他行為,使旁觀者更加關注他人的感受,約束或降低欺凌者欺凌行為強度。
(四)社會自我效能感
在網絡欺凌發生過程中旁觀者選擇消極或積極干預與否,與其自我效能感有關。選擇積極干預的調查者中,25%的人選擇了干預的原因是認為自身有幫助解決問題的能力,表明在欺凌事件中,旁觀者的社會自我效能感越高,進行積極干預的可能性就越大。有25%的人認為個人能力無法解決正在發生的欺凌問題,與部分受訪者表示自己過去的受虐者經歷相同,使自己即使能對正受虐者產生強烈的共情反應,體會到其中的痛苦,意識到對方需要幫助,但是基于對自身解決問題的低效能感的判斷,并未挺身而出。
(五)風險評估
在面臨多種可能的行為途徑選擇時,個體需要根據風險水平來權衡收益和損失[11]。當旁觀者參與網絡欺凌事件時,其存在參與者角色、身份、地位等方面呈現出不對等時,為避免卷入事件使得權益與安全被侵犯而選擇消極旁觀者角色。網絡欺凌行為的局外者中,約有5%的人表示萬一做錯了將引火上身,而不做則可以規避責任。部分受訪者表示因互聯網輿論,在面對某些可能或正產生激烈對弈的觀點時從不主動發表看法,即使認為自己有能力去減輕欺凌事件中的施虐強度,也會選擇舉報等間接方式避免直接參與,“保護受欺凌者不僅僅是一種親社會行為,也是一個風險事件或者說是一種冒險行為”[12]。
三、他者之痛到旁觀之助:旁觀者的轉化策略
網絡欺凌行為與社會公共道德和價值觀念相違背,旁觀者消極行為是個體道德在行為上的具體表征,以道德教育為引導方向,通過家庭道德教育、學校道德教育、社會道德教育引導大學生形成正確道德認知,有利于其從感受旁觀受虐者之痛轉變為為旁觀者主動出手相助。
(一)以新時代公民道德培養為依據,加強學校道德教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加強公民道德建設、提高全社會道德水平,是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13]。網絡欺凌中的旁觀者道德,是現實社會道德文明在網絡空間的延伸。網絡欺凌旁觀者的消極干預是道德認知的偏差,傾向于工具主義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忽視了崇高的社會道德認知。高校要以新時代公民道德教育為依據,從課程與課外實踐活動等方面入手,加大宣傳力度,加強網絡道德素養的提升,利用校園網絡、報刊、廣播等平臺,精選案例,引導學生了解網絡道德行為的權利與責任,引導大學生提升道德認知,進而促使個體發生道德行為。
(二)以新時代家庭道德教育為遵循,引導正確道德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肯定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意義,認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個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14]。許多家庭忽視家庭教育對子女道德養成的作用,將知識學習與道德養成均交由學校承擔。良好的家庭道德氛圍,有助于子女身心健康,養成良好道德品質。少數大學生由于受到多元價值觀沖擊,家庭環境中缺乏良好的道德氛圍,缺少道德榜樣等重要他人,將造成個性自私與道德冷漠,產生道德失范行為。因此,家庭教育要主動承擔大學生道德教育的任務,家校社協同引導大學生進行正確的道德認知與實踐。
(三)以回歸生活的德育觀,培育社會責任感
道德是人們所選定的特定的生活價值,道德教育就是要幫助人用道德作為參照點來確定生活的方向和道路,使人能夠生活得“更像一個人”[15]。將社會的內涵與生活相聯系,以生活教育作為大學生道德養成的路徑,提升社會責任感。大學生網絡欺凌事件旁觀行為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道德相違背。生活的建構并非是可以隨心所欲的,教育的引導就要使人的主觀生活期待、生活意志得以與生活的現實基礎趨于統一[15]。家庭道德教育與學校道德教育要回歸生活,在社會生活中尋找道德認知形成的素材觸發學生道德自覺,在課堂中引入社會生活的道德案例,營造道德情境,通過貼近大學生生活的道德事件形成正確的道德觀念。
四、結語
網絡欺凌旁觀者不同角色對欺凌事件的發展有重要影響,而網絡社會不斷發展,網絡欺凌也可能產生不同的特點,未來需要聚焦于網絡發展與大學生道德發展,營造積極向上的網絡價值觀。
參考文獻:
[1]第5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發布" 互聯網激發經濟社會向“新”力[EB/OL].(2024-03-25).https://www.cac.gov.cn/2024-03/25/c_1713038218396702.htm.
[2]鄭清,葉寶娟,葉理叢,等.道德推脫對大學生網絡攻擊的影響:道德認同的中介作用與性別的調節作用[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6(4):714-716,683.
[3]孔明安,王雅俊.無思的普遍性與個體的選擇及其責任:從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的無思性談起[J].道德與文明,2024(1):65-74.
[4]宋雁慧,孛志君,秦穎雪.校園暴力旁觀者的調查研究[J].中國教師,2013(15):46-50.
[5]黃巖.“旁觀”現象成因的多維審視[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4):35-40.
[6]HAWKINS D L,PEPLER D J,CRAIG W M.Naturalistic Observations of Peer Interventions in Bullying[J].Social Development,2001(4):512-527.
[7]孫琳丹,田雪,楊蓮蓮,等.受欺凌對主動性攻擊和反應性攻擊的影響:暴力態度和共情的中介作用[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24(2):400-404,360.
[8]顏志強,蘇金龍,蘇彥捷.共情與同情:詞源、概念和測量[J].心理與行為研究,2018(4):433-440.
[9]沈倩如,李巖梅.父母教養方式對大學生社會責任感的影響: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20(5):1042-1046.
[10]梁芹生.積極心理學視角下青少年的網絡利他行為研究[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7(23):24-26.
[11]鐘毅平,占友龍,李琎,等.道德決策的機制及干預研究:自我相關性與風險水平的作用[J].心理科學進展,2017(7):1093-1102.
[12]吳紅,尹敏,張靜,等.校園欺凌旁觀者行為選擇:共情與風險認知的作用[J].貴州師范學院學報,2022(3):42-50.
[13]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9:1.
[14]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習近平關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17-18.
[15]魯潔.道德教育的根本作為:引導生活的建構[J].教育研究,2010(6):3-8,29.
作者簡介:李偉(1994—),男,漢族,湖南郴州人,湘南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秦林姿(1993—),女,漢族,湖南郴州人,湘南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管理。
(責任編輯:王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