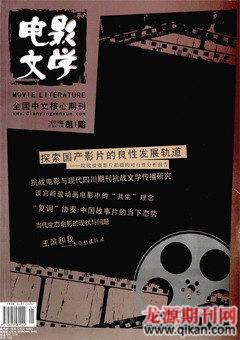憂傷的牧歌
秦凌燕 粱復明
[摘要]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美學的基本問題,這一基本問題在《邊城》中體現為一曲曲終奏雅的“憂傷的牧歌”,“牧歌”構成的內核便是社會性(人)與自然性的關系:它因社會性與自然性的和諧融合而優美,因社會性與自然性的沖突而憂傷。《邊城》中的社會性與自然性雖然有不協調的一面,但是它的主題流向是趨于統一的,因此在整體上呈現出“牧歌”的和諧美好。《邊城》的牧歌品質中最為本質的因素是人類對回歸自然的理想的生活狀態的追求。
[關鍵詞]《邊城》,自然性;社會性;和諧
《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作之一,可謂深入人心。1984年,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制了改編自沈從文同名小說的電影。該片由姚云、李雋培編劇,凌子風導演,并于1985年獲第5屆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獎。電影忠實于原著,承襲了原著清新、優美、溫柔、寧靜的整體風格,馮漢元飾演的爺爺、戴吶飾演的翠翠表演相當質樸、本色,基本與原著刻畫的人物性情相吻合。該片在湘西美麗的山城、沈從文的故鄉——鳳凰拍攝,青山、秀水以及依山而立的吊腳樓,展現了迷人的民族風情。原著的故事情節完整、人物形象的內涵比較外顯,環境天然化,容易轉換成富有表現力的電影畫面。依此,影片成功地將間接的文字形象轉化為直觀的視聽形象,電影藝術符號與原著的文字藝術符號相得益彰。
一、“憂傷的牧歌”的構成內核:
自然性與社會性的關系
牧歌是一個來源于西方文學的一個術語。作者沈從文對《邊城》的“牧歌”的品質有相當自覺的追求:“我準備創造一點純粹的詩……完美的愛情生活并不能調整我的生命,還要用一種溫柔的筆調寫愛情,寫那種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與我過去的情感又十分接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學術界對邊城的評論也認為它有“牧歌”的品質:“其小說的牧歌情調不僅如廢名之具有陶淵明式的閑適沖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艷幽渺。”根據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對“牧歌”“品質”進行大概的描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多用它與“情調”、“氣息”一類的詞搭配,對那些回避現實矛盾,抒情氣氛濃郁的鄉土文學作品作印象性的描述;牧歌中最為本質的因素是人類對回歸自然、回歸鄉土、回歸單純質樸的生活的追求。牧歌是以理想化的筆墨處理鄉土題材而筆調柔和的有濃郁抒情品格的藝術,牧歌不限于寫鄉土的喜和樂,它本身含有哀傷成分,牧歌的“情調”和美感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于這種“憂傷”的成分。
現在再來看“自然性”與“社會性”。自然、美、善是歷來人們對《邊城》評價中用得最多的詞語。自然性是與“社會性”相對應的一個詞,“自然性”是指超功利性、非教化、非社會化;而這里“社會性”則是指現實的功利性、群體性、教化性。《邊城》這曲“憂傷的牧歌”就是由“自然性”與“社會性”的這兩根“弦”彈奏出的“和諧音程”與“不和諧音程”相連相交的“變奏曲”。也就是說,《邊城》牧歌品質的內核是自然性與社會性的關系:它因自然性與社會性的和諧融合而質樸、閑適、幽美,它因自然性與社會性的沖突與不協調而傷感。《邊城》就這樣成為“憂傷的牧歌”。
二、自然性與社會性的和諧統一:理想樂園的整體詩性建構
關于《邊城》的創作動機,沈從文說:“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著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凡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得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作者試圖從遠離塵囂、風光秀美的自然生活和優美、健康的人性等方面構筑自己的理想樂園。這個理想樂園的“詩性”就表現在“非教化”而形成的美好的人性,即作品中所表現的美好的、善的人性并不是社會“教育”的結果,它是自然而然的東西,是天然造就的。但是這種美好的“人性”恰恰又是群體的一種關系,也就是說,這種美好的人性是“自然而然”的,卻又是群體性的。在這里,“自然性”與“社會性”是和諧交融的。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文明小村”:一切都平和安詳,井然有序,就連在別的作品中令人很不舒服的甚至是丑陋的風塵女子,都是質樸可愛的,“這些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
這也正是《邊城》的深意所在。人們對《邊城》的喜愛正是體現人類群體對回歸自然的追求和對自然家園的精神守望,《邊城》的牧歌品質最為本質的東西其實是體現在這里。
三、自然性與社會性的沖突:翠翠的愛情悲劇
翠翠的愛情故事是《邊城》的敘述主體。這個故事本是“順理成章”的卻又呈現為悲劇,正說明了自然性和社會性的沖突。這種沖突體現在下面兩個方面:
1現實功利的因素對田園景觀的滲透。
現實功利的因素對田園景觀的滲透,在《邊城》中表現為碾坊所代表的金錢交換關系對純潔愛情的破壞。翠翠和二老相識兩年后,碾坊介入了他們的關系,給他們本來純潔的愛情蒙上一層陰影,小說第十節,老人去看龍舟,卻被一個熟人拉去欣賞新碾坊,其實熟人的目的是替大老的婚事探老人的口風。探口風為什么要選擇在碾坊呢?其中的蹊蹺細讀后便能看出,電影對這個場景也有恰當的展現。熟人知道這碾坊的分量,渡船老人當然也是知道的。電影用畫面的切換很好地表達了原著的內容:這邊的熟人拿碾坊施壓,那一邊在吊腳樓上,順順以家長的權威,在兩個“候選”兒媳之間排出座次:團總女兒“占了一個最好的位置”,而翠翠只能靠后邊,接著的是中寨人有意或無意的編造了二老同意與團總女兒的婚事的謊話,直接挫傷了爺爺對翠翠婚事的希望和信心,加上后來的一連串誤會,致使翠翠的婚事終于落空了。老人憂慮翠翠的命運,迅速衰老,最后在一個雷電肆虐的暴風雨之夜離開人世,離開他放心不下的翠翠。這意味著金錢交換原則的現實,功利的勝利,我們所欣賞所向往所陶醉的作者充滿愛和溫暖營造的鄉土詩情嚴重遭受破壞。這是自然性與社會性在《邊城》最為激烈的沖突。但是這個“激烈”的“沖突”依然被表現得相當的柔和,因為從整體上看,金錢對翠翠的愛情的破壞是有限的,所以沒有損壞作者說的“用一種溫柔的筆調寫愛情”牧歌氣息,只是清晰的揉進了悠遠的哀傷成分。
2翠翠的“愛情責任事故”。
既然從整體上看,金錢對翠翠的愛情的破壞是有限的,那么直接促使愛情悲劇產生的原因就是一連串誤會了,忠實于原著的影片的下半部分,除了表現爺爺死去這個情節以外,其他所表現的都是誤會的場面:爺爺和大老之間的誤會,爺爺和二老之間的誤會,二老和爺爺、翠翠之間的誤會,爺爺和順順之間的誤會。很多人把直接促成悲劇形成的原因歸結為命運的陰差陽錯,“這是一曲愁緒縹緲的人間情愛悲劇,然而在這些人性皆善、性自然的人群中,辯不清社會制度和文明的梗阻。它充滿著原始人
類陰差陽錯的神秘感和命運感,自然安排了人的命運,人無怨無艾地順其自然,融乎自然,組成一種外化之境的生命形式,組成一曲曲終奏雅的人生抒情詩。”“悲劇發生的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一串誤會。”“因為誤會的頻繁發生和非合理性,它成為‘天意、‘造化的顯現形式,渡船老人的行動的悲劇性的,每到關鍵時刻,他的努力就被造物主化解得干干凈凈,他越是迫切,情勢向那預設的結局發展得越快。人與命運的沖突,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這些說法都是很有道理的,應該說這些說法也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作者正是用這種“天意”來渲染一種自然性的牧歌情調。但是,我們還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說對于渡船老人即爺爺來說,“他的行動是悲劇性的”,那么對于愛情悲劇的當事人翠翠來說,則不是這樣,因為在整個過程中,翠翠一直沒有真正的“行動”。生命中的悲劇性的事實,一定是通過人物的行動而得以展現。所以從翠翠的角度看,她因為沒有行動,因為不是呈現悲劇沖突的行動者,就不能成為引發人們的悲劇感的核心人物。從作品本身的角度看,過分渲染了的自然性,卻跟人的社會性發生了沖突。從人的社會性的角度看,人是有明確的主體意識的人,是能朝著預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人,是能對自己的行為自己的命運獨立的承擔起責任的人。可是實際上,翠翠沒有去主動追求愛情。雖然她和儺送兩人一個有情,一個有意,但翠翠一直是處于相當被動的狀態的。假如翠翠的主體意識增加一點,思想稍為解放一點,勇敢地去追求愛情,他和儺送就不會失之交臂,留下了悠長的遺憾——這遺恨一直留給今天的讀者和觀眾。她甚至不知道天保是因不能得到她的愛而憂郁出走落水身亡,不知道儺送是因為不能得到她的愛而離鄉遠行,也不知道爺爺突然離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慮奔忙而心力交瘁,只有這一切都已發生,陪伴她的楊馬兵向她說明后,她才如夢初醒“哭了一個夜晚”。直到結尾,她還在等待那個“也許永遠不回來了”的人。
這一切都說明,翠翠沒有明確的愛情“策略意識”和現實的“愛情行動”,在“哭了一個晚上之前”,她因迷茫也不能夠獨立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和命運。這個愛情悲劇有點像“責任事故”:因為翠翠的主體意識的薄弱而造成的“責任事故”。我們在欣賞《邊城》的時候往往被它的自然性豐裕而生成的優美情調所陶醉,對翠翠的愛情悲劇送去的是一聲帶著無奈的嘆息,而忽略了作者對不和諧一面的揭示和因此而引發的憂郁。這也是造成“牧歌”悠遠而深沉的憂傷的另一個原因。在這里,自然性與社會性的沖突不表現為矛盾狀態,而表現為不協調狀態:自然性的過分與社會性的匱乏造成的不和諧。因此,這憂傷來得比較平靜,表現得比較幽雅,但因為這憂傷有了更深層的原因,因此它雖然沒有驚波巨浪式的痛苦帶來的那種震撼力,卻因為含蓄柔和而更具悠遠的韻味。
四、自然性與社會性的沖突的有效節制:“生生不息”的希望
雖然《邊城》有自然性與社會性不協調的一面,但是這種不協調是受到節制的,作品的主題的流向是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所以作品才會在整體上呈現出“牧歌”的和諧美好。
翠翠是小河邊一朵掛露的花蕾,儺送是山腳下一頭熱情健壯的小牛。兩人愛情路上唯一的障礙是儺送的父親順順,順順雖然不同意兩人的婚事,但是態度也并不強硬,并沒有使用千百年來沿襲下來的封建家長的權威橫蠻干涉,他還是讓兒子自己決定的。在爺爺去世后,順順還表示過要接翠翠到家里。一切充滿了善意和希望,然而到處是“不湊巧”。這“不湊巧”表面上看是一連串的誤會,或者說是命運的陰差陽錯,但它的本質是自然性和社會性的沖突。但是沈從文并沒有把這種沖突引向極端,而是讓沖突的不和諧趨向于解決,于天地的自然運行間迸發出一種強大的力量——生生不息。于是,自然性與社會性又趨向于和諧統一了,一曲“憂傷的牧歌”有了一段漂亮的充滿生機的“尾聲”:翠翠接替了爺爺的工作,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對于讀者,“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