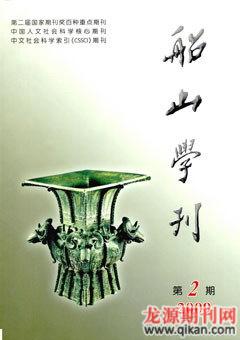旁觀與偏見
羅新河
摘要:現代主流文學是以現代性啟蒙為基本訴求和主要特征的文學而錢鐘書的文學追求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此傾向的偏離,他以旁觀者的視角,對主流文學表達了自己獨特的一偏之見,構成了現代文學別具一格的文學景觀。
關鍵詞:錢鐘書;啟蒙;理性精神
中圖分類號:I1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7387(2009)02-0186-03
在20世紀中國社會多災多難,痛苦焦慮,憂患不斷的歷史變遷中,貫穿著一個走向現代化的總主題。這深刻地影響到了這期間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內部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學的基本面貌和走勢,賦予它相應的文化內涵及歷史品格。因此。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二十世紀上半期(1917—1949)這一特定時期的文學形態。其“現代”兩字,不僅僅是一個線性的時間標識,更是深深地包含著身處國家現代化歷史變遷中的中國現代作家豐富而獨特的空間體驗。于是。有研究者指出:“現代性是決定中國現代文學史性質的核心。它既是中國文學從古典向現代轉型,中國文學史進入現代階段的決定因素和主要標志,又是貫穿中國現代文學史,決定現代文學的發展方向和基本特點的關鍵所在。”
何謂現代性?這是一個內涵復雜,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概念。著名文藝理論家錢中文先生以為。現代性基本而首要的特質是一種理性精神。啟蒙精神?。就中國現代文學來說。它的發生與發展即充分表明了這一點。回顧中國現代文學史。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認為,沒有理性精神與啟蒙精神就沒有現代文學的生成與發展,正是在理性精神與啟蒙精神的要求及推動中,現代文學才成為文學史衍進的必然結果。啟蒙精神與理性精神為現代文學的發生與發展提供了契機,從而也為自身的進一步拓展創造了更便利的條件。現代文學順應國家歷史變遷的需要,從整體傾向上,所張揚與體現的正是這種理性精神與啟蒙精神。因而,我們不難理解。雖然現代文學在不斷衍展的過程中呈現出錯綜復雜、變幻多端的主題群落。以及此起彼伏、紛爭不息的流別格局,我們還是能隱隱約約梳爬出它一以貫之的主流敘事脈絡。即啟蒙化與理性化寫作。這一點在學術界早已取得共識,有一批學者直接將之寫入教科書作為現代文學發展的主線進行文學史敘述。在他們看來,“‘五四文學革命乃至抗戰爆發前的各種文學思潮。著重強調的是文學與社會改造的密切聯系,文學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思想啟蒙作用。”而且抗日戰爭的爆發。救亡也并未如李澤厚所言完全壓倒啟蒙,只不過戰爭的巨大影響使“文學的啟蒙對象及其目標”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由抽象的個人轉向具體的社會大眾,個人的現代化開始讓位于國家和民族的現代化。”如果我們不糾纏于特定的意識形態觀念,深入現代文學內部發展架構。著眼于中國社會“現代性”走向這一總體趨勢,我們就不難發覺這一論述的合理性。
但正像社會歷史轉變的性質經常會呈現出復雜多變的形態一樣,中國現代文學主流“啟蒙主題”的延伸與衍化,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在不同的流派及作家那里。也呈現出復雜多變的歷史景觀。在現實的歷史演進中,并沒有自然地在我們眼前展露出一條如當前的文學史家所總結出的、條貫清晰的文學史脈絡。我們固然可以較明確地把握那些“以天下為己任”的作家們的啟蒙化寫作線索,但更多的作家的啟蒙意識及書寫卻是以一種超越了我們固有的啟蒙理解的獨特形式或隱或明地存在,拋開那些以文學啟蒙為指歸的啟蒙作家,如文研會諸成員,魯迅,巴金等人不論,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就是創造社浪漫主義作家,以及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革命作家。也自覺不自覺地在進行某種程度的啟蒙化寫作。創造社的浪漫主義作家們在極度地抒發情感。張顯個性,敘說苦悶的文學敘事中,自然而然包含了個人現代化的啟蒙內核;革命作家們以一種烏托邦式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話語,對文學的功利性作無限夸大,本質上還是啟蒙的,只不過企圖以一種暴風驟雨般迅猛快捷的方式對下層民眾愚昧、麻木、不覺醒的國民性作一勞永逸地改造。因而完全墮入一種粗疏、竣急與空想的浪漫情境之中。就是30年代的自由主義作家,他們雖然保持一種遠離政治致力于精心營構自己的文學的希臘小廟的超然姿態,但從他們對健康、優美、自然的“原始人性”的極度贊美以及回歸自然的文學趣味和審美傾向中,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他們改造國民靈魂的精神內涵。其對終極理想,終極價值的樸實化追求,對人性之善之美的呼喚,同現代文學的基本信念并行不悖。
然而,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動力不單來自新與舊,現代與傳統的對立。也來自現代化自身內部持續不歇的質疑與反思的聲音。當啟蒙或理想主義或甚至被稱之為浪漫主義的話語在現實文壇上,成為不可置疑的霸權話語。理所當然的占據話語空間時,它的逆反面——反啟蒙、反理想、反浪漫的話語也在不斷涌現,雖然它們無法對主流話語構成實質性危協和沖擊,但它們往往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對主流話語旁敲側擊。或者獨行其是。與之一道構成現代文學豐富和復雜的矛盾性景觀,體現出現代文學所特有的魅力。
錢鐘書的文學創作就是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文學史語境中。偏離于主流話語之外、帶有某種叛逆性或者至少是不那么馴順的話語形態。其早年文藝觀念憑恃著青年人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特有之英銳。冒天下之大不韙。向在三十年代文壇學苑早已成為經典話語的五四啟蒙主流文藝觀單槍匹馬的發出了挑戰。
眾所周知,進化論是五四反傳統的理論前提,運用于文學領域便成為現代文學的核心價值理念。文學進化觀是啟蒙作家用以批判舊文學,倡導新文學的有力思想武器。可以這樣說。在中國近現代特定的歷史語境下,進化論代表著的不再僅僅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立場。上升為一種神話。但錢鐘書對它表示了自己的質疑。在一篇《論復古》的文章中錢氏借對當時的主流文藝理論家郭紹虞先生的名著《中國文學批評史》進行了激烈批評,指責其以文學的歷史進化觀念來判定歷史上的文學復古與逆流現象。失之莽撞與武斷,指出郭先生將“文學進化”與“事實進化”即自然進化,混為一談。并且他還認為,專就歷史事實而言,對于“進化”兩字也得仔細斟酌,不能隨便談論,因為,“進化”包含著目標,除非我們能確定地知道事物所趨向的最后目標,否則“我們不能倉卒地把一切轉變都認為是‘進化”,事實是我們并不能確定知道事物所趨向的最后目標,因為據他引證:“即使對天演極抱樂觀的生物學家像Julian Huxley,對于文明的進步極抱樂觀的史學家J·B·Bury都不敢確定天演的目標。”所以,他認為,“在無窮盡,難捉摸的歷史演變里”,郭先生所謂的歷史進化觀念只是一種完全“依照自己的好惡來確定‘順流、‘逆流的標準”的個人主義,“無論如何,不能算是歷史觀。”這樣,錢鐘書在批評郭紹虞先生對文學進化論的理論運用時,實際上也就取消了文學進化論的理論操作性,從而從根本上瓦解了以進化論為核心理念的五四啟蒙話語。表現出對五四的偏離傾向。
從此種傾向出發,錢鐘書幾乎對整個五四文藝觀念都表示出懷疑或異議。甚至可以這樣說,五四所倡導的他就反對,五四所反對的他就支持。如五四反對傳統文學的“文以載道”,“言之無物”。“無病呻吟”,以及用典與貴族化等文藝傾向,倡導寫實,言之有物,真情實感,不用典,以及平民化大眾化的現代文藝理念。錢鐘書先生都分別——表達了自己的不同意見。針對文以載道。他以為。“在傳統的批評上。我們沒有‘文學這個綜合的概念,所有的只是‘詩、‘文、‘詞、‘曲這許多零碎的門類——‘文以載道中的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來涵蓋一切近世所謂‘文學。”而且他在《論復古》一文中進一步認為“文以載道”根本就不是一種文學批評,只是古代道學家們進行學科建構的必要的語言規范而已。“‘文以載道只限于道學的范圍。”通過概念的梳理與考論,錢鐘書使我們感到“五四”所謂古人“文以載道”文學觀。純屬望文生義,子虛烏有。而五四理論家們卻將之作為古代文藝理論的一個核心命題不遺余力地進行猛烈批判,這無異于無的放矢,庸人自擾。關于五四先驅對古文學言之無物的批評,他運用西方形式主義理論。指出這也不過是無稽之談:“自文藝鑒賞之觀點論之。言之與物、融合不分;言即是物,表即是里;舍言求物,物非故物。同一意也,以兩種作法寫之,則讀者所得印象,迥然不同……故就鑒賞而論,一切文藝,莫不有物,以其莫不有言;有物之說,以之評論思想則可,以之欣賞文藝,則不相干。如刪除世眼之所謂言者,而選擇世眼之所謂物,物固可得。而文之所以為文,亦隨言而共去矣。”至于五四對傳統文學所置啄之無病呻吟一說,他搬出修辭立誠說為之辯護,“不為無病呻吟者即修詞立誠之說也,因而惟其能無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讀者信以為有病。方為文藝之佳作耳。”關于用典,他更是認為無可非議。“在原則上典故無可非議。蓋與一切比喻象征性質相同,皆根據類比推理來。然今日之典故尚有一定之坐標系。以比現代中西詩人所用象征之茫昧惚恍,難于捉摸,其難易不可同年而語矣。”嗍五四所批判舊文學的貴族化傾向,錢鐘書卻認為這正是文學的本位化追求,“竊謂至精文藝,至高之美。不論文體之雅俗,非好學深思者,勿克心領神會,素人俗子均不足與于此事,更何有于平民。”由上所論,我們不難看出,五四文學的核心理念,錢鐘書幾乎都表示了質疑或反對,明顯的表現出偏逸于五四的超然獨立姿態,構成了五四主流之外的獨特風景。
錢鐘書早期的文藝姿態即預示著他后來的話語策略。如果說現代文學主流話語多多少少閃爍著對于人、世界以及未來的進化論式或烏托邦式理想與希冀的光芒——如魯迅的不恤用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那么,錢鐘書的創作就是力圖去遮掩或撲滅這種理想和希望的光芒,任何人若企圖在錢鐘書的文本世界中找尋什么可以稱之為肯定性價值,積極的因素,以及值得追求的理想信仰都將是徒勞的。它所描繪之人物幾乎無一不是一無是處。“無毛兩足之畜類”,丑惡、貪婪、盲目、自私、庸碌、無能,讓人厭惡與失望透頂;所展示之人生與世界更是一無可進,一無可去的圍城,陰慘黯淡,毫無出路。令人悲觀絕望至極。這種寫作傾向是典型的非理性、非理想、非啟蒙、非樂觀的。因此。錢鐘書的整個創作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是“沒有改造的和非理想化的;嘲諷地觀察而不是發掘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很顯然錢鐘書這一反理想反浪漫化的創作傾向從根本上逸出了現代文學主流理想主義啟蒙主義價值觀念的運行軌跡。
更為讓人注意的是,錢鐘書不但在話語立場上與現代文學主流價值觀相偏離,而且他對整個現代文學及其文壇都持一種輕蔑、嘲諷和挖苦的態度。早年他在文章中屢有抨擊新文學之言詞。并對新詩表示過自己的輕蔑。而且頗為令人奇怪的是他幾乎從不評論現代文學作品,甚至在自己的學術著作中也不提及。這對于一個身處現代文學場中近二十年的作家來說,應該不完全是研究旨趣問題。而是存在某種輕視,就像他清華同學吳組緗所說“瞧不起”。因而美國學者E·岡恩認為錢鐘書“拋棄而不是肯定或繼承以前數十年的成果”。不光如此。錢鐘書似乎也瞧不起現代文學作家。E·岡恩說:“錢鐘書常常表明,他非常樂意偏愛自己的自然觀、加入詆毀過去十年文壇的行列。”事實確實如此,錢鐘書在展示其相背于現代文學主流的文學傾向與風格時,作為表現其意旨而極力加以貶損與丑化的形象符碼。往往就是現代文學的主流作家。只要我們稍加索引的眼光去研讀錢氏文本,我們當不難發現我們熟悉的很多現代作家的影子。據研究者指出,其中就包括周作人、徐志摩、曹禺、巴金、蔣光慈、沈從文、林語堂、朱光潛、葉公超、林徽音等人。他對現代作家諷刺面如此之廣,以致夏志清先生說:“錢鐘書看法獨特,把作家本身看作社會文化墮落的一個重要成分。”錢鐘書晚年在美國進行學術訪問時,他曾特意向大家表明自己是一個“反動者reactiolner”我想,就他早年一反新文學主流,頗為叛逆色彩的文學傾向來說。此種稱謂可謂夫子自道。
其實,錢鐘書這一反主流化的寫作傾向是基于一種自覺的創作意識。他在新文學寫作伊始,就在《<寫在人生邊上>序》一文表明自己旁觀于人生。放棄啟蒙擔承。偏離于主流的寫作策略。直到晚年他還說:“立宗開派,覺世牖民,既無此心,亦無此力耳。”就錢鐘書蓋世才學而言,我們當知他無心是實,無力有謙,此種心聲之語。乃是對他文學創作與文化活動的最佳闡解。
錢鐘書曾在《旁觀者》一文中稱西班牙哲學家加賽德為旁觀者,實質上他自己就是這樣一位旁觀者。是超然于人生的旁觀者,也是偏離于時代主流的旁觀者。既是旁觀,所見必有所“偏”,因而錢鐘書的文學觀念及文學創作,我們可以視為是對整個現代文學主流的一個“偏見”——一個偏離了文學發展主流的作家以冷然和戲謔的神態在隔岸觀照中發表的奇拗而精審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