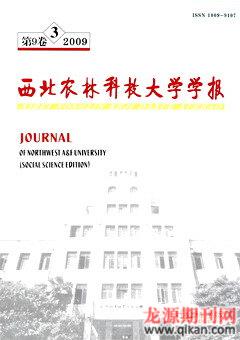論清代陜西回族經濟生活變遷原因
申莉琴
摘要:有清一代陜西回族經濟生活發生很大變化,同治年間回民起義前經濟結構以農耕為主,兼營畜牧和商業,農業經濟活動日臻完善,達到相當規模。起義失敗后演變為以商業為主,兼營畜牧和農耕。導致這種變遷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漢族在經濟上對田族的依附。從回漢經濟結構互補到漢族對回族經濟上的過分依賴,極大阻障了回族農業生產的發展。第二,回漢民族關系的緊張。隨著人口的增加,土地資源日顯窘迫,加之清政府“護漢抑回”政策影響,使得回漢兩族人民關系緊張。第三,伊斯蘭教推崇商業的精神和鼓勵經商的思想,無不滲透于回族社會經濟生活中,對其經濟發展有一定影響。
關鍵詞:清代;陜西回族;經濟生活;變遷
中圖分類號:K281/28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09)03-0127-06
回族自元代“回回遍天下”到明代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共同體登上歷史舞臺以來,就是一個集農耕、畜牧、經商為一體的民族,陜西地區回族亦是如此。然而有清一代陜西回族的經濟生活因同治年間回民起義而發生大的變遷,進而形成今天陜西回族以經商為主的經濟結構,對于這個時期陜西回族經濟變遷情況及原因,學術界相關研究篇幅非常有限,筆者試就這個問題作以探討。
一、清代陜西回族經濟生活的變遷
清代前期陜西回族分布廣泛,經濟結構上以農耕為主,兼營畜牧和商業,整個回族的經濟生活顯示出一派繁榮景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陜西巡撫畢沅的奏折中有“至西安回民大半耕種畜牧及貿易經營,頗多家道殷實,較其他處回民稍為體面”的記載。然而同治年間的陜西回民起義卻給陜西回族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從此以后陜西回族的經濟生活狀況也隨之發生改變。
(一)回民起義以前陜西回族的經濟生活狀況
清代陜西回族遍布全省,尤以關中之同州府、西安府和風翔府為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陜西巡撫畢沅在奏折中說:“查陜省各屬地方,回回居住較其他省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屬之長安、渭南、臨潼、高陵、咸陽及同州府屬之大荔、華州,漢中所屬之南鄭等州縣,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為稠密。西安省城內回民不下數千家,城中禮拜寺共有七座。”到同治元年(1862年)以前,陜西人口已達1200萬人,其中“民七回三”,分布在全省的七府五州,僅關中地區回民就有800多坊,西安、同州、鳳翔三府和乾、邠、鄜三州的20多個州縣有七八十萬到一百萬人。回族人口的不斷壯大對陜西農業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以農耕為主而兼營畜牧業、商業等一直是清前期陜西回族社會經濟結構的主要特色。
1、農業。回民起義前,陜西回族主要從事農業經濟。在渭河流域及其支流地區,回族農村星羅棋布。陜西回族不僅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而且其農業經濟活動日臻完善,達到相當規模。就當時陜西回族的農田水利與農耕技術而言,已與當地漢族的水平基本相當,有些方面甚至還超過了漢族。如馬長壽在《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序言中提到“在臨潼縣回回道,一位老鄉引我們到回回道的高崗上,遠指渭河以南,說明當年回民在某處種藍靛,某處種麥子,某處引渠,某處鑿井。”這種田地經營方式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在耕作技術上,陜西回族在開墾荒地的同時,利用水利建設創造的條件,發展了水澆地,采用“休間”、“輪作”、“套種”等先進的耕作技術,把沙田經營成“金糧”產區。另外,在生產工具的改進方面,清代出現了一種便于在沙地行走的“回回車”,現在仍在渭南、大荔一帶使用。
關于清代前期陜西回族的耕作數量和規模,我們可以從馬長壽的《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之大荔縣調查紀錄中得以證實。“我是羌白鎮青池村人,原來青池是回民村莊。村里在同治初年有一個回族大地主,名溫紀泰,他占有的田地很多,難以數計。家里的耕牛亦很多,相傳有賣牛籠頭的至村,他全部買下,還不夠使用。他家耕地時,牛馬成群,如同過會。當時附近有一漢人村在演戲,但群眾們不想看戲,而要看溫紀泰田里的耕地。”以此來看,清代前期陜西回族的農業經濟已經發展到相當規模。
2.畜牧業。對清代陜西回族來講,在多種農業經濟成份中,畜牧養殖業也是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清代陜西回族畜牧品種較多,主要有牛、羊、馬、驢、駱駝等。但由于回族飲食習慣的特殊要求,即穆斯林喜食牛羊肉,使養牛羊更為普遍。由于清政府保護耕牛的政策,加之養牛需要的成本大,所以養羊更超過養牛,在回族養殖業中獨占鰲頭,幾乎所有的農村回民家庭都有這個行業。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的原因之一“地畔相爭”,也是由于回民的羊跑到漢民地里啃麥子而引起的矛盾。
另據《大荔縣志·物產》記載:“大荔之馮翊有苦泉,羊飲之肥而肉美……沙苑所出有小耳大尾之羊,通志謂之繭耳羊,府志亦言繭耳羊出同州,大耳羊畜于此耳無不小,蓋其地脈所產者然此亦理之不可解……此大荔之獨絕者也”。因為宗教民俗和飲食需要而大力發展養羊業,加之大荔獨有的水源地理優勢,使羊飲之肥而肉美,“羊冠全省”,由此觀之并非徒有虛名。
3.商業。清代陜西回民,尤其是居住在城鎮附近的回民,大都在農閑時從事商業,多以牲畜販運業為主。如同治年問,一些陜甘回族商人經常“私販馬匹”,參與鎮壓陜西回民起義的欽差大臣勝保甚至說,陜西回民“多系販馬出身,馬匹極其精壯,多至萬余”。所有這些都足以證明陜西回族早在清代不僅販運牲畜,而且頗具規模。當時西安地區最知名的富戶是馬德興,在西關當騾馬羊的經紀人,很有能力,收入也很多。像這種回民經紀人,不論在城市或農村,為數不少。
此外,一些回族因經商而發家致富,如“大荔縣禹家莊的禹得彥,在四川開設鹽井,在西安有房產、地產和商業;還有明清之際咸陽渭城灣的茶商木士元,他的茶葉是從湖北起運,經過西安、涇陽一路,然后遠銷于甘肅、新疆各地,從明末到清初幾十年問,他獲利很多,終于成為同行中的‘通行領袖,后世子孫繼此為業,在渭城灣聚族而居,建筑宏麗,稱為巨族大姓。”
(二)回民起義以后陜西回族的經濟生活狀況
清代道光咸豐年間,陜西旱、蝗、水、雹、風、疫、地震等自然災害不時發生,接連不斷的天災和統治階級的壓榨,使陜西各族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陜西回族所受苦難尤為深重,政治地位明顯下降。清朝封建統治者誣蔑回族是“獷悍”、“好亂”、“性與人殊”的“奸民”和“異類”,又在民族政策上制定“以漢制回”、“護漢抑回”等分而治之的策略,還利用漢回人民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的差異,挑撥漢回關系,制造漢回械斗仇殺,致使陜西漢回兩族人民關系緊張,在華州圣山砍竹事件的影響下最終爆發了陜西回民起義。起義從華州、渭南、大荔開始,很快燃遍關中平原,至同治元年5月下旬,起義軍控制了關中
平原大部分地區。清政府為了挽救危局,多次派軍鎮壓,終因力量懸殊,回民敗退,并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甘肅董志原(今甘肅寧縣西北)組建十八大營,繼續與清朝統治者作斗爭。直到清光緒三年(1877年),陜西回民起義最終才被陜甘總督左宗棠剿滅。起義失敗后,絕大部分陜西回民死于戰爭,幸存者寥寥無幾,除西安城內及陜南少數人外,在甘肅戰敗的陜西回民被強迫安插在甘肅東部窮鄉僻壤之地并受到嚴密的控制和歧視,進入俄境的白彥虎余部則形成了東干族。
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使陜西回民的經濟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與前期不可同日而語。關于幸存西安城內回民的經濟生活狀況,在西安回民馬光啟遺著《陜西回教概況》一文中有這樣的記載:“又令回民[可]外縣購地營業,而該地紳民不得阻滯。由是,吾教人往外縣典房營業者日眾,然大宗不過牛羊肉行而已。”。另有“吾教人既罹城圍之困苦復遭饑饉之災,以致十室九空,生活程度日益過高,謀生之道,多感困惑。所以吾教貧苦之人每日所入不敷用度者計居十之七八;豐衣足食者,僅居十之二、三,經濟困難,營業蕭條。”
由于回族宗教信仰的特殊性,除了經商貿易,清真飲食業便成為回族群眾從事的主要經濟活動之一。約有30%的回族兄弟祖祖輩輩都在經營飲食業。其主要以擅長生產經營清真飲食、肉食、糕點、副食業而聞名。常見西安鼓樓一帶什字街口、半間門梢,高懸式牌,上繪焚煙香爐、貯水湯瓶、標寫“清真教門”、“西域回回”老馬家、老白家、老童家等等,此外更無商號,普遍所售食物為鍋盔大厚餅、水盆熟羊肉等。清朝末期,陜西西安又出現了賣臘牛羊肉的“老童家”、賣泡饃的“同盛祥”、“鼎興春”、賣餃子的“白云章”、賣炒菜的“清雅齋”、“老孫家”等以及西安市的大麥市街和麻家什字兩個回民傳統小吃集中的街道。但這些小吃經營狀況蕭條,清真飲食業發展緩慢。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家政策對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重視,清真飲食業才得以迅速發展。到目前為止,西安回族清真餐飲業在全國乃至世界都有一定知名度。
至于在甘肅安置的陜西回民,“安插定妥由官劃給地畝酌發種子農器,俾得及時耕種,并發賑糧,俾免饑餓秋后停止”;東干族主要從事種植業;陜南地區的回民因秦嶺之隔受戰爭的影響較小,主要還是以農耕為主,兼營畜牧業,這種經濟結構基本上一直保持到現今。
二、清代陜西回族經濟生活變遷的原因
回民起義前后陜西回族經濟生活發生很大變遷,作者認為導致其變化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點:
(一)清代陜西回族與漢族經濟生活上的依附性
在中國農業社會中,以農為主——這是回族和漢族人民在經濟上的一致性。但是,“漢民以耕種為生,回則善于經營,兼以貿易致富”。張克非在《清代西北回族經濟結構初探》一文中對此情況有分析,“廣大回民在經營農業的同時,兼營商業和畜牧業,這本來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種復合型經濟結構的形成,反而給回族經濟找到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不少漢民轉而改信了伊斯蘭教,許多回民抱養和收留漢民的子女,其根本原因不是別的,恰恰在于回漢兩族在經濟結構上的差異和優勢。”。由此說明了陜西回族與漢族在經濟生活上是相互依附的。
論及回漢經濟生活在清代的依附性,最典型的要數“地畔相爭”。“地畔相爭”是指回、漢地主對于毗鄰地主土地的競買和由此而產生的爭端。以大荔沙苑回族與漢族之間因為“地畔相爭”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為例。大荔沙苑早在唐代就被統治階級指定為回族的農牧地區,但自明代以來,外來的漢人不斷向沙苑的東、西兩端發展,在那里出現了諸如嚴、趙、閻等姓的漢族地主。另一方面,回族地主和高利貸者較之稍晚也相繼不斷出現,但因為回族地主出現較晚,所以回族地主必須高價才能從漢人地主手里購得土地。漢人地主一方面利用回民肯出高價,愿意出售土地,但另一方面又懼怕土地一旦售給回民便又不能買回來了,所以又不愿賣給回民。在這種矛盾的驅使下,即產生了“塵土火灰換麥子”以及組織“羊頭會”等辦法。“塵土火灰換麥子”是漢人欺騙性地將塵土摻在火灰里面換取回民的麥子;“羊頭會”則是回民放牧時,羊吃了漢人的田禾,漢族地主便號召群眾捕羊而殺。這些辦法對回民是不利的,使得回民人均耕地減少,畜牧業發展受阻,也逐漸加深漢回兩族的矛盾。
此外,還有一種以純粹剝削搜刮回民的各種土特產為業的行當。再以沙苑為例。在沙苑周圍的漢村里有糧食行、水果行和干果行經紀人,這些經紀人的主要任務是為沙苑周圍的大地主和大財東服務。這些大財主和大財東同時又是高利貸者,平時他們已經有大量貨款貸給回族農民,貸款的抵押品就是每年出產的糧食和土特產。而且在封建社會,地主財東大都是把頭,外來客商想購貨物必須通過把頭,因此貨物經由大地主和大財東一轉手之間就可獲得很大利潤。回民辛苦勞做一年,到頭來利潤卻分別落在了大地主、大財東的手里。在農業生產上收入微薄,嚴重影響了回民對農業生產的信心,進一步阻礙了回族農業生產的發展,這對回族經濟結構轉型具有極大的驅動力。
(二)回民起義前后清代陜西漢回民族關系的緊張
從明代至清前期,陜西回漢民族之間關系比較友好和融洽。比如前述馬長壽先生《調查記錄》中記載:“時有漢民改奉伊斯蘭教”,“有的回民沒有子嗣,便抱養漢民子女為子嗣。”又如馬光啟《陜西回教概況》中記載:“在省城之西南鄉,其后散居務農,與漢民雜處,頗稱敦睦。”而且,回漢兩族在反抗封建王朝和地主階級的斗爭中,能團結一致聯合行動。比如咸豐六年(1856年),渭南縣渭河以北的漢族農民,反抗官府對他們所進行的鹽課攤派剝削,聯合起來成群結隊到縣衙“交卸農器”。農民隊伍途中路過倉頭、蘇村、拜村,各村回族農民亦持農器來助。
但是,隨著清代陜西漢回人口及經濟的快速發展,本來就有限的土地資源日顯窘迫,在此基礎上,漢回兩族中的大地主、富商、高利貸者之間爭奪土地、市場的矛盾逐漸尖銳,階級分化日益加深。由于對土地的占有和市場的壟斷,使原本較為和洽的回漢民族關系逐步轉人對抗化。此外,清政府“護漢抑回”的政策更使回漢民族關系緊張化。盡管平日里漢回基本都能友好相處,但也不排除兩民族偶爾發生睚眥小忿,如回民放牧時踐踏了漢人的田禾,漢人為了報復而“截斷了羊腿”甚至繼而成立了所謂的“羊頭會”等。本來這類矛盾只是屬于日常相處之間難免發生的一些小摩擦,采取公正的態度是可以調解的,但地方官卻偏偏袒護漢人,導致回族民眾對漢族的極大不滿和怨恨。如“漢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時候,裁決很少對回民保持公正態度,漢族官員本人有偏見,滿族官員又通常左袒漢民”。對于民間訴訟,“任意出入其法,回殺漢者抵死,漢殺回者令償斂葬銀二十四兩”,更有甚者,遇有回漢糾紛,“無知
官吏不肯詳細體察,但系回民皆曰為‘賊”。最后連清朝統治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該回民等久隸中華,同受國家覆育之恩,食毛踐土二百余年,其間登仕版者,亦復不少,豈無天良?何至甘為叛逆?推原其故,始則由地方官辦理不善,遇有互斗等事,未能持平辦妥,以致仇釁日深。”嚴酷的法律再加上不公正的司法,回族人民如雪上加霜。
更有甚者,清朝封建統治階級利用宗教習俗的差異,對回族的宗教活動、風俗習慣橫加指責;又乘回族內部新舊派相爭之際,從中挑撥,支持一派,壓制另一派,玩弄分而治之的手腕。甚至為了達到統治目的,不惜一切手段挑撥漢回關系。比如前面以“地畔相爭”形式出現的漢族“羊頭會”,隨意捕殺回民牛羊;有回民小販到漢村叫賣,因細故而遭毒打;逢年過節唱戲,也免不了漢回相互斗毆的現象。這些看起來是小事,然而卻逐漸加深了回漢兩族之間的隔閡和矛盾。加上漢族地主對回族經濟上的肆意剝削,回民生活每況愈下,終于導致回漢兩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終在華州圣山砍竹事件的點引下,爆發了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起義失敗后,陜西巡撫劉蓉將西、同、鳳、延、鄜、邠、乾七個州府原屬回民的土地皆作為“叛產”沒收入官,陜西回民耕地占有量嚴重不足,人多地少,難以滿足生活需求,只好轉而從商,以維持生計。
(三)清代陜西回族的宗教文化特征對回族經濟發展的影響
傳統文化決定一個民族的經濟觀念,影響本民族經濟的發展。回族是一個全民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伊斯蘭教規范著回族的社會經濟生活。伊斯蘭教崇尚經商。在穆斯林看來,經商是真主喜愛的職業,那些依照伊斯蘭教規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將會被給予高貴的榮譽。此外,在經濟活動中伊斯蘭教推崇互惠互利、公平交易、反對投機取巧的原則。《古蘭經》中有“傷哉!稱量不公的人們;當他們從別人稱量進來的時候,他們稱量的很充足;當他們給別人或稱給別人的時候,他們不稱足不量足;難道他們不信自己將復活,在一個重大的日子嗎?”“我的宗族啊!你們應當使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稱,你們不要克扣他人應得的財物。”“他曾規定公平,以免你們用稱不公,你們應當秉公的謹守衡度,你們不要使所稱之物分量不足。”這將回族的經商行為置于內心的道德自律和契約化的他律之上,為回族贏得了良好的商業信譽。
基于回族的宗教性,回族的經濟生活具有鮮明的宗教特色,并對其經濟發展產生一定影響。我們可以從同治年間起義前后陜西回民的經濟生活狀況變化中窺之。起義前,陜西回民的經濟結構是以農耕為主,兼營畜牧業和商業。又因為伊斯蘭教對回族飲食有諸多禁忌,所以回族人在滿足自己飲食需要的同時,開發出了一系列鏈式產業。這個鏈式產業從牛羊騾馬的飼養開始,由此派生出運輸業、牛羊騾馬行、農閑時節的騾馬販運、屠宰業——又派生出清真飲食業和皮毛加工業等。起義后,陜西回民的地產被沒收入官,其經濟結構變為以商為主,清真飲食業成為這一時期陜西回族主要從事的經濟活動之一,規模增大,但因為戰爭留下的創傷而發展緩慢。不過還是慢慢走出困境,逐漸發展成今天這樣的規模。
仔細分析一下清代陜西回族的經濟生活變遷情況,可以看出起義前是在農耕的鋪墊下從商,并由畜牧業派生出了一系列與商業相關的鏈式產業;起義后則是直接從商,兼營畜牧與農耕,在經濟結構側重上具有明顯的變化,商業性突顯。而在回族所經營商業類別中,因伊斯蘭教的飲食禁忌,絕大多數都和牛羊相聯系。馬光啟在遺著《陜西回教概況》一文中有“省內有回教居民,……中等營業除牛羊肉行為大宗外,其他商業則不過少數。”其清真飲食業開始時也主要以牛羊為主,后來才發展為多種經營。由此可知回族的宗教文化特征與其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成為支撐回族適應經濟生活變遷的強大動力。
總之,回族善于經商以及良好的商業信譽在回族經濟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樹立了回民在經濟活動中的威信。在回民起義后艱難的經濟生活中,遵循著伊斯蘭教的宗教思想和經濟思想,找到一條新的適宜于自己民族特色的發展道路,從而慢慢走出困境。
三、結語
從以上對清代陜西回族經濟生活變遷情況及原因的簡略探析,我們可發現回族經濟生活隨著受漢族大地主的剝削以及與漢族關系的緊張而受到很大影響。“地畔相爭”導致回族耕地日趨減少,加上漢族地主的肆意剝削,回族以農耕為主的經濟結構遭遇很大障礙;起義失敗后清政府對回民地產的沒收使得大部分回民結束了以農耕為主的經濟結構,被商業貿易經營取而代之。此外,伊斯蘭教作為規范回族行為的典范,從信仰的高度指導和約束著回族的社會經濟生活。伊斯蘭教所推崇的商業精神和鼓勵經商的思想,無不滲透于回族社會經濟生活中,對回族經濟發展具有一定影響。